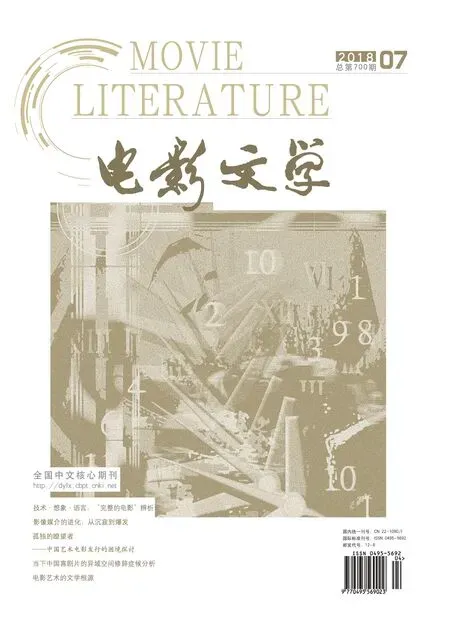电影叙事学视角中的《玛丽和马克思》
王 庆
(大连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4)
电影是一种视听型的叙事艺术。热拉尔·热奈特在其著作《再论叙事话语》中曾指出,电影就是叙事学的再现。而电影叙事学,指的就是借助影像的艺术形式来讲述故事或陈述一个涵盖时间进程与时间演变的故事的一套话语。可以说,叙事不仅是影像得以推进和延展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技巧性的艺术存在。叙事学范畴是电影阐述其意义层面时所涉及的根本问题。
亚当·艾略特执导的动画电影《玛丽和马克思》,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其文本表现是在影像叙事上兼具本体论研讨与实践意义的佳作。从电影叙事学角度而言,《玛丽和马克思》的叙事结构,几乎涉及叙事学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在讲述某个外化的故事,而且有意识地将叙事话语呈现为形象的、涵盖细节的具备视觉美感的体系。文章从电影叙事学的视角出发,依照罗伯特·艾伦所揭示的叙事学中“讲述什么”“如何讲述”及“讲述之外”的经典三段论,探究《玛丽和马克思》所展现的叙事艺术。
一、“讲述什么”:现实拷问下的友情童话与社会写实中的边缘抒臆
正如詹尼弗·范茜秋在其著作《电影化叙事》一书中所说的,所有的电影叙事,都代表着一种世界认知的影像阐释的角度和方式,电影叙事学首先是一种生活体验的话语重构。电影中的叙事,其核心是“讲述什么”的叙事空间。《玛丽和马克思》以一种质朴的形式构造,带领着观看者进入一个奇幻又现实、童话又写实的叙事空间中,引发观众对生活的种种感悟。
《玛丽和马克思》的叙事表达重心之一,就是一个在人情疏远的现代社会中,现实夹击下的友情童话主题,所要完成的叙事目的就是满足观众对纯真友情的期待。影片从两位主人公玛丽·黛西·丁格尔和马克思·杰瑞·霍罗威茨的视角出发,以双线叙事,强烈地呈现出荒芜年代的纯真友情的反差感和可贵之处,同时在一种充满现实拷问和悲情渲染的话语场域中,凸显友情童话的无奈。玛丽自小为脸上的胎记所困扰,她唯一的可交流对象就是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她不断地写信,寄托着自己的情感,终其半生储蓄辛苦挣下的钱财,然后买张机票飞往遥远的美国纽约,看望自己的笔友——情感上如影随形的马克思;而孤僻的马克思在与玛丽通信的岁月里也重获了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当他终于平静地在漫长的等待间隙安详去世时,胸前悬挂着的那本专门来辨识人表情的小册子,似乎也昭示着他时刻期待着会面人生中唯一的朋友玛丽……这样的叙事传达方法既有巴赞所论述的营造真实感、纪实性的一面,也传达出某种梦幻感。
《玛丽和马克思》另一个基本的“叙事现实”,则是一种在消费主义横行的商业社会里,边缘人物乃至芸芸众生在心理上漂泊无依、精神孤苦悲凉无可诉说的抒臆写实。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历经生活困顿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女孩玛丽和居住在美国纽约市的孤寂封闭又渴求人间温暖的马克思之间,由通信建立起了数十年的友情。但其叙事时的“话语主权”,依然是在后现代庞大的消费主导的社会机制下,以玛丽与马克思为代表的人物的卑微状态传达。而其制作中一般动画电影罕有的朴实、泥土捏造的人物外形和逐帧拍摄的技艺呈现,不仅为了抗议现今“科技”与“仿真”成为潮流的工业化影视生产体系,其叙事实质是有意展示一个充斥着精神危机的“人类公共事件”。玛丽生来身材样貌都很一般,家境又很局促,这一切都导致一个本身可爱的女孩逐渐被社会和他人所排斥,自身也在这样超负荷的精神重压下一步步走向沉沦;而马克思的生命状态更是已经濒临绝望的深渊,他患有亚斯伯格症(自闭症的一种),而且无法解读他人的表情,最喜欢的就是玩偶和巧克力,这样的小人物在纽约的繁华都市中注定会迷失,面临生存的压力,慢慢遭遇被毁灭的命运。影片的叙事,体现出的是电影叙事实践参与到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组建中的意图,是叙事学视野中“表现现实”的实践状态。
二、“如何讲述”:数字技术助推下的叙事认同与视觉文化转向中的梦幻体验
在电影叙事学中,“如何讲述”涉及的是电影完整的叙事结构。就《玛丽和马克思》一片而言,其叙事上的技艺可说是数字技术与视觉文化双向变奏的产物,但其叙事安排的可贵之处,即在试图突破既定的叙事模式,探寻叙事革新的同时,本质上依然是寻求理性的建构,从而扩展了叙事技术对社会空间的呈现深度。
《玛丽和马克思》的叙事表现力是数字技术辅助推动的成果。《玛丽和马克思》是当前动画电影中少见的黏土动画,它最大限度地依靠工作人员的手工制作模型,而非计算机直接生成图像,工作量非常大。数字技术主要是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加入的,这样,固定的模型就呈现为动态的图像,具有生命力。影片运用大量匠心独具的分镜头,特别是在表现玛丽与马克思写信的过程中,将相关叙事路径的线性逻辑所衍生的内容穿插其间,从而将影片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及其现实人生呈现出突破好莱坞动画程式的饱满。影片中稚拙的叙事空间变得更加贴近人心,叙事情绪中或失意、或悲伤、或迷茫、或焦灼、或自卑、或愤懑乃至滑稽都汇聚而为技术空间模拟所能达到的新水平。影片的叙事功能节点,有效地串联起马克思的感伤人生,也提点着小玛丽的压抑生活,进而从情节、理性与秩序上都超越了技术的区域界限,打造出多样化方式的叙事认同机制。这是叙事者找寻到恰如其分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后所展现的叙事艺术的胜利,其所凸显的体验和情感都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叙事认同机制中得到发挥。
《玛丽和马克思》利用视觉文化转向与重构的契机来呈现其新的叙事认知高度。自电影诞生伊始,它就是媒介记录和科技产品的附属品,在历史的序列中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艺术,其叙事认知、叙述解释向来是与技术环境密不可分的。动画电影又是叙事学中的“拟象本性”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是视觉文化时代最具标签式的艺术类型之一。一般而言,动画电影更加注重透过精心的声画组合以及叙事逻辑构建影像,进而将这些元素形成一个具有直观性、梦幻色彩的故事,并让观看者在潜移默化中投入影片叙事空间。《玛丽和马克思》将视觉文化时代大众所乐见的如同游戏一般的参与感的娱乐形式渗透入叙事的肌理之中,无论是玛丽的造型、给马克思写信的画面特写、马克思不断地清数烟头的装置、马克思住所封闭环境的模式设计、虚拟空间中单调而寂静的场景等,都不曾有炫目的视觉特效,不曾有英雄主义渲染。在色彩一明一暗的对比性视觉展示中,其合理散布在叙事段落中的情绪表达、视觉审美,却让电影所带给观众心灵上的震撼能多过一部好莱坞大片。这种叙事形式的成功,正是视觉时代转向潮流中审美嬗变的例证,观众对炫目的特效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而《玛丽与马克思》既借鉴又扬弃的姿态更加有效地扩展了其叙事的范围与渠道。
三、“讲述之外”:类型模式下的青春记忆与集体想象
从电影叙事学的视角考察电影,可知任何电影叙事都无法摆脱某些深层结构叙事表达的牢笼。电影叙事学面向的是语义关系和时空连续性及视听组合三者关联性的描绘,它是镜头语言与心理结构的特殊性呈现,其叙事意图和表现目的都离不开话语特有的限定性作用。所以,当我们运用电影叙事学的角度审视《玛丽和马克思》一片时,显而易见也必然将触及罗兰·巴特所言称的“表面叙事系统之外的结构叙事”。
一方面,叙事学范畴中类型化的青春记忆叙事在《玛丽与马克思》中占据叙事结构的重心地位。就整体的叙事安排而言,《玛丽与马克思》表面上将叙述主旨停驻在了纯真的玛丽和善良的马克思美好纯粹的友情上,但其实质却指向人类积淀性的深层心理结构需求上,即其“内心话语”弥漫着一股类型模式化的青春记忆的怀旧叙事姿态。比如,主人公玛丽的生命可说是悲怆性的叙事演练,其情感和人生困境主要并非来自外貌的不尽如人意,她所遭遇的家庭不幸、遇人不淑及其周边人群的言语打击,而其都只能被动接纳所有的戏剧性结局。因此,叙事安排中玛丽所有的行为和需求,诸如渴望理解、反叛家庭、生育小孩、呼唤友情、对纯粹爱情的幻想乃至渴求犹如父亲一般存在的马克思施与关怀,都不啻为类型模式电影叙事中“青春片”最常有的故事桥段,并以此表征爱情与青春的残酷性。可以说,《玛丽与马克思》的叙事深层是关涉友情元素的青春怀旧主题,传达的人类普遍感伤和怀念的青春、梦想与迷茫情绪,影片中诸如人物性格设置、情节构架、现实情境、声音符号等要素也都成为传达青春怀旧情绪的重要结构元素。只不过这段友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包括二人的年龄差异,也包括二人的从未谋面。
另一方面,在类型化叙事策略中,影片渗透着一种集体唯美主义式的想象,而玛丽或者马克思所代表的那些个体的生理或心理损伤,都自然而为时代精神创伤的表象或者隐喻所指。表面上,叙事动因只是两位各居地球两端的孤独之人,因为理解、善良与爱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18年的笔友关系,而在此期间,马克思和玛丽的人生犹如分叉的轨道此起彼伏,玛丽差点要与黯淡的人生说再见,而马克思也为焦虑症困扰几乎达到崩溃边缘。可以说,《玛丽与马克思》的叙事,从马克思写给玛丽的第一封信开始,就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唤起观众内心有关美好与纯真的所有记忆。玛丽与马克思两人所建构的那种类似“灵魂伴侣”(soul mate)的关系,也显然是富有意味的叙事设计,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使得二者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通行的男女情感或人际关系叙述之外,日益衬托出古典时代的唯美化。玛丽无知、丑陋、懒惰、缺乏主见,却依然渴望纯真、果敢和内心的强大;马克思肥胖而无能,几乎是社会的累赘,但是依然那么可爱,在困境折磨中会发明属于自身的词confuzzled,会给市长写信反映公众问题等,内心深处依然维持着可爱而顽皮的一面。马克思用其后半生所有的心血,守护着来自陌生地方甚至是从未谋面的玛丽。正如马克思信中讲述的,他和玛丽的友谊是建筑在一种“不完美”的残缺之上的,正是这种情感支撑着他超越“迷惑、伤害、不适、背叛、气喘与苦恼”,不断地给予玛丽这个唯一的朋友在人生旅途中最真挚的心灵拥抱。可以说,《玛丽与马克思》的叙事视角和策略,都是在极致地凸显唯美的想象,借此意指人们现实处境的尴尬与难堪,影片充斥着着某种依恋与缅怀,甚至哀悼之感。
综上所述,从电影叙事学视角出发,探究《玛丽与马克思》的叙事特征与叙事演变的主要脉络,不仅可生发在电影观念、电影技术等诸层面的新认识,而且可以折射出大众心理趋向乃至人类文明历史演化的某些基本特征所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玛丽与马克思》是电影叙事的“阶段形象”,更是我们面临现实处境时的“集体无意识”的显像。而这也正是《玛丽与马克思》作为电影其叙事的卓越之处与成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