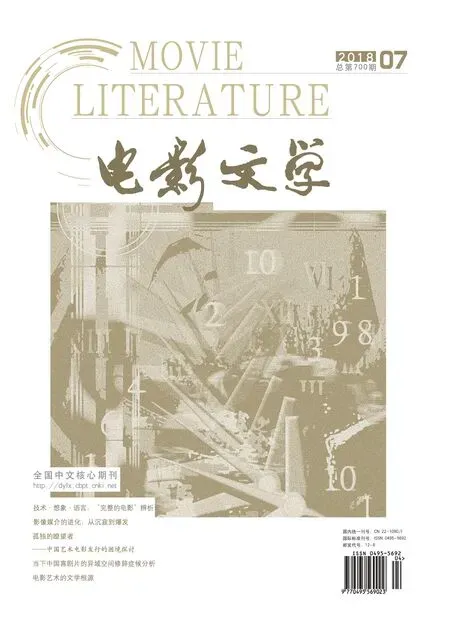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魔弦传说》的电影语言分析
关 迪
(吉林师范大学分院,吉林 四平 136000)
电影这门艺术通过画面与声音,在视觉和听觉上传情达意,将观众带入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活动中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电影是一门特殊语言的论断。在电影中又存在两类语言,即天然语言和非天然语言,前者即出现在剧本之中的人物对话、旁白等,这一类语言与人类在日常交际时所使用的常规语汇语言是基本一致的。对于观众来说,它们所交代的信息是意义较为明确的,后者则包括了电影在剧本语言之外的所有表达形式,包括画面形象、配乐等,这些同样是电影的表意手段。正如让·米特里所指出的,“图像是词汇的潜台词”,它们也负载着主创的思维和情感。但是这种表意手段又有别于观众日常对话使用的语言系统,因此并非所有观众都会对电影的非天然语言有着一致的理解。而在主创的主观思维发挥余地更大的动画电影中,这一类语言的指涉和交流功能也更为丰富和复杂。本文以特拉维斯·奈特执导的《魔弦传说》(Kubo
and
the
Two
Strings
,2016)为例,对其中的非天然语言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动画电影的电影语言表意方式。一、电影风格与表意含混
和天然语言存在风格一样,电影中的非天然语言同样是具有风格的。如同样是对一段情节或场面的处理方式,不同电影人在具体的镜头设计和色调选择上都会有所区别。动画电影亦然,不同动画人在设计同一客观物时所产生的心理图像势必不同,最终完成给观众以不同感官印象的动画成片。出品《魔弦传说》的LAIKA热衷于进行偏黑暗的、近乎哥特风格的表达,电影中拥有大量僵尸、鬼魂、古怪的小孩等意象,在剧情的设计上也近乎诡异、残忍,这是与走明快、温暖路线的迪士尼和幽默搞怪风格的梦工厂有着一目了然的区别的。这种语言风格也就使得LAIKA动画中有着更多的表意含混、令人感到阴森的电影符号。
以眼睛这一意象为例。在LAIKA的动画电影中有着反复出现的“夺眼”情节。如在《鬼妈妈》(Coraline
,2009)中,小女孩卡若琳意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并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对她和蔼可亲的鬼妈妈。但是有一天卡若琳发现鬼妈妈要在自己的眼睛上缝上扣子,用扣子给自己做新的眼睛,从此就可以将这个“女儿”永远留在这个世界,而在卡若琳之前,已经有三个幽灵小孩被夺去了眼睛,卡若琳即将是下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导演亨利·塞利克对尼尔·盖曼原著的改编,在原著中,鬼妈妈反复想欺骗卡若琳缝纽扣眼睛的情节是没有的,幽灵小孩们被夺去的是灵魂而非眼睛。但是电影强调了“眼睛”这一语言符号,在观众的视觉上形成刺激,使其进入到观众的意识中,形成一种“眼睛代表了部分生命或灵魂”的心象。对于观众来说,眼睛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器官。而电影则赋予了它更深刻的含义,特拉维斯曾表示,在《魔弦传说》中,他更希望体现出来的风格是古怪(weird)而非毛骨悚然(creepy),因此在对眼睛的处理上较《鬼妈妈》中显得温和了一些。久保在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平时靠长发遮挡自己的盲目,夺走他眼睛的人就是他的外公。在久保的成长过程中,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不仅要去卖艺照顾母亲,还要担心着来自外公和两个姨妈的追杀,对这种追杀的恐惧又具化为对最后一只眼睛也被夺走的恐惧。独眼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久保的童年是孤独的,他和母亲离群索居,和其他人格格不入。而外公本人则没有眼睛,双目惨白无光。电影中也借久保之口点明外公因为没有眼睛而看不到人心中的爱。而两个姨妈则戴着具有诡魅感的面具,既避免了形象的雷同,又同样可以暗示姨妈也没有眼睛。外公和姨妈的形象启示着观众在理解久保母亲感情这件事上的“有眼无珠”。与《鬼妈妈》类似的,作为反派的鬼妈妈和外公都有着执着的对主人公眼睛的憎恨,这种憎恨其实是他们对凡人在尘世中温暖情感牵绊的嫉妒的外化。他们认为只要拿走了主人公的视力,主人公就无法与人间和亲人交流,并且他们夺走人眼睛的方式都是充满暴力的。在这种表达中,眼睛这一意象被与情感和感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魔弦传说》中,最后外公失去记忆却恢复了视力,变成了一个善良的老人,观众也不一定能理解这种联系。这正是电影语言具有表意含混的特质导致的。这也是电影语言的“亚规范”性,即其中并不具备一套确立的、公认的能指所指关系。眼睛意象的含义脱离了《魔弦传说》和《鬼妈妈》后就未必成立了,它更是一种独立存在于具体电影中的表达范式。
二、隐喻与社会现实映射
电影语言同样具有修辞格,而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便是隐喻。电影艺术因其技术特点,是高度忠实于客观世界的,影像对于现实有着再现意义,隐喻的生成往往与某种社会现实有关,包括社会价值观或社会现象。
如在《魔弦传说》的开头,母亲和襁褓之中的久保在海上逃难,最终凭借具有法力的三味线才摆脱了追杀,此时观众和母子俩都认为父亲半蔵已经为了保护妻儿而被杀死了。这是一种对母亲照顾孩子,父亲在外工作的社会现实的映射。这种社会现实是普遍存在于东西方社会中的。而随后电影就跨越到了久保长大,母亲的精神状况则时好时坏,依赖久保喂饭照顾。这则是对东亚国家强调孝道的社会氛围的映射。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种家庭关系在动画电影中是较少见的(美式动画电影中的常见情节是子女对父母辈惊心动魄的营救,但这往往是现实中稀缺的),但是却是高度符合东亚文化对于理想亲子关系“母慈子孝”的期待的。
又如电影中的“two strings”,也是对于亲子情感的隐喻。久保的琴“三味线”因为断了弦而无法对抗姨妈和外公,但久保后来得到了母亲的头发、父亲的弓弦,再从自己的头上取下一根头发,终于用三味线弹出了让外公心魂俱散的强大魔音。一家三口以这样的方式团聚,电影强调了一种无法切断的、来自血脉的强大的爱。在传统美式动画长片中,同样是讲述主人公的个人成长以及正义战胜邪恶,主人公往往最终能够实现和家人的团聚,如《美女与野兽》(1991)中贝儿救出父亲,《功夫熊猫3》(2016)中阿宝找到生父,也成为养父的骄傲。但是《魔弦传说》却是反复凸显久保的孤独,以及他在无法阻止父母死去后对父母的深切怀念。正如他对外公所说的,他的父亲母亲都不在世上了,可他们依然活在他的记忆里。法力强大的三味线是喻体,这种略带酸楚的有着现实依据的亲子关系才是本体。如前所述,电影语言的“亚规范”表意导致了并非所有观众都能“读懂”这一点,但这并不影响观众理解电影在大体上的表达。
三、虚构与客观实在性
电影语言最终是服务于电影能给观众带来的审美体验的,而观众调动自身的审美能力,感受电影的表达,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对于常规语言,电影语言具有一种更为高级的表意层级。我们对电影语言的探究也不应该止于其表达手法这一层次,而应该认识到在情感表达的层面上,一部电影的语言有着怎样的追求。
《魔弦传说》无论就故事本身,抑或是一幅幅定格画面而言,其虚拟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旦观众能理解到电影所想表达的客观实在,那么就能够充分地领悟到电影的悲剧内核。电影在虚拟的外衣下讲述的是一种现实世界的逻辑,即所有人的父母或迟或早,都是会离开自己的。只是《魔弦传说》将这一逻辑强化了。久保的父母在孕育了他之后,又先后为了保护他而死。人生命的有限以及现实生活往往会给人造成打击与分离,这是一种观众承认的客观存在。《魔弦传说》也遵循着这一点。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贯热衷于拍摄“合家欢”的迪士尼却无意于在动画电影中重述这种有悖于人们情感的客观实在。即使是在反复强调“生生不息”、生命循环的《狮子王》(The
Lion
King
,1994)中,木法沙的死更像是意外所致,而辛巴的母亲则并未死去,而是见证了辛巴最后的王者归来与结婚生子。《魔弦传说》中却让父母离去,甚至离去两次。而“亲人/父母终将离去”这一概念更是在电影中被反复重申。如电影中村民集体放水灯,这是一种意味着人们接受了亲人离去了的行为。人们笃信随着水灯在水流中渐行渐远,已经“往生”了的亲人便将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这是一种对于凡人而言的,对亲人之死的接受。而对于神灵妖怪来说,他们同样要面对亲人死亡这个问题,只是“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在电影中,母亲先是罹患了老年痴呆症,这其实是因为她体内的法力逐渐离她而去。后来母亲化身为一只白色猴子陪伴、保护久保,这只白色猴子也可以理解为只是母亲部分灵魂的附着物。换言之,她是那个被注入了母亲精魂的木头猴子,而非母亲的转世。因此猴子才会一直没有认出甲虫就是自己曾经深爱到不惜背叛家族的半蔵。半蔵化身的甲虫曾经问猴子为什么不告诉久保自己就是他念兹在兹的母亲。猴子说她也迟早会离开久保的,因为她体内与久保母亲的记忆、灵魂等有关的法力并不是无限的,不如保守这个秘密,以免久保再接受一次丧母之痛。自始至终,猴子都有着清醒的对于死亡的认识。如当久保和猴子在路上听到天空中的飞鸟在唱歌,久保好奇鸟在唱什么时,猴子告诉他这些歌声和死去的人有关。而最终久保迎来了自己父母双亡的结局。
整个故事都是以“父母终将死亡/离开子女”这一现实存在作为虚拟情节和场景的基础的,电影主创既要对现实有着一定的参透,又要运用电影语言来完美地表达死亡主题,如久保父母的两次不同的死和生等。而对电影语言有着敏锐感触能力的观众,便能领悟到电影的思想内涵,甚至还可以做出更进一步的解读。如生长于儒家文化圈的观众,受“孝道”文化的影响,对于久保在小时候被外公夺去一只眼睛这一表意,会有着“子女也需要为父母做出一定牺牲”的理解。单纯将这种理解拈出,或许显得有些牵强,但只要与隶属于另一种语境的迪士尼动画电影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情节几乎从未出现过。儿童是被保护的对象,但“儿童亦有可能因为父母而受到伤害”这一客观实在却是迪士尼大量动画电影回避的。如同样是主人公父母双亡的《冰雪奇缘》(Frozen
,2013)中,安娜小时候差点被伤害是姐姐造成的而非父母或祖辈,父母因船难而死而姐妹俩完全没有受到来自船难的伤害,艾尔莎的自闭更多的是源于王室责任和对妹妹的愧疚,而并不是在孝道意义上对父母做出的牺牲。可见上述理解并不一定是过度解读。电影语言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封闭性的,因此观众产生这种认知是毫无问题的。电影既是一门复杂的、具有“亚规范”特征的语言,又是一门高度依赖接受者的艺术。如若没有观众,电影也就几乎可以被视为不存在的。电影语言得到观众在表意以及艺术审美两个层面上的理解,电影本身才具有意义。《魔弦传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特拉维斯浓郁的个人风格,他在电影中营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有别于主流美国动画的能指系统。对《魔弦传说》的电影语言进行分析,既是我们深入了解《魔弦传说》艺术成就和个性特点的方式,也是我们进一步确定电影语言表意功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