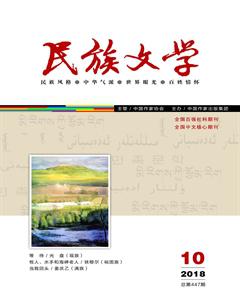命运门
周子湘
愿你的眼睛是陋室之烛
目光是烛芯
愿我是个盲人
盲到用心把你点亮
——保罗·策兰
一
他是循着她的味道来到这里的。这里?这里不符合他的身份,市化工研究所基建处处长刘唤生被人看到来这种按摩的地方,是什么影响。可他在乎不了这么多,那个影子,从他身边一闪而过,转进这家店面,再晚一步,她就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好在这只是一家盲人按摩店。
可她,怎么会在一家盲人按摩店?即使她……也不用在一家盲人按摩店。
唤生指着她的背影对店老板说:“我点她。”
她戴着一副很大的黑色墨镜,小心翼翼走进来,轻轻把毛巾搭在唤生身上,唤生就看不见她了,只感觉到她柔软的双手贴在自己脖子上。
仿佛还是那双手,只是柔軟中多了力道,手上也起了茧子,许是这么多年,她练就出来的。这双手曾给他织过围巾,还织过一顶帽子,现在他的衣柜里有的是名牌围巾和帽子,再也不会戴她织的围巾,可他一直没舍得扔,它们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
这双手给唤生做过饭。她能把市场上剩下的笋叶,放点木耳、鸡蛋,做成一碗热腾腾的笋叶汤端给他。他站在市场的寒风里,看着一棵剩在菜摊上的笋子,被她做成一碗水汪汪的嫩菜,叹息着世上竟有如此灵巧聪慧的女人。
他忘不了她的粉脸,小杨树般颀长的身材和一团小蘑菇似的粉脸,整天在他的眼前晃,晃得他眼睛和头晕晕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像一团寒风烈雪浇不灭的火,淋了雪的长发黑油油放光,像一块冬天的火炭。
唤生曾多少次想伸手摸摸这张粉脸,他憧憬着快乐,也得到忧愁。从冬到夏,他把自己往单人床上一扔,翻来覆去烙饼,一夜一夜,无论醒着还是睡着,脑袋里乱纷纷全是零乱的梦,美梦。
夜里的美梦多一层,他的悲哀就多一层。他没有勇气对她诉说自己的心事。在夜晚的梦里如醉如痴,在真实的世界里却残酷无比。如今的基建处,没有人知道刘唤生的来路——八年前,他只是大庆市场上的一名城管。
他天天从这个叫李翘的女人身边走过,却不敢用爱恋的目光看这个摆地摊的女人一眼。他管着她,却喜欢着她。他第一次看见她,她就在寒风里摆地摊,地摊上的手机外壳和各种小挂件,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她伸出手把它们一一拉回来。他看到那双瘦弱、被冻得红彤彤的小手。那双手看见他,停在半空中,有点担心,有点害怕。
他没有像别的城管那样,伸出脚把她的摊子踢翻。他蹲下身子,默默帮她把吹到马路边的小挂件捡回来,又帮她把摊子收起来,小声对她说了一句:“你晚上再出摊,我们七点下班。”
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单纯而清澈,带着感谢,又带着一点敬意。
那一眼,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如同脚踩棉花。第一次被人这样尊重,他忽然感觉到原来自己并不坏。网上那么多骂城管的话,可他今天,被一个长着一张小蘑菇似的粉脸的女人尊重了。
他从此做了城管中的叛徒。每次要来检查时,他就打电话给她通风报信。他让她藏到一个暖和的地方,等他们走了再出来。他心急火燎地检查完,下了班,脱掉那身灰色的城管制服,换上便装,来到市场上,帮她把摊子摆起来,帮她卖东西。
她耳后发丝里那颗红色的朱砂痣,让他足足看了半年。他喜欢看她扭头或说话的样子,每当她低头给顾客拿东西、说话,雪白的脖子和肩膀的抖动就让他心里一阵阵发麻,想甜蜜地哼哼一下,像接受温存的抚摸一样。
没有人知道唤生吃饭睡觉走路工作和以往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心里,这个年轻人的心里灌满了李翘的影子。只有唤生自己知道,他眼看快要完蛋了。
此刻的一双手,柔软而冰凉,多了一丝陌生的气息。她先按摩唤生的脖子,一下一下,手掌与肉的摩擦,从耳根到脖子,手法熟练而有条理。这是一个熟练按摩师的手法,不是那双织围巾做笋汤的手。
这个坐在按摩椅上,穿着白色按摩服的女人就是你了。按摩服上绣着“阿亮盲人按摩”几个字,绣得最密的部分坚硬冰冷,如铮铮铠甲。
再抬高一点下颌,让那曾经红润如今干涩的嘴唇照在房间有限的光线里。唤生就这样看清了她的整个脸庞。她的脑后盘着一个发髻,几根白发刺目地夹杂在黑发里,曾经那么黑油油的长发如今枯涩干燥。只有耳后那颗隐藏在发丝里的朱砂痣,带他回到八年前,回到那个明艳动人的李翘身边。
“老板,需要加时吗?”李翘用程式化的声音问唤生。
唤生拉下盖在自己脸上的毛巾,慢慢抬起头说:“你能把墨镜摘下来让我看看吗?”
那双在唤生身上按摩的手忽然停下来,随即又继续按摩:“我是盲人,老板不需要看我。”
唤生呼吸不畅,觉得自己正在死,灵魂已从脚心跑走了。他披着雪白的毛巾,紧紧握着毛巾一角,把一双瞪得发麻的眼睛,哆哆嗦嗦伸向对面的墨镜,向那黑暗的洞穴逼近。
这是一双曾经明艳动人的双眼,眼睛里的温柔和多情,劈开过多少个唤生黑夜的梦境和清晨的薄雾,太阳般照亮一个陌生新奇又鲜艳无比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无数次敞开过自己,让年轻的他冲动而惊诧,为那些绚烂的颜色深深迷醉。每一次与她对视,或偷偷望一眼,紧张中得到满足,却留下更多的迷恋,让他以为自己着了魔,全身烧着一团火,自己的心和身体膨胀得快要裂开。
可这个世界被一只黑色的大墨镜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唤生伸出手,猛地扯下李翘的墨镜。唤生终于看到了最隐秘最黑暗的一幕,他的心被人猛击一拳。
一只丑陋的独眼,无遮无挡地展现在他面前。眼睛上的皮肉扭曲地收缩着,好像一个被人掏空的山洞,凌乱地废弃在脸上。
震惊,愤怒,追问,一时间潮水一样涌上唤生的心头,肝肠一截截断裂了。唤生的心里一阵痛麻,墨镜啪地掉在地上,像被摔痛了似的,在地上摇晃、抖颤。
“为什么会这样,李翘?”唤生的泪止不住流下来。
李翘任凭唤生大声问她,任他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脸上,水珠沿着脖子往下淌,打湿他的衣领和衣服。她用一只独眼,慢慢寻找着,摸索着地上,摸到那只墨镜,抖抖地把它戴回眼睛上。
“唤生,我没想到今天能再遇到你。一切,都过去了。”
二
李翘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她面无表情地继续为唤生按摩。脖子按完了,该按肩膀了。李翘看着唤生的泪水,像没有看到一样,她一点也哭不出来,大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她像一个安分的盲人,世界在她面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需要看见。
李翘没有一般女人的动情和怯懦。她很实际。一个残缺丑陋的女人,活在世上只能靠自己了。如果唤生能加时最好,她就能多赚些钱。如果不能,她要赶快去按摩下一个客人,她的工资,是按提成算的。
八年前,唤生离开她去谋求国有企业化工研究所基建处的工作时,李翘在出租房的公共水池邊,一遍遍梳洗自己的头发,让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今后的生活。住在隔壁的玲花嗑着一把瓜子对李翘说:“翘,不是姐们说你,摆地摊能挣几个钱?你长得又不差,趁着年轻,不赚钱,难不成等老了去?”
水龙头里的凉水洗在头上冷冰冰的,李翘的心里也冷冰冰地:“玲花姐,怎么赚钱?”玲花收起瓜子,凑在李翘耳边说:“我们按摩院正招人,上次警察来,带走一批姐妹,现在正缺人手,你来,保你有的赚。”
李翘的手僵硬地停在头发上:“那是按摩还是……”玲花噗地吐出一口瓜子皮,蹦到李翘脚边:“你可真是死脑筋,有正常按摩和接待客人两种,你要介意,你做正规按摩不就行了?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就算做正规按摩,也比你摆地摊强,你看看你穿的这身衣服,寒碜成什么样了!”
李翘低头看看自己穿了三、四个秋天的毛衣,再看看自己仅有的一双皮鞋,鞋边已经裂开了一个小口,她下意识地把脚往里缩了缩。
“不过,你自己也考虑清楚,名分上,是委屈了一点。你那个刘唤生有天知道,可别嫌弃你。”玲花故意瞄了李翘一眼说道。
玲花提到唤生,李翘的心里像有把锥子,猛锥了她一下。唤生去了好单位,他怎么还会和一个摆地摊的女人好呢?唤生丢下李翘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有人会拒绝自己的好前途,即使不做按摩女,唤生也不会要她。唤生要的是一个好前途。化工研究所,是比城管好多了。
李翘苍白地笑了一下。她不怪他,曾经的美好回忆好像一场梦。但凡是梦,都有冷铮铮醒来的时候。剩下她一个女人,要活,要生存。
“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考虑的吗?玲花姐,我把自己交给你了,你要是顾及咱们做了两年邻居的情分,就给我介绍个好老板吧。”
李翘的手还在唤生的肩膀上按摩着,唤生一把抓住李翘的手说:“走,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坐吧。”李翘的声音像没有温度的水:“我正在上班,随便出去是要扣工资的。”“那就让他们扣!这些钱够不够?”唤生掏出钱包,一把扯出里面的钞票摔在按摩床上,他的声音大得吓人。
餐厅的窗外下着雨,李翘隔着玻璃看外面细雨蒙蒙的街道。唤生看着她,除了那副刺目的墨镜,这还是原来那个叫李翘的女人的脸。脸上的每一寸皮肤,他都曾经那么熟悉。
可是她变了。如果没有这张脸,那瘦削的肩膀和微驼的脊背,或许唤生真的认不出来了。八年,她身上消逝了灵动娇艳的气息,那张小蘑菇似的粉脸如今枯黄干涩,脸上明艳动人的神采消失了,棱角分明,坚硬而冷漠。
她穿着一件宽大的休闲衫,苗条丰满的身材如今瘦削而干瘪,衣服上还留着按摩店足浴中药水的斑迹,油腻腻、黄团团的一块,是永远洗不掉的污渍。她的手指又红又粗糙,骨节突出,唤生看着这双手,心里一阵酸楚,她按摩过多少客人,才会把手磨损成这样?
李翘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小蜡烛,她轻声对唤生说:“给我要一盒蛋糕吧。”唤生从餐台挑选了一盒最好的蛋糕放在李翘面前,李翘把小蜡烛一根一根插上去,一共插了八根。唤生不解地看着她,她只是笑笑。李翘第一次笑了起来,蜡烛的火苗倒映在她的大墨镜里,像把她的眼睛点亮了。
李翘的脸在烛光里变得晶莹光洁。
“你看,这火苗多明亮。”李翘长长呼了一口气,噗地把蜡烛吹灭。“明天是我的生日,提前过生日吧。三十八岁过完了。”
唤生在烛光里沉默了许久。
吃完饭,唤生要送李翘回家,他想看看李翘现在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了他的好奇,也为了他的愧疚。李翘一味躲闪着,可唤生不等她推托,出门发动车,让李翘上了自己的车。
车开到一个狭小的巷子口,唤生就感到扑面而来的荒凉和满地废弃垃圾冲出的臭味。唤生关上车窗,车里一下安静下来。巷子口站着一个男人。秋末冬初的时节,男人穿着单薄的衣服,衣服太大,在身上晃荡着,他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正从远处的工地上扛过来一大把电线,用铁丝把它们捆起来。
铁丝太长,男人捆不住,他举起一把斧头,朝铁丝重重砍下去。铁丝歪歪扭扭地挣扎着,因为用力太大,铁丝下垫的木桩被砍得爆出好几块木皮。车里很安静,唤生听不见斧头砍铁丝的声音。这无声的画面,让唤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看清男人的表情。男人砍伐使出的蛮力,让他的脸显得狰狞而笨拙,那双不协调的手,无意识地抖动着,不像一个正常人。
男人看见汽车开过来,先是惊讶,后是前后躲闪,唤生想开车绕过他,李翘忽然说:“停车吧,我家到了。这是我男人。”
三
男人看着唤生和李翘一起从车上下来,他警惕地看着唤生,脸上的皮肉抽动了一下。唤生在脸上堆起笑,想争取他的友谊,男人却往后退了一步,两手的指头交叉在一起,弄出很奇怪的形状。
唤生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对,突然从屋里钻出一个光头小男孩,站在门口,用愣愣的眼神看着他。男人立刻一把拽住小男孩,把他往后拖,小男孩不想进屋,男人蛮横地挥舞着胳膊,嘴里发出一声声不连贯的呵斥。
小男孩大叫起来:“妈妈,妈妈!”李翘走过去拍拍小男孩,这时,她麻木冷漠的脸上,绽放出温柔:“儿子,进屋吧。”
男人猛地把她拉开,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眼睛里要射出电。他指指唤生,再指指汽车和李翘,嘴里嗷嗷叫着,五官都在奋力质问,忽而挤成一团,忽而大开大裂,表情生动而可怖。
男人大声问道:“这个男人是谁?你为什么和他一起回来?”
“他是我哥哥。”李翘指着唤生对男人说。
“什么哥哥?”男人跺着脚喊叫,脸憋得通红。
“是我老家邻居三婶的儿子,从小就认了哥。”李翘的搪塞让男人安静下来。可她躲躲闪闪不敢看唤生,她怕唤生知道她现在是个会说谎的女人了。
唤生的心里一阵绞痛。这么多年,他也曾幻想过和李翘再见面的场景,可眼前的景象像晴天打下的一个雷,震得他措手不及。他转身打开车门,把车里的一盒巧克力拿出来,抓了一把给小男孩。男孩拿起巧克力就往嘴里送,外面的锡箔纸没剥就大口咬起来。
男孩张着嘴,呵呵笑着,傻傻地说:“甜!”李翘的男人看到男孩的傻笑,走到男孩跟前,一伸大手,一把夺过男孩手里的巧克力,他的动作和男孩的动作一模一样,外面的锡箔纸也没剥,一下扔进嘴里,两下,他就吃完了,接着又从小男孩的手里抢走几块。
“你什么都看见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李翘木然地对唤生说。
唤生不答,脚下石头路的冰凉已经穿透他的身体。
男人吃完几块巧克力,忽然走到李翘面前,把手中的一块巧克力往李翘嘴边伸。李翘闭着眼,摇了摇头。“吃,吃!”男人生气地叫起来,李翘还是摇摇头。男人一把抓住李翘的头发,往后扯着,她的脸被扯得仰起来,男人用两个手指捏着那块沾着他口水的巧克力,硬塞进李翘嘴里。
李翘的嘴很小,男人乌黑粗大的手指把她的嘴撑开,那两片嘴唇被扯得变了形。在那双大手下,李翘的脸脆弱而单薄。
李翘含着那块巧克力,不吐也不嚼,平静的脸上淡如死水。
男人为自己的胜利,也为对李翘的所有权,对唤生得意地笑着。
李翘也想对唤生笑笑,可突然红了眼圈,两汪泪冻得颤颤地不肯掉下来。也许它们想保留最后的尊严,可奈何无论怎样拼命挣扎,它们都不可遏制地涌出眼眶。
唤生说不出一句话,他用另一颗巧克力,换下那双抓着李翘头发的手。他把整盒巧克力递到男孩手里,男孩立刻抱着巧克力跑进屋,男人松开李翘,追着跑进去,和男孩抢夺着。唤生的手碰到李翘骨节粗大、红彤彤的手,鼻腔里泛起一阵酸,心也疼得紧起来,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双手。
“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唤生说道。
“这么多年,就这样过来了,跟着两个傻子过来了。我的男人是智障,生出的儿子也是傻子。不是傻子,谁会要我呢?”李翘把泪收了,脸上又恢复平静冷漠的表情:“进屋吧,别在风里站了。”
回去的路上,夜晚,偏僻的小巷没有路灯,唤生开车走在漆黑的路上。两束车灯照着漫漫长路,盘旋蜿蜒似乎没有尽头。车窗外的夜空,星光闪烁低垂。这个一直在压抑克制的男人,喉咙里发出哽咽,渐渐变成痛苦的哭泣。
这么多年,他平稳地走著自己的道路,不动声色,神情镇定。没有掉过一滴泪。仿佛只是遵循着他的理性在走,要抵达那个地方,实现他的目标。他再也不要当一个人人厌烦的城管,忘了这段来路,他,刘唤生,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体面的人。
他咬紧牙关,封闭掉内心的情感,不向任何人开放。他在黑暗里摸索前进,让那段来路和经历沉入心底,被记忆清除干净。他在化工研究所里奋力工作,他的生活由报表、会议、出差、吃饭应酬组成。每晚回到家,头疼欲裂,电视里体育频道的声音响着,他已经睡着。
改变作息时间,让大脑更新掉城管满街跑的工作习惯。早上醒来,淋浴,剃须,挑选好衣服和衬衣,拎着公文包上班。办公室在经济开发区高耸的办公楼里,电梯唰唰上升的时候,耳朵里有微微震动。耳鸣带来眩晕。他在这里,每天工作早至晚归。他试图拥有更好的职位,更多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更多的话语权和地位。
八年里,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他对成功和业绩有着积极的渴望,这是男性社会身份的认同。像电脑游戏里的孤胆英雄一样,他在他的生存世界里拼杀、升级。他屏蔽掉曾经的李翘,屏蔽掉生命里的热情和感性。
每天下班,直到这场游戏结束,他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前看到万家灯火,他忽然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自己究竟是谁。这是他的时间,被大口大口吞噬掉、不留下任何回声的时间。他从一个年轻男子进入中年,看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开始变钝、疲惫。
四
八年前,唤生的勤奋工作使他在化工研究所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基建处刘唤生的才能在这个天地里慢慢施展开来。研究所每季度的PPT演讲竞赛,唤生做的PPT是最专业、精彩的。他报了一个电脑班,每个周末去上课,电脑技术提升很快。在全所职工大会上,基建处的PPT总是得到领导表扬。工程处、环保处、检测中心、机关党办……各部门的工作汇报被基建处远远甩在后面。
采购、和工程商谈判,唤生拿捏分寸很到位,他监督采购的材料,在建筑工程中屡屡过关。刘唤生的名字,被化工研究所的员工不断提及,所长每次开会,都会朝这个精干的年轻人多看几眼。
唤生俊朗挺拔地走在人群中间,显得惹人关注。这天,唤生正在会议室和几个工程师讨论方案,一位年轻的女子走进来,很多员工主动和她打招呼,女子微微一笑,并不说话,在会议室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听唤生他们讨论。
女子漂亮的脸庞对着唤生看,两道热烈而佩服的目光时不时盯着他。唤生在工作中,焕发出一种男性的光彩,自信而有风度,侃侃而谈。女子静静看着,着迷一般,眼光里有羞涩,但更多透出一股有底气的女人的大胆。
开完会,女子走到唤生身边说,你讲得真好,能加你微信吗?唤生礼貌地掏出手机,加了女子的微信。
女子刚一走,几个工程师围上来,拍着唤生的肩膀打趣:“唤生,盼盼小姐八成是看上你了,头一次见她主动加别人微信!”
“她是谁?”唤生不解地问。
“她是谁?只有你这个笨蛋不知道,她是林所长的千金!”
晚上回到家,唤生躺在床上,他想起林盼盼看他时热辣辣的眼光,对于一个有恋爱经验的男人来说,唤生知道那目光里包含着什么。
可唤生忽然想起李翘来。李翘可爱的面容和乌黑的长发,还有她对自己的一片柔情。唤生不知为什么,会同时想到两个人。林盼盼长得很漂亮,但那是一种富人家的女儿强势的美,毫无顾忌,一切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拿到手的张扬的美。这种张扬是有底气的,是因为林盼盼的身份。
想到林盼盼的身份,唤生心里嘭地一动。他拼尽全力从一个满街跑的城管跳到化工研究所是为了什么?他拼命工作,苦练PPT,做方案,喝酒应酬又是为了什么?自己还那么年轻,正是一个男人闯事业的好时候,他的前途发展将会怎样?如果林盼盼能帮助自己……所长女婿的身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转折……
叮咚!唤生的手机响了一下,是林盼盼发来的微信。唤生拿起手机,和林盼盼在微信上聊了起来,他很热情,和林盼盼聊到很晚。唤生放下手机,有点内疚,又有点兴奋。内疚是对李翘,兴奋是和林盼盼的发展很顺利。两种感情在心里纠缠,但终究兴奋多一些。
一个多月后,唤生邀请林盼盼参加所里的PPT演讲大赛,这是他最拿手的比赛,是展示自己的好机会。他毫无意外地取得了名次,林盼盼坐在他的身边,看台上台下神采奕奕的他,眼神简直是崇拜了。很多人都往唤生这边看,所长千金捧场给基建处才子加油,大家都暗自心领神会。
演讲完,唤生顺理成章地请林盼盼吃饭。林盼盼很高兴,两人吃饭时要了一瓶红酒,她端着红酒对唤生说:“你真能干,我很高兴能和你聊得来。每天我都闷死了,想和谁聊聊天,满城还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他当然想和林盼盼走到一起。林盼盼各方面都符合自己的目标。所长的女儿,漂亮,她身上有一种毫不遮掩的底气,不被她吸引是很难的。更重要的是,林盼盼的家庭背景能提着唤生走上一个人生新台阶,那曾经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就摆在眼前。
生活是一种很现实的东西。现在,他不得不考虑他和李翘的关系。李翘很爱他,他的内心深处,也爱着李翘。李翘的美丽善良、温柔多情,都打动着他的心。但是唤生的心里很清醒:李翘这辈子,除了摆地摊,或者将来好一点开一个小商店,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而自己,在工作上不断走远,如果和李翘在一起,将来会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生活志趣吗?他不能和一个摆地摊的女人生活一辈子!
唤生痛苦而坚决地抉择之后,他帮李翘最后一次摆了一晚上地摊。李翘还什么都不知道,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粉色长裙,长发披在肩上,她为了唤生,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唤生看了一眼,感动得有点心酸。
唤生怕自己的意志被感情瓦解,一收摊,他就对李翘说:“翘,我想和你说件事。”李翘笑着说:“什么事,唤生?”
“说出来,怕你会哭。”
李翘一愣,但她还是说:“你说吧……我不哭。”
“我在新的单位里,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她对我很好……”
李翹雷击一样愣住,很长一阵沉默,她颤抖着说:“唤生,你要离开我了?”
唤生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他对自己充满了懊恼,自责,愤怒,却又心坚如铁。两行泪水从李翘的脸上雨一样淌下。她的两只手,痉挛地抓着装手机挂件的蛇皮袋子,整个世界在她眼前坍塌了,她摇摇晃晃地快步跑走了。
唤生走在夜晚的凉风里。一口气走到南湖边,把自己重重摔在草地上,他的心里刀绞般撕扯着,却始终,一滴泪也没有落下。此刻,他已经走上另一条路,再也不会回头了。
刘唤生和林盼盼结了婚。林盼盼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扮起唤生的生活。她让唤生陪着她逛街,买一大堆东西,唤生像跟班一样拎着购物袋走在身后。也会随时给唤生打电话,说说某一品牌的皮包出了限量版,或是准备要去哪儿旅行。唤生耐着性子听电话,他不感兴趣,却一直在听。林盼盼不会做饭,每天下班,唤生都会赶回家,脱掉西装赶紧做饭。
他在努力适应着,适应林盼盼的任性和强势。唤生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婚后不久,他一跃成为基建处处长。
五
从李翘家回来,唤生疲惫而无力,他的心像经历了一场地震,边边角角都破碎了。回到家,林盼盼正在包一束花,她手忙脚乱地让唤生搬来一把椅子,站在上面,从橱柜顶取出一盒丝带,又到抽屉里找剪刀,丝带不够长,包不住花束。
“明天小霞过生日,下午我上街给她买了束花,我嫌丝带不漂亮,想换上咱家的好丝带,可偏偏不够长!”小霞是财务处处长的老婆孙小霞,是妻子林盼盼的闺蜜,林盼盼此时正满头冒汗,为丝带的长短发愁。
好出身的女人经历都单纯,也是单调的。一束花包装得漂亮不漂亮,已经是林盼盼遇到的最大难题。她忙乱地拉扯着丝带,把花束收紧又放开,包来包去,包得不成模样,把包装纸也戳破了。
林盼盼一把把花束扔在桌上,丝带丢到地上,生气地喊起来:“什么破花,包装纸又难看又不结实,下次再不去这家店买了!”她使气抱起花束塞进垃圾桶,对着唤生发火:“唤生,你也不帮帮我,没看见我一个人不会包花吗?”
唤生一动不动,静默得像一根木头。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呆呆地看着,结婚几年,还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经历过似的,空洞,白净,会为任何小事发火,永远如此。
唤生转身走进卧室,他一头倒在床上,打开电视。他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仿佛要拿嘈杂的声音来填满心里的空虚。林盼盼见唤生不理自己,发出去的火好像枪打进空林子里,连个回声也没有,她心里更憋气了。她走进卧室,拿起枕头一下砸在唤生的身上:“刘唤生,你聋了吗,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唤生一把拉起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他的心里失望而烦闷。
一连几天,下班后唤生都去李翘的按摩店,可他只把车停在远远的地方,坐在车里看着,不进去找她。多少年了,唤生出入多少开会、吃饭的场面,和各种上下级打交道,侃侃而谈,他早已不会拘谨。可此刻坐在车里,他竟记起自己也曾有过腼腆的一面。
那时,他每晚陪李翘摆地摊,收摊后,走在昏黄的路灯下,街上只有他们两人,他却不敢和她紧挨着走路。尽管他心里很想紧挨着。他只好控制自己,故意保持一点距离。但一直保持距离让他心里难受,他就有意无意,碰一下李翘,碰着她温热的手和胳膊,心在寒夜里温暖着。
唤生坐在车里远远看着,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车门哗地被打开了。李翘忽然坐进车里,她今天穿了一件水红色的大衣,头发精心梳过,脸上抹了淡淡的腮红,整个人年轻、精神了许多。
唤生惊讶地看着李翘,李翘平静地说:“唤生,去南湖吧。我知道,你每天下午都来,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南湖,这个八年前的地方瞬间回来了,唤生的心里微微震了一下。
南湖的模样没有变,平静广阔的湖面,湖边一棵棵柳树长高、变粗壮了,那些叶子更迭换新,却还是曼妙多姿,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
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商业街的大庆市场,一个卖手机挂件的小摊位,摊位上琳琅满目,人来人往,有人要手机外壳,有人要装饰的吊坠,买两个手机外壳赠一个吊坠,熟人呢,送两个。李翘嘴甜,勤快,回头客最多。她一头乌黑的长发,惹得隔壁攤位的摊主都看她。
最爱看她的人是唤生。每天一下班,唤生就赶过来,帮她摆地摊卖货。只要收摊早,傍晚或晚上,唤生拉着李翘走到南湖边上,他买两只冰淇淋,两人边走边吃,走累了,就坐在南湖边看晚霞。一阵温热的风扑到李翘脸上,李翘皱起了眉头,眼前走着的唤生,与她早已各奔天涯了……
“我信了命。”一行眼泪从李翘大大的墨镜后面流出:“你走了这么多年,我想着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你走后,我心灰意冷,以前那么大的心劲,瞬间全空了。玲花让我去按摩院工作,我就去。赚钱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我的心冷了。说好的是做正规按摩,可进去就不由我了。一个客人看上我,让我陪他睡觉,我不愿意,还骂了他。可我不知道他是黑社会啊,他第二天就带人来打我,他们用摔破的啤酒瓶打我,玻璃戳进眼睛里,我瞎了一只左眼。他临走的时候对我说,破了你的相,看你再清高!我确实不能再清高了,我的心,全散了……”
唤生眼里憋着的泪哗哗落在脸上、衣服上。他手里捏住湖边一块石头,可石头一阵阵波动着,坚硬的石头仿佛南湖的湖水,抖动着,他捏不住。他捧起李翘的脸说:“是我对不起你,翘,是我对不起你……”
“不,怪我。如果我不去按摩院工作就好了,可我要活下去啊。我瞎了一只眼,只能到盲人按摩店。像我这样的女人,破了相,又是个残疾,谁会要我呢?我只能嫁给我现在的男人。第二年,我有了孩子。孩子一落地,我的心就紧绷着,老天爷,给我一个聪明的孩子吧,可不敢像他爸,是个傻子!可一年,两年,我的心彻底凉透了,你都看到了,终究是个傻子!”
唤生一把把李翘搂在怀里,他把头埋进她夹着白发的头发里,让头发捂住他的哭泣,把奔涌的悲声全都吞回进身体里,一点也不给她听到。他深深触到的悲伤,是她的,也是他的。
南湖的风一阵阵吹涌着唤生的脸,看着抖颤的湖水,唤生想起第一次和李翘走在南湖边,他们牵着手甜蜜的情景。今天的晚霞还是那样明艳、金红,可再也不是原来的晚霞了。
唤生一阵悲痛,眼泪大滴大滴落在李翘的头发上。他痛苦地沉吟了一声:“我这一辈子,得到了什么,可我又失去什么……”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