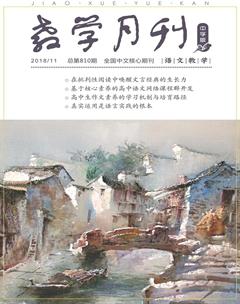用问题引领思辨阅读
梁全德
摘 要:思辨性阅读的起点是从质疑起始,立足生本,问题引领,解决“思辨什么”的问题;落点是在思辨中阅读,在阅读中思辨,学会思辨与阅读的思路与方法,解决“怎么思辨”的问题;终点是解决问题,指向发展,解决“为什么要思辨”的问题,它指向阅读能力与思辨能力的提高,进而有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终身发展。
关键词:思辨性阅读;阅读能力;语文核心素养
思辨性阅读是目前语文教学的一个热点话题,深受方家及一线教师的关注。余党绪老师结合具体的文本、整本书阅读来分析思辨性阅读的方法;朱明坤老师强调在文本矛盾处、不合情理处、文本无疑处等思维生长点进行思辨性读写;黄玉峰老师认为思辨性阅读要抓住文本的矛盾疑问处;王伟娟老师认为思辨性阅读要结合文本材料考虑读与写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才能相互提高。
以上多是从文本、经典著作的角度探讨思辨性阅读的方法与策略。若是立足于教学内容,从思维与阅读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思考,则有另一番天地。思辨性思维应该遵循问题解决的一般过程,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而阅读教学也应该遵循教学的一般过程,用王荣生教授的三点教学样式表述就是“起点、落点、终点”。
据此,思辨性阅读要解决“思辨什么、怎么思辨、为什么要思辨”这些关键问题,也应有起点、落点、终点。思辨性阅读的起点就是立足生本,问题引领,解决“思辨什么”的问题;落点就是分析问题,思辨阅读,解决“怎么思辨”的问题;终点就是解决问题,指向发展,解决“为什么要思辨”的问题。下面具体阐述。
一、思辨性阅读的起点:立足生本,问题引领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强调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对应到“思辨”与阅读上也是如此,即思辨与阅读是相结合的。这也符合语言与思维统一之说。
于漪也谈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思维是语言的内容,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有语言。”也就是说,语思是一体的。同样,作为对应的以语言呈现的阅读与思辨也是一体的。
读思如何结合呢?答曰:立足生本,问题引领,思辨阅读。思辨与阅读之间要有个中介,即问题。问题必须是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自然引起学生深刻的分析、思考。这里强调主体性,即疑问以来自于学生主体为佳。问题来源于学生发现的点,来源于文本与生活的结合,来源于学生自我的经历,来源于学生自我的初步感受。这样,问题就具有驱动性,能够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也有利于教学的开展。当然,这里面也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与教学智慧,应该思考“哪些是浅层问题,哪些是深层问题;哪些问题可以一带而过,哪些问题需要深挖;哪些问题是知识性问题,哪些问题是策略型问题;哪些问题具有思辨性”等等。
思辨的起点就是生成问题。问题的形式有三种: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目前阅读教学中多是“是什么”类的问题,而“为什么”“怎么样”类的问题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辨。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多用比较性思辨与假设性思辨,比如“为什么赵王派蔺相如赴约渑池之会,而不派廉颇”“为什么在鸿门宴时刘邦把一文一武都带上了,而在渑池之会时赵王不带廉颇呢”“假如你是范增,你会如何劝说项羽杀了刘邦,而真实的范增为何没有劝说动项羽呢”等等。
钱理群教授在《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中也列举了很多如何“立足生本、问题引领、思辨阅读”的案例,比如鲁迅作品的教学:以《五猖会》《父亲的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作品为例,寻找作者和读者的生命的契合点——“怎样做人之子与人之父”;以《祝福》为例,思考除了讲祥林嫂如何受到四种权力的压迫,能不能联系学生周围的生活,思考祥林嫂是一个不幸的人,以及她不幸在哪里,咱们生活中有没有不幸的人,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以《藤野先生》为例,可以从“写老师”的角度思考鲁迅是怎样写老师的,如果我们写自己的一个老师,可以怎么写;以《药》为例,抓住学生阅读的第一感受——“恐懼”,思考这个故事让人“恐惧”的地方表现在哪儿。
这里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已知概念出发的“求证式阅读”;另一种是从感受出发的“由外而内,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发现式阅读”。两种读法都是从文本与学生经验相结合的方式,以问题为中介进行阅读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立足生本、问题引领”就是在研究学情的基础上,在学生初读文本时自主生成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切入口进行思辨性阅读教学。若不立足生本,就会出现脱离文本、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等现象,就会出现违背阅读与思辨规律的问题。比如教学《愚公移山》时,若不以文本为依托,就会出现“愚公是在破坏大自然”之类的错误理解。
二、思辨性阅读的落点:分析问题,思辨阅读
思辨性阅读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统一体,即思辨与阅读的统一,具体地说是“在思辨中阅读,在阅读中思辨”。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重探讨如何分析问题,思辨阅读。
(一)在思辨中进行阅读
按照思维的规律进行阅读,才能更好地提高思辨能力和阅读能力。那思维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思维的内涵。
心理学认为,思维的过程有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抽象概括与具体化等。文秋芳教授提出了更具体的思维能力分层——思维能力层级理论模型。他认为思辨能力的认知技能包括分析、推理、评价三个技能,其中分析包括归类、比较、区分、阐释等技能,推理包括质疑、假设、推论、阐述、论证等技能,评价是指评析思辨的整个过程和结论。
根据思维能力层级理论模型,笔者思考:既然要培养这些能力,那么能不能用这些能力层级反过来进行阅读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通过分析、推理、评价、比较、分类、假设、矛盾等思维方式进行阅读呢?下面结合具体的事例谈谈分析式、推理式、评价式等几种典型的思辨性阅读方式。
1.分析式阅读,加强思维的深刻性
分析式思辨性阅读就是通过归类、比较、区分、阐释等方式分析文本在内容表达、情感抒发、构思特色、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处,深化对文本的理解。比如学生比较柳永的《雨霖铃》与《八声甘州》(两篇都描写了秋雨),生成“这两篇词作对秋雨的描写有何不同”这样的问题,进而提出“还有哪些描写秋雨的作品,又有何异同”的问题。用这个小问题既比较了两篇具体词作的写秋雨的特点,又以小见大了解了秋雨意象在中国诗词中的地位及作用。这就是用生成的具体小问题促进深层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促进由单一知识、能力学习向类知识、能力学习的转变。
2.推理式阅读,提高思维的批判性
推理式思辨性阅读就是通过质疑、假设、推论、阐述、论证等方式有理有据地进行推论,从而深入理解文本的内容与主题等。尤其是质疑文本的具体语言矛盾处、文本与学生体验不符处,更能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从而通过在文本中找依据深化理解。
比如《药》中说到华老栓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治病,花了很多钱买了人血馒头,结果华小栓还是死了。此时有学生问:“华老栓为什么去买人血馒头,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一点血来做人血馒头啊?”这个问题给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从问题生成的角度来看是个好问题。但是作为语文教学,要从语文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主题的角度来看,华老栓若是用自己的血来做人血馒头,只能表现华老栓疼爱孩子——为了孩子可以流自己的血。而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关键是这个人血是革命者夏瑜的。华老栓为了给儿子治病,不会关心“这是谁的血,这人是革命者吗”。华老栓用的是革命者的血,说明他对革命不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夏瑜革命被砍头,自己的血却被用来做人血馒头,可见其革命的悲哀。
从人物的角度看,华老栓若是用自己的血来做人血馒头,只能出现几个人物——华老栓、华小栓、华大妈,没有了夏瑜、康大叔、看客这些人,那么人物就局限于一个家庭的成员,人物之间的矛盾就单一了,人物形象也就不突出了。用夏瑜的血做人血馒头,就可以看出康大叔的凶残、贪婪,可以看出看客的愚昧无知、可悲,从而由人物关系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
从情节的角度看,华老栓若是用自己的血来做人血馒头,线索只有一个,就是华老栓给儿子治病,情节也就显得单薄了。用了夏瑜的血做人血馒头,可以引出“买药、谈药”等情节,从而看到许多众生相,更有利于表现人物形象及主题。这实际反映的是作者情节构思的特点。
由此案例可以分析得出评价式思辨性阅读的操作流程:从学生质疑起始,通过假设另一种情形,与作者的表达进行比较,依据文本内容,依据文体的特点,进行推理论证,从而批判性地理解作者如此表达的妙处。
3.评价式阅读,保证思维的正确性
评价式思辨性阅读,就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评析同学的或自己的见解与观点,从而对思维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价。简言之,即是对自我或他人观点的验证与评判。而验证与评判的依据主要还是来自于文本信息,这样才能验证与评判阅读的正确与否、深刻与否。
比如学习《祝福》时思考“祥林嫂是因为什么死的”这一问题,学生说出了“丧夫死儿”“没工作了,穷死的”“捐门槛问灵魂后无望”“别人对她不同情、不理解”等等理由,由此可通过文本细读,从文本中找依据,进一步验证自我观点的正确性;然后思考“这些死因中最致命的是什么”,由此可对祥林嫂人物形象与命运进行深层思考,思考一个人的悲剧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社会悲剧;最后以“祥林嫂死因之我说”为题进行写作评论,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既对自我观点进行了验证与评判,又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思辨,做到“读思写一体”。
要强调的是,评价式阅读并不仅仅是在阅读结束之后,还可以在阅读过程之中,即对思辨性阅读的思辨,主要体现为学生对思辨性阅读的方法、内容、观点等的评价。通过评价式阅读来提高思辨性阅读的能力,可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及思维的正确性。
(二)在阅读中进行思辨
阅读的核心是理解。从构篇的角度看,阅读是理解字词、句段、篇章的意思;从理解的对象来看,阅读是对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实用文等不同文体的理解;从理解的层次看,阅读既要理解文本的表面意思,更要理解文本的深层内涵,包括文中寄予的情感、文化价值等;从理解的取向看,不同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理解是需要思维的,正如方鸣先生說的:语言活动的背后是思维活动。
按照阅读的规律进行阅读,方可有利于思辨性阅读。每一篇文章都是由字词句段篇逐层建构的,可以依据这些构篇因素来进行思辨性阅读;而相同类型的文章归为一类,形成一个个体式,也可以依据这些体式进行思辨性阅读。
1.依据构篇因素进行思辨阅读
一篇阅读文本由字词句段篇逐步构成,从而形成“标题、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构篇形式。我们可以依托构篇因素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思辨性阅读。
“自上而下的思辨性阅读”是指从文本的整体到局部的思辨性阅读形式,即在阅读过程中,理解字词、分析内容、欣赏艺术形式,都要考虑文本整体特性对部分的约束关系,正所谓“字词是篇章中的字词,句段是篇章中的句段”,不能断章取义,不能肢解文本的整体。比如学习《故都的秋》时,只有抓住故都的秋“清、静、悲凉”的整体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写‘清晨静观、落蕊清扫等五种景色”,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作者认为牵牛花‘以蓝色或白色最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
“自下而上的思辨性阅读”是指从文本的局部到整体的思辨性阅读形式,即阅读过程中通过分析具体字词句段等内容及艺术形式,进而理解整个篇章的内容及特色等,也就是抓住 “诗眼”“文眼”、关键词、关键句、细节之处、标题,或者能够引起疑问的其他词句,然后把它放在整个篇章中进行品味。比如学习《琵琶行》时欣赏“前月浮梁买茶去”,可以思考这样一个思辨性问题:“如果把‘前月改为‘前往,好吗?”学生能理解“‘前月表明时间长,说明‘商人重利轻别离,而‘前往只是动作表现而已”。但是如果只是分析到此,那就是断章取义、宾主颠倒,因为《琵琶行》谈的主要对象之一是“琵琶女”,所以只分析到“商人如何”自然不妥,而应将此词放到整个文本中进行理解,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提升。“前月”实则突出琵琶女被冷落的境遇,与前面的年少时才貌并举形成对比,也为下面的议论——“同是天涯沦落人”作铺垫。
2.依据体式进行思辨阅读
上面谈的是依据文本个体进行思辨性阅读,下面阐述从体式的角度进行思辨性阅读。从体式的角度进行思辨性阅读,可以让学生的学习取得“由学一篇到学一类”的效果。梁启超先生说:“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所以,教给学生各种文体的欣赏方法,比单教一篇文章重要得多。
王荣生教授从教学内容的确定入手进行体式研究与实践,具体探讨了如何教学实用类、文学类、文言类文本。那么,依据体式进行思辨性阅读也是一个重要的路径。具体说就是在实用类、文学类、文言类文本学习中如何思辨。诗歌的思辨阅读,可以从意象的区分、比较、归类等角度进行。散文的思辨阅读,可以从写景类、写物类、写人类等不同的散文体式进行思辨。譬如写景类散文重要的特色是借景抒情,那么可以将景同而情不同的散文进行对比阅读,以深入思辨写景的妙用,也可以将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散文进行比较阅读,以思辨作者的行文风格等。小说的思辨阅读,可以从具体的情节细点、叙述视角、人物言行与心理、环境的比较等角度入手,深度思考小说内容为什么这样安排、揣摩人物言行背后的人物心理、若是变化叙述视角会如何等具有深刻思辨性的问题。戏剧的思辨阅读,可以从戏剧冲突、个性化的语言等角度进行思辨,并将节选内容与整个剧本进行联系,推测人物的命运变化,并将推测与剧本情节进行比较,思考作者为何如此表达。
现有思辨性阅读的实践教学,多是指向文学类作品,那么实用类作品能不能进行思辨性阅读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学习朱启平的《落日》,完全可以把各国写日本投降事件的报道搜集起来,然后思辨“朱启平为什么这样写而其他国家那样写”,思辨“作者为什么还要多写‘白马故事”,“事件报道结束文章就应结束了,为什么文章最后又增写‘投降书脏了这个细节”,最后思考“如果要是你来修改朱启平的这篇通讯,你认为可以有哪些改进,说说理由”。如此有助于理解事件通讯写作的要求及目的、作者写作内容与写作目的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从而设身处地地领会通讯写作的过程,并在理解与领会中提高思维与表达能力。
当然,分析问题、思辨阅读时,教师还需要教给学生一定的阅读思路与方法。“在阅读中思辨,在思辨中阅读”,意即:思辨从何而来,思辨从学生对文本的质疑而来;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从阅读中找依据,然后通过概括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阅读思路与方法。
三、思辨性阅读的指向:解决问题,指向发展
思辨性阅读的指向问题,需要思考的就是进行思辨性阅读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各方家都有所阐述。目前的主流看法是思辨性阅读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为目标,这是因为现在的阅读教学缺少思辨。吴格明教授在《语文教学应当倡导思辨性阅读》一文中认为,倡导思辨性阅读,就是要提高阅读教学中的思维含量,因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理性精神贫乏”,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娱乐文化的时代”。那么,对于语文阅读教学来说,思辨性阅读到底指向哪里呢?对此,笔者的思考如下:
在思辨中进行阅读提高了阅读理解能力,包含理解、鉴赏、探究、浏览等能力,其中理解能力排在核心位置;在阅读中进行思辨提高了思维能力,包含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论证、推理等能力。思辨性阅读是一种阅读教学,也指向阅读能力的培养,同时以思维能力的提高为重点。需要强调的是,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是思辨性阅读的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了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强调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那么,思辨性阅读的指向就不能只限于思维能力与阅读能力,它涉及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诸方面,而其中的思辨既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或者说既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一个教学目标。
详细一点说,读思结合的成果如何表现出来,要靠说、写。而无论是其中哪一种,都涉及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如李林甫老师在教学《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时,请学生填空:“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 。”有的学生填了“星星”,有的学生填了“天空”等。此时李老师将诗歌中对应的意象抽出来,问“这些意象有什么特点”。学生明确了该诗意象阔大的特点,此时再问填哪个内容更合适时,学生就明确了方向,即选择“天空”而不选择“星星”,或者把“星星”改为“繁星”。通过比较思辨,学生明确了写景特点,也学会了如何恰当地使用意象。
读思结合的指向也有文化的传承、审美的追求等方面内容。比如学习《琵琶行》时,读到“别有幽愁暗恨生”,有学生问:“为何不是竖心旁的‘忧愁而是这个‘幽愁呢?”通過引导学生联系文本,教师可以让学生明白“幽愁”不仅含有忧愁之意,而且有“嫁作商人妇”的幽怨,还有无人诉说的幽恨孤独之意。这样就让学生理解了情感,学习了诗歌的练字之美。而这练字之美既是中国诗歌文化的优秀传承,也是审美的表现。
每个人的思辨性阅读的方向、深度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体现了个性化。读思结合的最终追求就是促进个性发展、终身发展,关注人性、人生、个性、生命、社会等重大问题,正如连中国老师所说:“思辨应该始终指向‘人,并且始终关心‘人。”思辨性阅读应该“强调生命体验与认知视野相结合”。
在前面的这些指向中,阅读能力与思辨能力是直接指向,其中思辨是重点,因为阅读的本质就是理解,理解是需要思维的;语文核心素养的提高是思辨性阅读的高层次指向;重视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关注人性与生命,注重文化的传承等,则是思辨性阅读的长远目标。
综上所述,阅读教学活动、思辨性思维活动是同步进行的,思辨性阅读教学要遵循阅读教学、思维过程的一般规律,从质疑起始,在思辨中阅读,在阅读中思辨,最后指向阅读能力与思辨能力的提高,进而有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促进学生个性与终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