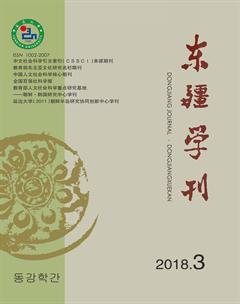近代日本共产党与“国学”的关系
史少博
[摘 要]大正与昭和时期,一部分日本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意识形态逐步开展各种运动。而当时日本近代“国学”主张“天皇至上、万世一系、君臣一家、忠孝一致”,其中,“天皇至上”“日本精神”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可知,日本近代共产党与“国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第一,近代日本共产党的初期思想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第二,近代日本共产党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反对天皇专制,反对近代国学者所倡导的“国体论”;第三,近代日本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国学”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近代日本共产党;国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30-05
早在大正与昭和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就开始被一些日本进步人士所接受,成立了各种组织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天皇专制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后,日本共产党终于在1922年7月15日正式建立。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经历,但都归属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明治时期的每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形成过程中,幸德秋水在阅读了夏福理的《社会主义精髓》后断定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在对社会事业产生疑惑时阅读了贝拉米的《回顾》,之后对社会主义有所顿悟;片山潜也称《拉萨尔传》使得他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社会主义,依靠坚持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政党。”[1](117)可以说,每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脱离不开原有的文化积淀,日本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亦是如此。
一、近代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儒学”
最初,日本用“社会说”“社会论”“社会党”代指“社会主义”。1878年6月,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文章,首次使用汉字的“社会主义”一词;1887年,“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流行。甲午战争之后,社会主义从冷遇、被理解的阶段步入了形成与应用阶段。正如朱谦之所言:“明治三十年(1897)以前,先进的欧美社会主义思想早已输入日本,例如明治十五年中江兆民创办的《政理丛谈》中,载有田中耕造译的《社会党》、日下东男译的《社会党主义》,介绍17至19世纪前半叶以法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潮。明治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中江门下酒井雄太郎的《在欧通信》中报道欧洲的社会党现状。明治二十六年作为《平民丛书》第六卷之《现时的社会主义》,简明而系统地说明社会主义各派的主张。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真正开端,乃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那时候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棉纺织工业、军需工业、金属工业、造船业等飞速发展,同时也就有近代的无产阶级与工人运动的产生。明治三十年4月在东京创立职工义友会,加入者有片山潜、铃木纯一郎等。同年7月劳动组合期成会创立,……发行运动之机关报《劳动世界》(半月刊),片山潜主笔。三十一年,社会主义研究会创立,开始组织学术团体活动,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用于日本。”[2](277)
其实,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最初的成员是以村井知至、安部矶雄等基督教徒为中心的。可见,其思想与基督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幸德秋水、片山潜、木下尚江等人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圣西门、傅立叶、拉萨尔、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得以流传。但这一时期改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
后来,经过“片山潜(1859—1933)、安部矶雄(1865—1949)、堺利彦(1870—1933)、幸德秋水(1871—1911)等人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期;又经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介绍《资本论》;高畠素之(1886—1928)完成《资本论》全译本,接受马克思理论和开展相关运动的条件逐渐成熟。也正是这一时期,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1880—1958)、栉田民藏(1885—1934)等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理论家崭露头角。然而,这一阶段每个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理论尚未真正应用到日本史研究之中,尽管在佐野学(1892—1953)的论著中可以看到雏形,但无论在理论诠释层面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具体运用层面,达到一定的水准还有待于野吕荣太郎的出现”。[3](72)
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科学性,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昭和前期一方面给人一种强烈的阴暗印象,例如危机、右翼恐怖、战争、超国家主义、皇国史观;但另一方面,明治以来日本学术通过吸取欧洲的学术文化而得以发展,经历大正民主时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即使学术界不得不在战时(大約1937年左右)迅速向军部统治、翼赞政治屈服,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客观考察本国历史的传统。昭和前期马克思历史学方法得到磨练,在明治维新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取得了为编年史式实证研究所忽视的重大成果,提示了日本近代社会、国家的历史观,但不断受到相关领域的刺激,起源于各种关注点的实证历史研究得到了推进和积累。”[3](88)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明治时期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在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之前,就已经是儒学者,如,“明治三十四年……会员们以‘社会主义协会为中心,努力把海外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介绍到日本。即在这一时期,片山潜从基督教的社会改良主义出发,通过与生长中的工人阶级的结合,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所写的《我的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及森近运平、堺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被称为明治时期的三大名著。”[2](278)虽然,在日本社会主义组织建立的初期,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思想相纠缠,但一些日本共产党员的思想也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正如日本共产党早期代表幸德秋水所说:“我从幼年起,即爱读最急进的、最过激的、最极端的、非军备主义、非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书,这些书都不是欧美文字的翻译,纯乎是我东洋人的著作,而东洋人多数不甚加以尊重的,即老子、庄子之书,释迦的经典……我是从儒家进入社会主义。”[2](285)由此可知,日本共产党明治时期的主要代表幸德秋水是从儒家思想过渡到社会主义思想的。
河上肇“大正二年(1913)留学欧洲,回国后任京都帝大法学部教授。大正六年(1917)发表《贫乏谈》,影响很大。恰如著者自述,此书‘打算奉孔子立场来论富论俭。书中虽也论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貫穿着儒教的伦理主义,要求为政者、富者施行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距离很远。堺利彦批评他是‘孔孟的仁道主义、佛教的精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维持现状的妥协主义等等即不彻底的混合物。”[2](430)显而易见,在明治时期,有些日本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相互交融的。
二、日本共产党与日本近代“国学”的国体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官方非常重视国学派。”[4](21)而日本近代“国学”推崇“国体论”。“‘国体一词自明治时开始使用,但关于其内容却莫衷一是。”[3](44)
日本近代的“国学”家,把“国体”解释为“君民同祖”“万世一系”的国家观,关注日本的国体、政体,强调国君对臣民的慈善之心;特别重视臣民对君父尽忠尽孝,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关于“国体”,从幕府时期就推崇“尚武”,对此,日本学者会泽正志斋这样描述:“国之体其何如也?夫四体不具,不可以为人。国而无体,何以为国也。”[5](215)
会泽正志斋认为,“日本建国之初就是尚武的国家,这些是他所见的日本自古以来优越性的独特性和‘国体。”[5](216)近代日本的“国学”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右派御用学者蓑田胸喜在他的《学术维新》(1941)中公开仇视马克思主义。蓑田看来:‘现今日本万恶的本源,毕竟出于可以目为思想参谋本部之帝国大学之违宪反国体学风”。 [2](390)日本近代的“国学”者热衷“国体论”,排斥社会主义思想,日本共产党员遂与之展开抗争。
日本近代共产党反对“国学”所主张的天皇至上、万世一系、君臣一家、忠孝一致。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要反对天皇专制,反对近代国学者所倡导的“国体论”。例如,自称为“纯正”社会主义的北一辉,于1906年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认为“国体论”中的天皇是由迷信所捏造的土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发生巨大变化,其主体应该是国家本身而不是其他。他批判天皇的神权,反对明治政府所宣扬的建国理念,称所谓的描述皆是不符史实的虚构理论,不应困守于天皇治国的神话框架。他说:‘今日之国体已非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为其利益而存的时代的国体,而是国家的实在的人格已作为法律上人格而被认识之公民国家的国体。……若不否定天皇论,便无法否定明治政府体制,便无法引进新的宪政学说,也就是他在宣称社会主义之际选择以否定天皇制来破题的原因。”[6](210~211)北一辉进一步说道:“日本的历史只可追溯到4世纪,而不是由神武天皇创世于公元前660年,在国家的形成、皇权的确立、政治与宗教的分合等相关具有指标性的文明发展议题上,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所谓日本是神国化身的‘日本神国论、开国以来便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统治的‘天皇治国论、军民关系是伦理亲情关系的‘家长国家论等,皆是虚构理论;明治政府所强调的国情特殊论,只是掌控政权的萨长同盟不愿意因西方宪政民主思想的导入而影响其政权稳定,所刻意制造的假象等。”[6](211)北一辉反对皇权专制,在政治上追求普遍选举的实施以及参与权的扩大等;在经济上提倡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他认为人的贫穷,其原因是资源的被垄断,社会正义的考量,其重心不在于财富的分配手段,而应该在于资源的划分标准,故而主张要实现资源国有化。
值得注意的是,北一辉虽然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反对日本“国体论”推崇的“天皇制”,但是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与当时日本国学者所倡导的“国体论”本质上仍具有一致性。因为“北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真正反对国体论者的主张,相反地乃是在‘社会主义名义的幌子下,给日本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2]( 393)可见,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而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鼓吹军国主义,推行对外扩张,通过“国体论”推行皇道主义与军国主义。故此,北一辉的“社会主义”与近代国体论者所倡导的“国体论”本质上是一致的。
明治时期,也有一些共产党员与国学者们所推崇的军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例如,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幸德秋水,“对于军国主义,幸德秋水指出其原因在于‘好战的爱国心‘虚荣心‘狂热心…… 他认为‘军国意味着腐败和道义的沦落,军备扩张会引发诸多恶劣影响……幸德秋水将战争描述为‘目的卑污‘手段陋劣‘狡猾‘欺诈‘阴谋‘诡计等……在他看来,所谓的‘爱国心与领土扩张政策的大肆宣扬等,加剧了帝国主义在当时的泛滥……幸德秋水提出了实施方法,即‘变少数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刈除掠夺的帝国主义也,是救之之必要也。即通过社会主义的实现来消灭帝国主义。”[6](140~144)
日本近代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国学者推崇的“天皇至上”的斗争中,有些被捕、被杀。例如,“古河力作在1911年的遗书《我》中提到,‘期待自由、平等、博爱、相互扶助、万人安乐的社会,而不是生活困难、贫困、生存竞争,没有牢狱、实现永远和平与四海皆兄弟的社会……天皇是与我们流着相同血液的人,必须打破国民的迷信。将矛头指向天皇制……在幸德秋水被判处死刑的1个月后,河上肇撰写《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称:日本当局之所以不让幸德秋水活下去,并非像西方诸国那样,是因为其害怕暴力……因为对日本来说,‘最至上的价值是国家,日本最害怕的正是‘破坏国家至上的主义”。[2](286~289)由此可见,日本近代共产党为了与近代国学所推崇的天皇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相抗争,不惜牺牲生命;主要代表幸德秋水等人的思想与近代国学者所倡导的“国体论”是直接对立的。
三、近代日本共产党与中国近代国学者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崛起,要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以振兴中华。“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洋务派官员张之洞曾说:‘出洋一年胜于读书五年。培养担任改革的人才留学很有效果。日本被选为留学国家的最大理由是,为引进欧洲的学问、技术而以日本的经验为参考。而且,清朝由于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而难以维持体制,而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的欧美各国更能够放心地派送留学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取得的学位逐渐可以代替科举获得功名。起初只有十几名的日本留学生到了1905年增加到8000名。1906年则急剧增加到12000名。” [7](120) “据统计,在1850年至1889年间日文翻译著作占翻译著作的15.1%,到1902年至1904年间已经占到60.2%。” [8](420)
大批留日学生,包括中国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通过日本翻译的欧美书籍了解西方近代思想,同时也大量地接触了日本近代的“国学”,并通过日本的各种学会、刊物摄取了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民报》,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民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梁启超主导的《新民丛报》。1906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国民没有能力实行议院政治,只有日本成功的开明专制才适合,于是两者之间开始了争论。” [7](137)两者相比,《民报》刊发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1年起,中國近代的国学者们不再相信清王朝的统治者会主动让权,进而东渡日本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在近代“西方东进”的浪潮中,日本无疑起了“中转站”的作用,中国的仁人志士通过翻译大量的日本文献,了解了社会化主义;聆听了日本社会化倡导者们的讲授,深受鼓舞。
康有为,博览群书。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讲学,“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所不讲。”[9]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其十分关注日本崛起的原因,对日本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以强敌为师”之主张,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勾画了社会发展的蓝图,有学者称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也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存在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从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能够看到,从1874年起他就开始关注日本。此外,日本学者也考证到:“根据(康有为)这些记载,康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关注明治日本。但是以上证言全是戊戌政变之后写下的,为了扩大先见之明,将时期提前的可能性很高。” [10](3)尽管学界对康有为关注日本的时间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对日本的近代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渴望将大量的日本书籍介绍到中国,而其在大量搜集日本资料期间,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梁启超,把日本近代的“社会主义”概念引入中国。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其《论强权》一文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据有关学者考察,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使用“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其接触社会主义概念,与“东学”有关,即在东渡日本期间,与接触到的日本思想有关。梁启超指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 [11](384)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梁启超是最早的介绍人之一。” [12](367)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尤为重要。梁启超自己也常常以“社会主义”理论家自居,认为他人不懂社会主义,如其所言:“彼辈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 [13](436)有学者研究称,当“马克思主义”与“国学”初遇时,梁启超评价康有为道:“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11](489)可见,梁启超显然是在国学视野下分析社会主义的。
刘师培,1902年与章炳麟结识,并与章炳麟、蔡元培、谢无量等一同进行反清革命。同时,其参与了《警钟日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著有《攘书》《中国民族志》《经学教科书》等书籍。1907年,刘师培夫妇应章炳麟等人的邀请东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1907年6月,受当时日本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等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了《天义报》和《衡报》,并以此为阵地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专制制度、废除等级制度,主张人权平等,且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1908年,刘师培携全家回国。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在成都国学院讲授国学,后与谢无量等人一同发起、成立了四川国学会。1917年,刘师培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国学。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等人一起成立了“国故月刊社”,在北京大学主导发起《国故学刊》,由此刘师培成为了国粹派。
黄兴,与孙中山一道是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策划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据学者考察,黄兴曾经先后进出日本共计10次。流亡日本期间,他受到了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所”所讲授社会主义思想的浸染,给予了黄兴很大的帮助。
李大钊也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之一。他于1913年东渡日本,1915年9月8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14年至1916年间,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安部矶雄先生在早稻田大学讲授“都市问题”等课程,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中有记载:“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 [14]后来,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为了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其思想是各种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认与接触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国学者中所萌发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与东渡日本,深受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1][日]劳动运动史研究会编:《周刊社会新闻》,东京:明治文献资料刊行会,1902年。
[2]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日]永原庆二,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日]重野安绎:《大日本维新史》,东京:善邻译书馆,明治三十二年(1899)。
[5][日]今井淳、小泽富夫编,王新生译:《日本思想论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7][日]菊池秀明,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清代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晚清(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9]卢湘父:《演讲万木书堂,缅怀学风纯正》,《香港华侨日报》,1959年3月14日。
[10][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と「东学」—「日本书目志」をめぐつて》,东京:汲古书院, 1992年。
[11]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12]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森正夫:《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北京日报》,1982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 朴哲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