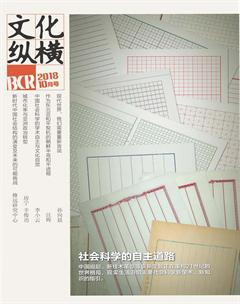迈向万物互联时代的新哲学
段永朝
以“文化重建”为己任的《文化纵横》杂志,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思想评论刊物。在智能科技日益介入人性、重塑物种的当下,充分反思科技哲学的底色,对于理解科技与人文融通的重要性,尤为迫切。谨以这篇小文,纪念《文化纵横》杂志创办十周年。
物联网近十年来中国与世界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信息革命的发生,这场革命起源自上世纪80年代,其凯歌高奏到今天的结果就是:技术狂人、商界领袖、政客和传媒记者们,在“无所畏惧”地创新并行动着。他们不停地“宣布”新的时代和“下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信奉“行动和实用的哲学”(阿伦特、杜威),他们仍然秉持“伟大社会”的进步逻辑,只是嘴上已经不这么说了而已。
这场信息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组成环节是物联网(其实根本上是互联网)的发展,其刻画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版图:所有的“物”都将联接起来;“物”和“物”之间将能“感知到”彼此的“存在”;任何一处“物”的移动、增减、分拆与合体,都将“瞬间影响”到另一处“他物”。物联网的喧嚣,从行动上彻底拒绝了古典哲学家从容不迫、慢条斯理地思考、紧张、焦灼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一切约化为连线、计算、唯一的识别代码、无线射频技术和分布式网络。“现代之后”的哲学家们,在面对纯粹自然的退隐(人工智能专家西蒙,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是“人造的自然”)、客体不断嵌入主体(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时代,以及200年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境遇时,不是滑落为权力、文本、语言的诠释者(福柯、罗兰·巴特、索绪尔),就是堕入深深的欲望、身体的困顿(梅洛·庞蒂、德勒兹、巴塔耶),任由爆裂的身体漂浮在能指符号的空间(德里达、鲍德里亚)。
以上这幅画面,是看待物联网——这是个生硬的、缺乏灵气的词语——的哲学问题的背景音乐。
一个“门儿清”的世界?
正如信息技术的先知凯文·凯利所说,我们的世界正在走向“机器的生命化和生命的机器化”(《失控》)。由此,对这个“人与物彼此嵌入的世界”的判断是这样的:这将有助于人,有利于人。这是好的,是善的。这似乎是一个“门儿清”的世界。在这个“门儿清”的世界里,丢失的钥匙会自主呼叫它的主人,窗户能感知雷电暴风而自行关闭,冰箱可以发出续订牛奶的订单,砧板上的鱼肉拥有唯一的识别码,吞咽下的药丸也能发出GPS信号……甚至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动分类。这个“门儿清”的世界,再也无法区分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那些被视为“客体”的物质,已经不是“独立地外在于主体而存在”。借用福柯的术语,关于主体/客体的哲学,将成为哲学的考古学。这个世界不但将万物融会贯通,更通过物联网,将无机界、有机界、生物界融会贯通。在这个彼此扭结、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里,传统“两分法”已不再适用。
换言之,物联网许诺了一种令人心醉的未来生活图景:信息就在你的指尖(比尔·盖茨语)。想象力丰富的技术天才们,敞开自己的大脑,让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为这个世界赋值,他们提供这个世界的不断更新的版本,他们致力于让生命徜徉于虚拟空间自由地嬉戏。技术天才的创造活力一再地被投资者、商人和政客俘获;而商人和政客的思维逻辑,迄今没有突破笛卡尔哲学的藩篱: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善,相信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完全可以配置好资源,相信这一切预示着伟大的进步。但是这一切,不幸全出错了。脱胎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工业革命,实质就是“速度革命”,动力、能源、大机器、流水线,一切自然的物的节奏和形态被打破,被重新安置。这种技术的力量并非完全外在于人那样“客观”,它简直就是人的具体呈现。
“坏”的哲学
总之,工业革命,乃至今天的信息革命从此拥有了一个“坏”的哲学。一个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扭曲了的哲学;一个给蛮力垦拓、贪婪占有、快速飞奔以合法性的哲学,一个道貌岸然、斤斤计较、呻吟作态的哲学。这个“坏”的哲学,有两点非常可疑:其一是崇尚抽象的思辨,对充满欲望的身体的贬抑和忽略;其二是崇尚时间,对丰富的异质性的空间的贬抑和忽略。而这两点,恰恰是物联网的“魂”之所在。
诚然,言及至此,试图构筑这个物联网/互联网哲学的冲动是难以勃起的。一方面,宏大叙事、终极叙事,一直是物联网/互联网行动主义者们有意无意地利用着的“死棋”,他们不肯将这些死子从棋盘上彻底清除。他们知道这些“死子”还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和感召力:比如技术的决定论、人的价值、进步的权力。另一方面,后现代叙事消解中心、剥离意义、解构文本、颠覆权威的暗流,不时地将“流变的世界”(赫拉克利特)、“欲望的生产”(德勒兹),与技术的兴奋感嫁接起来,用以迎合消费社会的兴盛,讨好体验世界的虚假快感。保持开放的姿态、保留控制的权力——这是物联网/互联网时代政商联盟的思想共识。将文本和批判的文本,统统吸收为冗长的符号消费列表中的条目。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战略制高点、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21世纪的重大方向……这些语汇的背后,无一不流露出物联网/互联网哲学的“骑墙”风范:用后现代、后消费社会、后结构主义,以及新媒体、新历史主义、新社会网络,撰写政论片/宣传片/广告片的拍摄大纲和解说词,选定机位、拼贴和混搭素材,将个性化、异质化和多样性作为渲染的调色板;以普适价值、进步主义、威权知识、道德情操、秩序与范式、革命与改良、气候与环保、幸福社会、快乐人生,作为恣意汪洋的基调、底色和潜意识。
平心而论,物联网/互联网为21世纪哲学的转向,提供了难得的思想土壤。不过,这个土壤目前正意气风发地沿着增长、繁荣、进步的道路挺进。在信息革命发生30余年来,物联网/互联网哲学的身份,一直被未来学家所僭越。他们信奉的口号是: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造出来!
一点曙光
据西蒙·克里奇利考证,西塞罗并非是第一个将死亡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人。有记载的历史表明,柏拉图比西塞罗早300年就提出“哲学乃死亡的排练”。文艺复兴思想家蒙田,在《蒙田随笔集》中写道,“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叔本华认为,“如果没有死亡,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马克思也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说过“辩证法是死”、“死亡是不朽的本原”这样的论断。“死亡”并非是哲学思考的对象,而是哲学思考的“情境”,是哲学思考驻留其间、审视其间、挣扎其间的情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造就了一种新的哲学情境,其特征就是“工程师化”。
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摆弄机器的工程师”逐渐替代思考“针尖上有多少天使”的科学家,成为历史进程的主角;这个深刻的思想寓意指向的是,“死亡”被驱逐出了哲学思考的领地。物联网/互联网的天才工程师们,与商人、政客、传媒的结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这个世界的模样。但是,数字原住民一代的兴起,或将带来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对这些沉浸在数字世界、虚拟空间的新人来说,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像木乃伊,而尼采/叔本华/萨特的哲学像抑郁症患者,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只不过是不停地呼喊“皇帝未穿新衣”的小孩儿,德勒兹/巴塔耶的哲学处处闪亮着狡黠的目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思潮都将持续存在,并共同迎接哲学思想整体死亡与新生的到来。当然,死亡是不能被宣布和宣称的,也不能通过驱逐的方式催促其发生。哲学的死亡一定伴随着新生,在宏大与卑微、大叙事与小叙事、还原论与整体论、表象与意志、欲望与身体的交织缠绕下,同台共舞。
这或将是未来哲学充满悖谬的土壤。那么,这还是一个“门儿清”的世界吗?
(作者单位:北京苇草智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