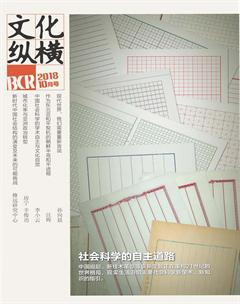城市化率与亚洲政治转型
房宁 丰俊功
[文章导读]二战以后,亚洲诸国家或地区普遍经历了20世纪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型。然而,政治转型给各国家或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却各不相同。为什么政治转型在有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带来的却是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和发展停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抓住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这一深层动因,提出了分析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一套理论框架,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在城市化率与该国家或地区政治转型的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
引言:城市化率与政治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本、韩国、台湾为代表的一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这些国家与地区实行的均是权力较为集中的威权体制,而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又纷纷从“威权体制”转向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多元体制”。尽管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政治转型在动因、条件、推动力量以及衡量指标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正是这些相似性,为我们探寻亚洲政治转型的规律打开了一扇窗口。
本文认为,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其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会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阶级和利益集团会产生新的政治参与诉求,并带来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的相应变化。而纵观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转型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发生政治转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转向多元政治体制后往往仍能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与多元体制的稳定运作;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的国家,在建立多元体制后均出现经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迟缓的现象。从以上经验可以得出一条规律:以城市化率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政治转型能否成功的核心指标。
一、政治转型的动因和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特别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建立了一种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实行“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可以称之为亚洲的威权体制。[1]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威权体制”,包括日本的“55年体制”、 新加坡的“59年体制”、 韩国60年代初建立的“军政体制”、印度尼西亚1965年以后形成的苏哈托体制、伊朗战后恢复的君主制等。无论是建立的时间(1960年左右)、实行的时间(约30年),还是权力主体及其采取的基本社会政策、发展策略等,都是基本一致的。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纷纷进入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阶段。认识这一转型的动因、确认这一转型的条件,是研究亚洲政治发展最为重要、最具价值的问题。
(一)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的相应变化。[2]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台湾地区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原有的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我国台湾地区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阶层、集团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强,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多种社会矛盾逐渐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与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会发生分化。这种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并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最终导致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外部压力以及国内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典型的例子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的最终下台。
(二)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条件
从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看,在诸多实现了所谓“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有的国家比较顺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普选型的多元体制;有的国家则在转型后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国家长期动荡,影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政治转型的不同结果?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思考“政治转型”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尽管各国政治转型的道路不同,但多元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影响。从亚洲各个国家政治转型的普遍情况看,经济发展最终会对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我们分析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和依据。本文认为,只有在当工业化、現代化初步完成的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并且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新社会结构的形成、新精英阶层的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社会保守意识的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3]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在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后,新的利益关系逐步稳定、固化,就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因此,只有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后,开放政治权力并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才不会扰乱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这是权力开放与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稳定和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不同精英集团之间整合与协调关系的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于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并且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为体制转型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比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左翼思潮逐渐衰落,而198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教的温和化。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轉型的关联。
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步完成,新型社会结构稳定形成、新精英阶层整合和新保守意识形成三项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新型多元体制才最终较为稳定地建立起来,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型”也才会开启。
二、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兴社会集团
亚洲诸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是现代社会政治转型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4]它们争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各国政治体系的变化。
(一)新兴社会集团推动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机制
亚洲各国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改变与国家政权的更迭,从根本上讲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结果,而利益结构变化中新出现的社会集团是推动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其推动政治转型的内在逻辑如下:
第一,工业化导致新兴社会集团出现。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流动、身份改变、财富增加和社会集团关系变化,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出现,即社会学所说“巨型社会聚集体” 的出现,我们称之为 “新兴社会集团”。
第二,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引发政治体系权力结构变动。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体系的“陌生人”、“后来者”,不具备一些特定的法律地位,缺乏政治权力,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因此,新兴社会集团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
第三,政治体系中的政体结构与权力结构在吸纳政治参与上存在相悖作用。一般而言,政体结构具有开放性,而政治权力结构具有封闭性,政体结构一般在法律意义上平等对待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平等竞争来分配利益和权力;而政治权力结构则被既定精英集团掌握,具有排斥权力分享的倾向,这导致了新兴社会集团强烈的进入既有政治权力结构的动力。[5]而它们参与的障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正是导致工业化阶段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第四,新兴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进入政治权力结构,进而改变权力结构和政体结构,导致政治体系变化。政治体系变化同时也取决于既定权力精英集团的适应性,既定权力精英集团自身的调整能力及其对于新兴集团的制约与整合能力,决定着政治权力结构及政体结构变动的方式和程度。
概括地说,政治转型的动因是工业化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其内在机制是新兴集团和既定权力精英围绕政治权力的博弈。新兴集团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既定权力精英的制约和整合能力这两方面因素,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最终进程。
(二)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三种能力
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行动能力取决于三种能力:思想能力、组织能力和经济能力。思想能力即新兴社会集团的自我意识水平,表现为反映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韩国民主化运动中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我国台湾地区政党轮替中的民进党的“台独”论述、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现代伊斯兰思想的复兴等。组织能力反映了新兴社会集团内部的联系和组织程度,表现为新兴政治团体、政党的出现和活动水平。经济能力是所有集体行动的基础,它提供了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发动和维持所必须的奖惩机制。
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转型的进程,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主要取决于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不同的新兴社会集团在三种能力上有所差别,同一个新兴社会集团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上,能力表现也有所差异。一般说来,只有同时具备三种能力的新兴社会集团才具有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改变政治进程的能力。
(三)新兴社会集团推动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两种类型
在亚洲国家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大致属于同一类型,基本上属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社会集团改变了原有政治制度,即改变了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政体结构。而日本、新加坡似乎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们在开放、多元的宪政体制下,长期保持了政治权力结构不变,由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精英集团掌握政权。
韩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三大新兴社会集团——新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财阀集团,而韩国的政治权力为军政集团所掌握。在工业化初期,韩国新工人阶级(也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和工厂的工人群体和部分知识分子)反抗军政集团的统治,要求变革;城市中产阶级基本上保持中立,置身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之外;财阀集团则站在军政集团一边。这一阶段,原来的军政集团主导的威权体制是稳固的。但随着新工人阶级反对的加剧,城市中产阶级转向了同情甚至支持工人运动;更重要的是,财阀集团与军政集团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部分财阀转向中立,甚至以追求民主的名义向军政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分享权力。这时,在国际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的由军政集团掌控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动摇和分裂,并最终走向政体的瓦解和转型。
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以本土族群为主体、依靠外向型经济获取资源和经济地位、以中小企业为骨干的“本土-草根”集团。与之相对的是以国民党为核心,以“军、工、教”集团为主体,“国营”、党营企事业为经济基础的上层集团。随着台湾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新兴“本土-草根”集团不断成长壮大,而国民党上层集团则不断分化,加之台湾外部形势的变化,以民进党为首的“本土—草根”集团最终实现了台湾的政党轮替,达成了政治权力结构和宪政体制的转型。
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战后日本、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出现了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等新兴社会集团。但是,经过一系列博弈和调整,日本的政、官、财“铁三角”,即职业政客、专业官僚和财团形成的权力精英集团广泛吸纳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同时实施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和管控,将绝大多数的新兴社会集团纳入到既定的制度体制之中,同时制约了颠覆性的政治参与。这些措施成功地维系了原有的一党政权,垄断了政治权力,维持了既定的权力结构。新加坡也经历了相似的进程,具有相似的体制机制。
三、政治转型的核心指标:城市化率
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说明,城市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关键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多元体制政治转型之后,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在1990年前后的政治剧变中转型为西方式的多元体制,即所谓“转型国家”。从下图可见,这些国家发生政治转型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城市化率也各不相同。 [6]
下文将以时间先后为序,呈現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中各国发生政治转型的相关过程:
1973年,泰国发生“争取宪政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猛烈冲击了他侬军政权,导致次年他侬政权垮台,泰国历史上第二次威权政体瓦解。1975年,泰国新宪法实施,并举行历史上第一次竞争性普选。此时泰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7%。由于社会结构基础的缺失,泰国的政党政治实验并不顺利。短短三年后,“民主实验”失败,泰国逐步转入所谓“国王领导下民主”的第三次威权政体。
1977年,时任印度总理英·甘地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实行大选。结果出乎当时执政的印度国大党的意料,由各反对党联合起来的人民党赢得了大选胜利。印度也由此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时代。这一时期印度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尚处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城市化率仅有23%左右。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的多党制转型导致了激烈的政党争斗与宗教冲突,使得印度政局长期动荡不宁,英·甘地、拉·甘地母子两代总理先后遇刺身亡,印度的经济也经历了20多年的停滞不前。
1986年,菲律宾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统治菲律宾长达27年的马科斯总统,结束了所谓的“宪政威权体制”,并开始实行自由竞争的多党制。菲律宾在二战结束后获得独立,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经济在亚洲居于前列,人均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1986年时,菲律宾的城市化率达到43%,在当时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多元体制并没有给菲律宾带来稳定和繁荣,反而使其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每况愈下。政治上动荡不宁,争端不断,腐败盛行,成为世界上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社会分歧严重,地方势力、宗教分裂困扰着国家。经济上则从亚洲名列前茅的位置一路后退,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垫底的国家。
1987年,也就是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运动”的次年,同样地处东亚的韩国延续多年的社会民主运动达到了高潮。1987年的“六月抗争”结束了韩国持续近30年的军政体制,实行自由选举。然而,民主派的胜利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在韩国被称为“文民体制”的民主政体的建立,而是由脱下军装的军人赢得了第一次大选。直到1992年韩国的民主体制“文民体制”才最终得以建立。这时的韩国经过30余年威权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步入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行列。1992年时韩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73.8%。这样的社会基础使韩国在实行民主后,虽然也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但政局总体稳定,经济继续增长,社会福利大幅增加,被西方舆论认为是成功实现“政治转型”的典范国家。
1992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经历了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强盛一时的苏联轰然崩塌,给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带来持续十余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与社会混乱。苏联时期,俄罗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1992年时俄罗斯的城市化率达到73.4%。这样的社会基础使得俄罗斯虽然也经历了痛苦的动荡和转型,但在十多年的混乱和衰退后,最后还是逐步稳定下来,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逐步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我国台湾地区于1987年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状态,开放“党禁”、“报禁”,逐步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多党制、普选制过渡。1996年台湾地区实行首次“总统直选”,正式开启了台湾地区的“多元体制”时代。2000年,在野的民进党赢得选举,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台湾实现“多元体制”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韩国类似,也是亚洲“四小龙”成员,经济步入了中等发达行列,城市化率1996年已高达78.7%。建立“多元体制”后,台湾虽然党争不断,岛内纷争迭起,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动摇和反复,也被西方舆论认为实现了成功的政治转型。
1998年,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局变动,实行专制独裁的苏哈托总统在金融危机和国内民主浪潮的双重打击下黯然辞职,结束了他长达33年的威权体制统治。1999年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自由选举,开始了印尼“多元体制”的新历史。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化总体处于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在东南亚居于中游,城市化率42%,与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运动”时相当。印度尼西亚实现多元体制后,总体情况好于菲律宾,但依然不容乐观。政党纷争和频繁的选举给印度尼西亚带来沉重负担的同时,还导致了政治腐败,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深受拖累。直至今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仍不及苏哈托时期。
从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情况看,在实行以普选制为标志的“多元体制”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除俄罗斯情况比较特殊,韩国和台湾地区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平稳发展与多元体制的稳定运作,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而发生“政治转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甚至更低的国家,在建立“多元体制”后,均出现经济社会秩序混乱、发展迟缓、政局不稳的现象,个别国家甚至出现政体反复。从这些 “政治转型”的经验可以看出,以城市化率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转型”是否成功和稳定的核心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高水平的城市化率(如达到70%以上)是亚洲国家实现比较顺利和稳定的“政治转型”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必要条件,是通往稳定的“多元体制”的一道门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注 释:
[1]房宁等:《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6~350页。
[2] [3]房宁等:《自由· 威权· 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3页。
[4]房宁:《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67~69页。
[5]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93页。
[6]房宁:《民主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