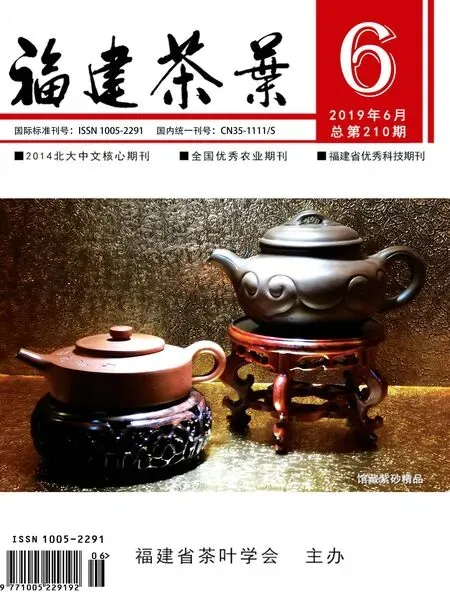行走于现实与虚幻中的真实
——比较纳撒内尔·霍桑与弗·奥康纳小说中之“神秘性”
贾 婷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在美国小说家中,纳撒内尔·霍桑与弗·奥康纳堪称文坛中的“近亲”。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代,素未谋面,但在各自小说的创作手法、主题思想方面却具有一定“亲缘性”,两人都受基督教信仰的浸润,作品均展示出对人性以及人的处境等诸多主题的宗教探索。同时,两位作家也都饱受学界争议,小说惊悚、怪异的情节与人物、各种神秘的元素,亦真亦幻,虚实难辨。学者们也尝试从多重视角进行解读:哥特式艺术手法、原型分析、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叙事技巧、宗教与历史批评等等,可谓是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然而,对于两位作家作品中存在类似的“神秘性”,却鲜有学者进行深入分析。细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不难看出,他们的作品与一般的现实主义题材很不同,小说人物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游走,充满魔幻与幻想,文学表征符号也模糊了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界限,造成文本阐释的含混多义。本文试图结合作家的创作观,宗教观,比较各自作品中表现的“神秘性”因素,并阐释其作品呈现的神秘性的本质。
1 超越性的现实:“人类心灵的真实”与“奥秘现实”
纳撒内尔·霍桑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霍桑曾在《七角楼》的序言中表示自己作品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而是“罗曼司”(传奇)。[1](p1)美国著名批评家奇斯在1957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中,界定了传奇和小说:小说和传奇的区别在于它们看待现实的不同方法。小说以详尽的细节忠实地反映现实。事件通常看起来是真实可信的,人物角色比行动和情节重要,而传奇是以更少量的细节和更自由的方式反映现实。人物角色大多都是平面两维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时有发生,它们通常产生的不是现实的意义,而是象征的或思想意识上的意义。”[2](p12-13)。霍桑采用罗曼司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是基于他的小说并非反映外在客观现实,而是要探索人物主体心理深层中的“人类心灵的真实”。[3](p253)出生清教徒世家的霍桑,深受加尔文主义原罪意识的影响,可以说,“原罪”意识简直就是他生活的思想基础和创作基础,使得他的小说无不充满宗教的神秘色彩。[4](p108)对于霍桑而言,真实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或者是外部世界当中,因为人的感官体验会被迷惑,而是存在于“心灵的直觉”。他曾不无感叹道:“人心啊,人心,这个小巧玲珑却无边无涯的渊薮,外界的罪行和痛苦不过为个中原罪的种种表现而已。”ibid(130)这也决定了霍桑在创作实践中,偏向描写内心隐秘的罪,无所不在的“恶”。罗曼司体裁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以便能够探索超越现实、历史与传统,在现实和虚幻想象中寻找一块模糊的“中间地带”,现实与想象交融而且相互渗透着,人物主体在经历某种虚幻和现实交织的体验后,促成主体对人性隐秘之罪的认知。
弗兰纳里·奥康纳,作为20世纪著名的美国南方小说家,她的作品始终围绕着对人类生存意义的不懈拷问。出于一个天主教作家的良心,她并没有将笔触深入到20世纪美国南方的现实社会深处,在她眼中,种族问题、女性问题等社会矛盾只是人与上帝关系疏离所带来的矛盾表象,而真正的“现实问题”在于人与上帝垂直关系的断裂。在奥康纳看来,现实应该包括可见的经验现实和不可见的奥秘现实。而作家则应该关注“更深层的现实主义”,因为“它涉及神圣的存在和我们在其中的参与。”[5](p72-73)深谙圣经传统的奥康纳知道,圣经是以故事、象征性的隐喻揭示神秘的宗教奥秘,因此奥康纳的小说尝试以她所生活的美国南方的风俗人情来讲述人与上帝恩典的神秘相遇以及救赎的可能性。“用故事来创造故事。它需要一个神秘维度的故事,——一个在其中任何人都能辨认出上帝之手的故事,并能想象它降临在自己身上。”[6](p55)
在创作手法上,奥康纳曾指出,她自己是霍桑的一个继承者。显然,奥康纳追随霍桑,把传奇文学看成现实与超验神秘之间的交界领域,一块充溢真理和神秘的地域。浪漫传奇给与了奥康纳扭曲现实的自由,在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方面进行处理,更突现“最本质的真理”[7](p167)显而易见,霍桑与奥康纳出于共同的创作目的,使他们在创作中都试图通过浪漫传奇体裁,借用神秘、怪异的元素,旨在探索隐秘世界的现实。
2 “中间地带”叙事与暴力叙事
霍桑擅长在小说中创造一个虚实结合的“中间地带”,把故事中的人物主体和背景刻画成似幻似真的特殊混合体。他或是使用梦境、幻想将现实环境虚化,营造出梦与现实交汇的点,从意识领域走向潜意识领域深层,探索涌动的思想暗流。在《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霍桑以梦的形式,把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真实世界与鬼神魔幻世界交织杂糅,巧妙运用了火光与暗夜的相互作用,产生明暗对照,同时他又运用了听觉技巧,使得古德曼还未见到参加森林集会中的人,却听闻他们的谈话,判断出他们各自的身份。幽林中的各种隐秘私语与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身份之间的巨大反差,让古德曼产生了瞬间的幻觉,也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模糊难辨的“中间地带”,令人难辨究竟布朗是在梦境中经历一切,亦或是他真实的遭遇。在霍桑笔下,这片森林既可以被解读为远离当时清教道德与规约体系的原始陌生领域,也影射出人类心灵中阴暗的潜意识领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刚刚皈依清教的布朗踏上了探索人类“原罪”的旅途,也是他重新审视人性复杂性的过程。另外,在“中间地带”创作中,霍桑常常凭借“大气媒介”(无论是阳光,月光或者火光)来产生光线,并且使这一“媒介”沐浴在平常的事物上。光与影的对照不仅改变了环境的氛围,反映了主体的内在心灵投射,同时物质被那不同寻常的光芒赋予灵性的异彩,失去了物质的实体,产生了某种奇异而遥远的品性。在小说《红字》中,多次提到绞刑架,分别出现在日光与夜色中。明暗交织下的对比,绞架成为一个“中间地带”,实体与虚幻相遇,并且相互浸润,寓含了真实与罪恶的双重意义:白日的光明揭露了罪恶与审判,而黑暗则代表隐匿罪恶与懦弱。
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奥康纳认同霍桑的基督教“原罪观”,基督宗教的信仰引导她透过繁华的表象洞察人性之恶和社会的症结。她看到生活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宗教意识渐渐退去,生命的奥秘被人类消减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中,缺乏了上帝统摄,社会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中。上帝的恩典被误解为仅仅是“温暖的和有约束力的,——而不是用基督的剑来收获”。[6](p59)对于具有天主教宗教背景的作家而言,死亡与暴力并非是罪恶的化身,反而具有肯定的意义,预备人“经历必要的与旧有的自我解体。以便神圣之火降临到人的身上”。[8](p135)在一个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奥康纳正是凭借死亡与暴力叙事的惊骇效果扩张人的世俗视野,打破宗教盲者的固步自封,从而引导人进入上帝的神秘视野中。在奥康纳小说中,暴力与死亡常常突然闯入,刺激读者在情感上去认同,预备进入上帝启示的恩典时刻。对奥康纳而言,“(人与神相遇的)神秘包含在属于人性的且往往是堕落的事物之中。”[6](p59)可以说,扭曲、惊骇的死亡和暴力图景是奥康纳增加作品超越于现实主义的神秘维度,把人的眼光从经验世界投射到不可见的超验世界之上。在《背井离乡的人》中,死亡突然降临在外表敬虔却以自我为中心的农场帮工肖特利太太身上,奥康纳对死亡来临的描述并非着力渲染死亡带来的恐惧和惊悚,而是突显死亡带给罪人超越自然的、超越人类理性认识能力之外的顿悟和神秘启示:
她脸上凶恶的表情渐渐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讶异,握紧的手也松开了。她的一只眼睛移向另一只,好像悄无声息地坍塌了,跟着她也不动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已经有了一次重大的经历,甚至可说在这个世界上脱离了曾拥有的一切……她们的母亲庞大的身体静静地仰靠在座位上,眼睛就像漆成蓝色的玻璃珠一样,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思量着她真正国度的广阔边界。[9](p224)
同样,《好人难寻》中的那位虚荣矫情的老祖母在一家人外出旅行时,遇到逃犯“不合时宜者”。暴力与死亡的突然闯入,也是上帝恩典降临到祖母灵魂的另一种方式。老祖母突破性地重新审视生命,用信仰的眼睛感悟到她和“不合时宜者“的精神连接,称他为自己的孩子。老祖母最后的死亡显出她与神秘接壤,灵魂重归孩童般的纯真与明澈。
显然,两位作家都避免宗教生硬的说教,而是巧妙运用艺术手法,将外在现实进行必要的扭曲和变形,以便与内部(终极)现实微妙调节,在历史的真实(南方的风俗)与罗曼司的想象(宗教奥秘)中赋予作品宗教的预言性与警示性。
3 象征手法与化身艺术
象征是作家广为使用的一种文学表现手法。象征往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通过隐喻、寓言、拟人化、符号、写意、对比等形式进行思考和表意,具有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混合的倾向。[10](p28)霍桑在小说中借用象征手法,将其作为一种表征模式,再现了主体的深层心理现实。象征的手法能更好地将诸如无意识、梦幻、欲望等复杂的非现实图景展示出来,增加了作品的想象的向度和诗意的神秘朦脓。霍桑小说借助各种意象挖掘和揭示笔下人物丰富、复杂和难以名状的内宇宙,呈现出比外在的物质世界更为切实可感的内在心灵世界。他的短篇小说《牧者的黑面纱》是其象征主义艺术特色的卓越体现,小说中,牧师胡珀脸上的黑面纱是故事里的核心象征,从一个安息日的早上直到他离世都不曾摘下,成为他与他的教民隔绝的标志。作家围绕黑面纱搭建了一个神秘的“多种可能性的王国”[11](p183),寓意神秘而深刻。黑面纱可以被视为某种隐秘的罪恶象征,文本中各种闪烁其词的线索隐约暗示了这一理解。牧师不肯摘下面纱,象征着和他过往所犯下的具体罪恶和悔改的行为有关。然而,面纱的寓意不仅拘泥于具体的罪恶,还指向更为广阔的人类心灵经验。胡珀在临终时,道出了他不愿揭下面纱的深意:
“当朋友、爱人间坦诚相见、推心置腹时,当人们不再徒劳地避开造物主的目光,处心积虑地隐藏自己秘密的罪孽时;到那时还把我当成怪物吗!因为生前死后都戴的那个标志!我环顾四周,啊!每张脸上都有一张黑面纱。”ibid(p219)
显然,牧师对于罪恶以及罪恶代表的黑暗力量有深刻认识:人人都有着或隐或现的罪恶。他选择戴上黑面纱的行为本身,昭示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布道的形式。这个象征性的记号无疑让教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人身份,让人恐怖不已,对牧师避而远之。但另一方面,牧师本人也对黑面纱恐惧不已,“从不愿从镜子前走过,也不愿俯身去饮静静地劝人,免得在它宁静的胸襟里,他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到”ibid(p214)。牧师虽然对罪恶有清醒的认识,偏执地用戴上黑面纱的举动希望使自己和教民的心灵得到净化,但是却终年将自己包裹在黑面纱的遮盖下,忍受着长久的阴郁与孤寂。从这个角度来看,黑面纱象征着牧师陷入到宗教偏执的泥潭中,割裂了人类友爱的链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黑面纱暗示了作家对清教主义的极端化持批评的态度。在霍桑的每部作品中,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意象,场景意象或是圣经原型意象比比皆是:《七角楼》中象征品钦家族罪恶与贪婪的房屋、《红字》中盛放的野蔷薇象征着在清教社会压制中苦苦挣扎的海斯,《胎记》中象征罪恶记号的胎记,均成为特定的思想荷载物,传达了作家丰富、复杂、矛盾的宗教伦理和心灵世界。
和霍桑一样,弗兰纳里·奥康纳认为,“小说家的特征不在于他的职责,而在于他的幻想。”[6](p19)作为一个具有天主教宗教视野的小说家,她认为“小说家关注的是包含在具体感官世界中的终极奥秘。”ibid神秘的超验现实包裹在可见的自然世界中,物质世界中蕴含着基督神性的力量。如何揭示和凸显“宗教”的奥秘,在于作者以“可见、可听、可感”的具体细节去勾勒具体的世界。奥康纳将这样的小说叙事技巧称为“化身”艺术。她的小说虽然立足于美国南方的泥土中,呈现出美国南方生活的现实社会图景,但是,读者总能在她的小说中寻找到某个意象,某个情景,同时连接和包容了可见的现实与超验现实,传递出具有宗教启示意味的神秘性。
为了达到这一叙事效果,奥康纳的许多作品中能看到频繁出现的自然景观,包含着上帝神秘启示的信息,冲破了读者的理性视野,有力地将神圣的精神注入读者理性认识领域。在《林中风景》中,奥康纳专门描述了冷酷的福钦先生看到太阳升空时的神秘景象:
将近六点钟了,枯败的树干似乎被抬高,进入一圈红光里,这是落到树林背后看不到的太阳迸发的光。老人盯着看了一会儿——好像被一种不舒服的神秘攫取住似的,这种感觉他先前并不真正理解。在幻觉中,他看到沐浴在血中的树林,仿佛树林背后有人受伤[9](p348)。
显然,这里关于树林的描写不是单纯渲染自然美景,而是充满宗教的神秘启示。树林中闪现的太阳的“血色”被视为耶稣的化身,让读者联想到耶稣基督受难时满身鲜血,忍受创伤的场景,展示出基督牺牲之爱。难怪,这样的景象让利益为上的福钦先生也无法无动于衷。除此之外,奥康纳也常常将太阳、天空、火等自然图景化身神意的存在,充满灵性,体现出上帝隐秘性的存在,总在小说人物顿悟时刻扮演重要角色。《人工黑人》中的海德先生在黑人雕像中领悟到黑人与白人灵魂上的平等,回家路上,一段关于“天空”的描写回应了海德先生行为的转变,暗示上帝对人类的普遍恩典和审视:月亮从云层后露出脸来,恢复了充盈的光辉洒在了空地上……。而在《格林利夫》中,面对试图掌控一切,顽固不化的梅太太,太阳化身为上帝审判的形象,闯入梅太太的精神和生活领域,预示着上帝对她生命现状的震荡和改变:
她刚停下来的时候,太阳是个肿大的红球,她站住观望时,它慢慢变得细长,颜色也开始变白,看上去竟像一颗子弹。突然,它冲破那排树障,滚下山坡朝她冲来。”[9](p329)
除了描写神性临在的自然图景,和霍桑一样,奥康纳也擅长象征手法,借助南方生活中的风俗来阐释宗教的奥秘,在奥康纳小说中,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城市和商业街道,虽然表明光鲜美丽,但是在浮华的背后,充斥各种欲望和无序感,暗示了现代社会人类信仰的荒芜和丧失。代表工业文明的汽车、火车在作家笔下,竟然恰似棺材,承载着故事中的人物走向死亡结局,日常生活中的报纸、帽子也超出了其所指功能,预指现代社会中,人类彼此冷漠和疏离的现实。奥康纳笔下的南方社会俨然是一个宗教隐喻的符号,浸印着宗教罪尤和救赎的神秘色彩。
4 小说神秘性的本质
小说家麦尔维尔在评论霍桑的作品中时曾指出:“霍桑描写黑暗的巨大力量是由于受到加尔文教派教义关于与生俱来的堕落与原罪思想的影响”转引自[4](p130)出生清教徒世家的霍桑对于人类内在黑暗力量有着深刻认识,这也让他的每部作品始终浸润在黑暗、阴郁的宗教内省式的拷问中。霍桑深受祖先在历史上参与审判1692年萨勒姆行巫案的影响,一生笼罩在祖父所犯之罪的诅咒中,因此他虽然笃信清教思想中的人性观,但是却对清教徒偏执、缺乏对个体的宽容、以及排他性产生质疑,霍桑将他这种矛盾的清教主义观念模糊隐晦地表达出来,这也让他的作品更像意蕴深远的寓言,没有给出一个确定性的意义阐释,反而以罗曼司体裁消解了虚构性和历史真实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让读者的想象发挥作用,各自展开探索人类内心真相的历程。因为读者的想象空间、梦境与神秘比历史的真实更接近真理本身。可以说,霍桑小说中的神秘性决定了他的小说,旨在传递出更为复杂、非单一性的人性心理真相。
作为弗兰纳里·奥康纳而言,她接受宗教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因为基督就是人性与神性的合一,完成救赎之工,好让人类与上帝调谐。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将基于经验和科学理性作为基本依据,形成基本的精神价值标准,排斥宗教中的神秘体验,不接受超自然的启示。奥康纳明确反对基督信仰中这种“祛魅化”倾向。她认为与基督宗教的神秘性密切相关的是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差异,人的有限理性视野无法进入到上帝无限的神圣视野当中。如果去除宗教的神秘性,实则是把上帝降格,最终形成人本主义的宗教观,带来现代人宗教观的丧失。在奥康纳在《新教南方的天主教作家》一文中说道:“能够加深我们对信仰感觉的不是抽象,而更多的是与神秘的一种遭遇。”[6](p58-59)这种遭遇,对基督教作家来看,是一种体认,是个体经历上帝神圣精神的体验。都具有终极的意义。
结语
霍桑与奥康纳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是他们都敏感于各自时代的社会沉疴,探索医治的途径。他们认为时代的疾病不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良,而在于探究更为隐蔽的内心黑暗的力量以及如何与上帝的恩典连接。因此,两位作家都在创作中,用宗教寓言式的写作,引导读者看到不可见的真实:隐秘的内心之恶与隐藏的神性奥秘。为了达到这样的寓言式效果,他们往往刻画惊悚、恐惧、死亡和超自然现象,将魔幻、现实、神秘彼此融合,消解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作品中的神秘维度是扩张读者的感知局限和神性视野的艺术手法,留给读者更多想象和阐释的空间,警醒和预示人们看到比外部现实更真实的真理。正如奥康纳所说:在“幻想的最深处,隐含着道德判断”[6](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