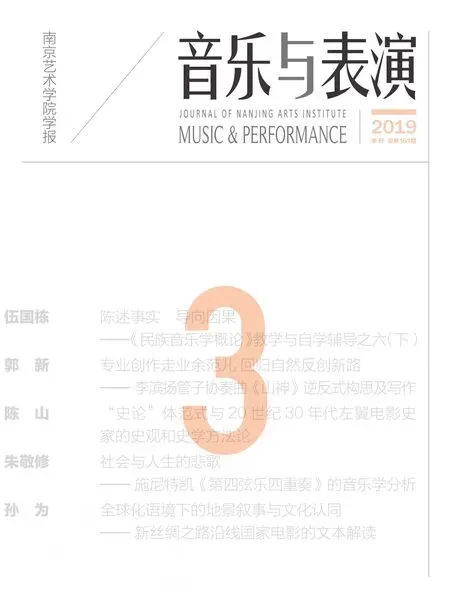师者有恒 习者无涯
—— 读茅原先生的系列戏曲美学文章
单 林(上海大学 音乐学院,上海 200444)
引 言
1958年11月至12月间,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国音协为推动戏曲音乐创作与表演,召集全国多个地区的音乐工作者,开设“戏曲音乐研究班”。该研究班白天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学习、讨论,晚上则是观摩多个剧种表演(研究班地点流动于南京、无锡和杭州等城市)。茅原先生代表南京艺术专科学校(1959年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参加了该研究班。此时的茅原先生既有作曲理论毕业生的基础,又有1954年在安徽民间音乐采风8个月的经历,更积累了1957年去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西方音乐多门课程学习的成果。这些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在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年轻人身上,很快便显现出巨大的爆发力。在研究班学习期间,作为学习成果的结业汇报,茅原与郑桦、武俊达三人讨论,并由茅原执笔完成了《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音乐美学问题》[1]。随着该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便有了相应的探讨文章出现,如《也谈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的问题》[2]等。为此茅原先生又执笔发表了三人的讨论稿《再谈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美学问题》[3]。此文的发表继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参与相关讨论的文章有《关于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问题的意见》[4]《论戏曲音乐形象等问题》[5]《论戏曲音乐的基本美学问题》[6]等。由于当时就有“左倾”政治的影响,来自官方的压力,使得这一原本属于学术性争鸣的广泛深入讨论未能继续。茅原先生曾经收到过一封某好心人用《人民音乐》编辑部的信笺书写的匿名信,信中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你怎么还不识时务,不要再争了。但茅原先生并未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等到环境相对稳定时,他又于1963年在《音乐论丛》上独立署名发表了《音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7]一文。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围绕音乐表现意义及其特征的美学范畴的探讨。这样的讨论是围绕中国最具民族特征的戏曲音乐的表现而展开,并同时获得实质性结论,显示出音乐美学、戏曲音乐创作、音乐史等多方面的成就与意义。
一
《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一文围绕戏曲音乐的具体的形态表现特征提出了其刻画形象的相关原则:具体性和概括性的音乐思维的统一,音乐形象的完整性和不完整性的统一,音乐形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的统一。该统一三原则的提出是对戏曲音乐形象表现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戏曲作品中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剧本的刻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具体的音乐形态结合剧情和唱词的表达,共同完成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该文通过大量的曲谱分析,强调音乐在其中的表现力,并且这些音乐的表现既在实现统一三原则,同时又在统一三原则下发挥作用。
茅原先生在这些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是围绕音乐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关系而展开。音乐的确定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学者讨论的焦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及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的思想根源均涉及音乐的确定性与否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式的话题。确定性与否在体现于戏曲音乐的陈述过程中的同时,也存在于更广泛的古今中外各种音乐类型中。音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实质应该是不确定性。因此《音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文在肯定音乐确定性的同时,分别从五个方面陈述揭示了音乐的不确定性存在的缘由。但同时指出,这样的不确定性是相对的,“而在本质上,相对不等于绝对,我们只承认在确定性制约之下的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性,而否认无限的不确定性。”[8]这样的观点在之前的文章中已有涉及:“也正因为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是有其一定范围的,它的不确定性才不会是无限的,它刻画形象的可容性又是具有其局限性的,不可以拿任何一个曲调当成万应灵药任意使用”。[1]“一曲多用”虽然具有不确定性的形象表现,但其又有着一定的空间范畴,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在这样一种生动灵活的关系中间,实现着形象的刻画和塑造。
茅原先生不仅从小耳濡目染多种民间音乐,并且很早就关注音乐的形态和表现。在讲授《声无哀乐论》时,先生说他少年时曾经在乡村的红白仪式中听到同一首曲子,并且确实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情绪感受;当然,他并非以此来评价《声无哀乐论》的观念(这方面他有专文论述),而是强调民间确实有着许多特殊形式的音乐。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对音乐思考的切入点。这也使得他在面对“戏曲音乐研究班”中的戏曲音乐时,就能思考相关美学问题。
中国音乐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形式及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自身的内容表现和形式选择。体现在具体的音乐陈述和结构形式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曲牌,包括文人音乐中的词牌和民间音乐中的曲牌。曲牌是中国音乐的极为独特的一种存在形式,特别是随着宋代说唱音乐和戏曲产生以后,更是迅速发展,包括联套曲牌,南北曲牌的合套等。即使板腔体的出现也未改变曲牌体的地位,甚至板腔体本身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曲牌体的陈述原则。在民间音乐史上,这些曲牌及其变体形式大多以一种变与不变的形式传承和发展。
在民间音乐系统中,曲牌的陈述方式均贯穿于民间歌曲、说唱、戏曲以及器乐曲中,它们包括了中国音乐的大多数形式,它们是结构,也是陈述方式,这样的陈述方式同时决定了音乐表现的美学原则。茅原先生只是从戏曲音乐的曲牌入手,而文章中所涉及的三个原则也同样可以运用于其他体裁中,如说唱、器乐曲、文人的词牌歌曲等。文章针对戏曲音乐中“一曲多用”的现象及其传统音乐陈述方式进行了具体事例的分析。他通过对大量音乐细节的挖掘和比对,深刻解读了“一曲多用”现象后面的美学原则,揭示了中国音乐最重要的陈述特征。戏曲作为中国民间音乐的最高形式,其中戏曲音乐刻画形象问题,以及“一曲多用”的现象,代表了中国音乐最为普遍的形式,并以此辐射其他种类。这是对中国音乐陈述手法及原则的本质性阐述和总结,其意义已远远超越音乐美学范畴。
二
中国民间音乐在过去历史发展中的传承发展多数是口传心授,虽然许多朝代都有乐学著作问世,但一方面这些著作多数停留于理论层面,并未为中国音乐的具体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另一方面民间音乐的生存空间在整个古代社会完全处于社会最下层,缺少理论的支持。古代乐调理论虽十分丰富,但实践性弱。1949年后,随着国家多个音乐机构的成立,音乐理论家们也开始具体的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方面理论的研究,如调式音阶理论、调式和声等。
中国古代戏曲自宋元兴起以后,始终以自身特殊的方式发展。它主要依靠艺人自身的创腔以及吸收其他音乐形式的材料来丰富补充,但缺少更多的陈述手法,而有关戏曲音乐理论的研究极为少见,包括戏曲音乐创作的特征、规律的总结也很少。因此,戏曲音乐发展缓慢,戏曲似乎更为重视剧本和表演。从民歌到曲牌,到联套曲牌,再到多种板式的运用等,这些要素构成戏曲音乐创作的主要脉络,并常常根据唱词内容与长短安排句式设计唱句的数量等。
茅原先生的系列文章虽然是以音乐美学立意,但其中涉及大量的戏曲创作原则和手法,这应该也是中国戏曲历史上最早利用专业作曲理论对戏曲创作的涉及,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戏曲音乐研究的作用。文章围绕“一曲多用”的现象进行深入陈述,对多种不同形式的用法进行比对分析,涉及调式、旋律、落音(终止)、节奏等多种形态,既有对这些形态的材料比对分析,也有内容表现的小结,实现了音乐分析中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和统一。事实上,“一曲多用”的本质是“一曲变用”。文章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深入剖析了这些“变”的手法和效果作用,特别是对于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作用。茅原先生并非戏曲音乐作曲家,但他对现有成果和材料的认识把握,对相关戏曲音乐创作有着生动鲜明的指导性。中国戏曲音乐在陈述及结构上以曲牌体为主,虽然有些剧种被认为是板腔体,但其实也只是多采用板式变化的曲牌体。因此,文中对大量曲牌表现手法的分析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曲牌体形式的陈述与展衍手法:如何融“变”于“不变”,“不变”中如何求“变”以及如何去“变”。
曲牌化的陈述以及“一曲多用”,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机械的创作方式。其主要原因是只看到概括性,忽视了具体性。当然,对于细节性变化的认识具有较大难度。“一曲多用”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有着复杂的背景,涉及民歌、歌谣、诗词、小曲、语言等诸多因素。其实,不仅是曲牌体是“一曲多用”,即使板腔体也有着极大程度的“一曲多用”,并且在板腔体音乐的具体陈述中,“一板多用”也是普遍的现象,它们同样也体现出概括性和具体性音乐思维的原则。人们多从音乐的结构原则上来看待曲牌体和板腔体间的不同,茅原先生则将它们理解为音乐陈述方式,一种作曲手法,即“用”的手段和空间,以致“一曲多用”。而“一曲多用”的背后是“一曲变用”,这是从概括性思维向具体性思维的转化和上升,是美学意义的质变。可以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戏曲音乐改革正是该美学思想和创作原则的生动而准确的实践。
三
茅原先生的系列文章的产生,凸显出鲜明的史学特征。这些音乐史特征涉及音乐美学、戏曲音乐、音乐分析等领域。中国戏曲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人最热爱的艺术体裁。1949年后,随着国家对民族艺术的重视,50年代又产生了大量地方剧种,如浙江地区就有姚剧、湖剧、甬剧等。其中,多数都是曲牌体形式,这些应该在“戏曲音乐学习班”中有所接触和了解,大量的戏曲观摩应该也是这系列文章产生的线索之一。在中国戏剧史上,对戏曲史研究多关注戏剧和文学部分,对于曲牌的介绍也多是从文学和词牌的角度,涉及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很少,而相关的音乐形态史则更为罕见。因为戏曲音乐的传承主要是口传心授,以谱面形式传承并不普及。刘天华给梅兰芳唱腔的记谱应该是很早的尝试。茅原先生的系列文章将戏曲音乐的相关现象和问题以谱面形式呈现,通过对具体戏曲音乐形态的梳理、比对、分析,在总结许多观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戏曲音乐形态的史学基石,且第一次以音乐形态形式对戏曲音乐的表现和特征进行概括性陈述和总结。这些文章一方面从美学的思路引出一条简约的戏曲音乐史的脉络,另一方面,文章本身也体现出鲜明的一般音乐史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批新剧种的涌现,戏曲创作及改革也如火如荼。由于题材的革命化、新时代化,创作手法在“一曲多用”的基础上,“一曲变用”现象也具有了更多、更大的突破。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戏”的出现,“一曲变用”也上升到最高峰,直至有主要唱段的“专曲专用”。但戏曲中的“专曲专用”并非是歌剧中的“专曲专用”,它是“一曲多用”及“一曲专用”的升华:其核心材料依然来自戏曲剧种,来自“一曲”。由此,戏曲艺术的发展也达到历史高峰。可以说,茅原先生的系列文章既是对传统戏曲音乐陈述方式的总结,更是对之后戏曲音乐创作的极大推动。这些文章对于戏曲音乐创作原则的揭示,以及技术手段的挖掘呈现,客观上影响着具体的戏曲音乐写作,为戏曲音乐的改革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当之无愧地成为戏曲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同样,这些系列文章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音乐美学研究的里程碑。纵观音乐美学史,古今中外探讨最多的就是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内容等范畴。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实质之一是通过音乐中哀与乐的有无,进而证明音乐的确定性与否;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中虽然始终纠缠于自律与他律的联系和冲突,但究其实质也是主要针对音乐形象和音乐内容的确定性与否。而茅原先生的系列文章则通过戏曲创作的具体现象将这样的确定性问题做了经典性的总结:“在戏曲创作中,一曲多用的创作方法常常是利用音乐形象的不确定性来达到音乐形象的确定性的。但除了在创作过程中不确定性起着作用之外,典型形象的构成总是依靠确定性来完成的。这种创作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音乐形象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互易主导地位的过程”[3]。他的结论不仅揭示出戏曲音乐表现中确定性与否的问题,同样也可以上升到戏曲音乐以外的其他音乐形式,事实上这也是对音乐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关系的极其深刻的总结和概括。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对音乐美学观点的一种进步与突破,也是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突破,是中国近代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起点。这样的美学研究完全建立在对具体的音乐形态的客观分析和结论之上,完成于严谨、科学、高度思辨性的阐述之中,即使在音乐美学研究蓬勃开展的今天,这样的一个起点还未被超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茅原先生还不是音乐作品分析专家,文章也未涉及完整的曲式结构分析,但其分析思维、分析视角、分析方法,对细节材料的关注、分析和判断,并以此上升到形象分析的诸多手法,已经预示他未来音乐作品分析的学术理念。即使在今天,无论是作曲课程,还是音乐作品分析课程,学生都很难见到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分析有如此细致入微的手术刀一般的解剖式分析。先生对于音乐作品的分析原则、分析理念和方法应该被后人继承,更应该有大的发展。
结 语
茅原先生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虽然他离开思考已近一年,但他的学术精神、学术智慧、学术成果将成为南艺永恒的坐标,指引着学术后辈。即使这样一系列以三十岁年龄写于60年前的文章,至今仍令学界振聋发聩,以致常常让作为后学的我手足无措、惴惴不安。这些系列文章以音乐美学切入,但涉及多方理论学科,特别是与戏曲音乐骨肉相连,值得探索的方面还有很多。在此用以上写下点滴学习心得,纪念他深邃的思维分析和精深的研究阐述。面对先生旗帜般的思考,我们的一切学习都是刚刚开始。
写于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