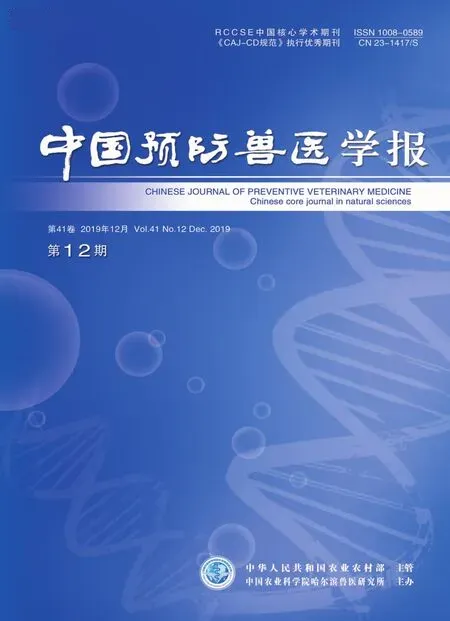STING的免疫调控作用研究进展
马瑞仙,李向茸,冯若飞*
(1.西北民族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工程与技术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730030;2.西北民族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干扰素刺激基因(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是在研究天然免疫信号通路过程中发现的新型接头蛋白,广泛参与宿主体内的多种信号传导过程。人源STING编码379个氨基酸,与鼠源STING基因同源性为81%,蛋白分子量约为42 ku,N端含4~5个跨膜结构域,C端含1个球状的C端结构域(C-terminal domain,CTD)[1]。细胞内的环状二核苷酸(Cyclic dinucleotide,CDN)可通过与两个STING单体形成的对称性二聚体凹槽相结合,进而激活天然免疫反应[2-3]。静息状态下,STING主要以无活性的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定位于内质网膜及线粒体内外膜中。当STING活化时,呈V型的CTD与cGAMP(cGAMP synthetase,cGAS)结合,使STING的空间构象发生改变,在内质网易位子系统的作用下向C端招募细胞质中的TANK结合激酶1(TANK-binding kinase I,TBK I),并将其转移至高尔基体或细胞核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和干扰素调节因子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等,磷酸化的IRF3形成二聚体转移至细胞核内与下游信号蛋白结合,诱导1型干扰素(Type I interferon,IFN-I)的产生,激活天然免疫反应[4-5]。
STING作为一种内质网驻留蛋白,在病毒、细菌及寄生虫感染触发的天然免疫反应、机体的肿瘤免疫过程以及细胞自噬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6]。STING可以通过自身的磷酸化、泛素化和二聚化修饰调节蛋白质合成和IFN表达,在机体的多个免疫环节中发挥关键作用。许多病毒可以通过与cGAS-STING通路上的信号蛋白相互作用,进而刺激机体产生与正常的免疫应答反应数量不等的IFN,引起病毒的增殖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细胞增殖能使抗原提呈细胞中的STING活化,从而激活T细胞介导的适应性免疫过程,发挥抗肿瘤作用[7-9]。分枝杆菌中泛素介导的自噬依赖于STING信号通路的激活[10],STING可与自噬相关蛋白相互作用,通过自身的降解以及对IFN信号通路的调节来影响肿瘤免疫过程。本文就STING在抗病毒感染免疫、肿瘤免疫和细胞自噬等免疫调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综述,以期为相关药物及疫苗的研发提供理论参考。
1 STING在抗病毒感染免疫中的作用
根据基因组的特点和复制方式的不同,病原体的遗传物质DNA或RNA被细胞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s)识别,并通过不同的途径激活cGAS,使其利用ATP、GTP合成2'3'cGAMP,2'3'cGAMP作用于STING,使其通过二聚化、磷酸化等方式发生构象改变,招募TBK1,进而从内质网转移至高尔基体,使IRF3磷酸化并向细胞核周围转移,促进IFN-α、IFN-β和IL-2、IL-12、IFN-γ等细胞因子的产生及T细胞和B细胞的增殖分化,进而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2,11]。最新研究显示,STING通过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或被病毒蛋白特异性切割等方式影响病毒的复制,参与宿主的抗感染免疫过程。
1.1 STING在抗DNA病毒感染免疫中的作用 DNA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被PRRs识别并与MDA5相互作用,随后通过线粒体抗病毒信号蛋白(Mitochondrial antiviral signaling protein,MAVS)激活下游的cGAS或IFN-γ诱导的蛋白16(IFN-γ-induced protein 16,IFI16)形成cGAMP,然后cGAMP与二聚化的STING结合,招募TBK I和IRF3,激活NF-κB信号通路,最终诱导IFN-I及下游基因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病毒作用[3,12-13]。最新研究显示,HSV-1的感染细胞蛋白27(Infected cellular protein 27,ICP27)可阻断STING二聚体与TBK1结合,从而影响TBK1介导的下游信号通路[14]。小鼠巨细胞病毒m152蛋白和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KSHV)通过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1(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1,IRF1)与STING结合,可抑制STING介导的IRF3信号通路,但对STING介导的NF-κB信号通路没有影响。KSHV的ORF52和人巨细胞病毒外膜蛋白pUL83通过抑制cGAS的酶活性来调节cGAS/STING介导的IFN-I信号传导途径[5]。
1.2 STING在抗RNA病毒感染免疫中的作用 与大多数DNA病毒不同,RNA病毒通过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被病毒蛋白特异性切割,两种方式作用于STING相关信号通路。登革热病毒(Dengue virus,DENV)非结构蛋白NS3及其辅助因子NS2B构成的蛋白酶复合物(NS2B/3)能特异性地切割STING蛋白,导致STING降解,从而使IFN-I减少[15-17]。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的血凝素融合肽(Hemagglutinin fusion peptide,HFP)通过抑制STING二聚化和TBK1磷酸化,阻断STING依赖性IFN的产生,从而促进IAV复制[18]。黄热病病毒(Yellow fever virus,YF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s C virus,HCV)感染过程中,其非结构蛋白NS4B可诱导细胞膜重排,主要通过阻断cGAMP下游信号通路中的重要接头蛋白的激活来抑制STING及IFN的产生[18]。SARS冠状病毒(SARS coronavirus,SARS-CoV)、人类冠状病毒NL63(Human coronavirus NL63,HCoV-NL63)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PEDV)的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PLP)可破坏STING的泛素化、磷酸化、二聚化及STING与MAVS、RIG-I、TBK1和IRF3的特异性识别,从而抑制IFN-β的产生[8,18]。
1.3 STING在抗逆转录病毒感染免疫中的作用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等逆转录病毒在感染细胞后产生的DNA-RNA杂交中间体(cDNA)和双链DNA,可激活cGAS/IFI16-STING通路。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IV)感染恒河猴细胞,使NLRX1的表达快速上调并与STING结合,破坏STING和TBK1的相互作用,抑制STING的磷酸化和下游信号传导[11]。在树突细胞(DC)、骨髓细胞等免疫细胞中,SAMHD1通过调节cGAS-STING信号通路,阻断HIV-1感染诱导IFN相关信号的传导,HIV-2病毒蛋白x(Viral protein x,Vpx)通过降解SAMHD1对上述过程起负调节作用[19-20]。在CD4+T细胞中,HIV的病毒蛋白r(Viral protein r,Vpr)诱导STING表达,启动STING介导的IFN信号通路[20],而HIV病毒蛋白u(Viral protein u,Vpu)则发挥相反作用,是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的原因之一[20]。
2 STING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
STING参与肿瘤免疫过程,并在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在结肠癌、黑素瘤和缺乏端粒酶等疾病中检测到cGAS-STING途径有效抑制了癌细胞的扩散。在STING缺陷型小鼠中,CD8+T细胞的活化和肿瘤排斥反应受到了抑制,这可能与DC中IFN-β的产生依赖于STING有关[21]。来源于肿瘤细胞的DNA、微核、细胞质染色质片段和游离端粒DNA,可激活cGASSTING途径并诱导细胞衰老、参与炎症反应和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18,22-23]。人乳头瘤病毒18(Human papillomavirus 18,HPV18)的癌蛋白E7和人腺病毒5(Human adenovirus 5,HAD 5)E1A通过抑制STING活性,进而促进肿瘤的发生[15]。在某些情况下,NK细胞依赖性肿瘤排斥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肿瘤细胞中STING的激活[23]。STING在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EBV)引起的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中,可以促进髓源性抑制性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的分化,抑制NK T细胞的功能,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导致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24]。研究表明,cGASSTING途径参与宿主细胞的肿瘤调节过程,但肿瘤细胞的DNA如何进入吞噬细胞而被传递给抗原提呈细胞,以及DNA如何从细胞核转移至细胞质中激活cGAS-STING通路的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25]。鉴于STING的激活与肿瘤免疫过程密切相关,了解cGAS-STING途径将为癌症相关治疗药物的设计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STING在细胞自噬过程中的作用
自噬作为细胞自我降解的一个过程,在激活和调节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最新研究发现,STING是一种潜在的自噬受体,与LC3直接相互作用,以非经典方式介导细胞的自噬[26]。有研究表明,STING在丝氨酸/苏氨酸UNC-51样激酶(ULK1/ATG1)的催化下促进第366位丝氨酸的磷酸化,引起STING降解并避免了超敏反应的发生[27]。STING能够诱导革兰氏阳性细菌发生内质网自噬[28]。此外,STING缺乏不能阻止饥饿引起的自噬,这表明STING对免疫原性刺激引起的细胞自噬过程同样发挥重要作用。cGAS与自噬调节因子Beclin-1相互结合,通过抑制cGAMP合成,阻断HSV-1感染引起的IFN-I信号通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自噬的发生。STING与ATG5、Beclin1、Atg9a、ULK1和p62等自噬调节因子存在共定位现象,DNA病毒通过激活cGASSTING-TBK1通路诱导p62磷酸化,并使其与泛素化的STING相互作用,促进STING向自噬体的转运及自身的降解,进而抑制IFN表达,导致病原菌扩散[29]。自噬可通过调节如NF-κB和STING等关键免疫调节因子,控制免疫过激引起的过度炎症反应的发生。研究表明,STING可通过抑制自噬,限制寨卡病毒(Zika virus,ZIKV)的复制及其在妊娠小鼠模型中的垂直传播,并且ZIKV复制与细胞自噬呈正相关[30]。
4 小结与展望
STING在细胞免疫调控过程中发挥双重功能,其表达量的多少对于各种病原微生物和机体内的细胞因子的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许多病毒均能通过cGAS和STING依赖性方式诱导IFN表达,主要通过病毒的不同蛋白与STING相互作用促进或抑制病毒的复制。其次,STING还能通过IFN非依赖性途径调节钙稳态,ER应激和T细胞存活,在一定条件下可通过未知机制引起肺部疾病和T细胞、血细胞的减少[31]。在细胞固有免疫的过程中,STING通过与自噬相关蛋白LC3、P62、Beclin-1等结合调节细胞内多种蛋白的降解,为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提供稳定的内环境。细胞内STING的表达量亦可对多种细胞的发育过程产生影响,进而调节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过程。此外,在疾病发生时STING的异常表达,激活下游细胞因子释放出大量白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造成局部组织的过度炎症、损伤并且降低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有研究显示,紫外线照射使角质层细胞损伤产生的DNA可以抑制ULK1对STING的磷酸化而引起持续的免疫反应。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中STING通过应激反应或摄入外源性的遗传物质活化STING导致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7]。虽然关于STING的研究很多,但其具体如何参与机体免疫调控过程的机制仍需进一步阐明。例如,RIG-I或MDA5如何在识别到病毒后将信号传递给STING?STING是如何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的?STING在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之间的转移是如何进行的?因此,对STING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天然免疫过程的理解,进而为新型疫苗和新药的研发等工作提供更好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