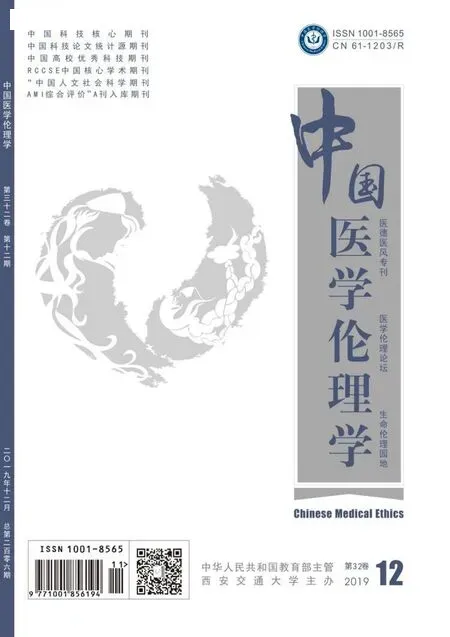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伦理学角度论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死观
——对《达洛维夫人》的伦理分析*
姚丹丹,刘丹翎
(1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外语系,陕西 西安 710018,yaodantina@126.com;2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1 研究背景
生死问题一直使人类感到困惑。无数的学者以及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生死问题进行过探索。从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伊壁鸠鲁的“死亡无关”论,到叔本华的人生悲剧论,他们都将死排除在生之外,认为生死对立,生是对死的否定。而在20世纪初,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却独辟蹊径,以死亡为切入点来诠释生存的方式和意义。与传统的生死观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当下的存在,死亡应被视为生命的构成部分和生命的最大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海德格尔以对死亡的探索为出发点,阐释生命的真谛,试图赋予人类存在更深层次的意义。基于这些思想,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借用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个短语,其思想对存在主义影响很大)。“向死而生”应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将死亡的可能性视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死亡是一种站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一种迫近的东西”;“死亡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伴随着死亡的确定性而来的是‘当下’的不确定性”[1]。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死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无法确定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学会始终面对死亡。“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人只有在对死亡的不断思考和领悟中才能真正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的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在她的小说创作中铺展着她对生存和死亡的关注和领悟。作为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驱,伍尔夫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因此她的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相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动成为小说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作为女权主义者,伍尔夫的小说往往以女性为叙述主体。她力图挖掘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生死的思考和感悟。因此,她对生存和死亡的探讨是从其对小说中主要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中展开的。
本文以女性主义伦理学为理论背景,以女性主义视角,通过“熔铸在女性身体里的经验”、女性的“性别意识的自省”[2]来探讨女性的生存形式和困境以及她们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对死亡的思考和领悟。通过分析伍尔夫意识流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克拉丽莎的内心世界来挖掘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生死观。通过对文本和人物深入地分析,笔者发现伍尔夫所表达的生死观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也有一些作者提出过类似观点,但有的作者忽视了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女作家以其女性视角对生死的独特的解读,有的作者对“向死而生”的深层内涵没有作详尽彻底的诠释。本文作者通过对伍尔夫经典作品的仔细研读,力图印证伍尔夫“向死而生”的生死观点,以期拓展其深刻内涵。伍尔夫通过对死亡的思索来探求生活的真谛以及人生的价值,她已经认识到生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认为人应该将死亡当作生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坦然地面对死亡,思考它,领悟它,只有这样人才会真正领会生存的价值和含义。“向死而生”不是对人生的悲观解读,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以“向死而生”作为人生态度,认为生死相伴相随、不可分割,就会摆脱对死亡的畏惧和焦虑,从而正视死亡,面对死亡也能积极地对自己有限的生命进行创造,最终在“向死而生”中获得生存的自由。
在这部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克拉丽莎通过对生死的思索和感悟,最终走出了生存困境,并积极地去探索与追寻女性生存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她们在男权社会所提供给女性的有限的、狭小的自我空间里创造着各自的生命价值。因此,笔者认为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生死观是积极的、乐观的。从她笔下所创造的人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
2 研究理论:女性主义伦理学及其主要观点
1982年,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发表了著作《不同的声音》,引发了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的思考和探究,奠定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她指出父权制的道德建构模式对女性的精神压制和对女性价值的忽视。她建立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把女性的道德行为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以保存自己为目的的是最低层次,以成就别人为目的的是中级层次,以及对别人和自己的需求都恰当关照的是最高层次。提出道德就是实现关怀和避免伤害,就是对人的需要作出反应,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关怀[3]。
肖巍[4]指出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仅限于研究“妇女问题”和“妇女道德问题”,而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道德问题,以女性主义视角看世界、看社会、看异性、看自身、看两性的关系,看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问题。”罗蔚[2]认为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以女性的生存形式为切入点,来研究现代伦理文化的问题。他们以女性意识的觉醒来批判那些男权社会制定的使女性受压迫的社会道德和规范。
3 伍尔夫在生活和作品中的死亡探索
伍尔夫是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她抨击父权制,提倡男女平权,争取女性教育权和财产权。在作品中,她尝试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揭露父权制压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探索女性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在她的小说里,她将女性人物作为叙事的主体,深度挖掘女性意识以及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对生死的思考和对生存形式的积极探索和追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一书中感慨道:“会不会是死的愤怒必须要时不时地遮蔽生的喧嚣, 免得它被我们撕成碎片?我们天生是不是必须要每天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死亡的滋味, 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存活?”[5]伍尔夫已经意识到生死的不可分割性,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止包含点滴的生命,还有无处不在、如影相随的死亡。在创作《达洛维夫人》时,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清晰地表明:“在这本书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6]事实上,生死问题是伍尔夫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从13岁开始,她的生活便蒙上了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1895年,13岁的她失去了母亲,沉痛的打击让她出现了精神问题。死亡的打击接踵而至,1897年,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斯特拉去世。1904年,伍尔夫的父亲也去世了。当她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恢复过来时,她最喜欢的弟弟托比在1906年突然去世了。随着她的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她的生活还没开始就被打破了。她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时常感到死者的存在,她的现实感有时会被过去的生动景象所扰乱。精神上的进一步崩溃,加上死亡的阴影,给她的世界蒙上了阴影,就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她的余生,她曾分别在1895年、1915年和1941年企图自杀。伍尔夫一生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她都在与死亡作斗争,持续的冥想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死亡的想法和想法。弗洛伊德认为,“引起任何神经症的未解决的冲突构成了文学的素材。”[7]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潜意识的外在表现。”[7]因此,生与死成为伍尔夫小说的主题之一。
4 《达洛维夫人》:向死而生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对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认为父权社会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源。因此,在她的大部分小说中,她都将女性置于叙事的中心,努力揭示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生死的思考和探究。因此,伍尔夫对生与死的论述是通过对女性角色内心世界的探索来展开的。
在小说开头,达洛维夫人为了举办晚上的宴会,去喧闹的伦敦街头买花。她是一位五十二岁的女人,但仍然很有魅力,活泼优雅,心中洋溢着对生命的热爱:“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叮当的铃声, 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呼啸声——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8]但在生的喜悦当中,伍尔夫却在时时提醒死亡的无处不在,达洛维夫人在生命浓郁的六月清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的生命最终必定会完全停止,这重要吗?没有她而这一切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吗?抑或,相信死亡使一切完全终结,不也令人感到安慰吗?”[9]一位看似完美的上流社会的国会议员的妻子,为何会时时感受到生活的危险、死亡的阴影呢?作为议员夫人,达洛维夫人的身份已经让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她有种最奇怪的感觉,感到自己是个隐形人,无人能见;无人不知……自己作为达洛维夫人;甚至也不再是克拉丽莎;这是理查德达洛维夫人的感觉。”[8]她时刻恪守作为达洛维夫人的职责,遵循父权社会所制定的女性的社会角色,她放弃了作为克拉丽莎的所有爱好,“她一无所知;没有语言,没有历史;她现在几乎没看书,除了床上的回忆录。”[8]她竭力地表现得像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和一个理想的妻子,顺从她的丈夫。正如彼得曾经评论的那样:“她具有他两倍的智力,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可她必须总是引用理查德的话……”[8]与此同时,达洛维夫人也意识到了她的生命核心一片虚无,“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她觉得自己只是生活的“局外人”“旁观者”,生活的喧嚣和美好让她更觉孤独和寂寥,甚至“终感到活在世上,即使是一天,也充满了许多危险”[8]。她在父权社会的生存困境让她在时时萌生的死亡意识中寻找慰藉。伍尔夫为了克拉丽莎的顿悟而牺牲了一位男性角色——塞普提姆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饱受炮弹打击的一战老兵,他拒绝被同化,成为被社会体制禁锢的没有思想和灵魂的人,他用死亡来反抗压制,保护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
塞普提姆斯,作为达洛维夫人的“分身”,是克拉丽莎的精神分体。他们看似毫无关联,实际上在精神上是同体的。他们热爱生活,但都是社会体制的受害者,偏离了自己的社会既定角色:塞普提莫斯拒绝做一个被压制的没有独立思想的老兵;克拉丽莎内心拒绝做一位父权社会体制下的理想的妻子;他们都是“被囚禁的灵魂,被他们所属的社会阻止其自由发展和充分表达”[9]。伍尔夫把塞普提莫斯和克拉丽莎·达洛维放在一起,想要揭示克拉丽莎的内心挣扎,根据的观点,“塞普提姆斯的疯狂是克拉丽莎心中不断激烈战斗的公开表现”[10]。
当塞普提姆斯的死讯传到克拉丽莎的宴会中时,她从开始的震惊,到感同身受,“他从窗子里跳了出来。地面冲了上来;生锈的铁围栏尖误扎进了他的身体,伤痕累累。他躺在那里,脑袋里有什么在重重敲击着,然后是一片黑暗的窒息。”[8]通过对塞普提莫斯死亡的想象体验,克拉丽莎也在精神上体验了自己的死亡。她虽与塞普提姆斯从未谋面,但精神上相通,她理解他为什么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种传递思想的努力;人们感到无法达到那神秘的捉摸不到的中心……狂喜消失,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死亡中有着拥抱。”突然,克拉丽莎不再同情塞普提莫斯了,“她觉得自己很像他——那个自杀的年轻人。她为他做了这件事感到高兴;他们活着的时候把它扔掉了。”他的死让她“感受生命的美”和“感受生命的乐趣”[8]。通过死亡,她明白塞普提姆斯的死亡是在传递某种重要的信息,在死亡中有拥抱,这种拥抱能让人透过死亡去寻求生命的中心。只有在死亡中,人们才能抓住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所逃避的核心和真实的东西。她整理思绪,在与死亡面对面的对峙中,她领悟到了生命的核心,认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勇气,选择回归到生活的急流中,回到她的宴会当中。小说的结尾与开头是遥相呼应的: 作为小说开头达洛维夫人“灵魂已死”的见证者,彼得惊喜地发现了从死亡中获得顿悟,重新回到宴会中的克拉丽莎,“是克拉丽莎, 他说。因为她来了”。名称的改变,“达洛维夫人”到“克拉丽莎”,暗示了克拉丽莎已从对死亡的思索中汲取力量,不再是冷漠、拘谨、时时感受到生活的危险的“完美女主人”,而是积极地投入生活的喧嚣之中并积极去寻求生命意义的独立个体。这时,莎士比亚的诗句又出现在她的脑海中,“不要再怕骄阳炎热 ,也不怕隆冬严寒”,这句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莎翁的诗句,暗示了克拉丽莎在死亡的体验和思索中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和力量。正是通过死亡,克拉丽莎“实现了过去的充实,现在的空虚,未来的新生”[11]。
5 伍尔夫的生死观:向死而生
伍尔夫一生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当中,亲人的相继去世给了她致命的打击,对死亡的思索一直贯穿在她小说的创作当中。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也是她人生的缩影,伍尔夫通过对她们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深刻的内心独白,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观点。从时刻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到从直面死亡的过程中,理解死亡中所包含的积极含义,从而从死亡中汲取力量,在“向死而生”的生死观中获得了生存的意义。
事实上,“向死而生”并不是悲观的,而是对生命的积极诠释。如果一个人认可“向死而生”的人生观,认为生与死是不可分割的,他就会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勇敢地面对死亡,把死亡当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一旦从死亡的痛苦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就会获得生存的自由,更加重视对人生短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伍尔夫通过对死亡的思索来探求生活的真谛以及人生的价值,她已经认识到生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认为人应该将死亡当作生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坦然地面对死亡,思考它,领悟它,只有这样人才会真正领会生存的价值和含义。以“向死而生”作为人生态度,认为生死相伴相随、不可分割,就会摆脱对死亡的畏惧和焦虑,从而正视死亡,面对死亡也能积极地对自己有限的生命进行创造,最终在“向死而生”中获得生存的自由。
伍尔夫在小说中也试图为女性角色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小说是以达洛维夫人为了准备晚上的宴会,到伦敦街头购买鲜花开始,以克拉丽莎在经历了死亡顿悟之后,重新回归宴会而结束。“宴会”作为贯穿小说的主题,在达洛维夫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作用。伍尔夫在小说中为达洛维夫人的宴会赋予了新的含义和深层次的内涵。“晚宴”是一种象征,是女性想要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找到生命价值的出口的体现。在小说里,通过克拉丽莎的内心独白,表达了她热衷于办晚宴的原因,“她每时每刻感到他们各自孤独地生活,不由得怜悯他们, 觉得这是无谓地消磨生命 ,因此心里想,要是能把他们聚拢来 ,那多好呵 ! 她便这样做了。”[8]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指出女性的最高道德层次就是兼顾到自己和别人的需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关怀。达洛维夫人的“晚宴”不是男性视角下的贵妇打发无聊时间的消遣,而是一种彰显女性主义情怀的人文主义关怀。伍尔夫以其细腻的女性视角,为女性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赋予生命的光彩和意义。在与死亡的对峙中,塞普提姆斯选择自杀来捍卫人格的独立,而克拉丽莎以其女性特有的智慧,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相互关怀,来驱逐生活中的孤独、困境和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获取勇气直面死亡,并能够在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中积极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