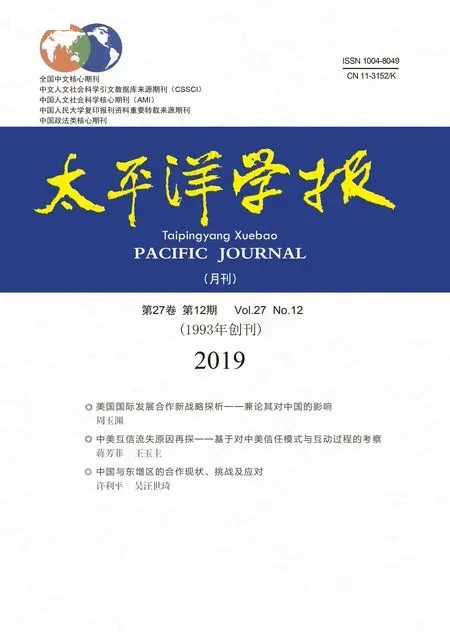“地缘竞争”与“区域合作”: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挑战与中国的应对思考
阮建平
(1.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一带一路”合作的逐步推进和扩展,不仅开创了区域整合的新方式,更具有深远的地缘经济政治影响,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性反应。随着美国日益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如何深入认识和应对这一挑战,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任务。
一、历史视角:“一带一路”合作的地缘影响
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积极响应。截止2019年12月6日,已有16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8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①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我国已成为‘一带一路’25个沿线国家最大贸易伙伴”,2019年12月13日,http://fec.mofcom.gov.cn /article/fwydyl/zgzx/201912 /2019120292171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5日。从地理空间来看,“一带一路”合作初步形成了以欧亚大陆为主体,逐步向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等区域延伸的发展趋势。随着合作的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些区域的资源整合,并客观上对全球地缘经济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合作重点在欧亚大陆,初步形成了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体、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为两翼的合作雏形,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与潜力巨大的中间腹地和边缘地区连接起来。作为全球土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大陆,欧亚大陆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拥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早在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hinder)就从地理位置和人口资源的角度分析了欧亚大陆及其“心脏地带”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突出地位,提出了“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的著名推论。②[英]哈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在他看来,随着未来这一地区铁路网络的普及和发达,“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欧亚大陆上那片广大的、船舶不能达到、但在古代却任凭骑兵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至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③[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7-68页。
对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后人提出了众多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有两个:一个认为,麦金德的理论是指导霸权争夺的一种战略思想。确实,无论是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长期争夺,还是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的思想,都受到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另一种认为,麦金德的推论并没有被历史作证明。其主要依据就是,二战后的苏联曾控制了从东欧、中亚、蒙古、西伯利亚到北冰洋之间广大地区,满足了麦金德推论的所有条件,但并未赢得与美国的竞争。
确实,贯穿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战略竞争。对此,他并不否认是“从战略机遇的视角思考帝国间的对抗”,并得出“‘世界岛’和‘心脏地带’是有关海权与陆权的决定性地理现实”的结论。④同③,第119页。为大英帝国服务是其宗旨,而被纳粹德国吸收则非其本意。但无论如何,麦金德对欧亚大陆,尤其是“心脏地带”战略价值的认识没有问题。苏联失去与美国战略竞争的原因众多。从地缘角度看,苏联虽然曾控制了广阔的“心脏地带”,但并没有很好地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或者说缺乏必要条件去整合。对此,麦金德在二战后期曾指出,苏联的中心在叶尼塞河以西,而叶尼塞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富饶的自然资源——木材、水力和矿产——事实上至今分毫未动”。⑤Halford J.Mach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21, No.4, July 1943, P.598.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弥补与美国竞争中资源的不足,苏联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油气资源。对此,美国不惜冒着与西欧盟友分裂的危险执意实施油气管道禁运,阻滞了苏联对该地区地缘经济潜力的开发。⑥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油气管道禁运的详细情况,参见阮建平著《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27页。
在麦金德的设想中,整合这一区域有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德国与俄罗斯的结盟,另一种可能是日本通过征服中国进而取代俄罗斯获得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①[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9-71页。麦金德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陆权国家,其唯一的海洋面主要被北冰洋所封锁,中国也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其实际范围不仅延伸进苏联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亚——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油气财富,还可扩展到3 000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的主要海上运输线。那里,中国拥有9 000英里的海岸线以及众多天然良港,其中大多数是不冻港。随着欧亚大陆与非洲的连接,作为欧亚大陆一个拥有热带和温带海岸线的最大陆权国家,中国占有全球最有优势的位置。②Robert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3, p.188.考虑到一战前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虚弱地位,麦金德当时的这一推断并不是指主体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一个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即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任何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具备了在全球竞争中的独特优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胜利推进,德意日集团的败局已定,而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中的牺牲和贡献赢得了同盟国的尊重,麦金德在1943年发表的《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中预见,“考虑到所有情况,如果苏联从这场战争中作为德国的征服者崛起,它必然位列全球最强的陆权国家。不仅如此,还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在恰当的时候,中国将会收到一笔数量慷慨的资金作为信用贷款,以帮助它从传奇冒险中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建立一种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新文明。到那时候,建立外围世界秩序将相对容易得多,英国、美国将与中国一道引导世界”。③Halford J.Mach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21, No.4, July 1943, pp.601, 603.
回顾历史,美国当代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和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等指出,麦金德实际上早已从陆海兼备的角度预测到中国的崛起。④布热津斯基认为,麦金德预测到中国将在全球棋局上最终取代俄罗斯,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 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p.48;罗伯特·卡普兰也认为,麦金德实际上后来更担忧的是中国的崛起,“仅凭人口和地理标准,麦金德对中国的预测至少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准确”,参见 Robert Kaplan,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3,p.189.而早在1942年美日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另一位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则从大陆边缘地带的价值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和影响。他预计,“中国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国土广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线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对于美洲地中海(即加勒比海)的位置相似。中国一旦崛起,它现在对于亚洲的经济渗透肯定会表现到政治方面”。⑤斯皮克曼提出对日战争胜利后要联日制中,参见[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王珊、郭鑫雨译,《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页。基于斯皮克曼对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地缘政治分析,美国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皮克曼启发了“遏制”政策。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45.卡普兰认为,中国在向麦金德所谓的中亚“心脏地带”进取的同时,也可能对斯皮克曼所谓的包括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在内的大陆边缘地带具有重要影响。⑥同②,p.211。他在2017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和美国的军事反应》一书中总结到,随着欧洲的式微,欧亚聚合起来了。这并不是要说欧亚正变得统一,或像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欧洲那样稳定,而是指全球化、技术、地缘政治的互动以及相互强化,正引导欧亚这个超级大陆成为一个分析意义上的流动的可理解的单元。而且,由于地中海盆地的重新统一,来自北非和地中海的难民涌入欧洲,以及跨越从印尼到东非印度洋互动的急剧增长,现在可以同时说“非洲—欧亚”。麦金德将欧亚大陆与非洲连接起来的术语——“世界岛”,不再是早熟的概念。中国在中亚基础设施的扩展与其在中国东海、中国南海的扩展直接相关。全球化以及对海上交通线路的强调,使中国向蓝水扩展成为必须。因此,就有了“一带一路”倡议。①Robert D.Kaplan, 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and the U.S.Military Response, Center of New America Security, May,2017, p.7, 21.美国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产生一个欧亚整合中心。②Nadè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A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转 引 自 Andrew Nathan, “Capsule Review”,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18-04-16/chinas-eurasian-century-political-and-strategic-implications-belt,访问时间:2018年7月12日。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似乎正在显示欧亚历史时刻的复兴。葡萄牙前欧洲事务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Bruno Maçães)指出,欧亚大陆的商品贸易早已远远超过跨大西洋贸易和跨太平洋贸易,其一体化将重塑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这是历史规律的回归。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加速这一进程。③See Bruno Maçães, The Dawn of Eurasia: On the Trail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llen Lane, 2018, pp.IV-V, 91, 99; Bruno Maçães, Belt and Road: A Chinese World Order,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2018, pp.12-14.但与传统武力征服或结盟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型区域整合方式,并对其他所有国家开放。
二、现实挑战:“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地缘竞争
“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推进,不可避免地会对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因此面临相关国家的竞争性反应。其中,尤以美国地缘竞争所带来的挑战最大。
基于对欧亚大陆地缘价值的认知以及维护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需要,美国长期以来的地缘战略目标就是:“确保在欧亚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获得将美国驱逐出去的能力,即使是削弱美国主导作用的能力也不行”。④Zibgniew Brezinski, “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 1997.p.51.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为代表的挑战导致美国国力严重透支,再次引发了对其霸权衰落的怀疑。与之相对,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崛起”逐渐从个别人的理论推测变成普遍认可的现实趋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
因此,美国政府和大多数战略学者从一开始就以警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将其视为中国建立势力范围、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秩序的战略举措。⑤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学界虽然有一些相对客观的评价,但大多都是站在维护美国主导地位及其秩序的立场上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新美国安全中心2018年9月发布的《权力的游戏》(Power Play: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和美国兰德公司2018年10月公布的《“一带一路”的黎明》(At the Dawn of Belt and Road)是其典型代表。美国政府更是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及其进展。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于2018年 1月举办了“五年来的‘一带一路’听证会”,邀请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新美国研究中心等著名智库专家发表意见。随后两个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一带一路”听证会,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ely)、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托马斯·瓦尔德豪瑟(Thomas Waldhauser)、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库尔特·蒂德(Kurt W.Tidd)等都到会参加。作为美国政府正式文件,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正式提到对包括“冰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怀疑,2019年4月海岸警卫队公布的《北极战略展望报告》及国防部随后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5月)和《北极战略》(6月)则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警惕。面对“一带一路”倡议逐渐由“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向“冰上丝绸之路”的渐次展开,美国不仅将北极纳入其“亚太再平衡”范围,更将后者进一步扩展为“印太战略”,并激活“大中亚计划”,试图通过强化前沿部署和联盟体系以及地缘经济竞争进行牵制围堵。
北极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比如可以为核潜艇的隐蔽机动和攻击以及反导系统的预警拦截提供有利条件。因此,美国对中国进入北极十分警惕。美国海军研究所2010年出版的《海上长城:21世纪的中国海军》指出,1999年中国“雪龙号”海洋地理研究和海底调查对中国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具有操作意义,表明中国可能已经在为北极地区的军事紧急情况做好准备。⑥Bernard D.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10,p.24.2013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的《奔向北方:中国的北极战略及其影响》认为,北极在“台海冲突”时可以充当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战略制高点。当气候变化使海上航线和资源变得有利可图时,中国可能寻求在白令海峡建立军事存在,以确保贸易和能源安全。如果认定供应中断或商业运输封锁威胁到其在北极的经济利益达到了影响其社会和政权稳定程度时,中国就可能运用军力做出回应。①Shiloh Rainwater, “Race to the North: China’s Arctic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pring, 2013,Vol.66, No.2, pp.76-77.显然,美国军方对中国未来北极行为的预测更多是基于职业习惯的主观臆想,而非基于中国的实际动机和行为。
根据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委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完成的《2025年亚太再平衡》报告首次将北极纳入进来。该报告认为,随着中国转向“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北极的主要活动正由科学研究扩展到与俄罗斯和北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并从2015年开始扩展至军事领域。而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安全主角,太平洋司令部主要集中在远东。为了确保美国在北极的利益和安全,该报告要求明确太平洋司令部在北极的作用,加强与训练北极部队的阿拉斯加陆军北方水域训练中心的联合行动,并推动与在北极活动的亚洲国家的合作,尤其是高寒训练。②2015年9月,由五艘海面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舰队进入白令海峡,穿过美国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参加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出现在北极地区,虽然没有违反国际法,但该报告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扩大在太平洋活动范围并越来越想成为一个极地玩家的雄心。参见Michael Green,Kathleen Hicks, Mark Cancian, 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Capabilities,Presence, and Partnerships——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U.S.Defense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17, 2016, pp.183, 190.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60119_Green_AsiaPacificRebalance2025_Web_0.pdf,访问时间:2016年 10月5日。2017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Paul Zukunft)将军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表示,北极目前的形势发展与中国南海非常类似,要警惕中国船只进入和停留调查的行动。③Nick Whigham,“Arctic Ambitions:Could the Opening up of the Arctic Because the Next China Sea?” August 29, 2017, 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environment/conservation/arctic-ambitions-could-the-opening-up-of-the-arctic-become-the-next-south-china-sea/news-story/c6aa32b7a02bc594ce2eb49301784c46,访问时间:2017年12月6日。2019年4月,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北极战略展望报告》认为,“冰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以及中国在北极经济科技存在的增长,可能会像在中国南海一样阻碍美国进入北极以及在这一地区的航行自由。④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rctic Strateg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2019, p.10, 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5973939/Arctic-Strategic-Outlook-APR-2019.pdf,访问时间:2019年5月10日。这一推断混淆了中国南海争端与中国参与北极合作问题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强化太平洋司令部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提供依据。事实上,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在尊重北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基础上加强与他们的合作,根本不存在与任何国家的领土争端,更不存在任何阻碍航行自由的可能性。
除了军事安全考虑外,美国也非常关注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2017年9月,中远集团(COSCO)与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长商谈合作跨北冰洋与俄罗斯北部各州的航线,并推动包括巴尔克曼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北德维纳河深水港口开发。除了俄罗斯北极地区外,中国还不断增加在芬兰、冰岛、加拿大等国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通过与芬兰合作的“数据丝绸之路”(Data Silk Road),中国正在铺设海底电缆,以更快、更经济地实现点到点的连接。同时,中国还在格陵兰岛建机场,与俄罗斯合作扩建穿越北极航线向亚洲运输油气资源的港口设施,在加拿大西北领土建立基础设施。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港口、机场建设和海上航线勘探具有军事目的,甚至猜想中国在格陵兰地区的开发可能威胁北约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由于俄罗斯在北极的行动以及与中国合作的不断加深,美国担忧这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在增加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和军事压力筹码的同时,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对此,美国外交学会的一份独立报告认为,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北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与中俄的竞争,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①Thad W.Allen and Christine T.Whitman, Arctic Imperatives:Reinforcing U.S.Strategy on America’s Fourth Coas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75, 2017, pp.ix, 3,18-19.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瑟·康利(Heather A.Conley)认为,在宣布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组成部分的“冰上丝绸之路”之后,中国政府与俄罗斯、北欧和北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高层外交倡议进一步推进,正整合成一个内在一致的北极战略。中国在北极基础设施和经济足迹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对该地区有更广泛的影响。②Heather A.Conley, China’s Arctic Dream, a report of CSIS Europe Program, February 2018, p.6.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0220_Conley_ChinasArcticDream_Web.pdf? 3tqVgNHyjBBkt.p_sNnwuOxHDXs.ip36,访问时间:2018年5月2日。2018年4月8日,美国海军俱乐部和国际海上安全组织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约翰·格拉迪(John Grady)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其经济政治影响超越亚洲,进入非洲和现在的加勒比,并最终进入北极。③John Grady, “China Making Aggressive Moves in the Arctic”,April 8, 2018.https://news.usni.org/2018/04/08/panel-chinamaking-aggressive-moves-arctic,访问时间:2018年5月12日。中美研究所执行主任洪农(Hong Nong)指出,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被很多观察者认为是为了追求“冰上丝绸之路”,就像向西扩展到欧洲、非洲和拉美的“一带一路”一样。④John Grady, “ China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Near Arctic”, April 27, 2018, https://news.usni.org/2018/04/27/panelchina-investing-infrastructure-near-arctic,访问时间:2018年 5月12日。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正常合作视为“地缘政治经济的扩张”,与当事各方的认知存在根本的背离,体现了美国一些人的狭隘和偏见。
为了应对北极地区的潜在挑战,美国与加拿大在2012年12月签署了《北极合作三方指挥框架》(Tri-Command Framework for Arctic Cooperation),作为进一步整合美国北方司令部(USNORTHCOM)、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CJOC)、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推进增强北极军事合作,明确在准备和执行安全、防务行动中的具体合作领域”。未来,其使命将可能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和海上安全,也可能成为讨论北极军事议题的论坛。⑤Dana Gabriel, “U.S.Arctic Ambitions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High North”, Global Research, July 24, 2013, http://www.globalresearch.ca/u-s-arctic-ambitions-and-the-militarization-ofthe-high-north/5343760,访问时间:2017年 10月 6 日。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在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对话。在重新评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修订案》过程中,日美战略合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强化弹道导弹防卫,宗谷海峡、津轻海峡的警戒,以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⑥T.Kotani, “ High Seas and Rising Tides U.S.-Japan Maritime Coop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Pacific Forum CSIS: Young Leader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9, p.21; Yasuaki Hashimoto, “Maintaining the Order in the Arctic Ocean: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among Coastal Nations”, in Yoshiaki, S.ed., East Asia Strategic Review,2011,p.66.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作为应对中俄的日美安保合作,事实上成为美国确保北极主导地位的“先手棋”。
从强化日美安保合作到“亚太再平衡”,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非常明确。而将北极纳入“亚太再平衡”范围,显示了对中国参与北极活动的日益关注。但这些规划不足以涵盖中国近年来对外合作的快速发展。特朗普上任之初对“亚太再平衡”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短期经济效率的考虑,但在战略上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崛起的警惕,相反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美国在2017年10月正式提出“印太战略”。⑦Rex W.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Washington, DC. , October 18, 2017.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同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进行一场取代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增强了其地缘政治渴望。对此,美国应加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和新加坡等地区盟友与伙伴的合作。⑧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25, 45-46.2018年1月美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概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需要美国军方认真对待的掠夺性经济政策,这一做法超出了其传统职责范围。①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Edge, January 2018, p.1.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访问时间:2019年6月10日。随后公布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提到“一带一路”倡议和“冰上丝绸之路”,认为中国试图运用该倡议发展与其他国家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塑造与中国一致的利益。中国如果想要为其维持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等遥远水域的海军部署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特定外国港口的投资就可能创造潜在军事优势。②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May 18,2018,p.111。《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继承了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的全球扩展为其军事扩展提供了新的需求。该报告还21次提到北极,认为中国增加在北极的活动为强化其军事存在铺平道路,包括可能向该地区部署潜艇,作为对核攻击的威慑。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 2019, pp.11, 114.同年5月31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此举被普遍解读为“印太战略”的具体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太战略”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扩展版。自2019年以来,美国日益明显地将北极、“印太”地区整合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竞争中来。2019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再次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掠夺性经济行为”,并对中国倡导的“冰上丝绸之路”和在南极的活动提出质疑。③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pp.I, 10.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访问时间:2019年6月10日。随后公布的《北极战略》正式将北极视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潜在走廊,认为该地区的变化将更广泛地影响与中俄在“印太”和欧洲竞争的相关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应该限制中俄利用这一地区的能力。④The Defense Department,the 2019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 Arctic Strategy,June 2019,pp.5-6.该报告只有19页,但18次提到中国,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n/06/2002141657/-1/-1/1/2019-DOD-ARCTIC-STRATEGY.PDF,访问时间:2019年6月12日。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做法,是因为美国日益将其视为与中国在权力、财富和影响力方面全球竞争的一部分。该报告建议,美国应整合盟友和各种公私资源,从地缘政治、商业和治理发展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对抗。为此,提出了包括联合盟友与伙伴强化军事态势、提供替代性开发项目和舆论攻击等九条对抗措施。⑤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018, pp.15, 21-27.其实质就是将美国过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对抗做法加以系统化整合提升,除了军事牵制和舆论攻击外,尤其要加强地缘经济竞争。201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价值1.13亿美元的“印太”区域投资计划。这被很多人视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⑥Alyssa Ayres, “Pompeo’s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just a Start” , July 31, 2018 , https://edition.cnn.com/2018/07/30/opinions/pompeos-indo-pacific-strategy-opinion-ayres/index.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5日。为了与中国在提供大型基建及发展项目的融资选择方面进行竞争,除了加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金融机构的合作外⑦“US-Japan-Australia Announc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Indo-Paci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July 30, 2018, https://www.opic.gov/press-releases/2018/us-japan-australia-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indopacific-infrastructure-investment,访问时间:2018年8月5日。,美国还不断整合国内资源。2018年10月5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法案),将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国际开发署相关机构整合成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⑧Press Office of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on H.R.5105/S.2463, 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BUILD) Act of 2018”,July 17,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h-r-5105-s-2463-better-utilization-investments-leading-development-build-act-2018/,访问时间:2018年8月2日;“A New Era in U.S.Development Finance”, October 5, 2018, https://www.opic.gov/build-act/overview, 访问时间:2018年 10月 12日。与此同时,美国重拾一度停滞的“大中亚计划”(CASA-1000)。①该计划是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rick Starr)教授提出,2005年得到小布什政府支持,2011年被奥巴马政府进一步调整为“新丝绸之路愿景”。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反恐和社会转型,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由于地区安全形势短期内难以改善,加之美国缺乏足够的融资手段,该计划一度搁浅。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推进,“大中亚计划”作为一种与之竞争的替代性方案再次得到了美国的重视。 Fredrick Starr,“A Partnership for Center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Vol.84, Issue.4, 2005, pp.164-178.俄罗斯学者认为,该计划就是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中亚地区的苏联共和国、阿富汗和南亚连为一体,推动与美国和北约的合作,脱离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最终导致该地区形成“可控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空间。②[俄]阿列克谢·帕霍林:“美国‘大中亚’计划付诸实施——‘可控地缘政治多元化’的一个版本”,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9年3月1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9年3月22日第10版。
综上所述,美国近年来的对华战略调整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日益如影随形,并由舆论攻击、军事牵制向地缘经济竞争扩展。这并非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体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行为构成了对“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的现实挑战。
三、未来出路:以区域合作化解地缘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地缘竞争,本质上就是新旧两种行为逻辑的博弈,即发展逻辑与竞争逻辑的博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区域合作化解地缘竞争。
3.1 地缘竞争与区域合作的对比
本质上讲,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就是地缘竞争逻辑,不仅与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还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力透支。因为美国地缘竞争的动机是确保其军事优势和安全主导地位,为此需要投入大量没有或较少“产出”的资源。而要巩固和扩展联盟体系,又需要广泛的安全承诺和大量的“经济让利”——就像冷战期间的“经济安全网”一样。在当今的世界发展趋势下,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时宜,还可能加剧国家负担。
从国际维度来看,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正逐步改变各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佳方式,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由排他性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向共生性的命运共同体转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日益强烈的时代要求。在这种时代趋势下,拼凑联盟、制造对抗的做法越来越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其实现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对个别国家而言,一定程度的中美竞争虽然可以给其提供左右逢源的“第三方优势”,但如果中美竞争加剧将导致左右为难的“第三方风险”。只要中国不真正威胁其核心利益,很少有哪个国家真正愿意冒险将自己绑在与中国对抗的战略上。对一个新兴大国而言,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是其最大的吸引力。
从国内维度来看,在缺乏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成为各国政府治国执政的第一要务。而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福利的分配欲望。要实现经济的尽可能发展,就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并确保其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顺利进行。如果要构建一个对抗中国的国际联盟,仅靠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强化军事部署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像冷战期间一样向其盟友提供充分的不对称经济优惠。而鉴于各国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其程度还要足以替代中国市场所提供的发展机会。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不仅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而且是美国绝大多数盟友的重要经贸伙伴。显然,美国很难提供足够取代中国的经济刺激。
从根本上讲,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是战略成功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资源“输出—输入”的正向互馈回路,任何大战略都难以持久,遑论成功。冷战期间,美国构建的经济网络既为其盟友提供了发展空间,自身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从而确保了在与苏联的长期冷战竞争中的资源优势。当前,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战略调整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基本上都是资源的付出。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安排获得补偿,长期下来只会加剧美国的国力透支;如果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则难以拼凑起足够的排他性联盟体系,这是美国当前战略调整的两难。虽然如前所述,特朗普政府开始运用地缘经济对冲“一带一路”建设,但热衷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资源去重建这种经济网络有待观察。特朗普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对外援助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①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访问时间:2018年 2月 16日。。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席、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前筹款人雷·沃什伯恩(Ray Washburne)此前表示,他们不是一个援助组织,而是为私人企业服务的。②Josh Zumbrun and Siobhan Hughes, “ To Counter China,U.S.Looks to Invest Billions More Oversea”,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to-counter-china-us-looks-to-invest-billions-more-overseas-1535728206? mod=pls_whats_news_us_business_f,访问时间:2018年10月6日。
与美国的地缘竞争逻辑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基于开放合作的发展逻辑,不是所谓“陆权”与“海权”的竞争,更不是中国版的全球化,它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积极响应。③对此,中国学界进行过深入的对比剖析。肖炼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 TPP针锋相对,参见肖炼:“‘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98-106页;杨国桢和王小东两位学者分析了对“一带一路”的主要误解。他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复兴陆权,不是恢复册封体制,也不是中国式的全球化,参见杨国桢、王小东:“‘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与理论探索,《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75-81页;腾建超批驳了美国前白宫顾问班农的观点,即“一带一路”是集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说”于一身的战略,以谋求对世界的控制。腾建超指出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参见腾建超:“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与‘一带一路’倡议”,《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第1-15页。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刘昌明、姚仕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与大西洋主义”,《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56-66页;孙绍勇、王文余:“‘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22-27页等。中国政府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2013-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通过贸易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左右。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年 4月 22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2/c_1124400071.htm,访问时间:2019年4月23日。美国学者罗兰承认,中国关于回报世界与合作共赢的说辞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欧洲,各国政府正如饥似渴地吸引中国的投资。⑤Nadège Rolland,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A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转 引 自 Andrew Nathan, “Capsule Review”,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18-04-16/chinas-eurasian-century-political-and-strategic-implications-belt,访问时间:2018年5月2日。更重要的是,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也有助于中国国力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会导致不可持续的战略透支。
3.2 以区域合作缓解地缘竞争
正如阎学通教授所言,虽然中美竞争包括军事竞争,但其最核心的是经济而不是军事。“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都需要以其他国家的配合为必要条件,如没有他国的配合,这两个方案都将无法实施。⑥阎学通:“关于一带一路,很多人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农业思维”,观察者网,2019 年4 月 25 日,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9_04_25_499086.shtml,访问时间:2019 年5 月2 日。面对美国的地缘竞争,中国的根本办法不是与之对抗,而是坚持开放的态度继续推进与各方的互利合作。
针对各种误解,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重申,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新华网,2018 年 8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8/27/c_1123336562.htm,访问时间:2018年 8 月 30日。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发现,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确保其再生产循环的顺利进行是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生产与市场的长期矛盾,唯有相互开放才是可持久的普遍发展之路。虽然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变迁不断,但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逻辑没有变。一旦其扩张受到严重阻碍,冲突就难以避免。近代西方大国的殖民扩展及相互之间的殖民争夺,以及美苏之间的冷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而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开放对于现代各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阮建平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各国的发展权利成为新的时代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使各国产业结构的重合率上升,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结构性摩擦。对此,麦金德早就承认,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被夺取高科技工业的份额。但这些工业紧密联结,各自为政或自由放任的做法都会导致普遍的伤痛。为使各国满意,必须设法保障国家发展机会的某种平等。③[英]哈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153页。基于历史教训,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要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主张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原则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注重发展战略对接。
区域合作不仅包括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与各国内部相关地方之间的合作,唯有如此才能深耕相互认同的社会基础。由于自然或历史原因,很多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途径不少落后地区,加强地方合作有助于促进这些国家地方的平衡发展。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还有助于缓解东道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深化和扩大社会合作基础。从区域一体化的规律来看,当经济合作达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政治互信层次和水平已不足以化解各国内部随之上升的对依附风险的担忧和对利益分化的不满,这就需要基于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协调及深植于大众心理的社会认同来为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分的动力和保障。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沿线国家相关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合作,以深化和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内社会基础。
综前所述,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猜忌和抵触,有着复杂的历史惯性和现实霸权动机,其反应带有浓厚的地缘竞争色彩。但美国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其“输利”与“谋权”的内在两难还可能导致国力的透支。面对挑战,中国不是与之进行地缘争夺,而是继续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逐步缓解地缘竞争压力,并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对待美国的一些批评,通过提升合作标准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化被动为主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④兰德公司在《一带一路的黎明》中认为,尽管中美在全球和某些地区是竞争对手,但合作也是可能的。距离中国越远,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越大,甚至是“平行伙伴”(partners in parallel)。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一带一路”认知的某种理性回调,但远未成为主流,更没有成为现实政策。参见Andrew Scobell,Bonny Lin, etc, “At the Dawn of Belt and Road: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 October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273.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2 月 1 日;美国亚洲协会2019年6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虽然依然带有美国的偏见和立场,但也承认“一带一路”的价值和中国政府对待批评的开放态度,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这体现了美国理性声音的上升,参见 Daniel R.Russel and Blake Berger, “Navig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Asia Social Policy Institute, June 2019,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6/Navigating%20the%20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2.pdf,访问时间:2019 年 7 月15日。实际上,在2019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政府与各方已将绿色环保、廉洁透明和财政可持续等要求都纳入进来,体现了对相关怀疑和批评的积极回应,也适应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同发展的新要求。参见《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2019年4月27日, 新 华 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7/c_1124425237.htm,访问时间:2019年5月1日。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竞争性反应,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甚至可能导致一些风险的连锁联动。这就需要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对各类风险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