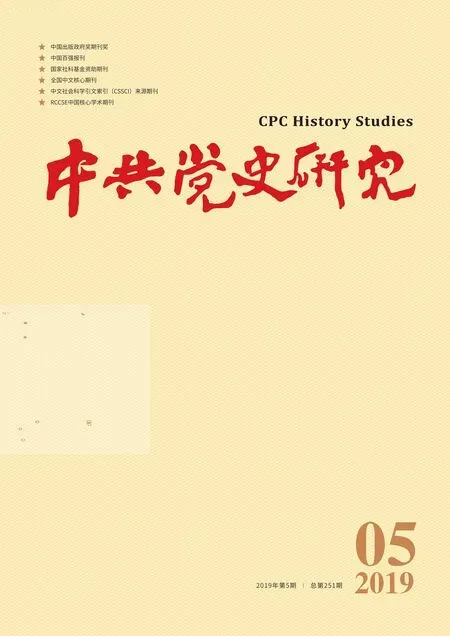乡镇企业改制的社会历史学分析*
——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严 宇 鸣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其间各地乡镇(社队)企业异军突起,企业产值在国家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快速增长,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转型的关键阶段,这类乡(镇)、村办企业坚持集体所有制性质,这一介于国有与私有之间的“模糊产权”形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形态得以抵御经济转型过程中私有化冲击的重要凭借。[注]Naughton, Barry, “Chine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ivation from Below,”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Vol.84, No.2. Lan Cao, “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63, No.4, (Autumn, 2000).然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受各类主客观因素影响,乡镇企业发展明显乏力,不得不接受以租赁、转让、拍卖或股份制改革为形式的转制处理,企业的集体所有形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就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曾有过集中讨论,先后提出“企业经济效益与地方财政关系”“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互惠网络”及“地方经济精英崛起对于企业管理的掣肘”等解释观点,为我们理解相应企业转制缘由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于改制行为本身,忽视了对企业在改制之前经历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变革的分析,这一做法事实上抽离了企业转制发生的历史背景,使得类似讨论更多表现为截面分析[注]研究综述可参见严宇鸣、桂勇:《财政激励、利益集团与经济精英: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动力的三种理论解释及其现实意义》,《社会学》2011年第2期。。有鉴于此,本文借助浙江省慈溪市[注]当地于1988年10月撤县立市,本文对应具体时段分别指称“县”“市”。不同于苏南或温州模式,慈溪乡镇企业发展及所有制设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浙北模式特点,即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同时较早放开对于联户、家庭工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限制,在“只做不说”原则的指引下实践“四轮齐驱”地区经济发展策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地乡(镇)、村办企业发展式微,地区集体所有制经济陷入困境,但由于同时期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地区经济发展主力得以平稳交接。一手档案及浙江省、宁波市内部出版资料,尝试就乡镇企业改制议题进行历史社会学分析,通过拉长研究关注时段,详细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乡镇(社队)企业发展的过程表现,并把“改制”议题的讨论细化为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改革”与企业所有制“转制”的双维度分析,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社会机制,并着重阐述相应机制受到不同历史时段社会环境影响的整体过程。
一、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的复苏与“联办”形式下的收益分配问题
慈溪地区工业企业的兴起,两个时间点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兴办,在大炼钢铁运动的带动下,各公社集中兴建小工业企业,与当时已有手工业生产组织一同构成地方社队企业雏形。然而,由于当地并非浙江省产铁炼钢基地,运动过后,县内公社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二是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颁布后,地方(农村)办工业成为中央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慈溪县各公社集中兴办企业470家,出现了一波地方(小)工业发展浪潮。70年代初,当地社队企业因中央政策调整而受整顿,不少企业被迫关停,但这次整顿并未扑灭地方(小)工业发展的火种。1972年,中央政策稍有放宽,当地管理部门便就社队企业发展提出调整意见,明确以“加强领导,合理布局,整顿提高,适当发展”作为指导方针,鼓励企业发展。是年年底,全县共有社队企业213家,总产值达到4045万元,实现积累511万元,历史上第一次达成年内积累翻番目标。[注]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慈溪县社队工业情况汇报》(1973年5月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到了1975年,“农业学大寨”氛围得到再次强化,加之中央开始鼓励工业城市对于周边农村小型工业的区域性带动,农村社队企业发展速度得到一定提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在慈溪县,浒山镇、周行公社、东方红公社社队企业年产值率先突破500万元,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接近亿元[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关于加强领导积极办好社队企业的意见》(1976年5月1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在之后一年时间内,慈溪县社队企业总数迅速增至1329家,职工人数67183人,全年实现工业生产总值16290万元,在宁波地区排名仅次于鄞县(19346万元)。县域内,浒山镇、白沙公社、东方红公社、长河公社、新浦公社与坎西公社社队企业年总产值均已超过500万元;包括长河阀门厂、鸣鹤石棉厂、新界农机厂在内的11家社队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万,高产值企业数量在整个宁波地区名列首位。[注]宁波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编:《宁波地区社队企业资料汇编(一九七九年度)》,第3、29—30页。
然而,相较于企业发展及其所作经济贡献,社队企业的角色依然暧昧。无论企业的具体所属性质如何(公社办、社队联办、队队联办或生产队办),延续原有行政管理思路,社队干部都很自然地将企业视为本单位附属部门,习惯性地对其施以行政化条线管理。联系所有制问题,虽然社队与社队企业都认可并强调企业“集体所有”性质,但两者的立足点并不相同,前者强调社队“大集体”属性,认为企业获利应由公社、大队集体共享,而后者则是更为强调企业与企业职工的“小集体”归属,在收益分配时有意对职工社员与一般务农社员作区别对待。综合看,各所属企业实则都存在这一问题,而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联办企业”。
为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了解“联办企业”形式在当地之所以兴起的历史缘由。在慈溪县社队企业的创办初期,县级管理部门倾向于支持公社办企业,而对队办形式持保守态度,为防止后者自由化发展倾向,地方上曾有明确规定,禁止队办企业承接外加工业务[注]慈溪县财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学习兄弟县的有关经验,进一步抓好对社队工业管理的请示报告》(1974年9月1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然而,这一规定在颁布之初便遭各公社大队反对,不仅纷纷兴办工业企业,更强烈要求解除对所办企业从事外加工项目的禁令。为解决矛盾,当地东方红、坎西及崇寿三大公社在1971年年初试行“联办”方案,即以“社队联办”“队队联办”组织形式规避政策对于队办企业的限制。是年,全县先后审批通过上述三家试点公社63家联办企业申请。此后,其他公社纷纷效仿,联办成为当地社队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相对于单一公社或大队办企业,联办企业的多主体共有特征决定了其在收益分配问题上的复杂性。按照当时县级正式批文规定,地区内联办企业经济收益核算及分配应采取“全社统一核算”或“分片核算”形式,前者主要针对“社队联办”或个别规模较大“队队联办”企业,后者则是针对大多数规模较小的“队队联办”企业。无论何种形式,规定都要求各企业实现相对集中的核算方式,这不仅是为了实现相应合作主体的联合,更重要的是便于公社统一管理。然而,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无论联办主体如何,联办形式只是为了帮助各生产大队突破政策限定的权宜之计,各地在实践中出现联办厂名不副实的问题非常普遍。即便是上述三家试点公社,按照政策要求,63家获准联办企业中的20家应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余实行分片核算,但实际仅有5家企业做到全社统一核算,分片统一核算的也只有19家,剩下的都只是“戴戴帽子、挂块牌子、盖盖印子”。[注]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对社队企业人员工资实行厂队结算的试行办法》(1973年6月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不仅如此,其他非试点公社在联办形式获得政策许可后,原有“公社办厂”形式随即受到冲击,许多企业放弃“社办”转而选择“社队联办”,但实际却又都只是“大队办厂”。所谓“联办”并没有统一的经营管理部门,公社对于各大队办厂的具体经营情况知之甚少,进行整体管理或考核的难度很大。[注]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关于公社工业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1973年8月2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 。据有关部门在1974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名为“联办”实为“队办”企业有500余家,管理形式普遍松散,“是否允许其继续存在”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注]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目前社队企业的情况报告》(1974年1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7。。就这一问题,最初慈溪县委、县政府、公社、大队之间实有不同意见,认为评定标准不一,如何调整需要再做观察。但在1974年9月巡视调研鄞县、上虞、绍兴三地后,慈溪县财税、银行及手工业局就该问题达成共识,效仿鄞县做法,对地区内各联办(实为独立)企业施以“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注]慈溪县财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慈溪县支行、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学习兄弟县的有关经验,进一步抓好对社队工业管理的请示报告》(1974年9月1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目的便是为了对那些行业种类各异、规模大小不等的生产组织在形式上设立统一管理部门,强调实现“一块牌子、一颗印子、一个账号”,涵盖各小生产单位,意图形成一种对外相对封闭、对内却又各自独立的生产管理组织形式。
正如基层管理干部所言,在众多被要求统一管理的项目中,经费的统一最为关键,而其中企业收益的分配处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可以想见,在独立核算的组织体系下,各类成本支出都对应于后期利润收益,收支关系明确;而在“联办”组织架构下,这一关系变得复杂且模糊。在经费管理的“统一性”要求得到行政命令强化后,难免出现“平调”“挪用”“账目不清”等现实问题。原本独立生产经营的小厂或作坊被以“车间”名义合并入“总厂”,失去了自身收益的自主分配权。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各“车间”收益差距的拉大,各自独立意愿日益强烈。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各“车间”纷纷提出撤销“总厂”要求。[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情况汇总》(1979年2月2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4-002。1976年底,当地原有500余家名义上的“联办企业”大多都退回“大队办”形式,大队办企业(595家)占到当时社队企业总数的72.47%。[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1976年工作总结》(1977年3月28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1。
联办企业集中退回大队办形式,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自身收益分配的主体地位,排斥其他大队或公社的管理介入,反映了社队企业在收益分配问题上的普遍态度。然而,这显然与当时国家政策方向有所出入。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浪潮中,地方管理部门一方面强调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中关于“(鼓励)集体办小工厂”意见,允许这类企业存在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实则更为强调指示中对于此类企业的全面控制要求,明确表示社队企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社队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目标,而非企业发展本身。[注]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社队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1975年11月12日)、《关于加强领导积极办好社队企业的意见》(1976年5月1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063-001-001。受这一认识影响,整个宁波地区在1978年进一步强化对于社队办厂集体性质的要求,其中重点谈到企业的“积累”与“上缴”比例问题,认为“‘过去只上缴30%利润,70%留厂自用’的作法不符合省委规定”,必须作重新划定,要求“除去5%企业提留使用外全部上交公社”,明确提出“兴办社队企业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过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两级没有’现象”,要求企业积累向上集中。[注]梁如林(时任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第三次社队企业工作会议报告》(1978年1月18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更关键的是,同时期开展的“一批二打”运动习惯性地将相应经济问题升级为政治斗争议题,明确提出“为深入开展运动,必须像当年发动群众‘打土豪’一样,开展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彻底找到阶级敌人的破坏”,虽然运动强调“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性,但就上述联办企业拆分问题,行政方面意见都是要求予以坚决打击,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斗争的全面胜利。[注]《宁波地区手工业、公社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情况的传达报告》(1978年3月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3-002。
二、改革的突破与局限:对于“承包责任制”制度实践的思考
就社队企业的行政管理而言,“左”的观念与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夕仍一度占据主导,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性,也使得相应集体所有权责关系变得更为模糊。如上文所述,具体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实则都通过各自方式抗拒这一限制,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无疑就此实现了整体调整。对具体企业而言,改革表现为“承包责任制”管理制度的整体引入与不断深化,这一工作贯穿于乡镇(社队)企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从最早的活力四射到后期乏善可陈再到被人为放弃,其间经历无不对应企业集体所有形式的价值变化,既显现了制度改革在最初的魄力与效果,也同时反映了这一制度改革本身的历史局限。
“责任制”“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当时国企改革意见中的“放权让利”主张相呼应,即意欲改变前期权力过度集中现象,允许具体企业在国家相对统一的计划指导下拥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调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及具体劳动者各方的生产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于社队企业“责任制”“承包责任制”的讨论,着力点在于就两者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爬梳地方档案文书,我们便可发现,自1978年至1983年间,地方管理干部在谈论社队企业改革问题时,更多使用“责任制”概念,在此之后相应表述才有变化,整体代之以“承包责任制”。对于这样的叙述变化,现有研究多不作细究,简单认为后者只是对于前者的制度延续与完善。然而,在笔者看来,“责任制”与“承包责任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就慈溪县社队企业制度改革的现实表现而言,正是其中的不同点微妙地影响了相应制度在后期的发展可能,这恰恰也是影响地方集体所有制企业兴衰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下半年,慈溪县地方管理干部原本相对偏“左”的观念与管理手段发生明显变化,不再像年前一般坚持以阶级斗争方式整顿社队企业,而是代之强调毛泽东在早期提出的“管理也是社教”理念,有意识地将运动主题从“斗争”转向“管理”。1979年,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先后下发,社队企业发展得到进一步肯定。慈溪县地方干部纷纷表示:“1979年对于社队企业发展是个大好年份,必须抓住机会,强化管理。”[注]陈文德(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供销工作会议小结》(1979年 10月1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4-002。
就管理制度的改革,地方干部非常自然地想到了“责任制”形式,这既是受当时农村农业管理形式调整的启发,也是社队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有意尝试的组织形式。在可查见的地方档案中,东方红公社是当地最早正式谈及管理问题并提出“责任制”理念的公社组织。1978年11月,东方红公社党委在提交上级部门的报告中详细分析社队企业管理问题,提出试行“责任制”方案意见,希望以此扭转前期极左管理方式的偏差[注]慈溪县东方红公社党委:《积极整顿,发展社队企业》(1978年11月2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3-022。。此后,其他公社及企业还就相应问题提出“生产岗位责任制”、“五定一奖”(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工时、定消耗,超产得奖)、“定额管理”、“定额奖励”等办法。至1979年末,慈溪县共有829家社队企业(占当时企业总数的78%)进行了责任制试点,调整并初步实行了新的薪酬及奖励办法。[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在县委党校召开的全县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记录》(1979年11月16日至19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4-001。在全年各试点企业经验汇总的基础上,县社队企业管理局进一步细化责任制内容,总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生产岗位责任制”“劳动定额管理制”“产品质量检验责任制”及“企业物资管理责任制”[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全县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纪要》(1979年11月27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4-001。。毫无疑问,相比原有社队统筹管理形式,责任制模式优化了具体企业的权责关系,极大地激发了相应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数据显示,1979年,即当地推行责任制的第一年,全县社队企业实现产值1.629亿元,年增长9.59%;到第二年,相应产值已达到2.37亿元,年增长率高达45.49%[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简介》(1981年),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6-001。。立竿见影的产值增长数据显现了责任制的管理效果,“从‘管’字上要产值、要利润”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管理局与大多数企业管理干部的共识[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关于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工作任务报告》(1981年8月21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6-001。。1981年,慈溪县实行责任制管理的社队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达到1372家,占当时社队企业总数的91.5%[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全县社队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议纪要》(1981年9月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6-001。。责任制改革整体提升社队企业发展速度。
详细考察这一阶段与后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表现异同,我们可以发现,责任制改革阶段的重点在于“定”与“奖”,即通过改革实现企业生产的定额管理,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超额奖励,这与后期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基本一致。但是,责任制改革阶段实则没有涉及“承包”概念,其间虽有过“大包干”提法,但这更多表现为企业对于社队作出的产值承诺,是表示两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象征符号。[注]张中樑(时任慈溪县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在社队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81年8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6-007。更准确地说,在这一制度的推行阶段,县级管理部门、社队或是社队企业实则都没有考虑企业实行责任制后“责任具体由谁承担”这一关键问题,直接且又简单地认定企业原有经营者(厂长)即是责任主体。按这一政策设想,责任制改革无非是在企业原有人事关系、组织框架不变基础上的管理机制调整,除通过超额奖励激励企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外,并没有考虑更多,自然也就没有人细想这一制度变革是否会对企业集体所有形式产生影响。
然而,具体企业对于责任制的实践并不完全遵循改革设想。政策落地后,有企业将完成定额责任分散至每位职工,有企业以车间、班组为单位分包定额,也有企业选择将相应定额任务打包给二三人团队,由个别经济能人统筹,甚至有企业直接将生产任务发包给外部人员,以赚取差价;规模较小的队办企业更是大多选择“一脚踢”包干形式,即发包单位只负责收取企业包干基数利润,其他一概不管。[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会议记录》(1982年8月29日)、《总结检查落实责任制情况会议记录》(1983年3月28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7-003、063-008-001。因为存在层层下包、转包或外包现象,具体企业责任实际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超出原有政策预想。相比改革前的统一管理模式,此时责任主体人事、组织关系的不确定性模糊了企业与社队之间的所属性质,部分“一脚踢”包干企业的基础利润收缴工作在当时便已出现困难。
就这类现象,慈溪县政府在1982年“整顿”期间曾有所干预,认为相应做法存在“瓜分集体企业”嫌疑,需要予以逐一清算。但由于前期“纠‘左’”政策的社会影响持续存在,这次整顿虽然严厉(关停了部分违规企业),但并不激进,更多还是强调改善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优化管理为手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会议记录》(1982年11月26日至27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7-003。1983年1月,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集中学习中共十二大文件及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重点讨论中央关于实行“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意见精神,并就该制度的地区落实条件予以分析[注]粱如林:《全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报告资料》(1983年1月3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8-002。。11月,浙江省组织全省社队企业管理局干部学习,传达中央领导在全国社队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总结报告谈及各地群众前期就责任制的意见反映,认为类似担心“瓜分集体资产”的顾虑实无必要,在肯定社队企业学习农业“双包责任制”做法的同时,鼓励企业“步子再迈大一点”“顺应群众要求,允许予以企业承包”。[注]王常枱(时任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管理局局长):《在全国社队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1983年11月1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7-037。至此,承包机制得到充分肯定,原有“责任制”表述相应调整为“承包责任制”。
客观分析,由“责任制”向“承包责任制”的发展,政府的改革意图与行政管理逻辑并未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打破“大锅饭”格局,增强当事人的责任意识,激发生产活力。在这一点上,“承包”机制只是更加强化了责任主体的责权意识。但是,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在于,承包责任制就先前多元责任主体的正式肯定,使“谁有承包资格”或“最后将企业承包给谁”都变成了有待正式讨论确定的问题。必须承认,就形式而言,这一机制是改革过程中制度进步的表现,当时众多诸如“鼓励经济能人参与承包”“打破厂长、经理承包垄断”的改革意见,实则都是对于企业前期在私下进行分包、转包及外包行为的政策鼓励,意在通过竞争进一步激发企业承包者活力。但是,这一实践导致的意外结果却令改革的主导者陷于尴尬,即承包主体的多样性使得那些原本隐匿于责任制面纱下相对含糊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腾挪转移现象变得尤为扎眼,地方管理部门难以再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在责任制阶段,由于企业的所属关系在形式上仍表现为上下对应,企业或企业经营者私下利润多留、多分的做法大多都被默许,在诸如“避免杀鸡取卵”“蓄水养鱼”等政策意见的指引下,这类做法甚至还得到了肯定。而承包责任制允许并鼓励了外部人员的进入,原有的非正式利益关系自然也受到影响。
1983年年中,慈溪县召开全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在肯定承包责任制经济激励效用的同时,华克明(时任慈溪县县委书记)指出:“有些企业干部和技术骨干,以承包为名,把集体设备、业务、资金分散到(个)人,自己雇用帮工,只向集体交少量积累,企业所得收入大部分进了个人腰包。”讲话中,华克明直接将问题归咎于承包主体的复杂性,并认为政府及公社作为企业的发包方在当时已处于弱势地位,指责承包者“在确定承包基数和利润分成比例时,不恰当地讨价还价,奖金要价越来越高,达不到目的,就以怠工、中断业务等手段进行要挟”。[注]华克明:《在全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6月29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8-003。在政府及社队企业管理部门看来,企业的有效收益被各类承包者占有,短期承包心理更是导致其急于消费,只专注完成产值任务,忽视企业整体效益,积累或投资少之又少[注]张友为(时任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干部):《在慈溪县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的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工作报告》(1983年6月28日), 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8-003。。纠正承包责任制下的此类问题一度成为相应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不仅要求分析具体企业留存、上缴比例,更是整体反思社队企业套用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做法的合理性,认为这一形式并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注]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区及浒山镇工业办公室:《工业工作负责人会议记录》(1983年11月7日至9日),县社队企业管理局:《社队企业供销工作会议报告资料》(1983年9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8-001、063-008-002。。
此后,慈溪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开始有意强化对企业承包过程的行政监管,不仅在承包合同签订时要求抬高承包基数,统一确定社队与企业之间3∶7利润分成比例,更要求承包者对产值、利润等指标予以同步承包,强调其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管理职责[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落实有关公司承包责任制会议记录》(1983年3月17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8-001。。从时间跨度上看,类似对于承包责任制制度完善的努力几乎贯穿整个80年代,直至乡镇企业转制终结。1984年年中,浙江省提出“一包三改”改革方案,要求企业在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注]沈祥家(时任慈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坚持改革、继续放权松绑,为完成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而奋斗》(1984年8月2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9-003。。是年下半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重点学习江苏省无锡县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经验,在“一包三改”方案基础上提出“一包五改”意见(增加“改变封闭经营,实现向外横向联营”,“改变原有单一银行资金获取渠道,实现多种渠道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成为全省各地进一步完善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工作的中心任务[注]宁波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查组:《关于全市乡镇企业三年来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11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50。。除了执行上级政策要求外,在慈溪县当地,由于县内大部分企业的首轮承包合同将于1987年到期,谢建邦(时任慈溪县县长)在1985年6月的乡镇企业工作会上就第二轮承包合同的签订工作予以行政动员,不仅要求核清承包企业的实际资产,提高新合同的承包基数,而且将产值、税收、产品质量、物耗能耗、销售率等多项指标一并纳入考核体系,对承包者进行百分制考评[注]谢建邦 :《在研究、部署进一步完善乡镇企业“一包五改”,落实1986年工作任务全县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10月20日),《慈溪县乡镇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百分考核办法》(1986年12月1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52、063-011-077。。
种种管理办法都是为了改善承包责任制的实践效果,尽可能制止承包者个人或团队对于企业利润的多留、多分,但从后期执行效果来看,这类监管政策实则很难落实,相反却因为承包压力过大导致少有人再愿意主动承担承包职责,经济能人大量外流,企业的内部管理与外部营销都因此受到影响。数据显示,1985年,慈溪地区乡镇企业产值的年增幅度仅为2.96%(同期家庭工业、联户经济增长64.33%),1986年1月至4月,乡镇企业产值、利润、利润率及上缴税金四项指标数值全面下滑,产值增长率下降至1.92%,利润总额同比减少22.67%;到年底,利润总额仅有4376万元,同比下降幅度增至27%[注]潘尧云(时任慈溪县副县长):《在全县乡镇企业先进供销员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86年9月6日),徐杏先(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关于我县乡镇企业工作情况的汇报暨在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5月1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1-003、063-011-015。。
三、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非公有制经济竞争关系及“联营”形式的讨论
上述关于承包责任制的讨论主要基于企业内部,而乡镇企业发展出现问题,同样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同时期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代表的个体民营经济的兴起,同行业之间的竞争的确是导致前者逐步式微的现实原因。在慈溪,两者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也尤为明显,产值、利润等各方面都有反映。学界的“竞争论”观点,即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导致同地区、同行业集体经济式微并最终被迫接受转制,具有一定解释效力。
然而,当我们遵循“竞争论”的解释路径,进一步深究地区乡镇企业后期转制表现,便会产生疑问:如果双方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在胜负明了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后的个体民营企业为何选择接手那些已处于弱势的乡镇集体企业?“带红帽”的需要只是这一问题的政治原因解释,就经济角度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发生于1985年至1986年间的“联营”形式改革。正是通过联营,当地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正式进入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内部,“集体所有”与“非集体所有”企业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合发展态势,这是后期转制企业得以迅速倒手的历史缘由。笔者之所以在这一关于“外部因素”的讨论部分分析联营形式问题,原因在于这一形式的选择本身并非出于当事人意愿,而是在外部要素变化下的被动行为。这些变化表现为当时产品市场需求、生产原料价格及电力能源供应等,但最关键的还是银行可提供贷款数量的变化。就这点而言,地方社会乡镇企业在此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恰恰是国家整体改革困境的缩影。
比较而言,进入80年代,1984年是慈溪县乡(镇)、村办工业企业发展最为快速的一年。当年,该类企业超额(122.39%)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实现产值6.8亿元,实现所得税单项收入1975万元,比年初计划多收345万元,超收幅度列各项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之最[注]慈溪县人民政府:《锐意改革、增强后劲,为夺取我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而奋斗》(1985年1月2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6-001。。如此优异成绩的获得大大激励了慈溪县委、县政府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信心,为超额完成1983年10月宁波市政府在乡镇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的“1986年相较1980年工农业产值翻番”目标,慈溪县委、县政府在1985年年初确定年度工农业产值增长目标,其中要求乡镇工业(包括家庭工业)实现年度产值8亿元至8.8亿元。采信档案表述,当时确定这一产值目标并非盲目冒进,具体数字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在纵向、横向比较慈溪县与国家整体及周边如鄞县、余姚等地乡镇企业发展情况之后的决定。[注]慈溪县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财政收支讨论稿》(1985年1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7-001。1985年第一季度,当地乡镇企业持续发力,单季度实现产值20090万元,同比增长93.42%。全县八个区,其中浒山、长河、龙山、安东四区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余各区也有60%至80%的增长。[注]裘启慧(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在全县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5年4月1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03。单就数据而言,当地乡镇企业在此时的发展势头的确令人期待。
然而,查阅1984年年度总结报告,我们发现此时慈溪县乡镇企业已经呈现“五多”特点,即“千万产值乡镇与百万产值企业增多”“新办企业增多”“新生产项目和生产产品增多”“新生产设备增多”“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收入增多”。这些在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看来是地区发展的优势表现,实则都是企业盲目扩张的证明。最关键的是,这些扩张性投资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数据显示,1983年慈溪县共发放乡镇企业贷款9966万元,这已是当地1978年贷款总额的10倍;1984年全年发放贷款额激增至17790万元,同比增长78.5%[注]慈溪县人民政府:《锐意改革、增强后劲,为夺取我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而奋斗》(1985年1月2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6-001。。这一数值虽然因为与后期银行改革有关难免存在水分,但乡镇企业生产经营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事实毋庸置疑。在当时鼓励“信贷杠杆”政策的影响下,地方管理干部不仅未对这一现象产生警惕,相反却是大力支持[注]中国农业银行慈溪县支行:《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1984年4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6-079。。如此一来,具体企业显然不会对自身造血能力予以重视。比较相应指标,在1984年,慈溪县乡(镇)、村办工业企业的销售率已有下滑,生产毛利润较1983年减少了近200万元,又因上缴税金及工资支出比例设定失当,当年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50.67%,仅有2633万元,其中还需要完成乡(镇)、村各类上缴1132万元,企业实际持有可流动资金非常有限(见表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宏观层面开始收紧银根,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资金锐减,并被要求偿还前期贷款;不仅如此,市场环境中各类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明显放慢,企业应收款难以及时回收。[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乡镇企业简报》第5期(1985年3月7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48.由于这一系列原因,1985年年初慈溪地区乡镇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各项需要现金支出的生产经营活动显得极为被动。
国家整体收紧银根,既是为了肃清市场环境中的诸多不当行为,更是为了纠正前期经济发展“过速”现象,主要针对的便是农村乡镇企业。然而,就该调控意向,国家与地方存在认识差异。浙江省政府、宁波市委干部在多个场合谈及发展速度问题时,都强调国家宏观“控速”要求主要针对其他省市,而浙江地区仍应保持速度。与之对应,慈溪县政府同样认为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需要速度支撑,但凡提出“减速”建议者,都被批评是“患上了‘恐速病症’”。[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1985年工作总结和1986年工作意见》(1986年1月1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12。
为保持计划发展速度,慈溪县委、县政府会同县乡镇企业管理局进行专门讨论,根据前期既定产值目标及1984年资金投入与产值比(100∶438)进行反向推算,在刨去上一年年末仍占用银行贷款(5000万元)、企业自有流动资金(6500万元)以及在1985年1月至3月筹得社会资金(2700万元)后,作出决定,要求全县乡镇企业通过各种办法筹集1亿元生产资金,以达成年初设定的产值增长目标(此份材料以“10亿”目标值计算——笔者注)。当然,除了政府行政命令外,不少乡镇企业自身也因前期启动项目处于骑虎难下状态而急需向外筹集资金。[注]具体企业案例可参见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各公司、区、乡(镇)工业办公室1985年度工作总结报告》(1985年1月至12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49。
很遗憾,在笔者可查见的原始资料中,并没有材料就这1亿元资金筹集工作的后续进展作确切说明,具体途径或完成与否都不得而知。但梳理上述在1月至3月所完成的2700万元资金募集渠道,我们便可发现“内外集资”(1000万元)与“联营引资”(1020万元)是企业筹集外部资金的主要方式,分别占到总数的37%与38%,而通过“预收货款”(211万元)、“催讨应收款”(236万元)及“职工储蓄”(223万元)渠道获得的资金数量有限(另有10万元标为“其他”)[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乡镇企业简报》第8期(1985年4月1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48。。具体分析,所谓“内外集资”,即对内鼓励职工带资入股,对外发放社会性集资债券、股票,该办法主要针对新办企业,募集对象多为个人;所谓“联营引资”,对象则是生产经营组织,即联合对方单位以组织形式注资乡镇企业,实现联营发展。进行前后时段比较,在资金问题爆发前,地方政府也鼓励乡镇企业向外寻找联营单位,但目的在于寻求技术或生产设备联合,对象多为高校、科研机构或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城市工业企业,而此时再谈联营,目的就是为了引资。
在当时整体资金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除少数原本已有合作意向的外部企业(多为上海配套生产单位)外,能为这类乡(镇)、村办企业提供现金支持的恰恰是当地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主。由于后期历经合并、转让或其他形式改革,企业档案大多已流失,很难再对具体联营过程作细察。但据原地方管理干部回忆,当时各厂主要通过摊派形式筹集资金,与其业务联系越多的配套加工厂,越会被要求“入股”,而那些原本便是从集体企业出走开厂的经济能人,但凡经营状况尚可,都会被要求“入大股”。一些乡(镇)办企业与入股者确定了分红比例,而村办企业,大多由于自身规模有限,也很难确切区分谁为主、谁为客。[注]笔者对原慈溪县二轻工业局局长的访谈记录,2012年2月4日;笔者对参加慈溪市经信局退休老干部联谊座谈会老干部的集体访谈记录,2012年2月6日。
相互混合且又模糊的联营形式弱化了原本集体所有企业与家庭作坊、工场的组织区隔。有意思的是,相比其他时期,在推行联营形式阶段,当地很少有人细究这一形式对于集体所有制、集体资产可能产生的影响,管理干部更是认为这一形式整合了地区内个体经营者资产,使集体所有的资产构成多元化。对于那些入股的个体经营者而言,虽然大多并不看好这一发展模式,但也少有人顾及联营后个人资产或入股资本的归属问题,毕竟集体所有的“红帽”对他们意味着更为安全的政治身份。这是发生于1985年至1986年间的社会事实,此时地区内已有部分乡(镇)、村办集体企业接受了租赁、转让,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转制还未到来。
四、乡财政的建立与乡(镇)、村办企业的整体管理弱化
如上文所述,至80年代中期,慈溪县乡(镇)、村办企业的经济发展已陷入困境,对于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整改以及自1985年起鼓励企业与家庭工业等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联营,都可被视为管理部门对于这类企业的坚持,即无论现实发展有多大困难都要尽可能保留这类集体所有乡镇企业,保证其在“四轮经济”中的主导位置。然而,这一管理态度在1987年发生了明显变化,曾被上级部门严令禁止的“一脚踢”承包形式在基层重新盛行。作为具体企业的发包管理方,乡(镇)、村以及该层级的部分事业管理部门都有意无意地放任对于所负责发包企业的管理职责,许多村办企业被一卖了之。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是影响管理部门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但这一转变之所以在1987年集中发生,这与当地在1986年建立乡财政体系的做法有直接联系。
作为地方“四轮经济”中的一轮,乡镇企业发展式微自然对地方财政产生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财政对此类财税的依赖有所降低。1985年,浙江省下达慈溪县财政收入要求10200万元,其中企业税、工商税分别为1150万元、8065万元[注]中共慈溪县委:《县委会议记录》(1985年3月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7-001。。1986年,国家整体税收任务增加60亿元,其中工商税任务增加近40亿元,浙江省、宁波市逐级分包税收增缴任务,落到慈溪县,单就工商税需要增缴250万元,全年共计需要完成税收12600万元。对此,县内再作分项目核定,计划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1494万元,这一目标数值是1985年实际收入(807万元)的1.85倍。[注]中共慈溪县委:《1986年1—8月(税收)计划完成情况讨论会记录》(1986年9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8-002。很显然,就当时企业发展状况,地方政府要完成这一税收要求,难度极大。但在当时,浙江省财政厅曾向地方县(市)透露过国家1988年财税体制改革意向,明示相应改革可能以各地1986年财税(地方包干及“三税”)的实际完成数额为基数,核定日后年度可用资金规模。受这一消息刺激,慈溪县委、县政府确定以“多收多支”作为1986年年度财税工作的核心原则,并就计划任务的完成下达了死命令。[注]慈溪县人民政府:《县长会议记录》(1986年7月1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8-002。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慈溪县财税着手推进地区乡财政体系建设,改变过去县乡财税统收统支做法,确定新的“划分收支、核定基数、收支挂钩、一年一定”财税原则,以调动乡(镇)一级干部对于本地区税收工作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慈溪县在1984年初便曾尝试过乡财政试点,但因各乡干部积极性不高不了了之。此时全县再推乡财政体系建设,县委、县政府态度坚决,对于基层干部的消极态度未作任何让步。
若仅考虑税源的划分,在确立独立一级财税关系后,乡(镇)、村办企业的税费被划为乡财政收入,乡(镇)理应更为关注对此类企业的承包管理,严格要求企业承包者足额、及时完成税收及管理费上缴[注]慈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乡(镇)财政的暂行规定》(1986年[27]号文),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8-017。。但当我们了解了乡财政建立后就地区内“预算外”“自筹资金”管理办法所作调整,便能理解为何乡(镇)、村及具体企业发包管理单位会弱化对于所发包企业的管理,甚至主动对其予以转让、拍卖处理。
在过去,就乡(镇)“预算外”“自筹资金”的管理一直是慈溪县县级财政部门的软肋,管理实权有限。以当地横河区为例,该区在1985年获得县财政下拨预算资金共计104万元,而“预算外”“自筹资金”收入高达133.6万元,占到总收入的56.2%(对应预算外支出同样占总支出的50.5%)[注]慈溪县横河区人民政府:《在乡财政会议上的发言》(1987年4月2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9-098。。在县乡统收统支财政模式下,县财政很难完全掌握下属各乡镇每年“预算外”“自筹资金”的实际规模与具体用途,虽有意识地压缩下拨预算内资金额度,但面对下级部门“凡事伸手向上要财政补助”的局面,县财政也难以完全拒绝,导致自身承受较大压力。新的县乡财政关系确立后,县财政局第一时间向各乡镇下派任务,要求其就具体收入数额予以包干,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便是对各乡镇“预算外”“自筹资金”予以整体排摸。按照县财政局报告数据显示,1986年总计核实各乡镇“预算外”“自筹资金”1162.6万元,与当年预算内可用资金1158.4万元基本相当。对这部分资金,县财政并不作上缴要求,而是要求各乡镇财政予以透明化管理,与预算内资金统筹使用。[注]慈溪县人民政府:《关于198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讨论会记录》(1986年10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9-001。然而,即便如此,在乡镇干部看来,“家底”实则已完全暴露,日后不仅没有了向上申请财政补助的理由,乡镇内部也很难再以此进行奖金发放、额外投资或转移支付,乡级政府被迫承受上级财政压力。
面对这一变化,乡镇干部同样选择压力下移,不仅要求乡工业管理办公室即刻确定区域内各类企业的财税包干任务,更要求对本地区各部门、事业单位“预算外”“自筹资金”予以逐一清理,就这部分资金实现乡财政整合。以当地付海乡、石堰乡、天元镇、浒山镇为例,在乡财政建立后,乡镇政府大多只允许地区多种经营办公室保留信用社独立账户,诸如农科站、水利办、土地管理办、社会救助办、卫生院、汽车站、文化站、计生办等各类事业单位原有信用社专项存款账户均被取消,账内资金一律上缴乡财政,不允许再设“小金库”。[注]《全县乡(镇)财政会议上与会代表发言》(1987年4月2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39-098。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这类事业单位与所在地区乡(镇)、村办企业实则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数企业在创办初期便是相应单位的副业或三产车间。在承包责任制管理模式下,这类事业单位多作为乡镇集体的代表,负责具体企业的发包管理工作,所谓“小金库”即“自筹资金”,主要也来自于所负责发包管理企业税费的部分截留。到如今,这些单位(部门)纷纷抱怨“挣钱难”“自己挣来的钱不能自己花”,对于发包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受挫。
就这一问题,乡(镇)、村办企业同时存在,但其中尤以村办企业表现得最突出。在一份关于“一包五改”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明确指出“村办企业承包管理不力”,对当地长河镇、观城镇作了重点批评,指出两地村办企业承包多是“包盈不包亏”“只奖不赔,奖易罚难”,或简单采用“一脚踢”承包形式,对被承包企业的管理工作完全放任自流,大量村办企业严重亏损[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关于全县乡镇企业“一包五改”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8月20日),《1987年工作总结和1988年工作意见》(1988年1月2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23、063-013-002。。在就全市乡镇企业承包问题的讨论中,宁波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同样以慈溪县胜西乡作为反面例子,指出当地集体企业承包存在大量短期行为,在缺少有效管理特别是财务审计制度的情况下,承包者多贪图眼前利益,为谋取额外奖金收益弄虚作假、滥报虚利,而管理部门只关心所得税征缴,完全不顾企业自身发展,“办厂却不养厂”问题严重。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大量村办企业负债累累,亏损倒闭。[注]宁波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查组:《关于全市乡镇企业三年来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11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50。汇总众多汇报性质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况并非一乡一镇之个例,整个宁波市乃至浙江省在当时都受到类似问题困扰。
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整体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理念,针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四制”改革意见(经营承包责任制、厂长任期目标制、股份制、租赁制)很大程度影响了地方干部对乡镇企业经营管理的认识,认为国企改革已走在乡镇企业前面,乡镇企业管理部门不能再墨守成规,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强调在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应对微利、亏损企业采取租赁承包、合伙承包或个人承包,对那些濒临倒闭企业,允许予以转让或拍卖[注]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关于完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几点意见》(1986年11月10日),许行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在全省乡镇企业工业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6日),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1987年任务和要求》(1987年1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1-096、063-012-050、063-011-002。。1987年6月底,慈溪县就全县2430家乡镇企业完成“一包五改”工作情况作调查,发现其中仍坚持“以厂长为主集体承包”形式的企业1340家,承包给个人或由个人合伙承包的企业940家,另有110家企业已被转让或租赁[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关于全县乡镇企业“一包五改”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8月2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23。。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曾有中央文件专门指示“合伙或个人承包形式并不改变乡镇企业集体所有性质,地方政府将其视为个体企业并予以相应政策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注]农牧渔业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乡村集体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意见》(1987年7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50。,但事实上这类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且很难依靠政策规定予以行政化纠正。到了1988年,整个市场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前期看似活跃的商品市场实则是通胀压力下群众持币抢购的市场乱象,产品价格涨落不定且滞销风险剧增,乡镇企业面临继1985年银行贷款收紧后的第二次整体性危机。在这一情形下,慈溪地方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已不再就集体所有形式予以更多坚持,而是直接讨论产权转让问题,在已有个人承包、合伙承包、转让及租赁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口径,允许并鼓励对微利、亏损企业进行拍卖,且明确表示相应拍卖“既可以卖给其他乡镇企业,也可以卖给个体户”,强调这种出卖或转让并非“败国家、集体家产,而是变‘死钱’为‘活钱’”[注]谢建邦:《明确目标,落实措施,努力完成今年我县各项工作任务》(1988年1月14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38-019。。
基于后期各乡(镇)提交的分析报告,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末,慈溪当地在名义上仍被称为“乡镇集体企业”的企业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实行传统厂长负责下集体承包责任制企业,这类企业数量最少。第二种是实行厂长个人承包责任制企业,其中又分两种:1987年前建立的企业,一般都将企业动产拍卖给个人,不动产予以集体承包;而之后兴办的企业,由于采用联营形式,创办之初大部分资产投入即来自个人,因此承包基数较低,只按销售额的1%至2%征缴费用,其他一律不管,即通常讲的“一脚踢”承包。第三种便是“挂牌”企业,大部分是集体企业倒闭后经转让、拍卖给个人,但仍保留集体牌子,也有部分是个人办企业挂集体牌子,两者都不承担集体企业义务,只向所挂牌集体上交固定费用。[注]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对“挂牌”集体企业和“一脚踢”承包企业引导管理的若干意见》(1991年12月3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41-189。虽然各乡镇三种类型“集体企业”的构成比例不尽相同,但后两者合计比例一般都已占到所在地区企业总数的70%以上[注]慈溪市周巷区、三管乡、逍林镇、雁门乡(干部代表):《在全市进一步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动员会上的发言》(1991年12月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41-173。。
五、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与实际结果
在了解上述发展变化事实后,我们最后分析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股份制改革”对于乡镇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股份制改革是乡镇集体企业所有制变化的形式路径,且强调地方经济精英(企业经营者)的崛起左右了整个改革过程,理由在于很多接受股改的企业在随后即出现股权集中现象,经营者个人(或合伙)凭借资本优势将企业转手变为个体民营企业[注]谭秋成:《乡镇集体企业中经营者持大股:特征及解释》,《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不得不承认,就这一现象,慈溪地区亦是如此。但是,结合历史环境作过程性原因分析,我们便能发现上述解释过于简化事实表现,在当时当地,股份制改革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改革意图与改革结果并非只是受到当事人经济意志与行为的影响,政治环境的变化才是关键性因素。
早在1985年,慈溪地区便有关于进行股份制改革意见的讨论,当时主要为了解决乡镇企业资金不足问题,有意引导地区农民及企业职工将消费资金转为生产资金。此后,股改意见与个人承包、租赁、转让及拍卖意见一同出现,都被视为对国家“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改革理念的实践。但是,与其他处理办法不同,股改对象并非微利、亏损企业,而多是效益相对突出者,由于此类企业接受改革的迫切性并不显著,相应管理部门的工作推进也显得较为迟缓。1987年5月,浙江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召开全省股份制试点座谈会,形成《关于乡(镇)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重点论述改革意义及改革对于传统集体所有制形式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求各县(市)政府将股份制改革作为前期承包责任制的升级,实现企业管理优化。[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关于乡(镇)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1987年5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4-012-050。然而,从慈溪县地方材料看,这份《意见》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地方工作仍旧围绕“一包五改”展开,集中讨论如何制定、落实地区企业第二轮承包方案,或是推进具体企业的租赁、拍卖,其间虽然也有部分企业(40家)试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非是地方政府或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的关注重点。比较前后时段,在这一时期,当地政府多只鼓励新办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筹措创办企业资金,但就已有乡(镇)、村办企业进行股改事宜,仍持迟疑态度,未作政策强调。[注]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1987年工作总结和1988年工作意见》(1988年1月2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3-002。
直到1988年9月,慈溪县召开全县深化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陈仲方(时任慈溪县县委书记)与谢建邦(时任慈溪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分别在会上就前期乡镇企业改革作经验总结,并指出股份制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必然趋势[注]陈仲方、谢建邦:《在全县深化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88年9月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38-085。。10月,徐杏先(时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在全县重点骨干企业工作会议上讲话,分析当时国家宏观降速调控措施的影响,明确表示必须着手对地区内骨干企业施行股份制试点[注]徐杏先:《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促使乡镇企业健康发展》(1988年10月21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3-003。。1989年6月,徐杏先(时任慈溪市副市长)在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上作报告,指出地区乡镇企业已再次陷入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企业发展尤为被动。就资金筹集办法,管理干部不断强调“眼睛向内、向外、向下”,主张“采取挖潜、入股、集资、拆借、引入等多种办法筹集生产资金”。[注]徐杏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稳定发展乡镇企业》(1989年6月),罗士荣(时任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全市乡镇骨干企业工作会议报告》(1989年6月1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4-003。除要求企业“练内功”(增加自身积累)外,管理干部确实把股改视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遗憾的是,此时的股改意向仍未得到落实。由于市场波动及政治风波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在1989年年中出现强烈震荡,慈溪市乡镇企业同样未能幸免,相应产值自5月起连续10个月大幅度下跌,全县企业月产值总额从原来的2.8亿元快速下降至1.77亿元,整体面临“塌方式”危险,再无精力顾及股改工作。[注]罗士荣(时任慈溪市科委主任):《在市级重点骨干企业厂长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10月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5-004。1990年3月,地区经济企稳回升,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考虑的影响,各级政府就股改的目标设定发生微妙变化,不再是为了帮助企业融资,而是强调通过改革整肃前期地区企业所有制乱象,意图通过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整合、统一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差异。不必讳言,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风波的发生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和平演变”等政策的主导下,浙江省各级政府及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被要求必须对辖区内“集体企业受到冲击”现象给予高度重视,并予以彻底纠正。[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许行贯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10月1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40-180。
客观分析,当时这类政策的目标指向并非个体、民营经济,而是强调必须制止集体厂厂长、供销员跳槽或是集体企业“日公夜私”“化公为私”等公私不分现象,批评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此类现象报以无动于衷态度,认为这是大量集体企业在当时几近瓦解的原因所在。政策落实到地方,慈溪市政府的反应相对有所迟缓,但仍旧在1991年12月颁布专项处理意见,要求对地区内“挂牌”及“一脚踢”承包企业进行资产所有权划分。对实际已经为经营者个人占有部分,提出“风险抵押”“赎买转借”或“股份转化”三种处理办法,清理个人资产份额,重新确认、强化该类企业的集体所有属性。[注]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对“挂牌”集体企业和“一脚踢”承包企业引导管理的若干意见》(1991年12月3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41-189。考虑到前两种办法属于资产买断形式,经营者大多选择“股份转化”,即将个人投资与企业集体资产同时核算为股份,并在形式上承诺集体股不低于企业注册资金的50%,以换取地方政府对本企业集体所有性质的认可。与此同时,这类要求自然也连带涉及对个体、民营经济管理的调整。浙江省层面在1991年2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强调合法经营的重要性[注]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管理的通知》(1991年2月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41-191。。遵照这一要求,慈溪市委、市政府对原有“四轮齐驱”[注]“四轮齐驱”是浙江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地区经济所有制形式设定的政策提法。“四轮”指的是国有、地方(政府)所有、乡(镇)村集体所有与个人所有,“四轮齐驱”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参见慈溪县手工业管理局:《慈溪县社队工业情况汇报》(1973年5月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01-003。政策提法作出修正,虽然在名义上依旧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但却开始强调划分主次,严格规定这类企业不得与集体企业争利,并在行政上明确引导个体、私营企业转为集体企业的要求[注]中共慈溪市委、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稳步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89年9月29日),《关于加强个体、私营工业管理的通知》(1991年12月30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39-183、001-041-189。。为妥善处理这一关系变化,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提出“联合投资”意见,即向规模较大的个体、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厂房或设备,而对较为分散的家庭工业采取“股份联营”,目的都是为了赋予这类非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企业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地区改革并未就具体对象进行类型区分,而是统称“股份制”改革,并采取了形式相近的资产核算、股份划定办法。回头来看,许多现实问题在当时被简单化处理,实际所有制差异较大的企业被行政化认定同一身份,并接受统一改革管理,即以股权划定、股权集合的组织形式实现集体与个人资产的组织联合,以“股份合作制”形式为各类实质上的个体、民营经济“戴帽”,规避政策限制。
客观地讲,慈溪市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此类企业“戴帽”,目的是为了保护而非占有个体、私营企业资产。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非公有制经济再次得到肯定,慈溪市政府对于由企业提出的“摘帽”要求予以积极回应,重新承认其个体、私营身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务院批转下发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意图力推基层企业股份制改革[注]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转发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的通知》(1992年5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47-239。。考虑到国家政策的持续性以及整体改革对于股份制形式的极力推崇,慈溪市委、市政府会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就地区内规模较大“戴帽”企业给出另外处理意见,要求“原来实行合伙、合股或联营企业,已‘升格’(意指前期‘戴帽’——引者注)为乡镇办集体企业的,现企业有要求,可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关于1992年乡镇企业工作总结及1993年乡镇企业工作思路》(1993年1月13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02。。换言之,地方政府希望这类企业能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改,加速企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为鼓励这类企业接受股改意见,慈溪市政府作出各种努力。陈冠群(时任慈溪市副市长)在改革会上多次表态,强调“改革的目标方向并非严格意义上股份有限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而是相对宽松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注]陈冠群:《在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7月6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28-003。。在一些企业的股改促进会上,乡镇政府更是承诺不就企业“集体股”提分红要求,企业只需缴纳税费即可,并主动表示愿意在合作期满后退出股份,不强行要求续约[注]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2期,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35。。种种承诺都是为了宽慰这类企业经营者,扩大股改辐射面。相较于上述优惠条件,慈溪市的政策倾斜更直接表现为对相应股权设定的地方性调整。不同于浙江省作“乡(镇)村公股”“企业集体股”“职工股”设定[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关于乡(镇)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若干意见》(1987年5月15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2-050。,慈溪市就“职工股”再作类型拆分,分设为“职工劳动积累股”与“个人股”,前者针对职工群体,以职工劳动贡献大小核定个人购买股份资格,而后者则无类似要求,虽然名义上可供任何人购买,但实则却是专门为企业经营者所设,并允许其将先前投入资本核为股份,或另称之为“法人股”[注]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1期,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35。。毫无疑问,相比浙江省层面的政策设定,慈溪地区股改政策更利于个体经营者,对应于当地政府“鼓励‘戴帽’企业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政策初衷。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地区企业股改多表现为经营者个人出资购股。以当地一个塑料加工厂改革为例,该厂股改核定资产总额152万元,镇政府承诺出资76万元购买“镇集体股”(其中以厂房抵扣股金33万元),其余76万元原则上应包括“企业职工集体股”“个人股”及“社会法人股”,但实则都由厂长一人承担,且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改文书对外只是笼统告知:由厂长个人负责统筹募集股金。[注]《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2期,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35。事实上,在各家企业的股改案卷中,很少见到职工集体或个人出资购买股份的记录,相反却是多见职工接受一次性补偿清退案例,股改后仍旧留在企业者也多由“固定用工制”改为“雇佣制”。在个别允许职工购股的企业中,依然是领导购股占据绝对多数(60%至70%),其次是中层干部或骨干职工股(15%至20%),普通职工群体购股比例一般不超过10%。[注]慈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巡回指导组编:《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3期,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35。对于这类现象,地方改革巡视组不仅了解且予以肯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通过清退补偿工作,既为企业重组甩掉包袱,也为转制铺平道路。”[注]《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简报》第2期,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8-035。在可查见的企业改革案例中,三年股份合作期满后,那些名义上划为乡镇资本的集体股权一般都以较低价格完成交割,其中一些乡镇也会就企业股份合作期间享受的税费优惠提出折现要求,要求企业予以现金偿还[注]边福春(时任慈溪市周巷镇副镇长):《在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上的发言稿整理》(1993年7月10日),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主编:《乡镇企业简报》第8期(1985年4月12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10-048。。考虑到前期投资大多属于“戴帽”性质行为,乡镇在折现过程中的损失实则较为有限,反而借助这一方式盘活了地区内原有固定资产,增加了现金收入;而企业经营者更是乐于接受现金折抵,从而将企业完全纳入个人名下,不再受前期所谓集体所有名义的困扰。
必须承认,由于“戴帽”行为的隐秘性,笔者并不能依据档案文本记录区分具体企业的真实性质,也很难准确判断“戴帽”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在股改企业总数中的各自占比。但是,毫无疑问,就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前者对于后者产生了明显示范效应,个人占多数股、个人控股很快成为地区股改的主导趋势。数据显示,在慈溪市接受股改企业的总体中,1993年“个人股权”仅占总股本的38.2%,一年后便升至72.8%;1994年共有214家企业完成股改,其中“集体股权”占比超过“个人股权”的企业数量快速减少,个人不仅控股,而且占据绝对多数股[注]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一九九四年乡镇企业管理工作总结与下一年乡镇企业工作思路》(1995年1月),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3-020-002。。“直接转私”现象在当时大量存在,地方管理部门虽强调予以监管、纠正,但实际未能落实[注]《九五年慈溪乡镇企业工作目标和大体思路》,《慈溪乡镇企业报》1995年1月10日。。加之地方政府在此期间进一步加大租赁、兼并及拍卖工作力度,接受此类转制形式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1994年年末,被租赁、拍卖及转让企业分别有820家、286家、22家,虽然仍有720家企业沿用传统承包责任制形式,但由于经济能人大多已出走而发展艰难;1995年上半年,仅仅通过拍卖形式转为个体、私营企业的便有78家,集体所有企业数量快速减少,仅存企业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注]建国:《九四年转制回眸》,《慈溪乡镇企业报》1995年3月10日;《上半年乡镇企业转制情况》,《慈溪乡镇企业报》1995年7月25日。。到了这一阶段,慈溪市政府虽然在政策宣传层面仍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但此时所谓“公有制经济”更多指向地方国营企业或大集体二轻企业,对于原有乡(镇)、村办企业的集体所有性质实则已不作强调,而是将其视为地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构成主体。
毫无疑问,在宏观的改革制度设计层面,股份制形式曾被寄予厚望。一方面,这一制度的资本集合及权利分配形式对应于市场化发展要求,体现了改革意志;另一方面,集合形式本身又带有集体所有色彩,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要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社会“集体所有制”对于市场环境所作的现代化适应与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地方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段实现股份制改革缺少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具体矛盾并未得到完全消化,股份制的制度意义被忽视,而形式化改革的结果只是肯定了资本的价值,既承认了早期“一脚踢”承包或“挂牌”企业的个人私有性质,同时也将当时仅存的部分乡镇集体企业转为了个体(或合伙)资本所有,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步入民营主导格局。
六、余 论
本文写作的价值立场,即通篇论述并不偏向于集体所有制或是对转制现象持有类似“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批评意见,对于慈溪地区家庭工业、联户经营企业主,笔者报以由衷敬意,正是后者的努力为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得慈溪市能够多年在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中位于前列。摆脱好恶判断的影响,理性分析这一过程变化,讨论乡镇集体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与所有制转制,意义在于回应中国社会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处理坚持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在制度设计层面与具体实践层面的异同性。
毫无疑问,坚持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两者辩证统一,相互整合。邓小平在80年代末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多次讲话,都有强调这一点,明确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诚然,之所以需要反复强调,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各主体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即使是政府行政管理干部在很多现实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也难以做到知行合一。本文就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与所有制转制过程的讨论,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微观实证。
举例来看,在前文中关于“承包责任制”制度的讨论部分,笔者详细论述了该制度设计与管理效果相悖的社会现象。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一现象实则反映了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性提升后的必然矛盾。回到档案文书的记录话语,在前期诸多关于推进社队企业“责任制”改革的工作会上,基层各级干部习惯于强调“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关系”,认为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三者之间能够实现“国家多收、集体多留、职工多得”的发展愿景;而到了“承包责任制”阶段,相应表述整体变为“处理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四者之间关系”,“集体”概念不再涵盖社队企业,换言之,所谓“集体多留”到底留给谁成了问题。如果单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分析,将企业从“集体”中剥离,确立其独立的组织身份,这是相应管理制度进步的表现;但是,从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一关系变化使得地方管理部门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必须贯彻改革意志,对于企业经营予以放权处理,但在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防这类企业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或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已经部分摆脱了过去斗争思维的限制,但是县管理部门或社队干部在当时仍旧难以完全接受企业或企业承包者个人(团队)多分、多占企业利润的行为。既要“放权”但又要避免“失权”,这便使得地方管理部门及社队更倾向于对企业利润采取“多收多支”办法,既向企业自下而上地收缴更多利润、税收,同时又通过政策资源返利形式(如税费减免、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自上而下地回馈乡镇企业,让这类集体所有企业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拥有更多行政资源支持优势。
这一管理模式在原有的计划体系下,或许可行,但在市场环境中却难以发挥效用。市场及其他外部要素不断变化,作为管理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很难完全根据上级或自身意志行动;但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管理部门却又仍旧无法摆脱诸如财政税收、地方工业产值等硬性指标的数字化管理要求,加之转型过程中最终指向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些直接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地方干部尤其是开展具体工作的办事人员实则很难作出决断,要么对政策执行予以敷衍,要么便是一味加码以确保自身的政治安全,基层改革往往因此陷于被动。
当然,慈溪地区乡(镇)、村办集体工业的消解以及同时期以家庭工业、联户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是成功的。这与国家整体明确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是受益于改革过程中相对公平的机会获得环境。笔者自2009年至2013年多次赴慈溪调研,除了在前期集中查阅相应档案及地区文史资料,还有意识地走访了当地大部分乡(镇)、村,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接触、访谈了50余名当地居民,其中既包括较大规模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县(市)级与乡镇级干部,也有开办家庭作坊、工场的个体户,还有普通务工村民。在这些访谈对象的记忆中,他们的确认为乡(镇)、村办集体企业转制存在“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利益受损的最大主体即是普通职工,不仅失去了原有“固定用工制”的稳定性优势,更因为基本未能获得企业股份丧失了就企业所有资产、年度收益主张分红的权利。但是,在这些受访者看来,集体厂倒闭、转厂与家庭企业的兴起是改革作用下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允许个人办厂的大环境下,乡(镇)、村民实则都有共识,即认为“最有能力者吃肉,次之喝汤,再不济者啃骨头,没饭吃者最无能”。因此,慈溪地区在乡镇集体企业转制过程中并未见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各个家庭工业、联户企业得以兴起的情况下,因集体企业关停而被影响的职工工资及用工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稳妥处理[注]慈溪市人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记录》(1992年1月30日至2月1日),慈溪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0-047-001。。毫无疑问,这是改革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亦是改革在基层社会得以普遍推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