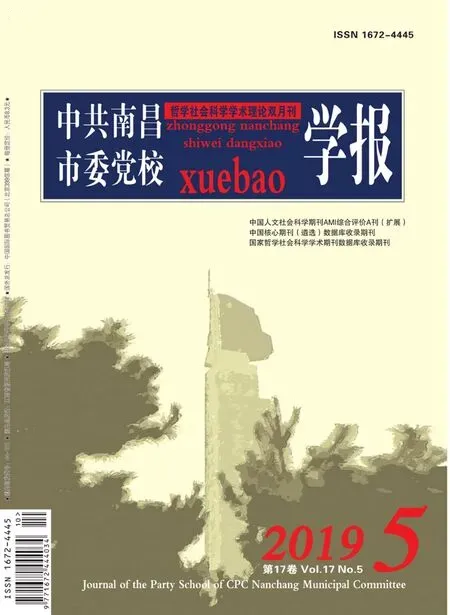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约束及应对
吴 昌
(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浙江 临安 311300)
观察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过去的社会精英经常抱怨农民不会利用时间。他们觉得农民的生活懒散,无组织无纪律”[1](P93)。然而,现代中国社会,无论是广大的农民还是市民,毫无例外地触碰和接受了现代社会时间,接受了一种新的时间纪律、作息时间及基于时间而形成的权力,“时间开始变得重要,变得有价,已成为要进行合理安排、有效管理的对象”。“有了时间这个新管家,人们开始变得不那么自在了,生活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由了”[2](P109)。人们不仅主动参与,也常被有序的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务。
近年来的社会治理中,无论是参与度还是参与面,群众逐渐被有序动员起来,参与形式与内容不断创新,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时间约束问题,即时间对人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一种显而易见又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经常感到时间的缺乏”,“时间资源稀缺化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并对社会治理构成挑战”[3](P31)。尽管社会治理中已认识到时间要素,如基层减负就试图让人从耗时的形式主义中抽身出来,但仍需进一步梳理和分析时间约束问题的表现及根本所在,并寻求应对措施,以更好地推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一、现代社会时间与时间约束的产生
传统乡村社会,民众的生活是基于自然作物生长的节律性时间的安排,“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这体现出的正是传统乡村民众对于时间的年度安排策略”[4](P65)。这是由传统农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决定的。时间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慢、重复、日夜交替、季节转换、年复一年等,时间虽可被测量,但早一点迟一点并不会有很大影响。
进入到现代社会,人与时间的联系逐渐被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时间所影响甚至取代。较之于空间,时间的隐蔽性特征淡化,时间能够被发现、感知和利用的手段也越来越高超。时间从原有的自然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以被社会切割和科学计量的单位,并需要精确到分秒,可被量化、比较。最为明显的就是“工作时间”“时间表”“分秒”等的广泛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时间意识的出现,如“时间就是金钱”。这种“新的时间观念搅动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在一系列连续反应、深刻变革以后,一个全新的快速率、有节奏的生活图景即将庄严地展现”[5](P159)。当然,传统自然时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从某种程度上看,“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可以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间都更为复杂”,“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产生的异化,实际上都是立足于时间本身。”[6](P7)。
明确可度量的时间及时间意识的出现让时间成为一种可以被利用、分配的资源。人们习惯性地根据精确化的时间来安排生活,也常常被精确化、制度化、程序化地安排各种事务,或对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利用,也成为可以衡量和评价的标准,例如考勤制度的出现和普遍化使用。时间作为一种资源,驱使着人不断对时间进行开发与利用,追求更多的时间,追求时间效率最大化,却导致更多事务被安置于新的时间中,新的时间被再次占用。如此循环往复,人无法摆脱其中。有人也许会说,人完全可以回归到自然生活状态中去,但处于高度组织化和社会化的人,要真正实现这样并非易事。现实中,时间越来越多,却又越来越少;社会和科技加速发展,人却越来越繁忙。
事实上,高节奏和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时间稀缺不仅仅是自我生活的安排造成的,也常常是被组织化的生活所左右和导致。时间可以利用、分配和调整,这也就意味着,人可以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重新规划时间,偶然性的时间可以随时嵌入到既定的时间计划之中。而这种调整必然会出现新的时间安排,时间在量的层面被扩大,但也伴随着高节奏和加速化,人被时间所左右,人的时间被挤占就是后果之一。生活时间被社会时间所挤占,如互联网文化中“996”的提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稳定的日常活动可以被修改、嵌入、重新调整,甚至是完全推翻。由此,不免会造成人身心上的焦虑、疲惫和忙碌。更为严重的,是个人的时间被剥夺和对人的奴役成为一种常态化甚至是制度化的现象,个体所代表的组织也无法置身其外。就比如高节奏时间中抑郁症、敷衍、消极、疲劳等现象和问题的出现,人无法自主,难以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时间成了人的痴想。个体或组织受时间约束的普遍表现就是:没有时间、时间有限、时间不一致。
时间约束问题随着加速化、高节奏、稀缺化的社会时间的出现越来越明显、细化。症结就在于,“现代时间是抽离生命的量化时间,是远离生活的均质时间,是疏离具体的抽象时间”,“社会生活的抽象即是现代性的突出表现,也构成了生命时间与现代时间的现代冲突”[7](P90)。
二、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约束问题
到了20 世纪后期,时间问题越来越明显,这必然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各个方面的管理造成冲击”[8](P102)。显然,社会时间取代自然时间,尤其是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和细化的当下,社会治理很难以固定不变的形式存在,需要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加以应对。
显然,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有时间的要求,即使是整个民主制的运行(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也是要有时间要求的。公共政策是一项重要事业,它需要时间、审慎的思考,需要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及使自己的意见被听取的机会,以及尊重他人观点的态度。[9](P19)与个体受到现代社会时间约束如出一辙,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时间视域中,同样会出现以加速化、高节奏、稀缺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时间所带来的问题。现实民主运行中,群众也确实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改革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10](P46)。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时间约束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能被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的人数和范围的有限。社会高度分工和时间差异化决定了不同群体无论是时间上、精力上还是专业程度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和高低之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有限的时间和时间资源的稀缺也决定了群众难以有时间去深究和权衡政策的利弊、可行性和正当性。这显然不仅仅是知识上的约束,更是时间约束带来的问题。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对于政府部门、组织和团体,要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必须考虑到时间约束问题。进一步看,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需要付出时间代价的,而时间的稀缺和差异,也就难免造成乐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际人数和群体范围的有限。即使是乐意参与社会治理,只要时间允许,群众也必须要考虑和面对时间约束问题。因为政府机构本身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给予自身所允许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变化的。就比如工作完成进度背后潜在的“奖惩”。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和更高效率的参与社会治理的事务必须不是很紧迫的,而且至少可以根据既有的经验和知识去应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较之于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者,事务的紧迫性影响了治理过程中能否让更多的人和不同群体加入其中,广大群众在处理和应对事务所要付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并存在差异化的。随着社会分工、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群体差异的扩大,群众能够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是未知的。至少群众自身所需要花费时间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势,而这无疑是更耗费精力的。即使是借助更为先进的技术和进步的制度手段也是如此,因为这本身也需要时间的付出。从时间约束角度看,民主赋予民众权利,但平等参与是有条件的,平等也不代表着意愿,而“当前基层群众自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群众的参与动力不足,热情不够,甚至出现参与冷漠”[11]。
我们仍需看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中时间约束的另一面,即群众是否自愿和乐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于其中。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社会治理就很难有满意的结局,它所能达成的目标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动员群众社会治理所利用的时间不当或耗费的时间过多,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就会产生新的时间约束和时间担忧。真正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众的多少,事务的实现程度会怎样都是未知的。例如,出于群众动员的需要,各种调研层层包围下的群众包括政府部门自身,能有多大精力和时间去完成是有差异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常常会被量化、仪式化、形式化,因为大家都很忙,就如动员能开到什么程度是未知的,我们进行了多少次的动员,我们如何开展了动员,最为明显的就是形式主义问题仍然存在,群众及动员本身很容易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看客。至于下一次的动员是否还能达到之前的效果就不可而知了,群众动员甚至会沦为某些群众进行非理性宣泄,出现某种偏离或反其道行之成为社会治理对象,成为社会治理所要担忧和直接面临的问题。例如,“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如何让互联网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的得力助手,而非扰乱社会、传播谣言的反面推手,需要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着力解决‘船’和‘桥’的问题。”[12](P74)
总之,差异化的时间和群体,让大家很难步调一致,及时、共时、随时地参与社会治理。随着社会加速化的发展和高度的分工化,面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作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方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更多。
三、时间约束下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应对
事实上,现代社会治理中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并采取了行动。例如,社会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出现和完善,网络咨政平台的出现和利用,但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时间约束问题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社会整体结构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时间约束问题将长期存在。对时间约束问题的有效回应,理应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
1.首先需要注意时间合理性。现实中,政府部门所期望动员的时间与群众所希望被动员的时间不一定是一致的,由此可能会出现如同座谈会人员的缺席或较为重要的人员不在场的现象。尽管政府部门非常注重时间的安排,但更多以自身需要考虑,而不是以被组织者对象的时间设定。从趋势上看,社会时间的开发造成了时间的稀缺,但这无疑提供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思路。这里的开发并不是要将更多的事务安排于新的社会时间中,而是在既有的社会时间中重新安排,需要我们在安排前,多听取群众的意见,能够深入到群众去,发现时间一致的最大化。这需要耗费时间,但无疑是必要的。
2.要注意置于时间中的群众的意愿。现实中,我们往往以时间纪律等行政性的措施,利用群众的工作时间,这也是较为普遍的,当然也包括生活时间的利用。这无疑会打乱群众既有的时间秩序,尽管事先会告知,但仍无法改变群众对时间调整可能产生的心里压力甚至是不满。因此,需要深入群众,分析群众时间安排调整的意愿度,这也是实现时间一致化必不可少的。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事务安排更容易发挥出实效,让时间利用真正有效。
3.要注意时间利用的多样化和灵活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并不应有标准化、固定化的模式去操作和衡量。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我们不能期望群众在我们所期望的时间内就达成,而是要允许群众有更多的、灵活的和自由的时间去参与。这一种随时随地自发的参与也更多的能给人轻松愉悦,也更容易形成一种自觉,以及超出期望的预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群众自发地根据自我时间进行的卫生清理行为。
4.要有一定的时间保障。这种保障是制度上的安排,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群众本身都是需要的。由于时间稀缺,大家的时间有限,因此,任何时间都不应该被浪费。构建时间保障制度,合理安排好时间,使得大家可以耐心、仔细地去解释、讨论,从而不会影响到个人生活时间,大家就会乐于其中。基层减负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对这一时间约束的有效回应。
5.要构建便捷、及时、有效的平台。就目前技术条件和制度政策看,网络平台是最为可行的。当然将网络纳入到社会治理仍需要耗费时间,但从群众利益上、政府操作性上、时间利用上看都是传统社会治理所不能及的。关键是以网络平台开展社会治理,仍要仔细考虑、分析和优化时间问题。比如,这种及时性的现代化的时间运用方式多大程度上将群众动员起来,群众动员起来后如何再组织等问题。因此,网络平台的优化利用之外,需要结合其他方式以动员群众。
6.要考虑时间价值。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群众多大程度上能被动员起来,利益因素不得不重视。如果动员起来参与的事务是关乎自身的,群众的积极性普遍会高于其他事务。但由于时间如此稀缺和宝贵,即使关涉自身,群众也有可能难以被动员起来。因此,这需要发挥出时间的价值功能。同时,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时间的科学规划、有效利用和分配,将有限的时间用到关键之处,能精准时间,提高效率。
总之,如果说现代社会治理重新发现了群众的价值,那么现代社会时间问题应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高度发展和分工细化,“现代时间所包含的现代劳动时间与人体生命时间的矛盾,成为现代性深层矛盾之一”[13](P28)。当我们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时间视域中,会发现以加速化、高节奏、稀缺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时间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时间约束着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和限度。实际上,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日益超出单向度组织尤其是官僚制的能力边界,通过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多方协作的供给模式已经在各个行政层级的服务供给中展开。由此,正视和有效回应对于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诚然,现代社会时间仍将并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和组织,但在找到这其中的缘由之后我们仍可以以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也必然能够进一步优化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