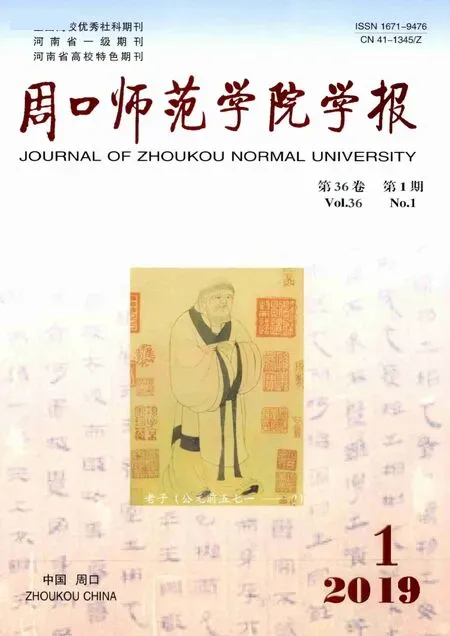孙鑛《评王弼注老子》研究
王福琳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孙鑛(1543-1613),字文融,初号越峰,中年更号月峰,别署月峰主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调礼部主客。后因抗倭有功,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人称“大司马孙公”。孙鑛最重要的贡献当属在文学评点领域的成就。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孙月峰先生批评礼记》卷首所附的《孙月峰评书目录》等文献记载,其评点总数多达60余部,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部类。明人张岱在《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中说道:“孙月峰鑛,精于举业,博学多闻。其所评骘经、史、子、集,俱首尾详评,工书媚点,仿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无一字潦草。”[1]张岱肯定了孙鑛高超的文学修养以及鲜明的评点特色,其评价可谓十分公允。
孙鑛《评王弼注老子》卷首录有熊克《道德经序》、河上公《老子道德经序》、晁说之《旧跋》以及《老子道德经音义》《老子河上公章句篇目》,正文根据王弼注本《老子》在眉栏进行评点,其中征引严遵、苏辙、陶望龄、杨慎、徐学谟、薛蕙、唐顺之等人之语,言简意赅。较之孙鑛的其他评点,《评王弼注老子》较少从字句章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侧重于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审视《老子》,注重对艺术风格的把握,概括艺术特色及其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从审美感受中体味行文之法。
一、峭:评《老子》章法
受复古运动影响,明代更多人认识到文学创作有不变之“法”,无论是秦汉派还是唐宋派,都试图取法于前人作品,以古人之法指导文章写作。孙鑛更是吸收秦汉、唐宋两派的文法理论,形成自己的文章观念,并借助评点的方式加以体现。故而,孙鑛评文时十分注重文法,但不同于对《尚书》《礼记》《左传》等作品字句篇章之法的直接分析,评点《老子》时更多从审美特征入手,通过审美特征反观文法的运用。因此,在《评王弼注老子》中,孙鑛少有“字法”“句法”“章法”的直接标注,而是运用“峭”“奥”“幽”“邃”等带有审美特征的字词表达审美感受,从侧面揭示《老子》文章之法的高妙。
孙鑛在评点过程中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学审美标准,即“雄肆质陗”与“精腴简奥”。他在《与李于田论文书》一文中说道:“弟四十以前大约唯枕籍班、马,以雄肆质陗为工。丁亥以后玩味诸经,乃知文章要领惟在法,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2]191翻阅孙鑛的评点著作,虽然因文本本身行文特点的差异,在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在总体上孙鑛始终以“雄肆质陗”和“精腴简奥”为标准审视历代文学作品,品评优劣。
“峭”是孙鑛文学评点中常用的字眼。“峭”,也作“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陖也。凡斗直者曰陗。”[3]“峭”字本指山势斗直险峻之状,也用于人物品评,形容人严肃刚正,后来运用到书法、绘画、文学等方面。孙鑛认为的语言之“峭”多体现在语句简洁而有深味,有言尽而意不尽之感。
孙鑛多从篇章设置的角度探求《老子》篇章之“峭”,如《论德》章有“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句,句式短小而富有张力,文字流畅且不失气势。在孙鑛看来,这正是《老子》之文的闪光点,故而有“语峭而气畅,此老得意处也”[4]487之评价。孙鑛还常常选取带有“峭”的特质的意象来表现《老子》跌宕起伏的行文特点。《益谦》章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在孙鑛看来,老子正是用一连串短小精悍的语句表现“世自与世反”的观念,其文颇具雄峭之气势,这正是“文势如剑剖石”[4]479-480的具体展现。再如《俭武》《偃武》章都涉及用兵的问题,《俭武》章讲到了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并认为像发动战争这样违背“道”的行为必然会招致灭亡,在表述中多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句式,行文颇有气势。《偃武》章承接上章,以礼喻兵,表明反战态度,语言较上章也更为平缓,比喻手法的运用也使得旨意更为深邃,因此,孙鑛认为“此段甚清夷,如陟危峰,忽就平衍”[4]483。除此之外,还有:
前后文字俱奇险,此章悠游闲适,令人泠然而鲜。(评《圣德》章)[4]484
悠畅赞咏,语转欲塞,道如是邪?倏然而来,倏然而止。来似银河,止如铁壁。吾无以名,名之曰玄。(评《虚心》章)[4]479
“剑剖石”“危峰”“铁壁”都是带有明显“峭”特质的意象,孙鑛用这些形象化的语言,表现自己对《老子》“雄肆质陗”文风的推崇。与此同时,孙鑛也看到了“峭”与“夷”的合理安排给《老子》带来在章法构造上的起伏跌宕之审美特质。行文需有波澜起伏,才能引人入胜,正是由于《老子》篇章结构的曲折多变、层层波澜,尤其是急与缓、险与夷的合理安排,才能形成起伏跌宕之美,体现出篇章构法之妙。
对《老子》章法的关注是孙鑛广泛阅读他所规划的“周文”之后的总结,孙鑛在《与吕甥玉绳论诗文书》中说道:
今拟欲祖篇法于《尚书》,间及章、字、句,祖章法于《戴记》、《老子》、三《传》、《国语》,间篇、字、句,祖意志于《易》、《周礼》、《春秋经》,间章、句,不获已,乃两之以《庄》、《策》;其纵而驰也,乃任途于《韩》、《吕》。最后陆沉于马、班,然亦慎言其余矣。执此道以精诣,需之数年或当有悟境也[2]213。
孙鑛主张学习周文之文法,周文数量众多,当从何处下手?在孙鑛看来,篇法结构应当师法《尚书》,章法结构应当师法《戴记》、《老子》、《春秋》三传、《国语》,如何用字应当师法《易经》《周礼》《春秋经》。如果在这些书中都不能悟得真谛,则应当参考《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数年之后应该会有所收获。既然是章法结构的典范,孙鑛在评点中自然不会忽视《老子》的篇章“峭”的美学特质。
篇章之“峭”固然能够增强文章气势,然而刻意追求语之劲峭则难免有矫揉造作之感。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篇》中说道:“孙月峰以纡笔引伸,摇动言中之意,安详有度,自雅作也。乃其晚年论文,批点《考工》《檀弓》《公》《谷》诸书,剔出殊异语以为奇陗,使学者目眩而心荧,则所损者大矣。万历中年杜撰娇涩之恶习,未必不缘此而起。”[5]王夫之认为,孙鑛刻意追求奇峭,使后世学者“目眩而心荧”,引发“杜撰娇涩之恶习”。这正是孙鑛以“峭”评《老》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语言之“峭”少了“法”的约束,则可能导致文学创作走向“纵肆”的误区,少了语言的腴奥之美。孙鑛追求“雄肆质陗”之文风,并非只关注篇章之起伏,同样追求“峭”后的余味,这也就是孙鑛所强调《老子》“精腴简奥”的意蕴美感。
二、腴:评《老子》意蕴
孙鑛在强调章法之“峭”的同时,也不忘追求语言背后的意蕴,用腴奥的语言表达深远意味。如《赞玄》章中孙鑛对《老子》的言说方式进行评点:“至道原无古今,若一句道破,便无意味,故奥衍若此。”[4]476《老子》所讲的“道”无影、无声、无息,是超出人的视觉、听觉、感觉的“混沌物”。它本身又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启示人们通晓古今变化、洞察万物始末。孙鑛认为,老子“指点‘道’妙,依稀欲尽”[4]476,却又无一句说破,以此突显“道”的神秘状态,其腴奥风格更是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再如《归元》章有“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其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老子通过现象解说自然界的平衡法则,强调返璞归真、保全自身。以“母”“子”为喻体,分析道源与道流的关系,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空间,语言幽邃,意味深远。所以,孙鑛认为“此章幽眇古邃,真青牛紫气中物”[4]492。除此之外,还有:
文字甚夷,旨趣则邃。善谓用功,复性必无功可用,乃为至焉。此寓言之祖。(评《偃武》章)[4]483
不过“上”“下”“静”“躁”字耳,说得如此开播深隐,他子书未易有此。(评《谦德》章)[4]495
“邃”“幽”“奥衍”“深隐”皆表示文字背后的深味,即孙鑛所追求的“精腴简奥”之美。道家向来强调言不尽意,推崇无言之美。《老子》更是在开篇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肯定了“道”的不可言说性。最后一章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指出达到无言境界是体道悟道的表现。《老子》的语言结构也非常简单,基本没有复杂的逻辑论证和推演表述,但简洁的语言当中往往包含超越表面字句的大量信息,同时,老子更是运用隐喻、象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使有限的字句包含无限的意蕴。这与孙鑛所强调的“精腴简奥”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孙鑛对《老子》幽奥之文风的发现与推崇,既是基于孙鑛本身的审美追求,又与《老子》本身微言大义的语言特征密不可分。
“精腴简奥”是孙鑛所追求的审美特征,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则离不开“文法”的合理运用。“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可不朽,岂轻以灾竹木。”[2]191孙鑛认为周人在竹简上刻字,比后人用纸张、毛笔书写更为费时费力。因此,古人写作时必须反复思量,使得文章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正是这种反复打磨、千锤百炼的做法,造就了周文独特之“法”,而“精腴简奥”正是“法”所成就的特征。对《老子》“精腴简奥”之文风的探究,也正是对先秦文学文法的揭示。
三、祖:评《老子》后世文学影响
明代强调文学复古,在对文章师法对象的选择与论证上更有秦汉、唐宋两大阵营。孙鑛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中修正和发展前后七子及唐宋派的复古观念,认识到“周文汉诗”才是真正应该师法的对象。他说:“于时志甚锐,力甚猛,必欲为周文汉诗以振终古之业也,鸣鼓以号众,无有应者无何被。”[2]193-194孙鑛还在《与吕甥玉绳论文书》中解释了“周文汉诗”的具体所指:“世人皆谈汉文唐诗,王元美亦自谓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以上,愚今更欲进之古,诗则建安以前,文则七雄而上。文则以《易》、《书》、《周礼》、《礼记》、三《春秋》、《论语》为主,两之《语》、《策》,参之《老》、《庄》、《管》;诗以三百篇为主,兼之楚《骚》、《风雅广逸》、《汉魏诗乘》。”[2]213可见,《老子》正属于孙鑛所提倡的“周文”。
《老子》作为先秦文学之典范,自有其文学价值。《文心雕龙·情采》有言:“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6]《老子》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艺术上也采用了譬喻、顶真、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重德》章有:“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这里列举了“重”与“轻”、“静”与“躁”两组对应关系,肯定“重”“静”,批评“轻”“躁”。其辩证关系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即论述“万乘之主”如何巩固和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老子》运用对立词语表现事物的特点,揭示事物的矛盾,言简义丰,孙鑛认为“理幽语胜,他子书无此妙”[4]481。再如《谦德》章中孙鑛针对《老子》语言的隐喻性进行评点:“不过‘上’‘下’‘静’‘躁’字耳,说得如此开播深隠,他子书未易有此。”[4]495孙鑛看到了《老子》语言之“幽”之“隠”,大赞其妙,这既与《老子》隐喻性的语言特点有关,又体现了孙鑛“精腴简奥”的审美倾向。
在对《老子》艺术魅力挖掘的基础上,孙鑛更是看到了《老子》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中国向来注重学术源流,后代文学创作往往在继承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批评鉴赏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孙鑛常常将《老子》与后代文学对比,体现出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对后世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源头意义。
在评点时,孙鑛常常使用“祖”“出此”“本此”等字眼,揭示后世文学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是艺术手法的继承。比如针对《象元》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孙鑛评道:“豪庄夔怜蚿,蛇怜风句似出此。”[4]481与《庄子·秋水》中“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一样,二者皆采用顶真手法,表现出流畅蝉联的美感,孙鑛正是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揭示《老子》对后世之文的影响。再如《偃武》章有“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一句,孙鑛认为:“文字甚夷,旨趣则邃。善谓用功,复性必无功可用,乃为至焉。此寓言之祖。”[4]483老子常常借助种种物象或经验进行说理,将抽象的哲学思想具体化,同时增强文本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按照中国古代的礼仪,居左为主,居右为客,老子以此为喻,以“用兵贵右”说明作为君子在不得已时才能动用战争,通过比喻性的话语委婉含蓄地表达反战观念,在孙鑛看来,后世以《庄子》为代表的寓言体皆源于此。另外,孙鑛还发现了《老子》的文学风格,并对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显德》章中写道:“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不成。”这正是老子对“善为士者”所具备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特性的进一步解读。从风格上看,前半部分句式相对整齐,形成了对偶式的排比气势,语气酣畅淋漓,读起来朗朗上口,显示出雄肆的文风,更是与所表达的内容相契合,而该风格对同为南地文学的楚国骚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孙鑛做了“洸洋恍宕,便为屈宋作祖”[4]476的高度评价,他发现了《老子》与屈宋之间发展继承之关系,肯定了《老子》对后世文学风格的影响。
四、结语
清人认为“经不可仅以文论”,而孙鑛却偏偏以文论经,挖掘“经”的文学特色。就《评王弼注老子》来看,较少涉及义理的分析和思想的揭示,更多的是运用文学性的语言进行《老子》文学价值的分析。在评点中,孙鑛并非一味夸赞,对《老子》文本中的不惬意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守微》章,孙鑛认为“语鬯而夹,理趣反似稍短”[4]497,体现出崇古但不泥古的变通态度和批判眼光。正如闵齐华所云:“(孙月峰)片语之瑜,无不标举;一字之瑕,亦为检摘,诚后学之领袖,修词之指南也。”[7]
孙鑛的评点颇具影响,但也多受抨击。钱谦益认为孙鑛的评点“非圣无法”,屈守元更是视孙鑛为“不解文义,乱下评语的妄人”[8],认为孙鑛的评点贬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实际上,孙鑛从《老子》中发掘“雄肆质陗”“精腴简奥”之古风,揭示古文有“法”,维护了《老子》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其研究角度与方法更是与传统《老子》研究形成互补,无论是在整个评点史上还是老学史上,其价值都是不应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