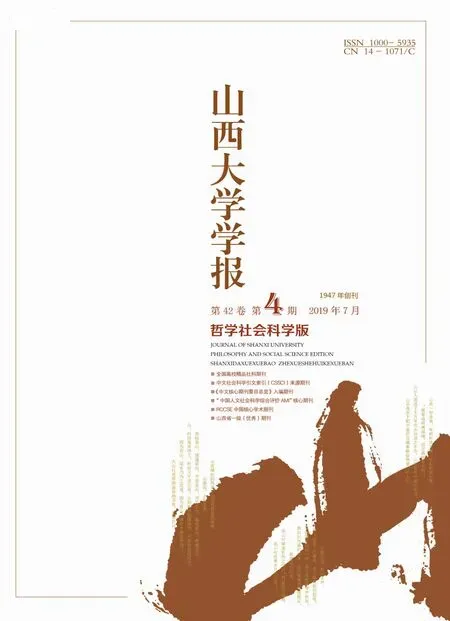河套区域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今日的河套地区分布在唐朝关内道北部,[1]331-440它夹在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与纵深的草原之间,沟通南北两个不同的地理文化区域,尤其是建基于其上而迥然有别的王朝,所以它具有的地位就超出一般。更重要的则是,它地位的凸显与收缩不仅关涉到它自身,更展现出唐朝治国整体框架的关联及其特点,因而这一区位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所承载的范围,具有全局性或者结构性的特质。但这只是就唐朝而言的,北宋以后则是另外的情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河套的地位为什么在唐朝具有战略性价值?它一直如此吗?本文就此略作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 以关中为核心宰制全国结构的形成
为什么说河套在唐朝的战略地位是宋朝以后所不可比拟的呢?这与王朝建国的全面布局有着直接的关联。
综观古代中国王朝的建构,以唐宋为界,在地缘政治布局中似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中原王朝以关中制衡山东、遍及江南,由此形成了控制全国的格局;宋朝以后的中原王朝则多以黄河下游尤其河北中北部为重心,进而宰制西部和南方,构成上下一盘棋的局面注本文所列前后期的布局及其变化,着眼于一统性王朝,且为大致说法。关于古代王朝的布局及其中心地域的转移,统一性与分散性诸王朝及都城的定位等相当复杂且不可同日而语,此处不赘论。相关内容可参阅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南京史志》1985年第3期;同氏:《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第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氏著:《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8页。。这种东西转移为旨向的整体性架构,与王朝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的衍变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制于朝廷与周边外族势力,尤其北方草原游牧势力消长之关联。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中原与北方游牧势力所处地理位置及其衍生的地缘关系,对南北(或更多)政权彼此之交往和争战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国家。即使在今天,地缘所决定的一国或多国之政治、军事走势,亦为不可忽略的要素。那么,在这种以关中为核心、以之制衡山东进而控制全国的唐朝架构中,我们是如何理解河套的地位呢?
以关中为全国地缘战略核心框架的确立,应始于西周的建国。周人系从西北东向进入关中,这意味着其生活方式转向了定居,他们再从这里向东发展并最终灭亡了商朝。灭商之后,周人并没有留居商朝都城经营他们的国家,而是选择了他们起家的关中,由此建构了控制全国的网络。这表明周人若要在一个陌生地区为中心建构国家,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隐藏其后的原因乃在于,周人推翻商朝单凭它自身力量还远远不够,它需要众多势力的鼎力协助,这实际上也宣告了周人建国能力的薄弱;倘若联合起来共建一个王朝,除了区分主次、内外有别、主辅差序的方式之外,似乎没有更优的方法。选择一个特定区域为统治中心、由此向周边递次展开的非均衡格局的确立,就是那种生产技术条件下人们建立政权的最佳途径。继承其后的秦朝同样出自西北,他们建国所走的道路同样自西向东,关中亦成为秦人经营的核心。就此而言,源出西北的政治势力一旦突破关中向外伸展势力并建构幅员更为广阔的政权,关中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起家基础,也是政权建构得以稳固的生存条件。与西周不同的则是秦朝的规模和幅员已扩展至农耕地区的极限,[2]政权性质亦从封建制转向了中央集权制。秦朝开创的这种局面又被西汉所延续,于是就演变成关中为地缘核心、统辖全国的模式。[3]关于这一点,谭其骧曾说:
娄敬、张良根据当时初建的汉王朝内部最突出的问题,即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之所以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关中足以东制诸侯。……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取得了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于都护统辖之下的伟大胜利,这和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这一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4]32
都城之选择,基于政治、军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考量,汉朝选择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同样有如此的战略安排。隋唐两朝亦选择长安作为首都,关中的核心位置如同秦汉,谭先生认为后两者的建国就地缘政治而言,实乃近于西汉,那就是从关中出发,对内既能制服山东和东南潜在的割据对手,对外又能抗御突厥、吐蕃这些势力的威胁。[4]18-38,[5]104-105这个论述侧重于王朝的内外形势走向,不可谓不恰如其分;然而隋唐之定都关中,与统治集团起家之处的密切关系同样值得考虑。如同陈寅恪所论,隋唐两朝之决策集团,源出于西魏宇文泰开创的关陇集团,其方针和政策的宗旨即所谓“关中本位政策”。[6]48-49这一统治集团产生与活跃的地区,均以关中为轴心呈辐射状发展[注]有关关中的地理形势,参见史念海:《古代的关中》,氏著:《河山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6-66页;《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氏著:《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5-244页。,其方式即如毛汉光描述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那样,他们多选择与己有利的地段作为统治与发展的核心。他列举北魏至北宋之间各自200余年的三个阶段,证明统治集团如何选择自己的根据地(核心区)而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进而经营和伸张各自王朝的事实。[7]1-28王德权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归结为时代条件的制约,即处于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联系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核心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进而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一脉络下,政治过程通常表现为“核心-周边”式的空间扩展,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格局。[8],[9]隋唐的全国性布局,应当就是这种关联的结果。[10],[11]
二 河套区域在全国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一,就地理范围而论。
河套地处关中北部,黄河自西转往北,又折向东,进而南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几”字形地域;[注]仅以套内的胜、夏、灵三州为例,距离长安分别为1853、1050、125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灵州夏州胜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100、110页。关于长安与河套诸州之交通,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之《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175-276页。黄河环绕的范围称为套内,即文献之“河南地”。这里属于农牧交错地段,[12]250-271河流途径之处多农耕垦殖,适合于定居生活;水草、沙地相间则适合于游牧生计。[13],[14]3-154这种复杂而多样的自然环境,给人们提供了诸多迥异的生活条件,形成了混杂生计的局面。换言之,自然条件的异态决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适应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就是人们熟悉的族裔或族群的差别。于是,河套内外众多而又大致呈农耕、游牧或半农半牧型的人群(采用当时通行的称呼即“胡汉”群体),于此汇聚成为独特而混溶的景观,一旦这些异质性族群分属不同政权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注]现今的研究告诉我们,河套地区的农牧多种生计形态并非亘古不变,而呈现着明显的变动,其中游牧生活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步形成。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93页;[以色列]吉迪:《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余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第二,从地缘政治角度着眼[注]所谓地缘政治,用陆俊元的话说,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见氏著:《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9页。。
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则决定了群体的划分,游牧人、农耕人或亦农亦牧的人群就此形成了。河套种类复杂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不同族群交汇和互动的集中地,这些族群又分别被不同的政权所控制,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于是,这种地理形势就衍化成为政权之间政治、军事纵横捭阖的场所。拉铁摩尔有一个说法对我们认识河套地区的特性有所启发,那就是:对于汉人视为边缘的地区(具体指的是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连结东西南北的中心。[15]305从中原农耕主体王朝的角度着眼,这里是其北部边缘;从草原游牧政权的角度说,这里则是他们的南部边地,恰恰这一各自的边缘及其相互的交叉,汇聚了不同生计方式的群体,进而变成了多元的聚合。就此而论,这里又成为不同政权和多族群文化交汇的中心地段。在这一混合区域之内,南部接近汉人生活方式的群体大体上倾向于中原政权,接近北部混合地带的人群更倾向于草原:人群处于变动无常的状态,是该地区鲜明的特点。[15]316
正因为如此,河套不论对南部的唐朝还是北部的突厥,都是保持自身安全的战略要地,亦系双方试图控制的必争之处。在关中为核心布控的唐朝眼中,河套有如郭子仪京畿道之“北大门”的称誉,[16]3464我们在文献中尚未发现京畿东大门、南大门之记载,显然,这“北大门”所指是有其特定指向的。众所周知,对中原王朝而言,它对自身安全最感担心的就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唐初则以东突厥为强,它的频繁南下也的确对都城长安构成了直接威胁。[17]147-185,197-202,[18]165-281突厥若进攻关中,必经河套。从地缘政治的效应看:一个友好并带来利益的政权,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相反,若怀有敌意,它所施加的损害也会相应地扩大。[19]16唐朝建国后一段时期的南北关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的相互攻防,尤其是突厥,因丧失了北周、北齐竞相投其所好的利益[注]北周、北齐相互竞争,为使自己能够战胜对手,双方均与突厥交好以壮大自己的实力。突厥也乐得其所,收受双方的财贿,诚如首领他钵可汗所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指北周、北齐)孝顺,何忧无物邪。”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1页。,遂对南方王朝展开了持续攻击,加之游牧势力壮大所依托的物质财富,单靠自身无法满足,这也构成了他们不断南下的动力[注]游牧政权壮大所需物质财富的支持,因其本身无法提供而不得不向外界索取,这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一般认为:向外通过军事(包括其他)手段获取资源的行为,是满足游牧政权自身发展并坐大的一个(或多个)必要条件。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过程原因的检讨》,《食货》(台北)新1卷第12期,1972年;Jürgen Paul, “ The State and the Military - a Nomadic Perspective ”, the Seminar of “Statehood and the Military” , the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Differenz und Integration”, Halle, April 29-30, 200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219页。;然而它南下的进攻,也对唐朝构成了威胁并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于是,沟通南北的河套区位重要性之上升,就势所必然了。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曾说:宁夏镇“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西魏以迄周、隋,亦以灵州为关中藩捍。唐开元中建朔方节度于此,用以捍御北方,士马强盛,甲于诸镇”[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宁夏镇》,贺次君,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41-2942页。顾祖禹在该书的另一处又说:“后魏之季,宇文泰亦以夏州发迹,遂并关中矣。唐贞观以后,声教讫于漠外,而边备未密,河西、朔方时有阑入之虑。”这都说明河套对关中的重要意义。同上书卷61《陕西十·榆林镇》,第2904页。。类似的描述,在今存《通典》《唐会要》和两《唐书》等文献中也多有反映,河套之战略地位确如文献所称,系属长安所在关中北缘的战略攻防要地。
第三,从内外关系来看。
唐朝近300年的运作,就其政治发展的指向而言,有一个前后的变化:前期倾向于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宰制全国[注]唐朝建国后统治集团如何拓展乃至维系全国的治理架构,曾有前后的反复较量,这通常是在政治党派于宫廷、外朝的斗争和博弈中实现的;这些派别的政治活动又从长安、洛阳东西两京的频繁游动中表达出来。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性研讨,应当以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书首开其端立为典范,其中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50-127页)尤聚焦于此。,后期则逐渐向东部转移,虽然它未能完全成型。这一转化的动力毫无疑问源自内部的博弈,但外部因素的制约同样不可忽视。如何说呢?如前所述,唐朝建国的统治集团多以关陇贵族为骨干,构建成关中制衡山东和江南、进而控制全国的格局。这种局势与起家关陇的政治势力之关联,密切到若不蜗居关中就不足以控制全国的地步。更为重要的则是关中北部河套迤北分布的东突厥,如同文献所称“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16]5155构成了威胁朝廷的首要势力。在两强对峙的局面中,对定居王朝而言,都城的核心重地倘若距离对方过远,防御的能力就会降低,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害。这表明,都城的适度安排及其边地防御网络的有效构筑,对定居王朝的重要性十分突出,这恰与“游移不定”的游牧政权适成对照。
内外形势的遽变,迫使唐朝确立全局性的外围防御战略,不可能抛弃河套而选择其他。这一攻防方略与唐朝前后相伴,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网络。[20]但在关中制衡全国布局的整个前期,关中-河套为要害的防御架构,始终成为唐廷部署的重心。具体说,唐朝北部防务系统规模性的建立,是在贞观四年(630)征服东突厥之后逐步形成的。唐太宗与朝臣曾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是选择羁縻府州的形式将他们安置在长城沿线地区,[17]227-272,[21]14-37河套同样也设置若干相配套的羁縻府州;[22],[23]145-157旋后又置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兼理军政,保卫关中和长安。[24]323-340,[25]263-277,[26],[27]然而东突厥复兴之后,其势力大增,开始频繁袭击唐朝北部边地;吐蕃又在西部向唐朝进攻,初期形成的周边战略攻势遭受严重挑战,迫使唐廷放弃攻战而转为防守,[28]329-352边地那些较小的军制单位与行军体系,就被较大规模的防御单位所替换,即如唐长孺所说节度使大军区的设立。[29]390-422作为这个防务体系的组成且有中心功能的河套系统,它亦随着整体形势的变化而改变,[24]315-322然而值得关注的则是,河套自身具有的战略核心,它的建设和转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部整个体系的变迁,这是毫无疑义的。
河套之成为唐朝北部防务战略之重心,是由唐朝与草原政治势力(譬如东突厥等)南北对峙架构中它所居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前面曾说关中之成为唐朝主宰全国的核心与李唐统治阶层源出关陇集团密切相关,这是从其建国内部因缘角度着眼的;然而这种格局恰与汗廷活跃在乌德鞬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北缘东突厥的构架形成了对应,看来并非巧合。隐藏在这种架构背后的,是支配着唐朝内政和外交的两条线索。
内在的线索即如上文所言自西向东转移背后潜藏的政治博弈。以往学界聚焦于关陇贵族与山东庶族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问题虽纷繁复杂,但矛头所向(西→东)的转趋相当明显。它实际表现为初期掌握朝柄的(西部)关陇势力,在高宗、武则天的当权主政下其权势逐渐被东部势力所取代的过程,这一转轨又是通过宫廷与朝廷的一系列政治较量和斗争乃至武周政权兴衰的变迁实现的[注]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收集了学术界有关唐初至武则天上台之后政治演变的诸多论述,涉及唐朝前期政治的转轨及趋势等。参见该书第25-43页所载内容(苏士梅,毛阳光等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支配这个西-东转移方向的就是朝廷的政治势力及其博弈,而博弈背后透露的则是一个特定集团(关陇势力)依凭特定地区(关中)与远超它自身范围的全国性政权内存的张力。解决这个张力的有效办法,就是扩大统治集团的范围以适应全国性局面治理的需求。这条道路虽然曲折震荡并伴随着波谲云诡的风险,但它的确是奔着解决这种矛盾和张力的问题去的。采用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的说法,唐朝政治与文化西-东向的转轨最终的归路就是“南朝化”,即中华传统的复归。[29]463-473,[30]
与内线相伴的外线主要表现为长城地区南北政治势力(集中于政权)的互动,唐朝前期突出地表现为草原铁勒诸部与朝廷的联系,尤其突厥的兴衰与再度立国引生的分合。就逻辑关系而言,这条外线依托于内线而展开,它的活跃建立在唐朝立国这条内线的基础之上。在整个前期,能够对唐朝政治产生辐射影响的重要势力主要来自北方的草原和西部的青藏高原,兴起于唐朝之前的东西突厥,依托于机动灵活的游牧军事力量,充分展现了它的攻击优势;继唐而兴的吐蕃,也从其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与唐朝角逐;[31]220-295其他较小的政治力量则依违于中原周边、往还于唐朝内外。
我们看到,外线固然依托于内线而成立,然而一旦它确立,它内存的动力冲击亦使它以突出的张力显示出来。这就是唐朝相继征服东西突厥建构超越中原、兼跨长城南北复合型帝国的出现、突厥降附又重新复辟并持续袭扰长城沿线给予唐廷的压力,以及吐蕃突破青藏高原对唐朝产生冲击导致一统化的破局。在此交往的过程中,唐朝既突破了中原传统的限域获得了超大型王朝形塑的成功,又经历了再度萎缩退守农耕边缘的磨难。[32],[33]这两条线索所昭示的[注]关于这个问题的引申讨论,可参阅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势和南北对立的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就是唐朝内政与外交的纵横捭阖,如同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所言,“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外族)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尤甚于以前诸朝”。[6]128,152在整个前期,它们是以内政的东西向政治势力的前后替换以迎合全国局面、南北沟通构建超越型王朝的愿景而呈现出来,这成为那一时代王朝运作的主旋律。正是依托王朝框架中两条线索的相互交织,河套才得以擢升为战略性而非滞留于区域性的地位;只要关中坐拥王朝经理之中心、北方势力对此构成的压力不减,河套的战略地位就会保持不变。
三 河套区域战略地位的前后变化
这里的前后变化是指安史之乱前后,即唐朝前后期的变化。这个变化同样体现在内外两个层面。[34]143-154
从内政角度讲,安史叛乱对唐廷造成的损害,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对全国直接控制的能力,特别是在河北道,其直辖效力因河朔藩镇自行割据而遭受重创,[35]如同陈寅恪所说“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6]25困扰后期朝廷的内政问题,应该以河朔和其他不服从管制藩镇的抗拒最为突出,不论是德宗削藩的失败,还是宪宗的暂时成功,嚣张跋扈的藩镇,构成朝廷的心腹之患,这些原本协助朝廷抗衡外部势力的军队,随着安史叛乱的结束开始遍布各地,[36]讨论、设计并实施如何震慑藩镇使之构成的威胁越少越好的筹谋,就成为后期长安君臣的议事日程。这在前期是看不到的。
与内政对应的边(外)政,后期也与前期颇为不一。首先是突厥势力的退出,唐朝面临的威胁大为减缓;继之出现的回纥(鹘),唐廷虽保持高度警惕,它的咄咄逼人并没有发展到频繁的“进犯”,当唐廷逢遭内难求它协助镇压叛军之时,回纥扮演的是出军助攻朝廷的角色,虽然它的要价不菲。唐、回这种相对的和缓,与突厥造成的压力适成比照。[37]62-101与此相应的则是,青藏高原的吐蕃趁安史之乱而占有唐河西、陇右等地,切断了唐与西域腹地的联系,其控制线直逼都城长安之西,成为唐廷的至要威胁。[38]182-209这种局势之下的唐朝如何因应,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朔方军被肢解的方式构建京城西北八镇的防御格局,[21]217-281表明唐朝防御体系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前期的唐与东(后)突厥的南北关系被后期唐与吐蕃的东西关系所取代,唐与回纥的南北关系固然也是重要环节,但它因威胁递减而不若东西关系那样突出。处在这种局势下,河套固然在吐蕃时常骚扰其地中继续保持着某种作用,但前期那种整体格局中的战略性角色却不再拥有,这从文献有关其地诸城的放弃以致常年人烟稀少导致荒凉场面的记载中得以证实。[39]106-107,113-114
整体而言,后期的唐朝,就其控制的幅度而言,已从长城南北的跨越蜕变为耕作传统的防守,其思想和主旨意识亦从兼纳并蓄、华夷共融转向了内外有别和畛域的分明。[40]209-226,339-382节度使的分权自立与朝廷的试图控制、长安内部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并夹杂着宦官势力的崛升,宫廷朝宦的互斗及引发社会的普遍对抗……朝野的这些矛盾和龃龉带给唐朝的最终命运,似乎除了灭亡而别无选择。[41]466-803,[42]与内政这条主线相伴的外线,唐、蕃的较量曾一度超越南北的互动,其他势力的再度崛兴,已成为唐廷面临并迫切应对的关键。以南北关系凸显构建的河套那种战略地位之下降,就势属必然了。可见,河套的地位与其说源自于自身,不如说由唐朝的整体构架所决定。当一个以关中为核心经营全国、又面临草原西部游牧势力威胁的局面形成之际,沟通南北的关键点——河套的地位就具有了战略性的重要;然而一旦这种结构发生变化,如同毛汉光描述的王朝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转移,即从关中本位转向了魏博汴梁东部之后,[7]22矛盾的交织与争衡的纽结使它地位迅速擢升,最终抟成为北宋的经国局面。面对东北契丹人辽朝的强大压力,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遂成为北宋经略的核心腹地,其北部今河北临近辽朝之州县则衍化为防御的战略要地,从而取代了唐朝的西北。宋以后的历代王朝,尤其一统化的元明清诸朝,其都城的核心已转向今河北北部,王朝依此控制西部和南方构建全局。在这种布局中,作为防护游牧势力南下的要害,其战略性布局就从西北转向了河北北部延至邻近的内蒙古东南,这里随之成为整体格局中的战略制衡点。[43]107-116如此看来,本文讨论的河套全局战略性地位的形成、确立和嬗变,纯系由王朝结构的整体框架所决定,只要这种布局不做根本性改动,河套的战略地位就不会丧失;相反,这一结构倘若发生任何变化,它的地位亦随之而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