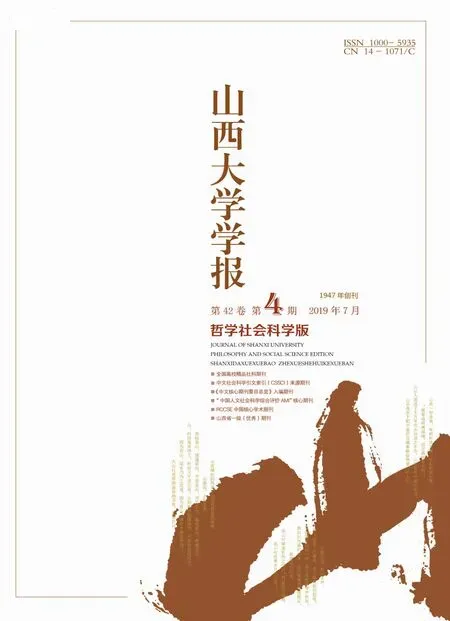“中国故事”讲述与小说新美学构建
——论毕飞宇小说及其小说理论
刘成才
(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1]62,对作家来说,墨菲斯特的这句话应该替换成“唯创作之树常青”,大多数小说家相信只凭借才华与直觉就能写出好小说,他们对艰深晦涩的理论通常没有好感,对理论批评更不以为然,甚至极端地认为只有“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2]。但这依然没能阻碍那些优秀的小说家建构文学理论的热情,略萨的《中国套盒》、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等,犹如一座座巍峨的理论高山,横亘在小说艺术史与文学史中。我想,这其中还应该加上一个名字——毕飞宇。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毕飞宇非常有理论建构的兴趣,他不仅喜欢和丁帆、王彬彬、李敬泽、陈晓明、汪政、吴义勤、张莉等批评家对话,接受记者采访,频繁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自我阐释,更重要的,他提出“写作是阅读的儿子”[3],在对《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鲁迅、汪曾祺、莫言、哈代、海明威、卡夫卡、奈保尔、莫泊桑、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中外经典作家作品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小说理论。是以,他对小说的阅读感受和评论持论精确如老吏断狱,时常有对作家匠心的敏锐体察,体现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敏感,所以他戏谑地称自己是“一个好吃的人最终做了厨子。”[4]
一 “始于零度海拔”:现实主义与人物尊严
毕飞宇有案可查的小说最早当属《孤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花城》杂志,之后发表了《那个男孩是我》《叙事》《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手指与枪》等近50篇中短篇小说。这些风格类似的小说让毕飞宇收获了一些文学声名,被贴上“先锋派”“晚生代”“新生代”等标签,但这些小说的风格是模糊的,不具有辨识一个作家独特性的品格,毕飞宇对此非常清醒:“我要说,它的原创性还不够,它还不是‘毕飞宇的小说’。”[5]
毕飞宇此时主要受1980年代先锋文学,特别是被先锋文学视为文学之神的博尔赫斯的影响。毕飞宇从不回避自己从先锋文学学到的叙事和小说修辞让自己一开始写作就占据较高起点,但同时,先锋文学在1980年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文学声名,也给毕飞宇带来“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毕飞宇反思,开始对被自己视之为神的博尔赫斯与先锋文学产生厌倦感,进而对自己的小说写作产生怀疑,开始谋求转变的可能性,“我渴望变,往哪里变呢?我不知道。我想强调的是,我所渴望的变化不只是叙事形态上的,而是我究竟要写什么,我到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与这个世界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6]1
更为关键的是,在毕飞宇开始写作的1990年代,文学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先锋文学强调的是语言创新与叙事变革,它之所以能在1980年代席卷文学领域,形成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并不是中国人在此时突然对文学产生兴趣,而是1980年代当代中国重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一个庞大的国家再一次直面“现代”,以西方文学为精神资源的先锋文学则在此时以“文体实验”和“意义消失”的技术实验应时而兴,在迅速颠覆既有文学秩序和文学传统的同时,让中国人在世界观尤其是情感上受到强烈冲击,“人们借助于文学,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感受生活,重新估量世界,同时释放压抑了多年的紧张。”[7]可以说,先锋文学是1980年代“中国故事”的最好注解。
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社会也因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而改变甚至颠覆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此时的先锋小说不但无法阐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甚至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8],故而,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扎西达娃等先锋作家才会纷纷放弃先锋文学,无奈地转向更具市场化的写作。所以,毕飞宇具有先锋风格的小说《叙事》在1994年发表之后,《钟山》杂志著名编辑黄小初充满遗憾地对毕飞宇说:“飞宇啊,你生不逢时啊,你要是早个五六年写出《叙事》就好了。”[9]95
“先锋派作家处理不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几乎是一种共识”[10],这背后的难度在于如何理解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当代中国。所以,毕飞宇认为“真正让中国作家觉得下笔困难的,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当代性。”[11]他在访谈和演讲中多次提道,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想象力,而是如何在文学中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这关系到作家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因为“理解力比想象力更重要”,如果对这一点视而不见,那几乎是“作孽”。[12]
如何通过文学表达对1990年代已经变化了的当代中国的理解呢?毕飞宇在怀疑与反思之后选择的是“睁开眼睛,低下头来,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亦即他所说的“始于零度海拔”的现实主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13]对毕飞宇来说,回到现实主义不是回到一种创作手法和小说修辞,而是回到一种“情怀”,即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连成一体,成为“一条船上的”[14]。
现实主义又何以能够理解当代中国?如何回到现实主义?毕飞宇的努力是激活在先锋文学中被边缘化了的人物,恢复人物在小说中的尊严,让人物重回故事之中,赋予人物以文学的可能性。所以在写作《玉米》时,毕飞宇曾自述一口气让小说中的施桂芳生了八个孩子后,他激动地直搓手:“孩子生下来我就好办了”[15]。这在先锋文学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先锋文学关注的重点是“有意味的形式”和“人的消失”,强调的是语言、概念、结构在叙事中的突出,压制人物在叙事中的作用,在远离中国文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的同时,也使文学远离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不具备直接面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叙事能量。毕飞宇则让人物直接处于小说叙事的中心,甚至让现实生活的逻辑服从于小说的逻辑,所以,他虽然对生活中的女性充满悲悯,却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充满害怕,因为“她们就在我的身边,甚至,弄不好,筱燕秋就是我自己。”[13]
由于筱燕秋、玉米、玉秀、三丫、吴蔓玲等女性形象的成功,毕飞宇被誉为“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但毕飞宇认为如果这样理解就把自己给窄化了,他的小说世界要“比这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他小说里人物都是无性别的,没有“女性”的概念,他关注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即“最基本的人的权利”。[7]所以,毕飞宇对莫言的《红高粱》大加赞赏,认为《红高粱》中的人物具有“自主的行为与能力”,充满着“蛮横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和解放的动机,《红高粱》是一首“解放的诗篇”,它给中国小说确立了一个下限,“小说到了这儿才能叫小说”。[16]
为了让人物在叙事中处于曝光中心,毕飞宇认为应该在写作中做到心“慈”手“狠”,唯有如此,才能不干预人物发展的小说逻辑。毕飞宇心慈,他对“失败的一方和卑微的一方始终有种近乎本能的兴趣”,筱燕秋、玉米、玉秀、端方、二丫、吴蔓玲、都红、小孔等,都是“失败的一方和卑微的一方”,但恰恰是他们“确定了生活的主体与本质”。[17]毕飞宇手狠,他在解读《水浒传》时,看到的是林冲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不想走,然而又不得不“走”这一所有偶然性都服从于悲剧的必然性,施耐庵通过林冲这一人物形象,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实现了批判的最大化。他在莫泊桑的《项链》中看到的是玛蒂尔德因为一晚的虚荣而背负十年辛劳,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在十年中慢慢老去这一践行契约精神的“‘文明的’悲剧”[18]。他还在《故乡》中读到鲁迅的基础体温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种独特的“阴刚”的小说审美模式构成了鲁迅的辨识度,“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19]108
伊恩·瓦特在研究小说为何会兴起的时候,认为现实主义“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20]8。毕飞宇小说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他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失败的一方和卑微的一方”,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背后蕴藏的人道主义悲悯和对人物尊严的尊重,以及对小说中人物推心置腹的信赖。在毕飞宇看来,他所经历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创作路径不同,但都“源于对现实主义一种反叛性的‘继承’”,他“始于零度海拔”的现实主义不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是在先锋文学注重语言与作者体验的基础上,以“一颗‘在一起’的心”凸显人物尊严,对他来说,现实主义“首先是凝视和关注”。至此,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宣告:“我的文学生涯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开始了。”[21]
二 “一个记忆回来了”:世态人情与文学传统
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小说《两个骠骑兵》时,卡尔维诺认为托尔斯泰试图通过这部小说“重新唤起一个当时已逝的年代”,在小说中“与其说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颂扬亚历山大一世时的俄罗斯而不是尼古拉一世时的俄罗斯,倒不如说他感兴趣的是找出故事中的伏特加,也就是驱动人类的燃料”。[22]164卡尔维诺所指的“伏特加”与“燃料”,即小说中对乡下贵族与吉普赛人狂欢夜这一世态人情的描写,托尔斯泰认为这是已经失去了的俄罗斯军事封建制度的自然基础。与此类似,世态人情也是毕飞宇小说的“伏特加”与“文学的拐杖”。
自《青衣》肇始,下启《玉米》《玉秀》《玉秧》诸篇,再到《平原》,毕飞宇的小说有一个潜在主题,那就是作为精神的1970年代。虽然在毕飞宇开始文学写作时,1970年代早已过去,毕飞宇本人也因年龄关系而没有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1970年代记忆并不深刻,但“毕式”一姓无根的尴尬以及父亲母亲在1970年代的遭遇,足以让毕飞宇对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先锋文学对1970年代的模糊化处理不满,也不能认同西方学者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他始终认为,作为“事件”的1970年代这个“十年”虽然随着时间段的终结以及政治大人物讲话而成为过去,但作为“精神”的1970年代却没有终结,并且造就了类似小说中的玉米、端方、吴蔓玲等众多的“带菌者”,只要这些“带菌者”生活在我们中间,就会有“人在人上”这个“鬼”存在,而“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23]。
在一次座谈会上,毕飞宇谈到了昆德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小说家,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24],毕飞宇认为,在昆德拉的理解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是通过他的小说“对人、对人物关系、对婚丧嫁娶、对酒席及对茶、茶杯的仔细描摹当中呈现出来的”[24]。毕飞宇的小说对1970年代的理解,也是从这些细节的描摹着手的。
与伤痕文学刻意展示灾难故事和先锋文学以荒诞的犬儒主义处理1970年代不同,毕飞宇放弃“历史与道德的审判者”[25]的姿态,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场景为着手点,展现1970年代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深入影响普通人的婚丧嫁娶与一日三餐这些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因背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最终失败的。所以,在毕飞宇的小说中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与你死我活,却处处可见钩心斗角的人情往来,一如暗水深流,平缓,却更具吞噬人的恐怖力量。
玉米的生活是如何被1970年代左右的?是玉秀和玉叶被村人侮辱后拼命摇晃的大声追问,是被彭国梁退婚时悔恨交加中抠进自己身体的那根手指,是在郭家兴身下癫狂换来的那句“好”,更是得知玉秀喜欢上郭左时不动声色地对郭左说的那句“玉秀呢,被人欺负过的,七八个男将,就在今年的春上”。对端方的左右,是大棒子被淹死时他对网子的拼命维护,是他求吴蔓玲时被一句“端方,你怎么做得出来”吓得膝盖一软跪在床边,更是得知被红旗看到给吴蔓玲下跪磕头时用麻绳勒住红旗逼迫其吃下猪屎橛。而对吴蔓玲的左右,则是到王家庄很快就在吃饭上练就的一身过硬本事,是被混世魔王强暴时屏住呼吸伸出胳膊关上的扩音机开关,又是狂犬病发时一口咬住端方时说的那句“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同样,玉秀被强暴后的堕落,玉秧沦为魏向东的暗探并甘心受魏向东的猥亵,三丫因出身问题的悲剧死亡,王连方书记刚被撤女儿就遭村人强暴,等等,俱是1970年代阴影所罩。所以,毕飞宇认为1970年代并没有过去,被吴蔓玲咬中的端方作为“带菌者”在今天依然活着,“他也可能是在南京某个工地上,是拿着棍子的包工头,他始终在茫茫人海。”[26]
在解读经典小说时,毕飞宇看重的依然是小说表现的世俗人情。评论者通常把毕飞宇的“王家庄”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并列,以此来论证伟大小说家都有一个文学共和国。但毕飞宇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文学世界比“王家庄”广阔得多,对他来说,王家庄不重要,“王家庄的那些闯入者,比如世界地图、手电、知青、右派,这些才是最重要的”[27],因为这些改变了王家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在解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时,他认为《受戒》的意义不在区域文化,而在它所表现的世俗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眼里没有阶级与斗争,更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只有人与日常生活,所以《受戒》里连庙宇与和尚也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汪曾祺是站在“生活的立场”写小说,他感兴趣的不是“乱世”中的政治经济,而是“‘小国寡民’的精致人生:安逸,富足,祥和,美好”[28]165。
他在读《红楼梦》时,透过曹雪芹反逻辑地描写王熙凤和秦可卿的关系,特别是王熙凤“一步步行来赞赏”这一细节,读出曹雪芹用“飞白”表现贾府人物错综复杂关系的背后是太通人情世故。“飞白”背后关涉到从《诗经》、南北朝艺术理论、唐诗、宋词所形成的民族审美无意识,《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背后还有另一本由“飞白”构成的《红楼梦》,是用“不写之写的方式去完成的”,而背后这个《红楼梦》的续写“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29],所以《红楼梦》注定是残缺的。
在毕飞宇看来,小说的技巧就是如何表现世俗人情,因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足以让小说跌宕起伏,所以作家要通晓世俗人情。鲁迅的《故乡》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鲁迅着力描写了少年闰土和“我”两小无猜的日常生活细节,但再次见面时,闰土却对着“我”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老爷”,这声“老爷”表现了太多的无奈与震撼。这个日常恰是鲁迅的伟大之处,“离开了真实的世态人情,《故乡》哪里能有如此生动的局面?”[30]
即使读外国文学经典,他关注的依然是小说中的世态人情。读《项链》时,他尝试着重写,把人物换成中国人,却发现小说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文学:《项链》所表现的1844年的法国,一条项链可以维持中产阶级十年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的法国是多么的正常”[18]。在莫泊桑的讥讽背后,毕飞宇不经意间读到的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18]。
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时,他感兴趣的是小说用三分之一篇幅描写的英国中部乡下奶场,认为这里隐藏着哈代“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全部秘密”:哈代事无巨细地写奶场、奶牛、挤奶、奶酪,用细节把苔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这一切都关涉到进行这些日常生活的“及物动词”——苔丝,这些日常生活足以让读者爱上她,那克莱尔自然也会爱上她,“这就是小说的‘逻辑’”。[31]
当然,关注日常生活并不是沉陷在庸常中,是因为小说即使选择传奇,也要考虑与日常生活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背后就是与文学相匹配的文化背景。在解读蒲松龄的《促织》时,毕飞宇认为,虽然成名儿子化身为促织的情节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化身为甲虫的情节类似,但化身为促织却不涉及对生命的自我认知等精神上的异化困境,而只是“有关生计的手段或修辞的问题”,蒲松龄的目的只是“借古讽今”,《促织》也只是劝谏文化中积极的部分,因而并不能据此认为“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32]同样,对于人们从晚明文化中读出的“本色”“性灵”“童心”“主情”等文人对日常生活的觉醒,毕飞宇则认为这恰是一种“病”,因为封建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坐稳奴隶”,晚明文人的狂放与玩世不恭是面临“道统”大崩而彻底绝望的“世纪末”状态,他们只能让自己隐身在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相伴的极度恐惧中,却“对真正的‘人’‘零度’冷漠”[33]。
在评论简·奥斯汀的小说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时,萨义德认为,虽然从简·奥斯汀小说中对奴隶制度和财产争夺的描写可以读出和时代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但简·奥斯汀的小说却“绝不可能还原成只是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力量,而是相反,它们处于一种尚未解决的辩证关系,同时,处于一个明显依赖于历史而又不能还原为历史的位置”[34]75。或者说,简·奥斯汀小说的经典意义绝不在于对“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力量”的还原,而恰恰在于被“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力量”控制下的时代生活。
毕飞宇的小说也可以从这一意义上去理解。经过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毕飞宇回到的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通过细致的白描与注重日常生活的叙事耐心向传统写作致敬。这种对世俗人情与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既是对先锋文学悬空现实的反叛,更是对中国文学传统中注重日常美学的接续,在表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的同时,让中国当代文学重回到重视本土经验的写作道路上,以“可以感知的形式”写“地道的中国小说”。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意味着“一个记忆回来了”,而毕飞宇则通过这一过程“充分确认了自己的文化位置,知道汉语在世界文化里面意味着什么”,在经历了“一个小说家真正内心上拓宽”之后,而更“渴望成为一个汉语作家”。[9]103
三 “小说内部的普遍性”:文学自觉与新的小说美学构建
1990年代以来,以浦东新区开发为标志,当代中国真正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中国,在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逐渐开始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领世界。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以重新组合的时空所构成的全球性抽象社会生活模式造成生活的“脱域”(dis-embedding),并影响到人们对生活的“再嵌入”(re-embedding),[35]18在迅速改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颠覆着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日常生活的时空裂变带来的是人内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对此,毕飞宇感受到的是“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与遇上一场战乱没有区别,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离子散”,“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如此繁荣、强大,其实内心破烂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内部不停地在拆迁。”[36]
对毕飞宇这一代作家来说,全球化既是不幸,又是大幸运。不幸在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转换的速度太快,毕飞宇的写作启蒙于1980年代,在先锋文学潮流的滋养下,他们的文学在潜意识中要处理的是来自西方文学的异化、荒诞等主题,然而面临的却是“历史的终结”似已到来的现实中国,“革命中国”的主题似乎已被遗忘,消费文化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城市与乡村俱已陷入悬浮状态,人与生活被庸常的现实生活所包裹,失去了参与历史的可能性。这也是毕飞宇认为不能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仅仅看作小说家的原因所在,因为对鲁迅来说,他们不仅仅是写作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实践者,而对毕飞宇来说,“我们这些作家最大的不幸就在这里,我们不再参与历史。这是作家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9]210。于是,如何用文学处理这一现实中国的繁杂与丰富性,如何准确理解这个时代的本质,就成为这一代作家不得不面临的写作难度与挑战。
但同时,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可能性的拓展,特别是全球化因素的融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卸掉了文学之外的约束与禁忌,特别是先锋文学的文体自觉与美学锻炼,已经形成一种文学遗产,极大地提升了毕飞宇这一代作家的文体意识与美学观念,让他们在价值、风格、语言等方面提前完成了文学素养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形成毕飞宇这一代作家的文学自觉,让他们有能力与意识去自觉地用文学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因此,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这种繁杂与丰富性又能够为他们的写作打开立体的可能空间,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完成对时代的文学讲述。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这个大时代对毕飞宇这一代作家来说,又是一种大幸运。
作为这一代作家中的代表,毕飞宇的小说以高度的文学自觉有效地处理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与曾经的“革命中国”的艰难撕扯,普通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血与泪,以及对一种有尊严生活的追求与渴望,并用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学有力地诠释了中国叙事的意义与可能性,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新的文学高度,构建了新的小说美学。
首先,毕飞宇的小说与小说理论融贯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具有真正的现代品格。与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更高维度上“重回”全球化格局一样,毕飞宇的小说也是在更高维度上“重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虽然毕飞宇多次提到自己在写作之初受先锋派文学“影响的焦虑”,以及对博尔赫斯从热爱到厌倦的心灵历程,但其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依然清晰可辨。
如同毕飞宇坦言的,“西方文学对我的最大影响还是精神上的,这就牵扯到精神上的成长问题,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尊严、法的精神、理性、民主、人权、启蒙、公民、人道主义,包括专制、集权、异化,这些概念都是在阅读西方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9]386,毕飞宇小说中的现代主义首先体现在对专制与集权的反抗,对尊严与人权的追求这些普世价值上。他在访谈与对话中一次次地强调自己在小说中关注的重点不是女性命运、乡村、城市这些个体化的主题,而是人的境遇、内心的疼痛与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这些普遍的主题,乡村与城市只是他表现普遍主题的空间。他反对把自己的平原系列小说理解为王家庄故事,因为王家庄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家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不认可把汪曾祺的《受戒》当作展现区域文化的范例,认为《受戒》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表现“爱”的普遍性。他赞叹莫言的《红高粱》以天纵才情为我们提供了“人”的可能性幻想,钦服莫言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能动身体与自由灵魂。他多次解读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等经典小说,把鲁迅小说理解为真正的现代主义,叹服鲁迅的启蒙精神与小说能力,认为鲁迅大幅度提升了中国文学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他认为白话文是中国社会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需要语言精确的必然结果,丝毫不否认“五四”文化先驱对现代汉语的贡献。他得意于自己的《玉米》《平原》等小说虽然是高度现实的,但却因叙事的自由与视角的主观而成为标准的现代主义作品。他憧憬“每一个人都像棕榈树的叶子那样,舒展、自然、常绿,在风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模样,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叶子,拼命地指责别的叶子没有到天空去翱翔”[37]85,主张小说有自己的美学与学术标准,应当比政治更自由,“在最高本质上,小说的思路只有一个:呈现人类在不同语境下的可能性和复杂性”[38],当中国作家因优秀作品而被世界关注时,才真正走向世界。
其次,毕飞宇的小说具有宏大的心灵。毕飞宇曾多次强调,对小说家的写作成长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重要”,因为当小说家对人性的理解力在写作中慢慢被拓宽的时候,心灵的宽度也会变得宏大。对他来说,这种宏大不是时间的跨度与空间的辽阔,更不是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规模与构架,而是“内心的纵横、开阖,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却雄伟壮丽,它是巍峨的,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是“一个人内心的秘密”。[9]386
毕飞宇的小说虽然从庸常的日常生活着手处理现实,但却没有被日常生活的庸常所沉溺,而是从中拓展心灵的宽度,并伴随着对人性理解力的增长。在谈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时,毕飞宇不止一次公开承认最喜欢的是玉秀,虽然玉秀身上有轻浮虚荣的毛病,但毕飞宇坚信她是无罪的,有罪的是生活。在《玉秀》的初稿中,玉秀被自己心爱的人强奸后怀孕而成为千夫所指的“烂货”,和一个男人在粮库的菜籽堆苟且时被菜籽淹没而死。这一结局虽然符合小说内部的逻辑,但却让毕飞宇一直被想象的恐惧所包围,并最终修改了小说的结尾,让玉秀遍体鳞伤地活了下来。玉秀这一虚构的人物让毕飞宇限制了小说家的权力,认为文学应该更怜惜人,更尊重人,应该以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包容人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清洗”。毕飞宇在塑造玉秀的同时,玉秀也对毕飞宇提出质疑,让毕飞宇的内心变得宏大,开始真正面对人类的基本情感,自此以后,“我一直保持着小说家的职业自豪,这就比什么都重要”[39]。
再次,毕飞宇的小说与小说理论具有强烈介入现实的意识。在重读卡夫卡的小说时,阿伦特认为卡夫卡虽然没有像其他受欢迎的作家那样对知识界造成强烈冲击,但却用简单、轻松、自然的语言建构了由“全权”(omni competence)这一马达驱动的机器吞噬人生活的运行以及“主人公为了朴素的人类美德而摧毁它的努力”,并且试图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40]258对毕飞宇小说介入现实的意识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会更加清晰。
毕飞宇小说有对作为精神的1970年代的批判与对“带菌者”的警惕,有对人悲剧命运的悲悯与同情,更有对尊严丧失的无奈与悲凉,同时还有对人的心灵、命运、婚姻与性的关注与凝望,这些都源于毕飞宇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热情。例如,在谈及他公认的代表作《地球上的王家庄》时,就言及小说发因于中国曾出现的拒绝接纳世界的声音,为了表现孤立的中国因闭塞而带来的愚昧导致的残忍伤害,毕飞宇用小说暗喻民族的普遍心理,王家庄作为中国的象征,帮助毕飞宇“完成了一个心理上的拼图”[9]333。
毕飞宇在访谈中多次不满评论者多从美学的意义上分析他的小说,而忽略了他的关注与热情。虽然毕飞宇深知自己的批判与怀疑很难有多大作用,但他坚信真相的前提是“说出来”,认为不能被言说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因为“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把文学的最高要求和基本底线理解为“你引导着你自己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并坚称“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一生”。[27]
毕飞宇小说的这三重品格把感性和智性叙事有机融合,以“地道的中国小说”诠释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在面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的焦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体压迫”时,感受到的不再是传统的“阴影”,而是传统的“庇护”,同时更是文学自信。毕飞宇的小说与小说理论丰富了当代小说美学,拓展了人类内心的宽度与广度,破除了中国当代文学在面临“现代”与“世界”时“得到的幻想”[41]184,这必将为今后的文学写作提供更多的文学经验与精神资源。
四 “中国故事”讲述与当代文学的时代使命
1884年2月22日,已经深陷孤独之中的尼采在给欧文·罗德的信中,依然狂妄而又无比自信地认为,虽然由于席勒的出现德语才成为一种语言,但他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语言的力度、灵活性和音乐感方面的有机融合让“德语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42]序言。而毕飞宇在给自己的《沿途的秘密》所写的序言中,则自负而又谦卑地声称“有这样一种极端,你所有的热血最后只是参与了母语,比如,这本书”[43]序言,这两者对自己哲学与文学的自信是何等的相似。
从1990年代当代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也以更为本土化的写作逐渐走进西方主流文学的阅读视野,参与世界文学共同体构建,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更具表征意义的是,以毕飞宇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真切反映当代中国人民内心与情感的同时,表达了作家对世界与人类的独特感受,以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讲述者,进而让中国当代文学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也因之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
但“历史”并未终结,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时代的“中国故事”需要当代文学更为精彩的演绎,中国人在复兴之途中的境遇与疼痛、艰辛与荣光、悲悯与尊严等诸种心灵的秘密,需要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找到认同感与归依感,这是当代文学不得不面临的时代使命与艰巨挑战。如何处理这种大时代中个体隐秘的灵魂,毕飞宇小说及其小说理论,在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学经验与精神借鉴可能性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