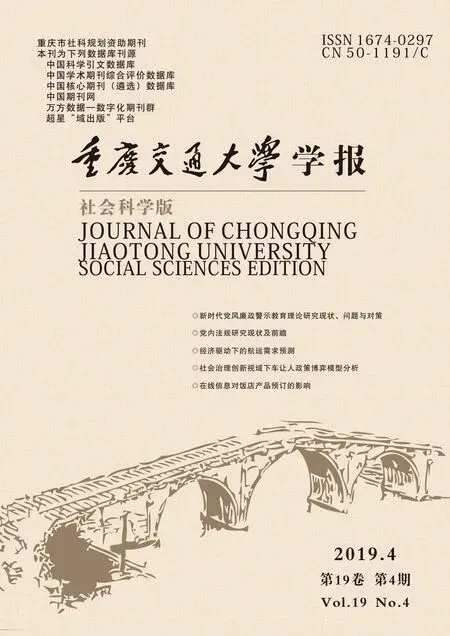历史写作中的真实与虚构——论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观
黄莉莉
(1.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2.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英国作家对历史题材的兴趣是一种悠久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本·琼森等就热衷于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历史,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尤其成就斐然,从司各特的系列小说《威弗利》开始,历史与小说的结合逐渐成就了一种成熟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类。对于英国而言,“19世纪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个世纪执著于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它渴望搜集历史的遗存和艺术,正如卡雷所说的,它醉心于被时代、过去、当下、未来所涵盖的思想”[1]76。20世纪以来,历史题材创作在英国文坛也蔚为大观,具有丰富的形式和主题,特别是历史小说,其中“所蕴含的文学能量和真正的创造性”非常值得关注,虽然这与文学传统和帝国情结可能息息相关,但这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化复归,也非是对现实的逃避。拜厄特从作家的角度指出:“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未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在英国,这包括黑人和女人的历史以及后殖民小说整个繁荣和辉煌的文化。”[2]23不列颠的昔日荣光和曾经的版图留下太多可供思考和打量的遗物,而它们和现实之间的纽带是不可除去的,英国作家们对此有着直觉的意识:“如果我们不理解先于我们并且塑造了现在的过去,那么同样也无法理解现在。”[2]24
对于巴恩斯而言,对历史题材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如上所述的一种与他的文学同行和先辈们共享的历史意识,虽然他一直声称福楼拜、列那尔等法国作家才是他非血缘关系的“至亲”,但是深厚而悠久的英国文化和历史不得不成为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和必然的写作背景。其次,拜厄特所言的历史意识其实来自于一种时代之声,对于巴恩斯而言同样如此,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流行使人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历史和历史文本。虽然巴恩斯一再声称自己并未读过海登·怀特等新人所著之书,但是他也坦言“不可否认有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3]56,这种所谓的间接影响便是西方文化中自尼采而至福柯最终传至新历史主义者那里的对于历史本质的反思之路,英国作家因为其所继承的历史意识,尤其深入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巴恩斯便是其中之一。他对此亦有清醒的意识:“旧的历史小说,试图模拟性地重建人物的生活和时代,这是本质上保守的做法,新历史小说进入过去,却对曾经发生了什么有着清醒的意识,而且试图营造与今日读者之间的明显关系。”[3]58
一、历史真相的不确定
巴恩斯以文学家的身份和方式执着于思考和探求历史问题,他多部小说都以追溯历史真相为主题。历史真相在他笔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捕捉到:《福楼拜的鹦鹉》中,叙述者一边追寻福楼拜的过去,一边不断追问“我们怎样抓住过去”[4]3;《101/2章世界历史》中的叙述者一边试图重写历史,一边质疑历史书写方式;《终结的意义》的叙述者一边追溯往事,一边概叹:“我们认为记忆就等于事件加时间。但是事实远非如此。”[5]90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用了一个奇妙而精确的譬喻来形容这种对于历史真相的追求:“我们能捕捉到它吗?当我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期末舞会上,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把一只身上涂满油脂的小猪扔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嚎叫一边在大家的腿间乱窜,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纷纷跌倒在地上,整个过程太搞笑了。过去往往就像那头小猪一样。”[4]4
过去为什么如此难以把握?巴恩斯认为追求历史之真必须首先承认真相的难以企及和难以描述,历史的真实面目也许不过就是 “多种媒体的拼贴”或“一些声音,在黑暗中回响,一些耀目的形象,一些传奇的故事,红极一时,然后渐渐淡去,那些老故事不断重复,彼此间有着奇怪的,牵强附会的联系”[6]240。传统的标榜确定性和唯一性的历史书写反而遮蔽了真相,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在《101/2章世界历史》中,所谓的“世界历史”被全面否定:历史的时序性被否定,历史的规律性被否定,历史的进步性被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被否定。
如果去除了时序性、规律性、进步性和客观性,历史会变成什么模样?历史又应该怎样被书写?是否就是那些媒体的拼贴、那些回荡在黑暗中的声音、那些不断重复的老故事?而这些分明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小说中留下的历史图景———更加模糊暧昧和难以企及。为什么历史应该如此?在《终结的意义》中,巴恩斯借主人公之口引述了法国作家帕特里克·拉格朗日之言:“历史是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5]108巴恩斯认为历史材料的不充分是必然和必须被正视的:“曾经生活过的人们都逝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认为是历史证据的东西不过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碎片……历史学家就应该更经常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做,这完全不符合性格,我们不会了解,所有证据都消失了。’”[3]53记忆的不可靠也被经常述及,自传《无可畏惧》中巴恩斯回忆童年家庭生活,发现同样一件事情在自己与兄长的记忆中往往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对此问题的理解,身为哲学家的兄长对巴恩斯可能有着一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相信记忆总是错误的‘通常是这样的,根据笛卡尔的烂苹果定律,除非有外部证据支撑,否则记忆是绝无可信的’,我要更容易轻信些,或者说更容易自我欺骗,所以宁愿继续相信我的记忆都是真的。”[7]5相对而言,巴恩斯更感性,这也是他倾向于用文学方式进行表达的原因。他对于语言表达具有天生的敏感:“我的哥哥不相信记忆的根本真实性,我不相信我们给它添油加醋的方式。”[7]29
不可靠与不可靠相遇产生的确定性必然只能是虚假的?历史书写者往往强调文本的唯一性和确定性,这使得历史书写行为本身存在一种根本的伪善;历史阅读者也总是迫切“想要知道整个儿完整的故事,想要知道所有的动机,想要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3]54,这使得历史写作与阅读过程中鼓励和强化一种“合谋共犯”[3]55的关系。确定性——巴恩斯对传统历史文本的批评的焦点——只能遮蔽历史的真相,或阻断人们对历史真相的继续追寻。
二、历史文本的虚构性
巴恩斯认为,必须承认,我们可见的历史文本只能是一种虚构(fabulation),无论是官方历史还是个人历史都是虚构的产物。在其历史小说中,官方历史中的“虚构”发生于各种话语权力场中:与政治息息相关,“历史是胜利者的谎言”, “历史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5]25;与学术息息相关 ,“历史并不是发生了的事情。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套”[6]241;还与性别不无关系,“历史是一个性感金发猛男”[8]113——巴恩斯对历史与性别的关系特别敏感,经常采用女性视角重写历史,他认为“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男性蛮力的偏见,这是指那些充满莽撞小子气质的事情,是关于权利和战争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部分文化的大部分历史里,统治权都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3]57。
当个体作为自我历史的见证人和叙述者,真实性有否保证?巴恩斯对此也表示怀疑:“记忆——有时很精确,有时却完全没有希望——总是不断地被你对自我的过去的重写所打断……似乎有一种修正装置,在你无意识的时候不间断地工作着,在调整着你的过去,将它们修改得更适合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自我版本,在你都没意识到的时候就加入一个段落进行修正。”[9]40因此个人历史叙述也是不可靠的。
在历史哲学领域,“历史真实”自古便是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W.H.沃尔什认为人们对“历史真实”的看法可分为“符合论”和“融贯论”,符合论即认为一个陈述与事实相符合,那么它就是真实的,而任何领域里的事实就是“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1]78,以奥古斯都·孔德为代表,其难点在于难以确立事实和陈述的边界。融贯论认为“如果一个陈述被表明可以和我们所准备接受的其他一切陈述相融贯或者适合,那么它就是真的”[10]76,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其代表。其最大的理论陷阱则在于,如果一切信念都是同等可疑,历史哲学很容易滑入相对主义和虚构主义的泥淖。虽然符合论和融贯论都具有致命的理论缺陷,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代表的沃尔什认为即使采取中间立场也并非无懈可击,它极易受到历史怀疑主义的批判,但作为实践中的历史学家而言,必须选择一种可行的姿态,这种处境必然是矛盾性的:“并不能期待我们去证明过去事件的存在,正如不能期待着我们去证明我们经验到了一个外在世界一样……这并不意味着,要分析过去以及外在世界之类的概念的哲学常识乃是徒劳无益的事,相反的,这类分析可能是真正有启发性的,然而,它却的确意味着,任何要靠给它们发现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基础而演绎出来它们的企图,则必定是要以失败而告终。”[10]87这种困境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也是所有20世纪以后的历史写作者和思考者有可能面临的两难。
1978年,海登·怀特以《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宣告新历史主义的出场,这可以算是后来者面对沃尔什所谓的两难处境的一种绝地反击。怀特在《元史学》中放弃了史学理论家一贯所持的身份意识,坦言宣称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才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11]2,同时,他不再纠结于“历史真实”问题的传统维度,通过进一步将“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于是“事件”便仅仅和“文献档案盒器物遗迹”有关,其他所有一切和历史相关的无不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或者在想象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之中”[11]5。他放弃了沃尔什对于“坚实根基”的焦虑,而大胆将罗兰巴特之“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其作《话语的隐喻》的题词,标志着历史哲学已经通过语言学转向和解构主义真正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回到巴恩斯,上述历史哲学相关的理论背景可以看作巴恩斯历史题材写作背后的宏观话语环境,它所传达出来的对于“历史真实”问题的关注、焦虑、反思、矛盾、背离、超脱、转移等心态的发展变化,正是巴恩斯与同时代人所共同经验到的一种文化气息和氛围,巴恩斯本人选择的是一种介于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元史学之间的历史观。
三、历史与小说
既然历史不过是“虚构”,那它在本质上就和文学无异,巴恩斯曾反复提到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你要么只写出那些历史证据,要么写得更多些,如果你尝试写一个更完整的历史,你就不得不用到虚构和想象……所以历史不得不是一种文学类型”[3]56,“历史只是另一种文学体裁:过去只是装扮成议会报告的自传体小说”[4]10。
巴恩斯认为历史不过是在有限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虚构性创作,它吹嘘彰显着自己的真实性身份,实际上却无从保证。它只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遵循着某种叙事策略。在这种程式化的叙事中,真相反而被牺牲了。小说这一标榜虚构的文体可以从另一蹊径通往真实,巴恩斯试图颠覆的实际上是传统对于“真实”与“虚构”的看法: “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讲述真相,它讲述美丽的,精确的,结构巧妙的谎言,那些谎言中包裹着坚硬的微微发光的真相”[12],“小说当然是不真实的,但它的不真实终结于对更大真相的讲述,更甚于任何其他的信息系统”[9]40, 而“写小说就是为了讲述真相,人们发现这是矛盾的,其实并不,这和政客们相反,他们讲述事实,是为了更好地撒谎”[9]40。因此巴恩斯大量选择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他认为小说反而能够到达传统历史文本难以触及的历史真相。他试图用小说表达真相,历史题材提供了基础:“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础……所有的故事和对于故事的讲述都发生在历史中,你必须将其定位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和一个特定的文化中……必须有个来源,必须有个基础。”[9]39
巴恩斯曾经以大量真实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此类作品可称之为显性历史题材作品。在创作中,巴恩斯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非常重视,譬如:1984年其成名作《福楼拜的鹦鹉》,在虚构的叙事框架中填充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生平和创作轶事,基础来自于他对福楼拜的强烈兴趣和常年反复阅读,其间充满大量的史料细节,开拓性的写作手法甚至曾使时人质疑其文体并非小说而是传记或者学术散文集。1989年出版的《101/2章的世界历史》中也充满大量真实历史事件,如美杜莎沉船事件、阿勒山地震、泰坦尼克沉船事件、1939年圣路易斯号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等,在巴恩斯笔下这些真实事件保持着时间地点上的精确性。1992年出版的“政治小说”《豪猪》(ThePorcupine)讲述冷战时期东欧一不具名国家发生政治变革,共产党领袖佩特卡诺夫(Stoyo Petkanov)被审判的过程。巴恩斯为了写作这一故事,与他的贝尔格莱德友人德米特纳·肯德瓦(Dimitrina Kondeva)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书信交流,并依据其建议对作品反复修改,以期用文学方式还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气氛。当《豪猪》最终在东欧国家地区出版时,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2005年出版的《亚瑟与乔治》拥有两条始于平行最终汇聚重合的叙事线索,其中之一是关于著名作家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生平和创作,另一条是关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历史人物乔治·艾德吉,一位立志成为律师却因肤色被误判入狱的普通印裔英国人。巴恩斯为此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最终收拢住大名鼎鼎的亚瑟的四射光辉,将其背后的“平凡”故事讲述出来。2008年出版的自传《无可畏惧》(NothingtobeFrightenedof)讲述自我成长经历,伴之以历史和文化背景,亦可以归入此类。而2013年出版的《生命的等级》(TheLevelofLife)更是将历史故事和自我经历结合在一起。在这部作品中,巴恩斯首先讲述了19世纪的三位热气球爱好者——英国上校弗雷德·伯纳比(Fred Burnaby)、法国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以及法国作家、摄影家菲利克斯·纳达尔(Flix Nadar)的经历,详细描写了纳达尔在写作和摄影中对美和精确的无限追求以及伯纳比与伯恩哈特之间的爱情悲剧,作品的后半部讲述“我”如何面对妻子死亡的经历,历史中的爱情和作者的爱情经验由此而被置于同一文本中。2007年出版的《时间的噪音》讲述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时期在艺术追求和政治自保之间挣扎的经历,肖斯塔科维奇是巴恩斯极为热爱和熟知的艺术家,和福楼拜一同被列入其无血缘关系的亲人之列,他的音乐作品和生平经历对巴恩斯均可谓如数家珍,即便如此,他依然为创作此部传记小说做了大量的文献工作。
在巴恩斯的创作中,另有一种以隐性历史题材为主题,即不直接以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但是却具有强烈的历史指涉和历史意识的作品,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在《后现代诗学》中所指称的“历史编撰元小说”中即有大量此类作品。1980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处女作《伦敦郊区》(Metroland)便可归入此类,这部作品可算是“成长小说”。它以作者少年至青年时代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同时将1960年代的英国郊区和和法国巴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并置对比,以揭示民族、时代、文化阶级等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中,发生于1960年代的英国保守政治政策和法国的学生运动都成为个人历史中不可或缺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巴恩斯这部处女作相对于其之后的作品现实主义色彩更浓重。1982年出版的《她遇见我之前》(BeforeSheMetMe)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相当历史意识的寓言体小说。在这部表面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历史教师,他对新婚妻子的过往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执拗的探索欲。当这种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毋庸置疑的优秀品质与爱情中的控制欲和嫉妒心纠缠在一起时,他便丧失了理智,也就是说,当历史事件的探索者同时也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的历史发现可能与自身情感和利益息息相关时,历史探索本身便失去了客观性和可控性,于是这场爱情悲剧最终也是历史探索的悲剧,它以主人公自杀的结局提示了历史探索的边界和立场等问题。1986年出版的《凝视太阳》(StaringattheSun)是一部关注女性成长的小说,在关注过去的同时也具有部分未来视角,在虚构性故事中女主人公简的生命历程从20世纪的战争时代一直延续至百年之后的21世纪30年代左右。巴恩斯展望了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科技和伦理革命,譬如大型智能计算机和网络云数据的发展与运用、老龄化严重的社会中老年人口为争取权益而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等,时间以线性的方式向过去和未来两个维度伸展开来,个人历史与世界历史在其中交织,彼此互为背景,这是一部在写作方式和主题选择上均相对传统的作品。在此文本中,巴恩斯尝试用完整而连贯的方式表现其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这种所谓的“传统”不可不说也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这部作品和《福楼拜的鹦鹉》创作于同一时段,在访谈中,巴恩斯曾说两部作品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鹦鹉》是一本向着各个方向发散的书,唯一能将其连缀捆绑起来的是一些蛛丝般细弱但却反复出现的短语和观念。而在《太阳》中成了具体的意象、事件和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深度和意义愈加显现,蹩脚的故事于是便成了隐喻。”[3]68从1989年出版的《世界历史》来看,《凝视太阳》更可说是一部其先期的“反向”尝试——两部作品几乎可以说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实现了对历史的诉说和表达。从读者反馈角度来看,《世界历史》因其反传统的写作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关注。1998年出版、被巴恩斯自称为“政治小说”的《英格兰,英格兰》也提供了一个虚构的或是未来的视角,它以一个虚构的故事来呈现“英格兰民族消亡史”,以此揭示民族历史建构的真相,虽然情节荒诞而充满闹剧元素,但对关注的主题要点——民族及其历史本质却挖掘得相当深刻。2012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终结的意义》看似讲述的是虚构的普通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是巴恩斯通过不可靠叙事等方式,从个人视角出发,揭示了个人历史讲述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与真实和虚构相关的问题。
四、不可放弃的“信念”——历史之真
在用小说文体对历史写作颠覆的同时,巴恩斯从未放弃对历史真实性的信念,他时刻避免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他重申对历史文本的解构和重写只是在寻找更有效的通向真相之路。他表示肯定历史研究和写作工作本身的价值:“我们必须相信,43%的客观真实,总比41%的客观真实要更好一些。”[6]242真相并不因其极其难得就被放弃,而要不断突破曾经的方式,尝试去接近它。他认为不懈地相信并追寻真相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完了,我们就陷入模棱两可,我们就对不同版本的谎言不加分辨的同样看待,我们就在所有这些困惑面前举手投降,我们就承认胜利者不仅有权获得战利品,而且有权控制真相……”[6]243
“真实”向来是历史领域中最被关注的问题,当然不仅限于历史领域。什么是真,是西方哲学界自古以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也是古典哲学中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要载体。现代哲学转向后,人们开始从认识论角度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语言学和现象学是主要思路。 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的“真实”概念,一种是柏拉图式的“真”,他认为只有永恒的“理念”是真实的,因此“真实”首先是恒常不动的,是不证自明的,它依次向下流溢,较为低级地表现为逻辑的或艺术归纳的规律性,最低级的表现才是感官接受到的种种变动不居的现实事物。柏拉图身上集中体现了古希腊人“反历史”的倾向,数学上的胜利强化了古希腊人的这种观念,由此开始了西方哲学以主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主流的历史。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西方人历史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另一种真实观的出现,那就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书写中所建立起来的“事实”,在当时,这种由“瞬间性”组合而成的东西不被认为是“真知”,只能是一种“意见”[13]。希罗多德之所以被称之为“历史学之父”,在于其历史书写和神权历史与史诗叙事上具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而此前的荷马史诗和圣经都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包括各民族早期的神话,都只能算作一种“准历史”。巴恩斯的历史观中可以说同时包含着以上两个层面的“真实”。身为作家,他坚持用小说写作者身份,不排斥虚构,认为虚构中包含着真实,用感性、非理性、审美方式来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追求一种诗性的智慧。巴恩斯曾明确表示传统历史、传记、新闻等写作方式都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而小说本身是虚构,但其中包裹着坚实的“真相”。这种观点可以说更加切近于亚里士多德对于历史和诗的看法:“诗比历史是更富于哲学意味的和更严肃的;因为诗所关心的是普遍真理,历史所讨论的是个别的事实。”[14]可见巴恩斯倾向于将“历史真实”理解为超越历史事实层面的“更富于哲学意味和更严肃的”东西,在实现“诗的效果”的过程中,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在对历史事件的书写中应该注意那些文献、证据和记忆无法到达之处,用想象去填充,或者保留一定的空白和隙缝,以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复杂性。
巴恩斯似乎总在提倡一种非后现代性的“信心”——一种对人的存在具有意义的“信心”——其对象不仅仅是“客观真实”,还包括后现代主义经常予以解构和抨击的核心概念:“我们必须相信爱情,就像我们必须相信自由意志和客观真实一样。”[6]244在巴恩斯那里,这几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世界历史,没有爱便会陷入荒诞……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爱情不会改变世界历史,但可以做一些重要得多的事情:教我们勇敢地面对历史……”[6]244他不断重复:“爱与真,不错,那是黄金搭配……爱与真,这是至关重要的联系,爱与真。”[6]244为“真”“爱”和“自由意志”呐喊——这里明显呈现出一种与后现代一贯持有的对宏大叙事的消解相悖的姿态。上述引文多出自《101/2章世界历史》的“插曲”一章,在2000年接受Guignery采访时,巴恩斯明确承认此处确是为自己立言:“‘插曲’之前,我已经给出了一些一系列各色的历史叙述……我觉得作为作者,是时候在这里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了……”[3]61巴恩斯似乎并未意识到他自己的思想存在某种深层矛盾(虽然以他的敏感和聪慧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智性层面,他的思考和写作方式都倾向于后现代,但在感性和实践层面,他又自觉地趋于保守和传统,或许只是他对这种矛盾不以为意。他从未认可加诸于己身的“后现代主义”标签:“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不,坦白地说,我从没有那样的想法。”[15]
相反,他对自我的定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你不能把我说得好像一个没有是非对错观念的老嬉皮士一样……小说家的部分责任在于尽可能地了解人类的各种可能性……但这不代表对于怎样生活、对于是非你没有强烈明确的个人观点……”[3]11对于历史之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奥威尔主义者,百分百的真相是不可知和不可诉的,但我们必须坚持67%的真相高于64%的真相”[9]40。在对历史的重述中,他运用娴熟的后现代叙事技巧,似乎隐藏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而实际上道德判断可能无处不在。这或许就是巴恩斯小说最值得被关注的复杂之处:对历史的质疑和重写,以明确的后现代姿态和方式,力图颠覆和挑战某种传统,与此同时,对历史之真的信念和道德主义的立场又悄悄使其折返向某种传统。于巴恩斯本人,不论这是一种无意识还是一种自觉,这种矛盾和悖论也许恰巧暗示了后现代自身的某种秘密。
五、结语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在根本上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出现和存在的[13]11,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巴恩斯对历史题材如此重视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历史真实”就是“人的真实”在历史中的展开,因而关注人在历史中的表现以及人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早期创作中,巴恩斯注意考察个体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之后则越来越关注人(个体或集体)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伦理困境和道德抉择,这也是他一再称自己并不是嬉皮士的原因。抛开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技巧和身上的“后现代”标签,他实际上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而这来源于他的人文主义立场。由此,在这位被称为当代英国后现代主义代表的作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人文主义传统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在某种层面上的融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