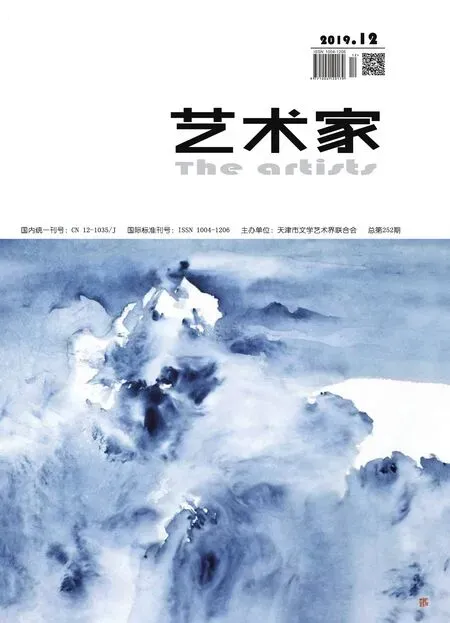当摄像可以重来
——关于对摄像成像后在创作的思考
□陈皛唯 丽水学院
一、自使命出发,向自由探索
1839年,摄影术的诞生无疑展现了一种比绘画更能征服人心的记录方式。但秉承传统观念的文艺家们以坚守艺术的高贵神圣为由,否认了摄影的审美价值。他们恐惧着摄影便捷的“录影”功能为绘画带来的冲击。如同现代主义鼻祖波德莱尔所说:“如果允许摄影在某些功能上补充艺术,在作为它自然盟友的大众的愚蠢帮助下,摄影很快就会取代艺术,或索性毁掉艺术。[1]”不过,并非所有声音都把摄影视为艺术的仇敌。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先驱,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摄影小史》中提出:“这种艺术观排斥了任何技术的进步,这些人一旦面临具有煽动性的新技术挑战,就感到了穷途末路。[2]”
经过时间的洗礼,摄影的创作观念和方法越发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地对客观事物的捕捉外,摄影师们还会运用荒诞、下意识、拼贴、隐喻等手法,表达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当下的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展现形式,已经在业界获得了普遍共识。
二、摄影成像后的再创作
为了不再被摄影与生俱来的使命所束缚,一些摄影师在创作中开始将“摄”和“影”进行分置思考。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不满足于循规蹈矩地利用相机截取人类眼前的世界。他在拍摄工作完成后,常常运用集成的思维,通过在创作手段和技法上融入其他平面艺术的表现方式,使作品容纳不同媒介所聚合的视觉元素,以期创作出“所有人类眼睛都看不到”的画面。达利的摄影创作是一种观念的突围,打破了绘画和摄影之间曾经的桎梏,极具实验性。
“我们可以有两只眼睛,一旦冲破单眼观察的限制,各种惊人的事情都可能出现。[3]”与达利相似,英国著名画家、摄影家大卫·霍克尼也善于按照自己预设的逻辑,用立体主义画派的思维对成像后照片中的画面元素进行分解综合、重叠交错。这种类似马赛克般的画面突破了二维空间的视觉限制,使图像产生了隐约的动感,为人们呈现出从未见过却十分熟悉的立体世界。霍克尼相信,只要有充分的思考,光学镜头的观看方式就会逐渐主宰绘画的面貌。
1965年,美国著名摄影家杰利·尤斯曼提出了“成像后(再合成)”的思论。“成像后”观念的核心内容在于两点:第一,摄影创作通过暗房技术可以容纳非凡的想象力;第二,影像的后期再加工可以完全打破摄影师按下快门前的拟设画面。
同是对拍摄完成的照片进行再创作,尤斯曼相较于霍克尼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在快门按下前并没有预先构思摄影作品的主题。他把象征生命和周期的树木、净化和变化的水流、自由与孤独的天际等意象,整合成了一个视觉母题,频繁地在自身建构的影像世界中分享。譬如,在图1和图2两幅作品中,虽都含有手和鸟巢这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但尤斯曼凭借有序而精准的把控,搭建出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前者扎根于大地的手臂坚定而有力,聚拢的手掌昭示着能为鸟巢中的新生命提供温暖安宁的成长环境;后者则删减了代表稳定的手臂,这里手指的状态显得更为舒展,掌心的鸟巢与天空中正在翱翔的小人相对应,体现了生命对自由的渴望。尤斯曼的成功为“摄影的重来”提供了一种确切的实现路径。他的“成像后”理念也被视作美国观念摄影的一个里程碑,引领着无数后继者对图像后期的各种可能性不断探索。
20世纪末,数字化艺术将社会全面带入了“读图时代”。运用计算机软件对一次拍摄成像的照片进行再加工,成了当时非纪实类摄影创作的主流技法。毫无疑问,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为摄影表达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它不仅为摄影师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而且促进了摄影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学科的交融。
三、寻找属于自己的歌
如今,技术的更新和发展已经远超人类既有的知识和认识。一些前所未见的影像表达出现在图片后期技术的操控下。在科技的强势介入中,一张静止的照片甚至可以化为一段三维的动态影像。这时的摄影再创作似乎变得更为便利和高效了。

图1 手·土地·鸟巢

图2 手·天空·鸟巢
诚然,技术的突破可以为摄影带来新意,但在大众文化消费的导向下,许多创作者对作品本身个性的诉说变得含糊不清。这些图像的二次创作逐渐沦为了一种机械化的流水生产。它们期冀以华丽的外观来赢得观者的一时之趣,却不料其中越发相似的视觉构成已在潜移默化中消减了人们的观看兴趣。被誉为天才摄影家的马里奥·贾科梅利认为,摄影的再创作如同乐曲的编写,最终的目的只为奏出一曲属于自己的歌。
结 语
总而言之,图像由心而构,“在外物中寻回自我”才是摄影的应有之义。如此,“摄影的重来”也能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