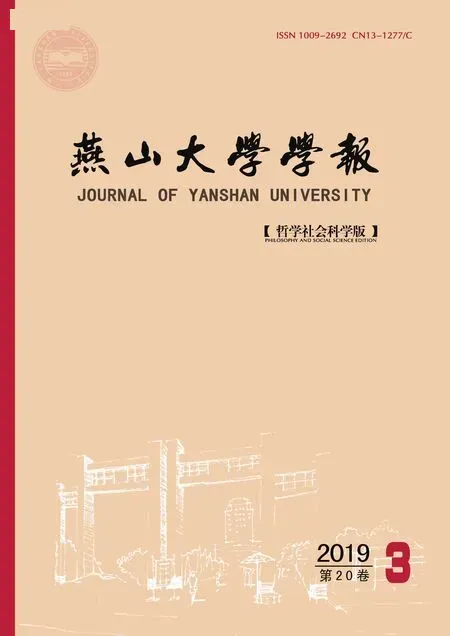儒家诗学在朝鲜王朝前期的发展
——以“文道论”为中心
朴性日(韩)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一、引言
“文道论”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概念。从韩柳古文运动时期起,文人开始以“复古”为口号提出“文道论”。至宋代,文人全面在儒家观念立场上探讨“文道论”,渐渐确立“道统”。明代形成的“复古风”和“拟古主义”是基于“文道论”建构出来的。郭绍虞指出,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造就了一辈古文家和道学家的文。①张少康指出了道学家对文学创作的否定的特征。第一,对文学创作上情和理的关系,做足了错误的论断,强调说理而否定抒情,提倡言志而反对缘情。第二,在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关系方面,亦即质和文的关系上,道学家的观点表现了突出的重质轻文、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片面性。第三,在文学观念上复归到古代文学和非文学混同为一的状态,取消了文学的美学特征,抹杀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第四,否定了文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把它变成了抽象的理学心性义理的图解,使之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这样就把文学和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隔离开了。②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文与道”关系的分析以及探讨,不仅仅是中国历代文论家所追问的问题,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古代朝鲜半岛同样也在追问“文与道”间的关系。13世纪后期全面接受性理学,后来朝鲜王朝从开国到灭亡,关于“文与道”的主张连续不断。建国初的朝鲜王朝标榜性理学之邦,文学主张就自然呈现出依据宋代性理学的美学观念。朝鲜初期文人徐居正文中虽然用“文以贯道”,可是他解释的文道实际上是接近于周敦颐意义上的“文以载道”。由此可知,朝鲜王朝前期是没有“贯道”和“载道”间的明确区分。16世纪道学派与词章派之争,突出朝鲜文人对文道论的见解。16世纪之后形成了以道学为主的美学观念和学苏黄的海东江西诗派。
高丽末朝鲜王朝前期文人李詹(1345—1405)在《历代有文者之来历》一文中说道:“问文者,贯道之器也,必深于斯道,然后为能至矣。有文字来,为文者甚众,而奇崛变化称庄周,幽抑愤郁称屈原,其二子之立言,果合于斯道欤?古今天下,盛称西汉之文章,抑未知奇峻富丽,马迁、相如其人欤?明达专醇,贾谊、杨雄其人欤?迄于大唐,韩退之、柳子厚之辈,各以日光玉洁,玉佩琼琚,见称于当世,其文之懿,可得与庄、骚并论欤?”③在其述中不难发现,高丽与朝鲜替代之际时的文人李詹虽然指出了“文道”与古文(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的关系,可是这只不过是比较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在文风上的优劣而已。在李詹对庄子和屈原之文是否符合“文道”的质疑中,可看出朝鲜王朝文人曾有过追问哪家的古文能够完美呈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文道”。也即是说,建国初期的朝鲜文人们尝试区分“贯道”和“载道”,其意义不在探究道统的渊源。道统之争后其意义更显明了,无论是“贯道”,还是“载道”,都在肯定文和道的作用。虽然这场“道统之争”缠绕着当时的政治党政,可是在文论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基于此,本文梳理出朝鲜王朝前期文论流变过程,特别是朝鲜王朝对“文道观”的接受以及流变。进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分析朝鲜王朝文论前期如何呈现出“文道观”。
二、“贯”与“载”间
公元1289年,高丽王朝后期忠烈王时期的文人安响与白颐正在元朝学习儒学,将儒学经典带到国内后,在高丽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颇为有趣的是,在高丽王朝全面接受儒学思想前,文论中出现过文道论。当时文人崔滋《补闲集·序》一文中揭示道:
文者,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然欲鼓气肆言,竦动时听,或涉于险怪。况诗之作,本乎比兴讽喻,故必寓讬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类。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④
通过崔滋对文的定义“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可知,他认为文只不过是追求“道”的载体而已。可是他在后部分谈及作诗时并未否定作诗上的修辞技巧。首先,从字面意义看,蹈字比较接近“贯”的意思。崔滋的文道观与王通在《中说》提及的文道⑤特征很相似,表明文与道的从属关系。从作诗观上,可视为与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古文精神有相同之处,原文中的“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和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文集序言中的首句“文者,贯道之器”⑥一脉相通,和韩愈在《题哀辞后》中的“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⑦亦有相同之处。朝鲜王朝末期,学者金泽荣在他的《韶濩堂文集》中梳理古代朝鲜半岛文风史道:
吾邦之文,三国高丽,专学六朝文。长于骈俪。而高丽中世金文烈公,特为杰出,其所撰三国史,丰厚朴古,绰有西汉之风。其末世李益齐,始唱韩欧古文,尤长于记事,再修国史,韩朝所作高丽史,实皆益齐之笔也。李牧隐以益齐门生,始唱程朱之学。而其文多杂注疏语录之气。自是至吾韩二百余年之间。⑧
金泽荣在上文中肯定,自高丽末李益齐开始提倡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体,到了李益齐的门生李牧隐之后,开始倡导宋代儒学。换句话说,他们是朝鲜半岛古文学史上第一批中国古代文道观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虽然崔滋是朝鲜半岛文论史上第一个提出文道论的,但难于断定其观念的源头。能确定的是,崔滋以后的文道观深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都是在批判当时浮华的文风,开始分析文与道的关系。李牧隐诗文《可怜哉》中的“所以载道者,而为物欲役,厮养不如也”显示了他的文道观,此后的文道观,不管是朝鲜王朝的开国文臣、还是反对开国的文人,渐渐崇尚宋代儒学的文道观。李牧隐的门生郑道传在《京山李子安陶隐文集·序》一文中揭示文道观道:“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诗书礼乐,人之文也。然天以气,地以形,而人则以道,故曰文者,载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诗书礼乐之教,明于天下,顺三光之行,理万物之宜,文之盛,至此极矣。”⑨郑道传作为朝鲜王朝开国功臣,他的文道观成为朝鲜前期文论的基础。在他的文道观中能看到周敦颐在《通书·文辞》里的“贤者德以学而至之,是为教”⑩的思想。郑道传在文中认为文道要有教化功能,一般来说,在传统儒学家那里,文为圣人参照天地之理所形成,圣人与天地之道的如此关系必然要求圣人之道的载体之一——文学作品的“文”来反映圣人承继天地之道永恒的规范文理⑪,文道观在此意义上能具备教化功能。朝鲜王朝开国前,没有明确区分载道观和贯道观,并没有从教化功能的角度探讨“文”与“道”的关系。由于建国初的朝鲜王朝想要构建“性理学之国”,建国初期的朝鲜文坛便尝试站在程朱学的载道观上进行探寻。与郑道传同时期的文人权近在《郑三奉文集·序》一文中揭示:“文在天地间,与斯道相消长,道行于上,文著于礼乐、政教之间。道明于下,文寓于简篇笔削之内,故典谟誓命之文,刪定赞修之书,其载道一也。”⑫与郑道传一样,权近也主张“文道”的教化功能。权採在《圃隐集·序》梳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道观”变迁史道:
文以载道,故诗书礼乐。威仪文辞。皆至道之所寓也。三代以上,文与道为一。三代以下,文与道为二。盖诗三百。蔽以思无邪之一言。夫子之文章。无非天理之流行。所谓有德者必有言。而文与道初无二致也。汉魏以降。以文鸣于世者若王,徐,阮,刘,曹,鲍,沈,谢。下逮唐宋刘,柳,苏,黃之辈。代各有人。然不过风云月露。模写物状。倂俪沿袭之工耳。其于道也。槩乎其未有闻也。故其文章虽或可取。夷考其行,皆无足论。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而文与道始歧而为二矣。吾东方礼乐文物。侔拟中华。⑬
权採简述了中国文道观史,后部分表明朝鲜半岛就是在摹仿中国文论,但没有确切分析文道的接受以及流变。在原文中值得关注的是,他简述文与道关系时,用了“文与道为一”和“文与道为二”。若从传播史的角度去分析,朝鲜王朝属于后者“文与道为二”。前几段分析崔滋“蹈道之门”时,崔滋并非主张文道合一。全面接受儒学思想后,当时的古文家都倡导唐宋古文运动精神。再者,朝鲜王朝初期文道论的第一个特征是属于文与道为二。成宗时期,成宗实行“崇儒抑佛”政策,这时候的文道观更接近于儒学意义下的文道观。当时文人徐居正在他的专著《东人诗话》和《东文选·序》中对朝鲜半岛文风史有更为详细的梳理:
高丽光显以后,文士辈出,词赋四六,秾纤富丽,非后人所及。但文辞议论,多有可议者。当是时,程朱辑注,不行于东方,其论性命义理之奥,纰缪牴牾,无足怪者。盖性理之学,盛于宋,自宋而上,思孟而下,作者非一,唯李翱,韩愈为近正,况东方乎?忠烈以后,辑注始行,学者骎骎入性理之域,益齐而下,稼亭、牧隐、圃隐、三峰、阳村诸先生,相继而作,唱明道学,文章气习,庶几近古,而诗赋四六,亦自有优劣矣⑭……六经之后,惟汉唐宋元皇朝之文,最为近古。由其天地气盛,大音自完,无异时南北分裂之患故也。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高丽,极于盛朝。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贯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规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則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矣。如或文于文,不本乎道,背六经之规,彟落诸子之科臼,则文非贯道之文,而非今日开牖之盛意也。⑮
与郑道传和权近不同,徐居正在这两篇文章中用“况文者贯道之器”和“文非贯道之文”,表明他的文道观有两面。一般意义上说,贯道是指自文而出道,而载道是指传达道的手段,若按照这种说法来阐释后世的“未纯乎道”比较偏向于贯道,而今之学者“心与道”则偏向于载道。我们能看出徐居正虽然没有直接用“载道”这个词,但他的立场多站在“载道观”这边。在这里,我们能看出前期的贯道观和载道观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王朝前期的一系列文道观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颇为相似。刘勰在《原道篇》中揭示圣贤在文中如何处理“文与道”的关系:
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⑯
从原文中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难以断定刘勰的文道观到底属于载道,还是贯道。可是,我们能看到《原道》里的文与道的关系是通过圣人而形成的。正如唐宋文道观的演变,在朝鲜王朝树立儒教性理学之国的过程中,文道观不仅在政治理念上,还在文化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标榜文治主义的朝鲜王朝初期,文道就是一定要具备教化效果的观念。到了朝鲜王朝初期的最后阶段,对文道观念渐渐有了区别。建国前期的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文学观念主张上产生了冲突。有趣的是,这不只是稳健派和激进派间的观念冲突:一个是对文与道关系看法上的冲突,另一个是追求理想和现实间的差异。
三、“道学派”与“词章派”之争
成宗时期,随着参与国家政治的词章派人士增加,到了中宗时期,在文论观中出现了立足于朱子学的两派:一是重道轻文的“道学派”,另一个是重视“文”的现实效用的“词章派”。建国初,在文论上没有道学派和词章派间的冲突,其原因为政治体系上重视道学派,而文化方面上支持词章派。道学派主张以经学及“道”为主的学风,与道学派不同,词章派虽然认可经学的重要性,但主张面对时代现实。关于道学派与词章派,成宗时期的成伣在《慵斋丛话》中认为“经术文章非二致”,并指出“道文合一”,可是他批判词章派不知以经为本,道学派不知作文⑰。观察成伣的表述,道学与词章显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道学派与词章派文士对科举制度的看法不同——道学派认为采取作诗赋的科举方式有问题,而词章派认为若采取经学方式考核,难以考核考生的实际实务能力。道学派与词章派的对立不局限于此,在文道观上也有差异。前期道学派的代表人物金宗直在《尹先生祥诗集序》一文中解释经与文的关系道:
经术之士,劣于文章,文章之士,暗于经术,世之人有是言也。以余观之,不然。文章者,出于经术;经术,乃文章之根柢。譬之草木焉,安有无根柢,而柯叶之条鬯华实之秾秀者乎。诗书六艺,皆经术也,诗书六艺之文,即其文章也。⑱
金宗直不赞同成伣的说法,他认为文章是从经术而生成的,所以经术乃是根源。实际上强调的是“道主文从”。金宗直解释文章与经术的关系和朱熹在《论文上》提出的“文者,道之枝叶”⑲相似。颇为有趣的是,金宗直不是完全排斥文的功能,在《永嘉连魁集序》中肯定了诗赋的教化功能⑳。在这点上,金宗直认可文章的观点有二程的作文害道特征㉑,其理由为:在他那里,文是作为传达经术的道具。那么,道学派意义下的文道与建国初期所主张的载道观一样,是主张文从道出。与金宗直一样,同属于道学派的赵光祖在《谒聖試策》云“夫道也,本呼天而依之于人”,表示人作为道的媒介,这里的“人”是指“人工”的,指的是“文”。与道学派相反,词章派重视文。《中宗实录》记载了当时的道学派和词章派的意见对立:
南袞曰:“今者以科举之文为廢学而害正学云,然科举之学,三代以下,所不得廢也。若取士如三代鄕擧、里選,以德行、孝悌为本,则可矣,不然則不得已,以科举取之矣。虽科举取士,而亦有賢者出焉,終为君子大人,如宋之程子、朱子,皆由科目,出者也。且为词章者,豈盡浮薄;治经学者,亦豈盡不浮華哉?尚词章之事,其来已久,所为隋唐、宋进士,是也,以科目而猶可为三代之治矣。唐时贵进士,而贱经学,至有诗句曰:‘焚香禮进士,撤幕待经生。'如此习尚则非矣。词章、经术,所当如一,不可偏廢也。”㉒
南袞主张重视词章。他拿中国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事例披露词章的重要作用,主张词章和经术为一。在这里,我们发现自成宗时代起,朝鲜文人阐释文与道关系时,就使用经术与词章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经术不完全等同于道,而词章不完全等同于文,是因为道学派认为经术也有文章的作用,而词章派肯定词归于道。金宗直的门生金驲孙与南袞一样,他的文道观偏向于词章派。他认为词章本身不是才能,但是具有道的人一定会有文,语言精密而使人产生感奋称之为诗,所以词章不是违背道的㉓。粗略一看,这两种词章之意有差异:前面的词章指的是“为文而造情的”,而后面的词章指的是“文能宗经的”。与道学派同样,词章派肯定了作为道的经术,而与道学派文士不同的是,词章派文士主张包含“道的词章”。也许,在道学派看来,词章派有贯道的一面。道学派批判词章的立场,好比朱熹回答才卿问的怎么看李汉的文以贯道问题。朱熹回答云:“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㉔。道学派文士虽然没有直接区分文与道,但在肯定文作为媒介的基础上,道学派的立场多站在文以载道和作文害道。词章派文士曹伟提出“文与质”,主张文是体现出“质”的,没有文就不能表露“质”㉕。曹伟肯定了文从质出的同时,也肯定了文与质是并存关系,而这是与道学派很大的区别。朝鲜王朝前期的文人权近在《提州乡校记》一文中提及词章的必要性道:
为学之方,具载方册,然其要,只在乎正心术而已。心术既正,然后事亲事君,理宫理民,百事可做。不然则虽能读圣,能工华藻之文,终亦不免为小人之儒矣,可不免哉!㉖
在前一章节笔者提及了权近在他文章中提出载道观,但他实际上更偏向于词章。从文道观的接受史看,词章派乃是文道观的流变,甚至它的流变程度比道学派剧烈一些。道学派在表述上稍微有一定的流变程度,文与道关系上仍然秉持“载道观”。与此不同的是,词章派包含贯道和载道。另一方面,词章派的文与道关系可以从柳宗元的“明道观”的角度来探讨,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书》中提及了“道借辞而明,辞通道而明”㉗。在此意义上,可视为词章派文道观多偏向于明道观。道学派与词章派在“文与道”关系观念上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朝鲜王朝前期文论中的唐宋古文运动的折射。道学派与词章派在观念上的复杂关系不仅限于古文与经学之对立,也体现在“文道”和“文与道”观念上的差异。
关于区分文与道,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Liu)表示:至于表现的和实用主义的批评家区别,则体现在对文学和个人性情关系的认识上,前者把文学看作为作家个人性情的表现,而后者却把文学视为控制、调节读者性情的工具㉘。廖可斌教授认为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刘若愚和廖可斌都表示了中国文道论的复杂性。㉙笔者认为,古代朝鲜王朝前期文论中的“文道论”恰恰如此。不只在前期,到后期虽然在读解文与道关系上比前期明确,但仍然处于文论论争的主题范围。
总之,词章派的胜利终结了朝鲜王朝前期的理念之争,但并非彻底的推翻道学派。这种对立只不过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导致的两派对立而已。从文论的角度去看,就是载道观和明道观间的对立。若从《文心雕龙》的角度比喻,则是宗经与通变之对立。
四、结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接受阶段到前期与中期之际的道学派与词章派对立,我们发现前期的文道观流变史和中国文道观演变史一样,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文道观。与中国文道观不同的是,朝鲜王朝在同一个时段产生过观念差异。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没有发生过贯道与明道观念上的对立,至北宋周敦颐和二程间在载道观上同样没有过对立关系。相较起来,朝鲜王朝前期的文道观颇为独特。前期的文道观影响了中期的文艺思潮:道学派的文道观引起了尚古主义,而词章派的文道观发展出海东江西诗派。到了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朝廷大力支持道学派,但是在文论上仍然出现区分贯道和载道的尝试。从中期到后期就不再出现对文与道关系见解上的对立。
朝鲜王朝前期的文道论,其接受和流变特征比较明显。当朝鲜文人在文章中表述文与道的关系时,实际上没有确切区分贯道和载道,引起了文与道观念的分歧。拿追求圣贤之道的程度来比,词章派的文道观没有道学派深。倘若他们的争斗在文坛上继续下去,词章派还是能获胜。道学派虽然强调“文从道出”,可是从获取道的渠道去考虑,道也是从文而来的,从而经术仍然属于文。简而言之,道学派只肯定作为教化的文,否定了作为艺术的文,这是导致失败的原因,然而在尝试体现道文为一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意义。与道学派不一样,词章派不仅肯定了作为教化的文,还肯定了作为艺术的文,也就是说,词章派的文道观较为全面。
注释:
①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30页。
③ [李朝鲜]李詹著:《双梅堂先生箧藏集·卷之二十二·策问》。引自“韩国古典信息库”电子资源: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031A_0040_020_0020。
⑤ [隋]《天地篇》:“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乎济意。”见《中说译注》,张沛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⑥ [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⑦ 《题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于今者?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04-305页。
⑧ [李朝鲜]金泽荣著:《韶濩堂文集·卷八·杂言四》,1925年。引自“韩国古典综合电子信息库”资源: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658A_0150_010_0040。
⑨ 收录在[李朝鲜]徐居正编:《东文选·卷八十九·序》,本文选成书于1478年。引自“韩国古典综合电子信息库”资源: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GO#/dir/node?dataId=ITKC_GO_1365A_0920_010_0100。
⑩ 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宋]周敦颐撰:《周子通书》,徐洪兴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⑪ 李伏青著:《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
⑫[李朝鲜]权近著:《阳村集·卷三》,民族文化推进会编,,1997年,第44页。
⑬ 收录在《东文选·卷九十三·序》。
⑮ 这是主编者徐居正本人的序文,详见[李朝鲜]徐居正编:《东文选·序》。
⑯[南梁朝]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29页。
⑰ 《慵斋丛话序》:“经术文章非二致。六经皆圣人之文章,而措诸事业者也。今也为文者不知本经。明经者不知为文。”[李朝鲜]成伣著:《慵斋丛话·卷一》,1525年。引自“韩国古典综合电子信息库”资源: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GO#/dir/node?dataId=ITKC_GO_1306A_0010_000_0010。
⑱[李朝鲜]金宗直著:《占毕斋文集·卷一·尹先生祥诗集序》。引自“韩国古典综合电子信息库”: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066A_0240_000_0300。
⑲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箇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宋]黎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3319页。
⑳ 《永嘉连魁集序》:“文章,小技也。而诗赋,尤文章之靡者也。然而理性情。达凤教。鸣于當世,而传之无穷。诗赋实有赖焉。”[李朝鲜]金宗直著:《占毕斋文集·卷一 》。
㉑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
㉒[李朝鲜]《中宗实录·卷二十九·12年8月癸酉(明 正德 12年)》。引自《朝鲜王朝实录》电子资源:http://sillok.history.go.kr/id/kka_11208030_007。
㉓ 《题权睡轩关东录后》:“若夫词章特末矣,然有道者必有言。言之精而有以感发乎人者为诗,则词章亦非与道背驰者也。”[李朝鲜]金驲孙著:《濯纓先生文集·卷一·杂著》,1512年。引自“韩国古典综合电子信息库”: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092A_0020_020_0070。
㉔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5页。
㉕ 《善山养素楼记》:“素者,质也,俭也。文质虽不可偏废,而非质文无所施。”[李朝鲜]曹伟著:《梅溪先生文集·卷四·记》,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影印,1988年,第331-332页。
㉖[李朝鲜]权近著:《阳村集·卷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編,,1997年,第231页。
㉗ 《报崔黯秀才论为书》:“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唐]柳宗元著:《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0页。
㉘[美]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㉙ 廖可斌:“‘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光明日报》,2016年7月15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