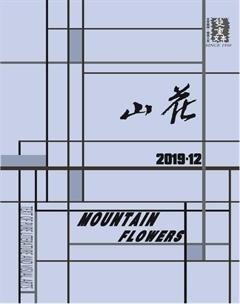中间
朱强
我从小对于“中间”就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比如我六岁时,随我舅舅去凤岗水库度暑假。作为水库承包人的舅舅在水库旁边盖起了简易的木头房子。临近傍晚,红色的云倒映在水库中间。我表哥很满足地站在岸上观看,但是作为有去往“中间”兴趣的我却死活要舅舅用木筏把我送到水库中央。又比如长辈们在客厅里说话喝茶,我总是很陶醉于端一把小椅子坐他们中间。享受在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从小有去往“中间”的心理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是一种极度的自卑或者自信,抑或某种冒险精神与求知欲的体现。总之,到各种中间去,已成为了我在处理外部经验时的一种常规做法。可是,我从没想过,要去大坝的中间。因为,在我的世界中,只有床的中间,客厅的中间,电影院的中间,人群的中间和庭院的中间。大坝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太远了。我只在有限的知识框架里找到像大禹治水啦,李冰父子啦,许逊啦;还有都江堰啦,长江三峡啦,葛洲坝啦——这些仅仅停留在词汇本身。不过,它们基本上都和伟大有关,和人的力量战胜自然有关。在这些伟大的工程中,我看到了人民的伟大,看到自然正在被人的力量改造成人所需要的样子。而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要到伟大的中间去。因为,在伟大的中间,我就觉得自己越发的渺小了。谁愿意去看见自己的渺小呢?并且,我也实在没有想过大坝还有所谓的中间啊。在我的概念中,它不过是一个类似于闸阀的东西,骄傲地放在河床中间。于是水便不流了。它不像李白手里的刀,抽刀断水水更流。它是具体的存在。它和水流以及河床的关系是果断的,并不像文人的性格,优柔寡断。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是具有银色外表,没有所谓的中间一说,它的外表就是它的中间。表里如一。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内脏,没有情感。浑然一体。只是个类似于“大块”的东西。大块假我以文章,而它什么也不能拿出来作为给予。然后,这大坝就在我心里定格下来了,成了实验室里的标本。
直到某日。风飘飘而吹衣。一行人在大坝面前垂手站立。这些人的目光徐徐地伸向不远处的大坝。这所来的,都是文人,他们像完成古代的一次雅集,从幽暗的书斋来到山水之间,白皙的脸与干净的手指暴露在孟夏的阳光中,像被水洗过了一样。一同被暴露在阳光下的,还有深刻的思想与敏锐的洞察力。那一刻,大坝和众人见证了,平地发一声吼,响声振聋发聩。文人们心潮逐浪高,开始了各种腔调的抒情。原来,这大坝并非头脑中沉睡的那一个。
这是峡江,天蓝得不怀好意。水在河床里流。对岸是矮山,石头山。像用了千吨万吨的铁水浇筑。那么结实的河床,像一种不可撼动的权力,水被它统治了。工程局小王穿白色衬衫,血气方刚,左耳大于右耳,厚厚的眼镜片背面是两个黑色瞳孔。诗人甲问问题,他回答;乙问问题,他回答。这河,这大坝,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被具体化了,成了一大堆数字与专有名词。我紧跟其后,内心茫然,表情回应得却特别及时,点头与微笑总是恰到好处地递出。比如,当初大坝在选址问题上有做过哪些考虑?一诗人问。小王拧一下眉。这也是他化解问题的惯常动作。同样是眉头,在这个世界上,文人的眉头总是越皱越长,而工程师的呢,却越皱越短。因为诗人向来是问题的制造者,而工程师恰好是问题的消灭者。我的目光随他手指方向移至河流上方,万顷碧波在眼里荡开了。那是千里赣江的最窄处,也是大坝选址最先考虑到的位置。可是,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方案终于被否了。否则大坝将承受起巨大的水压,整个工程的难度系数势必增加。那就必须找一处相对较窄,但又不是太窄的河道,既能节约施工成本,又能够保证安全。这当然不是一个作家凭想象力所能完成的,它必须依靠一个个力学公式去作准确的测定与确定。大坝的位置终于被确定下来了。没过几年,图纸上的大坝就矗立在河流中央。水断了,奔腾的赣江停下来。水在一侧沿着高高的大坝上升。汹涌的河流被驯化了,它的野性与放荡被消灭了。
通往大坝的铁门开了,雪白的阳光被拒之门外。眼前,是一个封闭形建筑。一根一根铮亮的钢架,被油漆刷过的混凝土墙在眼前亮了。那是巨型动物的胸腔。你就在这些肋骨的中间一根一根地数着。小王告诉我,混泥土墙背后,正埋伏着十米深的河水。水,一层层压下来,大坝底部被巨大的水压推动。那是十万只巨人的手臂!可以想象,如果墙是透明的,就可以看到绿色的水以及裹挟在里面的众多生物。这些生物的视觉普遍很弱,对于任何人的观看向来无动于衷。然而,那大坝墙终究不是虚无的,终究是用一吨又一吨的混凝土夯成的。在这遮蔽中,我们终究不能感受到它承受的压力以及这背后隐藏的危险。在大坝中间,危险被深藏起来了。因为,危险你看不见,你可以在这歌唱、朗诵诗歌,甚至安静地看电影、翘二郎腿、打瞌睡、放松地伸懒腰或谈恋爱。在大坝中,每种人的心态终究是不一样的。即使,同样意识到坝体背后的汹涌与激烈,每种人,他们各自对忧患与危险的认识也大相径庭。想象或虚构一种忧患和认识并剖析一种忧患,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后来,你又通过楼梯,被带到大坝深处。在狭窄、潮湿的昏暗通道中,你越走越深。你无法获知自己已经抵达河床的哪一处了。你像鲇鱼。外面的世界被隐藏起来。但你明白,水就悬挂在你身体的上方,浩浩汤汤的河水正从你头顶经过。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领域,样子有点像小说里的龙宫。在通道顶部,你看到蓝绿色的铁管。尽管上面标注的符号是陌生的,你却感到欣喜,自认为可以将它们抓住。但假使你已经抓住。它们的两端又将通往哪呢?你被更大的疑惑吞没。问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或许也意识到,处于此地,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虚妄。一个发电站一年能发多少电?大坝建设要耗多少资?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整个气氛沉陷在一片死灰般的安静中。所有人的耳鼓都重复着发电机工作的声音。那是大坝的心跳。在微弱的光线中,工程师与作家,它们眼神间的秘密交流被切断了。一切都断了。只有手机在疯狂扫射。同行者一次次地找角度,试图拍摄到那个真正属于大坝中间的部分。他们像一个个优秀的艺术家。样子仿佛已经到了江面、城墙、群山之巅或某个热闹的十字路口。盡管他们对于艺术都表示出了极大的虔诚,可镜头中的所有肖像无一不是虚构的,无一不是来自想象。在工程师的世界中,无论是剪力墙、钢屋顶还是水流都连接着精微的刻度与精确的数字,任何伟大,都需要依靠精密仪器去完成。可是,散文家用一个念想就完成了。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他们甚至可以虚构出一百座这样的大坝。
我想,其实这背后站立的,是两种不同的大脑,当然,也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与世界观。一万颗不同的大脑在大坝中就会有一万种不同的念头。这是事实,也是人在世界中间所享有的最起码的权利。大坝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作为一件伟大工程,它的建设,无疑让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感到骄傲。这样一条流淌了不知多少亿年的母亲河,终于掌握在她子孙手里了。无论防洪、水利灌溉、还是发电与航运,它都扮演起重要角色。这样的话语多数被写在了教科书与地方政府的宣传册上。可是,当你果真到了大坝中间呢,你可能被它的某个局部,某个细节给吸引,你在这种吸引中感受着世界的宽度,但你也可能因为意识到某种无形的危险而深陷于恐惧之中。也许,这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活在感官与情绪中的人最真实的部分。我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世界并不是一元的。世界并不是稳稳地射在箭盘上的那一支冰冷的箭,并不是判断句与句号。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一元论就可以解释得清。比如,关于大坝,它绝不只是一个重大工程,绝不只是挖土机、起重机、大卡车、图纸与建筑工人参与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各种复杂因素。比如,移民、拆迁、抬田工程、古建保护。这些看不见的事物共同构成起真实的大坝。巴邱镇,一个现在被沉在水底的小镇,一个钉子户在家里备的不是煤气罐而是几大坛子的酒,它指定要某某领导来家里陪他痛饮一壶,他才同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你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很难想象类似事件在大坝建设中所占据的分量。也许,这就是世界的横切面,就是人心。所谓中间,大概也就在于此。我想,即使大坝果真是一个类似大块的东西,即使它的外表就是它的中间,它也始终拥有一个独立的“中间”。存在就是它的中间。
在大坝中转了多少圈,竟忘了。鼻子里都是潮湿水汽,像吃了一口冷香丸。工作人员站立在门口,把帽子收回,好像在收回一种看不见的权利。门外的世界在阳光的照射下白得晃眼。白光和门内的暗影在门槛上划上了一道线,线条硬朗而明确。工程局小王和一个作家朋友不知为何都笑倒在门前。此刻,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被这奇怪的笑声融解。我想,任何领域,它们中间,都可能存在这样相互重叠的点。任何冲突中间,都可能存在交集的部分,落于此点,大家的观点与感觉是一致的。科学家自认为在用生命解释真理,而文学家眼中的世界呢,总是由道德和理想构成。他们都自认为处在世界中心,已掌握某种真相。可是,当处于其中,他们又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始终都只是自己,看到的始终是世界在自己内心屏幕上的成像。走出大坝,猛烈的阳光刺进双眼。你像遭遇了刺客,眼睛里一阵漆黑。世界被短暂地关闭了。几秒钟后,你又陆续地看到蓝天,看到孟夏的绿树,青色的水流。世界再一次地回到你的感官中。你习惯性地刷起了朋友圈,作家们陆续地把大坝中间的照片晒出来。他们中间,没有告密者,但所有人的行踪都被暴露了。
然后,车遥遥以轻飏,你就告别了大坝。这些年,你总是在各种告别中一次次回到那间熟悉的卧室。此后,大坝时常会从你的梦境中出来。在梦中,你并不能立马作出判断,那是什么?你被囚于黑暗之中。这是哪呢?外面的世界成为未知。梦醒了,你看到绿树蓝天。昨晚的画面又使你想到在大坝中经历的一切。就这样,你在这中间自得其乐了一段时间。某天,你又被另一波人从你的城市带出去,去往另一个城市。这是诸暨。西施的庭院。西施当然没有在西施的庭院住过,西施的后裔也没有在里面住过,住里面的,是一种对于美的持久的想象力。我觉得拥有对美的发达想象是一个时代繁盛的标志。西施殿后面的医院搬走了,剩下了一个镂空的水泥建筑,门窗洞开,据说很快也会被装修一通,改造成西施纪念馆的一部分。也许是痛苦与美放在一起,就让人对美的欣赏显得拘谨。现在,水池里的荷叶出水已经很高了。我觉得西施也就是荷花的样子。荷叶罗裙一色裁。那时西施的脸上,也应该长着现代女孩爱长的青春痘。豆蔻年华,不长点痘总觉得有点虚度了光阴。今年荷花还没有来得及开,池子里只是碧绿的叶。莲叶田田,一张一张的莲叶疏密有致地叠在一起,阳光从庭院的上方照下来,照亮了西施雪白的脸。深浅不一的绿色也照在我脸上,使我眼睛里布满了绿色血丝。用一个巨大的园子来纪念一个女人,這样的事在别处并不是没有啊,更何况这是西施,一个长久地被作为天下第一美人来供奉的对象。当然,西施的美并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西施作为一个真实的女人她在吴越之间,在几个男人中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心境。人总是活在人与人中间的。因为人扮演着中间的角色,情绪也总在痛苦、欢喜、愧疚之间纠结,即使寂寞者李白也活在“对影成三人”的中间,这也许是有关于人的最诗意的“中间”。但西施在这几个男人中夹着,像夹心饼干一样夹着,并不怎么好受。吴国和越国之间,仇恨无论多大,其实和一个民女都没有太大关系。按理来说,享受正常人生的西施应该是织一织布,浣一浣纱。她年轻时的理想,也许就是在苎萝村附近找一个结实善良的男人,结庐造屋。门前种上桃李,阳春布德泽,桃李灿烂。儿女绕膝,安静地过她的日子。
我在西施殿的柱子下仰起头,看见了西施的蜡像。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西施的目光对视。好美的人啊。当时给西施塑像的师傅会不会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呢。他用一个男性的审美,借助某种强烈的情绪,塑造出这样一个美人。我没敢多想,早餐没来得及吃,头晕。美也是让人头晕的东西。我头重脚轻地随着采风的作家们穿花度柳,曲径通幽,感觉像是在大观园里感受封建时代腐朽阶级的腐朽生活。中途看到亭台水榭,还有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水,蝴蝶在阳光下飞舞。有关于西施的碑林,成了大家评头品足的对象。西施的庭院终于迎来了与它气质相吻合的客人,我很淡然地站在人群的外围,对于他们的议论,总是微微一笑。在我看来,这些石碑,顶多只是勾起了我少年时临写《曹全碑》《张猛龙碑》的往事。简单说来,这不过是一大群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意淫之举,这种癖好,经过隔代的传染,因此也成为了历朝文人们的一种时尚。西施这一个人,原本也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怎么说呢,这是我在查阅史书后获知的一桩秘密。早在管仲与庄周的年代,那时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都还没有出生呢,西施就已经在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但那时的西施也只是美,和乐府诗里的罗敷一样,美貌如花,天底下这样的美人多呢。西施生早了,吴越国间的战争还要等两百余年才能爆发。真正让西施成为天下第一美人的是一本叫《吴越春秋》的书。这一次,西施再生了,她像一个美的幽灵,在两个国家与几个男人中间。稳稳站住。巧笑倩兮,她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表达着一个国家的意志。《吴越春秋》像一出大戏,把西施给捧红了。让她的美——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惊天动地。因为这一件事,让我对“中间”的理解也更加地深刻了。中间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啊,很多原本无名的人,因为被时代夹了一下,因此也就有名了。我奶奶我妈我姨娘以及我见过的众多美人她们都没有西施美,问题的关键也并不在眉眼肌肤以及身段。最主要的,是她们美得多么无聊,美得和时代多么无关,美得多么的小资小调。只是在闺房里梳妆照一照镜子,所有的美只在有限的人眼里存放。即便潘金莲还能够在武大郎武松西门庆的中间,她们能在什么的中间呢,因为什么中间也不在,她们的美就这么白白地浪费掉了。
因为吸取了早上的教训,中饭我早早地就坐在了餐桌上。不仅吃了西施豆腐,还吃了沉在水底的白鱼以及吹弹可破的红烧肉。三两碗米饭下去,那是彻彻底底的饱了。饱得有点昏昏欲睡了。醒来就到了璜山镇溪北村。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庭院。这是徐家人的祖宅,叫新一堂。这院子里当然没有什么美人了。当年的美人都老了,我觉得这世界上有美人的地方就很可能成为中间,比如古代的苏杭,现在的广州上海。我要说说这个庭院里的什么呢。那还是先从“新一堂”三个字说起。我觉得“新一堂”就像我外公买了几十年的翻领呢子大衣。几十年来,也没见他穿过几回,始终庋藏在樟木橱里。在他看来,这是他最时髦的衣服了,尽管这个时髦早就已经不时髦了。写在厅堂牌匾上的“新一堂”早就已经不新了,时间把它斑驳成了沧桑该有的样子。可以想象,新一堂当时作为整个溪北村最崭新的房子,在它的雕花的柱子,窗棂以及房梁上都蒙着一层透亮的光。木料里的水分当时还没有完全地蒸发掉,走进去,整个庭院都是一股呛鼻子的木头气味,斧凿的痕迹也是新鲜的,还看得见。那时的新一堂无疑占据着整个溪北村的中间。它像个刚刚嫁来的新娘子,脸被红红的盖头蒙住了,让你在想象中兴奋好一阵子。我去新一堂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下午两点来钟,每一条巷子里都铺满了阳光。白色的阳光从墙身上淌下来,石头地面都是雪亮的。风吹着树叶和落花。墙角的大黄狗把尾巴晃成了一根粗壮的扫帚。新一堂刚刚举办过一场婚礼,喜联挂在黝黑的房梁下,上面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我在庭院的中间仰着脖子四处张望。雕花构建,旗杆石,上扬的檐角,石阶,阳沟,木头门栓,山墙。这些细节作为新一堂最初的存在始终和这个天井里的白云,雨水,星光构成对话的关系。站在天井中的空地上,阳光从头顶落下来。我想到博尔赫斯的诗句:庭院是天空通往屋舍的通道。这是用来交换思想的场所。庭院在中国古人的世界中,始终扮演着中间的角色。晒被子、浇花、喝茶、看星星、吵架、祭祀甚至死亡。在这个公共空间,任何人其实都处在边缘位置,只有庭院,属于中间。现在,新一堂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门窗关闭了,据说徐家人的祖先就供在里面。每到重要时刻,族里人就要集体前来跪拜。屋子的隔壁是一户寻常人家,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住着老两口。头发花白,衣冠简朴。我猜想他们应该是徐家人的后代。男的在摇椅上看报纸,女的在屋后面收拾碗筷。电风扇在屋子上方慢悠悠地转动,咔嚓声像一种催眠曲。这种原本十分日常化的生活现在看来总觉得像看一场艺术展览。现在的确已经很少有这么一种生活了,这是一种严重萎缩、甚至濒临灭绝的生活。新一堂以前是用来生活的,它承载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各种信息与指令都从这向外发射。但现在呢,这种生活已经快速地从新一堂撤离出去了,包括房梁上的燕子也撤出去了。戏演完了,一切都离场了,以往的那个“中间”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位置。也许,这就是时代,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相应地就来了。比较起来,我觉得西施的美是多么地坚固啊。当我站在西施的庭院中,作为万人想象的那个西施也站在中间。那一刻,“美”是在场的。美在场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美作为一种有效的介质始终在平衡这个世界的关系,它处于其中,发挥作用。在新一堂,我的内心是纠结的。这纠结的根源主要来自整个乡村生态的改变。在改变中,作为这个庭院“中间”的力量一直在被削弱。它由一个年富力强,威信十足的形象转变成了一个身份透明的老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崭新的事物。在溪北村,我看到挂在屋顶的白云,清澈的水流还有碧绿的田野。很多人家的门前屋后都布置了各种文化景观,总体给人一种温馨气氛。但另一面呢,我确实感到这里的萧条,那是一种内心的萧条,古诗中的乡村气氛完全看不见了。民国时,浙江都督府总务处长徐文耀是溪北人,他作为一个有商业头脑又有乡土情怀的觉醒者,带领溪北人种桑养蚕,发家致富。因为经济上的殷实,也使这里长期流传着一句话:“溪北人的屋,斯家人的竹”。可另一面呢,我也看到另一个“中间”在悄悄地建设,那是人心里的“中间”。新一堂,这个被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每年的维护费用并不会少。它的存在,仅仅只在精美的工艺以及作为文物的價值?我想,更关键的,新一堂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魂,是人心中间的一根柱子,它稳稳地立在这片青山绿水间。门前溪水潺潺,青山在屋后成为屏障。它作为溪北人中间的一种有效介质,始终在传递这样一个内在的声音。
就这样,走马观花,该看的也都看了。这一趟,你在酒桌上朗诵了李白的诗。在一句句“呼儿将出换美酒”中,你试图把自己灌醉。但事实上,你也没有那么爱醉。这是诸暨,你生活的外部。在这里,你感觉到水、空气、还有阳光那么新鲜。各种景物在你的感官里常常会造成一种触电的感觉,你碰到什么,你也说不清。比如,陌生人,还有未曾吃过的美味,这里不是你熟悉的中间,是异乡。当你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它们又再一次地成为梦境。成为缥缈之物。
现在,你又开始在熟悉的生活中活了。这也是你作为一个现代人始终无法突破的局限。诗仙李白与别的古代文人的生活一直是你的向往之境。他们的肉身在大地上漂移,并不属于任何一座城市。可是,现在的你——被各种世俗之物束缚。在远方,你获得片刻的悠游,但很快,你又被一个无形之物召回,回归到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中间”。你一次次从这“中间”去往陌生之地,然后又一次次回到这“中间”,这,很可能会被人误解成是你的故乡。也许只有故乡,才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但事实上,这只是你“关系”所在的城市,这儿寄存着你的档案、银行卡、公积金账户、朋友圈与一切可能拥有的未来。你被牢牢地栓在这柱子上,像古老的农民被土地栓牢。夏天了,城市又一次成为“火炉”。早上的蝉鸣会把你从梦中叫醒,然后,你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白云像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那些伸进天空的树木。建筑、道路、路边的广告牌,它们始终是那么熟悉地扑入你的眼帘,成为你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你一万次地想象,世界只有你一人啊,你活在自己中间,可以不受任何事物的制约,在你的想象中,世界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但很快,视野中第二个人出现了,第三个人出现了,你感到绝望,感到无奈。然后,你被挤入人群,电梯门开了。这是你去往单位的另一段路。五年前,单位刚从旧城搬来,这周围只是一片空地。天气晴和,远山与河流的脉络清晰可见,大地显得无用而荒凉。没有几年,高楼就把空地给消灭了,天空被吞没了。在电梯中间,你的每一寸肌肉都是僵硬的,你习惯性地收腹,屏住呼吸。严肃的气氛在汗臭与香水中发酵,人那么密集,居然没有一丝儿声音。他们之间,朝夕相见,彼此应该都有印象,但没有人愿意向对方微笑、寒暄。当电梯急速上升的片刻,你又一次想到大坝,想到那个与外界隔绝的“中间”。你想,假如电梯就这么一直运行下去,再也不能停止,再也没有打开的一刻,所有人,唯有在这封闭之中,上升抑或降落,唯有在这未知里成为无意义的部分,如此,作为工程师、作家、商人、政客、甚至美人西施,一切标签一切大脑,一切时代一切曾经拥有的都消失了,时间也消失了,在这中间,所有人是否将重新看待彼此,看待命运中稍纵即逝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