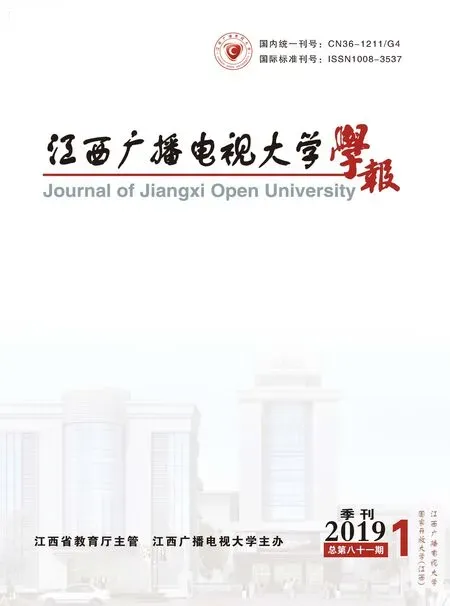图像话语关系探究
段德伟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在这视觉文化产业勃然兴起的今天,我们不免想起海德格尔曾说过的话,世界已然进入图像时代[1],此言不假,图像以它无孔不入的态势进入和活跃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柯指出,所谓知识型的基础是某一时期可以发现的“关系”的总和[2],在国际之间、各地区之间围绕着以视觉文化输出为核心的视觉话语权争夺中,在现代性话语围城和后现代性话语撕裂的拉锯角逐中,本文试图通过对图像话语关系的解析和探究,揭示趋同化和泛俑化过程中的现代图像话语现象的背后,深层的图像话语机制和运作端倪。
一、图像话语的符指关系
1、图像形象的可认知性是界定其是否具有指涉功能的分水岭。我们知道,文字符号是人们通过将具有同构关系的符号表象物与指涉事物的连接来实现知情解意的诉求的,而图像是通过形象的可认知性直接指涉现实事物,但形象可以分为具象形象和抽象形象。具象形象的可认知性和指涉性自不待言,而抽象形象,或者如福柯所说的作为线条、色彩等视觉形式的“词”因为缺乏可认知性则不具有指涉功能,它们只有象文字符号一样经过了社会教育、公众传播等社会推广和普泛化的编码过程之后,才能作为能指去指涉“物”。
2、图像指涉结构由点线型延异向线型延异嬗变是图像话语发展的历史必然。德里达在论述胡塞尔现象学本原与替补结构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文字是对言语的延异和替补。我们知道,图像不象文字有着严谨、系统的符号体系,在表述上无法上升到详实和具体的高度,所以,自文字出现之后,它就作为文字的帮仆,是延异的延异、替补的替补,也因此,有关历史及历史事件的记载,文字首当其冲且连篇累牍,而图像总是零落不齐。实际上,从德里达的观点来看,在图像指涉机制中,经过了保持——原印象——预持[3]这三重结构的程式之后,图像作为第三级延异,它所指涉的是经过多次文字延异的叙事表象,而不是所谓的“原印象”。因此,从古代史来说,图像指涉结构呈现出一种跳跃式的、关联不大的点型延异结构,而在近代和现代,摄影和复制技术的出现和高度发展,使得具有直观性表述功能的图像攀升到与文字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图图延异、一俑干觞、变俑、泛角多于始俑的现象便成为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这也就使得图像指涉结构由点性结构嬗变为线型结构。
3、在一词多义的象征指涉上,事物的各种象征语义的主次地位取决于社会文化语境对其与事物绑缚力的大小。绑缚力越强,则该某种语义位次排前,否则居后。几乎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各种象征语义或涵义。一般来说,大部分现实事物基本上有其象征指涉的首义所指、次义所指、第三语义所指、第四、第五语义等各级所指。但是,事物与其语义指涉关系稳固与否与社会文化语境对这一事物的影响力有关,影响力越大,那么该事物与某种象征语义的绑缚力就越强,其语义的主次地位则越排前,反之则居后。这样就会发生两种情形:其一、事物各级次义所指会逐步游离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粘连、捆绑,成为那一事物的各级所指,比如:贪婪游离于老虎之外与狼捆绑。其二、事物的某级语义闲置不用,久而久之,将自行发生塌缩,直至消失。
4、图像事物或内容物越多,形式越复杂,指涉难度越小,但修辞效果越强。但是,此种情况超过极限,导致事物、形式之间的逻辑链断裂,它们就只具有自指功能了。图像话语的机制在于:它依赖同构逻辑链将不同形象和形式的事物连接起来,共同构造出图像的所指及最终所指,即主题,如果图像事物及形式在内容、范畴、时空跨度越大,种和数的差别越悬殊,那么由于对比的作用,图像话语效果越强烈,所指越明确。但是如果这种差别之大超过了极限,导致图像事物、形式及其话语相绝相抵,各表各意,直至逻辑链断裂,那么图像只能是它们自己的所指了。在后现代图像话语碎片拼贴的拟像游戏中,很多艺术家将毫无形象同构点和逻辑关联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指涉反转、主题空无、完全让人不知所谓,如果说到意义,那就是只能是没有意义和颓废的隐喻。
5、图像不仅指涉事物,还凸现出国际间视觉文化紧张的角力格局。在现代理性、中心化的潮流冲击下,各国、各地区淡化了界限,其文化也朝着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共同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核心向其他国家进行强势话语渗透的态势,这一态势集中体现在面对同一本体,而喻体趋同的指涉现象。比如:无论在哪个国家的视觉话语中,玫瑰都象征爱情,而主张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后现代性则裹挟着保护本土文化的诉求与之进行激烈的对抗和拉锯,而这一切无不凝聚于图像指涉的词物匹配上。
二、图像话语的读图关系
1、作者、读者和图像的关系。作者为读者的阅读执法,读者为作者的言说立法。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这个原理:一个社会的文化、信仰、价值、权力体制、实践结构共同构筑成某种观念,并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视觉方式被经验和固定为多种视觉范式[4],这些视觉范式构成社会知识型的主干部分。我们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围绕着图像载体进行视觉文化的生产运作的。作者在创作观念的支配下将自己的认识、思想、情感诉诸图像,而读者总是在某种视觉范式中将自己的理解、感受通过泛本创作、圈内舆论、公知评价等方式反馈给作者,使作者的创作至少靠贴某种知识型。然而,我们知道,图像是作者表象的折射,进一步说,读者表象也是图像的折射,所以,自古以来,言象难达全意,偏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只要这种“误读”存在,这种言看互动、互制的模式始终处于一种循环和微调之中。
2、原本和泛本的关系。除非典传和惊世杰作,现代图象泛本的符号化和社会化地位凌驾于原本之上,而阐发却又脱离不开对原本的依赖。说泛本压倒原本是因为:其一、由于技术介入艺术,灵韵的光晕褪去,且使得键盘创作技法变得通俗易懂,尽人可学可用,众多人群热情地参与到对原本图像进行多元化、边缘化、游戏化的篡改和消遣中,这一广泛的平民化运动无疑使得原本成为泛本的素材和附庸。其二、新崛起的大众文化消弥着审美标准和审美品味的差别,文本沦为一种对读者的谄媚与迎合,原本的膜拜地位不再取决于它自身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价值,而是社会或圈内以泛本读者和作者为主的大众民主推定及权力操控下和资本运作中的热炒。其三、随着自指性代替相似性,对事物的表现和表征让位于对象征和隐喻话语秩序的重构和广泛使用,被分类、修饰、重组、剪接的诸多拟像强势地突出了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通行话语法则和社会规约,这就使得原本的创作必须弯下身段、委身趋附。说泛本依赖于原本是因为:其一,对泛本的解读需要原本解读的前理解结构作为桥梁,以此引导读者深入作者的世界、时代与社会背景、创作环境,并以知识和人文考古学为指导,才能尽觅、尽解文本的重要内涵和话语秩序。其二、泛本需要原本所根植的文化据点和美学高度去抬升它的价值,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厚重为依托,泛本就不会有现实的重量和轮廓,没有原本审美先验和经验的源点,泛本的视角、趣味的形式就没有可容延伸的范畴空间。其三、泛本中的偶像崇拜需要原本帮助廓清和还原人物的历史真实,偶像尤其是英雄形象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等价符号需要原本的时空赋于他体温和脉博。
3、亲知、描述、共知和知识型的关系。亲知和描述构成共知,而共知支撑起社会的知识型。首先,媒体信息社会中的亲知作为想象和体验的根据或参照在不断收缩,而本本相传的图像描述在全球产业一体化的进程中,早已突破了国家地区、民族的界限向周边剧烈“外爆”。后现代性所倡导的个性和差异性不断刺激着象征语义或隐喻涵义的裂变,不断挑战着视觉体验的极限,它们在向本就视觉疲劳的人们要求一个更为巨大而庞杂的共知。其次,共知的知识体系、科学、理论形态、实践结构等要素交互渗透并形成知识型,而知识型也反过来廓清共知要素的形态和规定性。这两者共存共构、相辅相成。
4、图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自古以来直到现代社会,文本主体与客体的主次关系向来被界定为主述因素与从属、配合、辅助和反衬因素的关系,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主体在去中心化运动中被消解和边缘化为多个中心,但主体依旧隐遁于某个中心或主题之中。所谓文本主体是指文本中发散和主导读者立场,观点、思想、情感的意识源点,它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图像中任何一种人物或事物,它以万物以人作尺度的古希腊哲学学说为发端向后世衍传,同时也是作为对中世纪人受造、受命、受治于神的神主思想的反弹,而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启蒙运动中。索杰认为图像是重构现实的技术理性空间,并将之称为第二空间[5]。与文学曲折、晦涩和隐蔽的描述将读者引向主体的意识场不同,图像作为第二空间可以通过对聚焦、构图、位置、形式等话语秩序的经营与组构,直白地将主体、客体及他们的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使其在主体的意识场中聆听其说。随着现代理性和一体化思想的阐发和普泛,主体俨然兴盛于意识形态和文艺形态之中,它通常占据着道义和审美的高点,批判和拷问社会、激情扬浊。而到了边缘化、多元化和多点化的后现代社会,主体往往隐藏于其中的一个或一种视点或视角中,它需要读者自己在图像话语碎片交叉、重叠、拼凑成的公共意识场中将主体找出来,或者通过对文本主题的品嚼中将之找出,于是,原本是明确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多言同堂、主客难辨的关系。
5、抽象与具象的关系。其一、抽象物可以借由与之具有逻辑同构关联的具象物来表达。其二、无论具象或抽象的能指作为江河水系都将无一例外地汇入最终所指,即抽象主题的大海。首先,再抽象的感觉和概念,它们都有与之相关的合乎逻辑的演化和转化过程及关联事物,只要我们找到与之具有同构关系的事物就可以借由它来完成对抽象物的表达。比如:陶醉的表情可以表达花香。其次,任何图像作为能指都有所指及最终所指,而最终所指都是抽象的主题,比如:鸽子的图像作为能指,所指是鸽子,而最终所指是和平和希望。我们以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图像的解读模式来论证此观点:(1)具象图像。对于具象图像的解读,一经辨识就可以直接指向现实事物,而其最终所指是这一事物的抽象属性,当然,在象征和隐喻话语甚于表征的现代社会,一经辨识,所指明确之后,则需要借助知识型和社会规约的解码,我们才能明白其最终所指。(2)抽象图像。抽象图像或抽象形与文字一样同属于一种非直观的指涉符号,都需要社会教育、公众传播的普泛进行编码之后,读者才能将抽象图像进行具象的解码还原,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解读抽象主题。(3)半具象或半抽象图像。这类图像通常被称为超现实图象。它的特点是:具象的形象和悖常的组合、解读此类图像一经辩识环节之后,将还原后的形象和逻辑与现实事物进行比对,在知识型和社会规约的参照下,逐步剖析出作者的动机、意图及最终所指—主题。
6、图像话语的真实、现实和非现实的关系。真实是条件,现实和非现实都是目标,真实是神,现实和非现实都是世界。进一步就真实和现实来说,真实是现实的属性,现实具真实的本源,真实需要现实为其直观夯筑立体架构,而现实需要真实为其存在增添可感描述。我们再更进一步就真实与非现实的关系来说,真实是非现实的脊柱,非现实是真实的自由王国,真实需要非现实提供延伸性状和美的空间,而非现实需要真实为它的实在公证和宣示。言及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现实和非现实,它们都需要真实的话语描述拱筑起文本逻辑的实在性和可证性。下面我再就这两种文本的解读模式细加论证:(1)现实文本。对现实文本的解读总是以真实人物或事物的素材或原型作为参照,在合乎真实的尽度中沿现实逻辑的演绎线路去感知、推理和想象,经过心灵碰撞、情感升华,最终围绕着现实冲突紧收为伦理思辩和意义追问。(2)非现实文本。对于非现实文本的解读需要依据文本的话语导向,假如话语导向是理性压倒感性,那么解读会以悖逆现实的文本逻辑去充盈真实性和可能性,而最后根据文本事物的关系、架构、情节脉胳的相似性,还原到现实中,而假如感性压倒理性,图像解读将会以某种审美模式进行。
二、图像话语与社会建构的关系:
1、图像话语与社会学科的建构关系。现代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为现代文明的兴盛提供了技术支持,尤其是生活的日常审美化,使视觉、语言规律与技巧的探索涉足社会各研究领域并与其相关学科渗透和联姻。在这米歇尔所说的去学科化进程中,图像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一方面因应用需要对社会各学科进行粘连、重组,一方面对它们的学科体系进行细化切割并整理,这样就使得图像学在兼融其他学科的同时也消融于它们之中。
2、图像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建构关系。在图像技术和多媒体应用的普泛伴随着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全球产业行销一体的共识中,各国政府突破时空的限制,将自己的文化深掘、包装并整体行销为系列视觉产品,如:电影、网游、服装、纪念品等,这些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在各媒介平台被图像话语炒热的同时,它们的外表、躯壳,即文化表征符号被好事人群剥离、视觉放大和热捧,这也就使得图像话语自身的文化应运而生。这就是视觉文化,图像话语炒热了其他文化无形中也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体系。
3、图像话语与社会消费的建构关系。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者的身份、地位、趣味、生产的品级、规制、数量全部被纳入到社会符号系统当中,图像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价值的符码标识,而是一种极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着购买欲、消费方式等等。另一方面,社会消费群体也以各种方式和机制监督和规定着作为商品的图像的生产,丰富、矫正和修改着图像话语。
4、图像话语与社会形态的建构关系。在信息社会中,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消弥,一反从前的交流方式,图像话语在缺场的双方象像对照、像像对话、图文互济中大显身手,图像虚拟和拟仿的技术被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及娱乐之中。可以这样说,图像话语无论在信仰、价值、体制、权力架构等各方面颠覆了我们过去的社会形态,如果说社会形态是他山之石,图像话语无疑是阔斧利凿。
以上我们以图像话语的符指、读图、社会建构这几个重要区块为要域,在对图像话语的发生机制、运作规律、形态和特点的剖析中,就各话语要素的关系依次作了以点带面、深入浅出的论述和较为充分的论证,挂甲漏丁在所难免,但我们相信深入剖析和厘清图像话语关系对于图像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图像话语命题的重新立义、乃至于对视觉文化体系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