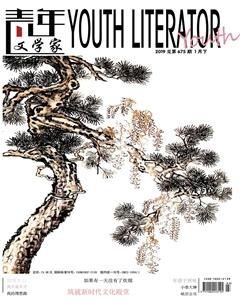喜福会中他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摘 要:作为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谭恩美通过16段故事的讲述,向读者展示了母女两代人面对父权制度,种族冲突时产生的身份危机以及文化身份建构,谭恩美的双重身份以及英文书写提供了多视角的研究途径,对于东西文化交流、西方眼中的国人形象,以及波伏娃所提出的“他者”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伽德摩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因此,语言是进行构建文化身份最根本的要素,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从语言的角度来阐释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美籍华裔的文化身份构建。
关键词:喜福会;文化身份;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马玉贞(1994.6-),女,青海人,青海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跨语言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2
一、引言
1.1作者简介
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1952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她将外婆和母亲的经历著成小说《喜福会》。作者创作的动力都是源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通过借用母亲们在中国的故事,试图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文化处境,表现她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心态。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不但存在身份认证的困境,追求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在不断地打破不平衡,调整身份以达到与现实的和谐,建构华裔美国人自我的国家身份与双重的文化身份。1989 年该小说一经出版就在美国文坛引起极大的轰动。
1.2喜福会简介
《喜福会》用第一人称讲述了1949 年以前移民美国的四位华裔母亲吴素愿、许安梅、江林多、顾莹映,与她们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四位女儿菁美、罗斯、韦弗利、李娜之间因各方面存在的差异而产生冲突,但最终在了解了各自母亲的过往经历之后,开始了解母亲的夙愿并与其和解的故事,小说由四个部分组成——“千里送鹅毛”、“二十六道凶门”、“美国解读”、“月亮娘娘”。每个部分又由四个小故事组成,这 16个故事反映出这8位美籍华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两方面都作为“他者”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视,女儿们也在自我认知与身份建构过程中处处碰壁,然而四位母亲通过用特殊的方式讲述自己人生故事,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帮助女儿们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
二、母亲的身份危机
2.1中国文化中的“他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性在人类范畴中建立的一个概念,而这个人类范畴是个男性范畴,男性是普遍的,女性是次要的--是第二性,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强行赋予的。黑格尔认为,被允许成为真正的主体,即内在存在,这种意识“绝对性”似乎不要任何理由。但波伏娃的观点是,对于扮演此种角色的男性来讲,女性必须被赋予一种相应的身份“他者”。而中国传统女性扮演的角色与社会家庭地位所反映的事实也恰恰印证了波伏娃的观点。
四位母亲中除了吴素愿是遭受战争才不得不只身来到美国,其他三位母亲皆为封建思想禁锢而导致悲剧的命运。江林多在两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定下娃娃亲,后来因为天灾父母离开并将自己作为童养媳送到黄家。对此她被无选择,因为从小她所接受的所有教育皆为如何做一个优秀而隐忍的妻子。如波伏娃所言,除了謀求自我解放并无他法,而许安梅的这一切心灵创伤都因目睹了母亲的不幸遭遇而起。
许安梅的母亲守寡后被强迫做妾,她本身也是受害者,但仍然遭到百般凌辱,最后被逐出家门,最后被迫嫁给富商。这本不是她的错,女性卑微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并没有留给她申诉的途径,然而世人却将所有的过错都怪罪到她的身上,而且在这一责难中竟也包括她自己的亲生母亲,同样为女性的她不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是最为严厉的斥责者。在对女性的身份定位始终处于性别“他者”的环境下,血亲也只能望而止步。
面对强势的男性身份地位,另一位出自富贵家庭的母亲顾莹映也未曾幸免,她本心性高傲并总觉得自己能够未卜先知,当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们问她想要嫁给什么样的人时,她说:“我一个都瞧不上”。她虽洞察身边一切事物,将人的内心看得透彻,但却始终未曾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因此最终包办婚姻和被无情抛弃的命运也还是降临到她身上,至此,她也无力与父权社会抗衡改变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只能以扼杀腹中子的方式发出自己无声的反抗。
2.2美国文化中的“他者”
中国传统文化已在四位母亲脑海中根深蒂固,而她们在美国的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截然不同的异国文化,在这种文化碰撞中她们的自我身份陷入两难的困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聚居在唐人街,每周一次喜福会的麻将聚会是她们寻求身份重构的寄托;西方人眼中,他们是被边缘化的“他者”,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社会地位,在家庭内看似强势的中国文化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文化相碰撞时,自己的中国文化却于无形中变成弱势的。
另一方面母亲们的身份危机也转嫁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希望她们长大后实现真正的美国国家身份,另一方面,母亲们又希望女儿们能够秉承中国人良好的品格。《喜福会》第一章序言中吴素愿回忆起多年前,来美国之前在上海买的一只鹅:本是只丑小鸭,硬是伸长了脖子而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然而最终在踏上美国领土的时候被美国移民局工作人员强行收走,只留下一根鹅毛。但仅剩的鹅毛不仅代表着她所有美好的愿望,更是她中国身份的象征。然而这些华人后裔从小接受美国主流的文化教育,反感自己的华人身份和中国人的特质,对父母所体现的中国人固有的言行做出本能的反抗,对美国的一切则趋之若鹜。如江林多所说:“她们吞咽的可口可乐必眼泪好要多”。由此,母亲们便又成了女儿眼中的“他者”。吴素愿秉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子女应听从父母,然而受个人主义熏陶的菁美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将母亲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扼杀在了摇篮里。象棋天才韦氟利也无法接受母亲整日将自己的成绩拿来当做 谈资和炫耀的资本,而母亲许安梅则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告诉她母女本为一体。
三、女儿的文化身份危机
如吴素愿的鹅毛象征对女儿无限美好的希冀一般,希望女儿拥有完美的美国文化身份并融入主流社会,女儿却想极力摆脱母亲的影响,但潜移默化中她们仍将自己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家庭观念,性别观念传递给了女儿。
波伏娃也在《第二性》提到了女性气质并不是天生的,另一位学者弗里丹则认为这种温柔善良,自我牺牲,隐忍的女性气质只是为了让女性满足于家庭主妇的命运,并从中获得幸福感。而这一观点在江林多与莹映的女儿身上得到印证。许安梅看到女儿罗斯对丈夫的行为隐忍默不作声时说道:“尽管我一直努力的教她相反的东西,但她还是像我一样,都朝着同样的方向。”然而罗斯自幼一心崇尚美国文化,并且她认为美国版的观点都要比中国版的观点好得多。在妈妈提醒她泰德是个美国人时,罗丝骄傲地宣城: “我也是美国人”。然而她内心建立的美国文化身份在见到男朋友泰德的母亲时第一次遭到冲击,泰德母亲所言代表否认罗斯的西方身份,无疑这是整个美国社会“他者”观念的映射。在婚姻问题中处处碰壁,她也把这一切归因于自己是被中国式的谦卑观念带大,认为女性就是应该清心寡欲,吞下自己种的苦果,而这也正是对性别“他者”的映射。
李娜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美国人努力把眼角往中间挤,但中国人的外边使她不得不接受种族“他者”的偏见。以及在与哈罗德交往过程中她坚持经济独立,以及保持婚后的财务独立,但在婚姻中依然没有维持平等的关系,甚至没有勇气与丈夫沟通交流,以至于逐渐失去自我,效仿独立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让李娜完全赢得婚姻中的性别公平,她依然是“他者”的卑微形象。
菁美认为自己对母亲并不了解,一方面,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截然不同使母女之间的代沟始终无法填平,也缺乏沟通的契机,菁美一直都无法理解母亲抛弃自己的双胞胎姐姐,但她也不曾亲身经历母亲遭受的残酷的战争;然而母亲认为女儿应顺从父母,并在无形中将对双胞胎的遗憾强加到了菁美身上,不得不接受母亲专制的爱和教育。另一方面,向往自由身份的菁美她似乎也理解母亲的失望,因为那是母亲为老钟免费做清洁工,才换来她学习钢琴的机会,但她还是坚持反抗。但是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氛围的夹缝中生活的她也陷入身份危机。
华裔为融入美国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他们成为美国人。他们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母女两代人都在异国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四、他者的身份构建
《喜福会》里的三位母亲都曾无奈遭受婚姻失败,为了寻求自由,她们选择移民美国,而这就建构了她们的“他者”身份。阔别了40年之久,当喜福会中母亲江林多再次返回中国时,她认识到自己不再是纯正的中国人。江林多所说的这张 “面孔”,反映了母亲们的复杂身份,即早已不是纯正中国人,但也还未完全蜕变成非美国身份;或者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
后殖民主义代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与协商转换理论与此相印证。许安梅信仰上帝,但也敬仰龙王,在儿子宾溺水之后带着圣经在海边祈祷,但讲的却是中文。信仰上帝也是许安梅进行文化身份建构的印证。虽在父权的强压在遭受了婚姻的失败,但许安梅面对女儿时却鼓励她勇敢站起来为自己发声,这也是母亲帮助女儿进行身份建构的体现,使其摆脱种族“他者”和性别“他者”的束缚。
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解释到:“对认同而言,身份绝不是先验的东西,也不是成品,它只能永远是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而萨义德则认为“自我身份的建构关系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以及对于‘我们的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
中华裔母女两代人同时拥有中美文化意识,她们只有彼此理解的自我身份后才会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最终确立属于自身的美国国家身份。小说中的罗斯最终以重现自信的形象找回了自己,也挽救了几近走向失败的婚姻;而莹映看到李娜婚姻的不幸,也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让女儿有了切身的体悟,而最终也走出阴影,变得坚强起来;韦弗利在与里奇的蜜月旅行计划中也逐渐容纳了母亲。菁美向往自由的美国身份,如谭恩美所说,母女本为一体,菁美与母亲虽缺乏互相理解,但她也秉承了母亲所传递给她的中国善良忍让的品行。尽管母亲中国式的家庭历史和婚姻阴影对女儿的婚姻影响产生负面效果,但中美文化的良好融合并重新建构文化身份在此帮助她们找回了自我,发出女性独立的声音。
五、结论
因此,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日趋频繁的文化交流,《喜福会》试图为这群拥有双重文化身份,深陷身份困惑境地的华裔外国人指明了方向,如何更好地秉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兼收并蓄外国文化的精华,追寻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建构真正的所在国的国家身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伟.浅谈《喜福会》中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与建构[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3).
[2]譚恩美、程乃珊等.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邱畅.论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身份缺失与建构[J].
[4][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5.
[5]王朝杰 .困惑、追寻、认同——谭恩美《喜福会》华裔身份认同的建构研究[J].2014.
[6]王伟强.批评性语篇分析视域中的身份建构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