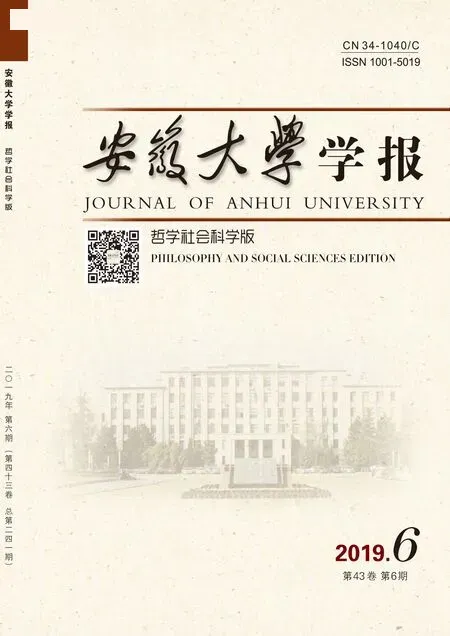吴孟复: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
王达敏
桐城派源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开宗于康乾郅盛之世。晚清以降,该派学者经受欧风美雨洗礼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撞击,一部分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一部分坚守华夏传统文化本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桐城派这两部分学者,与其他新生力量一起,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新的灵魂。1949年后,天地一新,桐城派在回肠荡气地腾跃数百年之后,终于进入终局阶段。而在苍茫的历史尽头,岿然屹立着的,是那位瘦骨嶙峋、目光炯炯的江淮学者吴孟复(1919—1995)。
一、皈依桐城
在吴孟复成学过程中,桐城派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吴孟复甫髫龄即与桐城派相接。八岁那年,吴家延聘张仿舜教读。张氏原在京城坐馆,曾与名流往还,能诗擅对,视野开阔,非乡曲之士可比。他教吴孟复研读清代善化李绍崧纂《左传快读》和钱塘姚祖恩纂《史记菁华录》。李、姚虽非桐城一脉,但其所选评的《左传》《史记》则是桐城义法的源头。同时,地方名流刘竹轩、高钝叟等常到吴家,睱时考询吴孟复的课程,审阅其诗文,教其围棋。高钝叟更为其讲解桐城文派。自此,他知晓这世上有方苞、刘大櫆、姚鼐和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诸家(1)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吴先生女公子吴布藏稿。。1929年,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锓梓,这是桐城派研究的奠基之作,吴家获赠一套。十二岁那年,吴孟复阅读家藏刘氏之作,虽不甚懂,却增加着对桐城派的感性认识(2)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见刘声木撰、徐天祥校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9页。。
吴孟复真正皈依桐城,在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期间。
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是吴汝纶高第弟子,因吴氏爱惜、诲导而得桐城派神髓(3)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见邓国光辑释《唐文治文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33页;《自订年谱》,见《唐文治文集》(六),第3666页。。他继轨桐城,潜研诗文吟诵,创制了影响深远的唐调。面对西学冲击,他挽狂澜于既倒,把无锡国专建成了弘扬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国学重镇。吴孟复1934年春首考无锡国专时,题目为“王、黎两《续古文辞类纂》的比较”。王先谦辑《续古文辞类纂》追踪姚鼐纂《古文辞类纂》,黎庶昌辑《续古文辞类纂》蹑迹曾国藩纂《经史百家杂钞》,在清季民国风靡一时。无锡国专以此命题,可知其办学祈向。1934年8月,吴孟复更名后再试,被录取。此后直到1937年7月毕业,他在无锡国专读书三载,授业师有唐文治、钱基博等。钱氏论学为文虽不规规于桐城,但也不出桐城范围。他“自谓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敩萧选,植骨以扬、马,驰篇似迁、愈”(4)《钱基博自传》,见《江苏研究》第一卷第八期,1935年12月15日出版,第3页。关于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任雪山撰《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有深入论述,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1~286页。,乃曾国藩为学家数。
在无锡国专,吴孟复与马茂元的相遇成为其转向桐城之学的关键。马茂元出身桐城名族,祖父为马其昶,祖母为姚濬昌之女,外祖父为湖南桐城派名家郭立山。他幼承庭训,夙有为桐城派传灯之志,曾拟撰《桐城派文学史》。1935年刚一跨入无锡国专之门,他就与吴孟复结为莫逆。他们一起以道义、学问相濯磨,一起出游唱和。1935年,吴孟复寄马茂元的诗作有《和懋园病中感怀诗兼以慰之(时余亦病意)》《归兴并柬懋园》,马茂元则有《与常焘同游惠山归,而常焘有诗纪游,步韵和之 》。1936年,吴孟复寄马茂元的诗作有《寄怀马懋园、耀彤、方重禹》《坐雨呈懋园》,马茂元则有《自题与山萝合造像》。马茂元力劝吴孟复规步桐城派,说:“桐城文最能尽意。所谓尽意者,盖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嫌短。能增能减,皆非尽意也。”吴孟复听了马茂元之言的反应是,“余谢以不敏。茂元曰:‘吾知君能之。’问其故,则曰:‘君有赠某君诗:“未知学问今何似,但觉交亲久已真”,此即桐城文心之妙,亦即所谓尽意之术也。’余若有所悟,请试为之。其年寒假,乃访君于桐城,登堂拜母,复偕谒蜕私先生与仲棐丈,益究桐城之文章义法与刘姚诗篇,而于《昭昧詹言》所言若有心得焉。复读梅、管、张、吴、马、范文集,益溯源于欧、归、方、姚”(5)吴孟复:《马茂元与桐城派》,见陈所巨、杨怀志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1993年,第184页。内部发行。。由于与马茂元交契,吴孟复得与马氏姊马秀衡申以姻娅。在马家,他得读马其昶所撰《屈赋微》《老子故》《庄子故》等著作,一窥其治学阃奥(6)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见《相麓景萝稿》,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5页。。从此,他耽于桐城之学,溺而不知返。他曾心怀感激地效曾国藩之语云:“吾之粗解文章,由懋园启之也。”(7)吴孟复:《马茂元与桐城派》,见陈所巨、杨怀志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第184页。
由于与马茂元交亲,吴孟复得以常去桐城亲炙桐城派耆硕姚永朴,并列其门墙。姚永朴为姚范玄孙,姚鼐曾侄孙,姚莹之孙,姚浚昌之子,伯兄为姚永楷,弟为姚永概,姊适马其昶,妹姚蕴素归范当世,一门因累世为桐城之学而享天下重名。在刚入无锡国专时,吴孟复闻悉姚永朴在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教书,致书请益。他说:“姚先生两目昏眊,但仍给我回了信,字大如钱,写了十多页,其吃力可以想见。还把他著的《蜕私轩集》《惜抱轩诗训纂》《论语解注合编》《旧闻随笔》《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等多种相赠。老辈之爱人无已、诲人不倦之精神,使我感极泪下”(8)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1936年2月,马茂元偕吴孟复同谒姚永朴于里第,“先生为讲群经大义、文章义法、先辈轶闻,口说指画,曲尽神情,虽不甚识字者闻之皆心领意会,先生亦乐而忘疲。一日,日且暮,讲方辍,起视庭阶,雪深盈尺矣”(9)吴孟复:《书姚仲实先生〈文学研究法〉后》,见《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51页。。
由于与马茂元交亲,吴孟复得闻桐城方守敦、方彦忱等前辈謦欬。方守敦为方宗诚之子,夙承家学,颇娴诗文,书法尤享时誉,曾随吴汝纶东渡扶桑考察学制,归而协助吴氏创办桐城学堂。他对吴孟复等晚辈教诲不倦。一次,他觞吴孟复等于桐城西南的勺园。勺园为刘大櫆归馆张氏之所,其笔下屡屡言之。同集者有姚永朴弟子疏达,时为安徽大学讲师。疏氏当时所撰《三通序注》,吴孟复以为是“有用之书”。方彦忱乃马其昶弟子、姚永朴之婿,京师大学堂毕业。他对吴孟复等晚辈爱护备至。一日,他邀吴孟复等出桐城东门,过大河,经月山,而至方家所属的莱园。在过河时,水中置石,大家皆履石而过。方彦忱指点说:“这就是《诗经》所说‘深则厉’之‘厉’。《说文》古文作‘砅’,从石从水,会意,即此‘厉’字。”方氏莱园在龙眠山口,园中一泓清池,众木扶疏,木梢望龙眠翠色,十分美妙。出园归城,方氏复告以月山老茔上有方苞所书碑,乃带大家往访(10)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此外,吴孟复在桐城期间,结识老辈诗人许复。许氏为陈澹然弟子(11)陈衍:《石遗室诗话》(一)卷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3页。,和方守敦至好,极赞吴孟复诗才,有诗云:“谁欤使我眼中青,吾子诗才可阮亭。”(12)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
由于与马茂元交亲,吴孟复得与桐城诸阀阅之家青年俊彦友善。这些英流除马茂元之外,还有方守敦之孙方筠德、方珪德(舒芜),马茂元从弟马茂烱、表兄潘晓麓等。他们常常群聚吟诗作文,游山玩水。一天晚间,诸人在桐城南门酒楼饮酒,喝醉后,出来走在大街上,高声朗诵古诗,一唱彼应,闹得街上人都争着来看。他们曾一起游投子山,马茂元归作《游投子山记》,渲染游山之乐,吴孟复许久之后忆起,仍怀念不已(13)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
由于与马茂元交亲,吴孟复得从桐城派学者李诚问学。1922年,姚永朴主秋浦周氏宏毅学舍讲席。这是民国时代继无锡国专之后又一个弘扬桐城派的学府。1924年至1926年,李诚在这里受到了桐城之学的系统训练,成绩卓出,受到姚永朴青睐。1929年至1932年,由姚永朴推荐,李诚到马氏家塾教读,学生有马茂元、马茂炯和舒芜。1933年至1936年,李诚在贵池旧溪方家教馆,同时常到桐城趋谒姚永朴请益。当是在1936年初,寒假期间,吴孟复因“师蜕私而友茂元,因得从先生问学”(14)吴孟复:《敬夫李先生传》,手稿由李诚哲嗣李高兰先生收藏。此文收入《李诚全集》时有删节。。吴孟复家住江北庐江县石咀头新兴圩,后其父吴南陔又在江南的郎溪花赛圩置地数千亩,因此吴家在郎溪也筑有新居(15)吴孟复:《自传》,未刊。。1937年上半年,由马茂元推荐,李诚到郎溪吴家任教,与吴孟复之间有了更多切磋学问的机会(16)此段史料摘自李诚档案,未刊。。
吴孟复就读无锡国专的次年(1935),其父吴南陔移寓上海,命其执贽同邑诗人陈诗门下。陈氏阅吴孟复诗,喜甚,将之刊入《尊瓠室诗话》,并将其携至袁思亮家受业。袁氏为两广总督、曾国藩门人袁树勋的长君,“劬学,工诗词,尤善桐城派古文”(17)陈诗:《尊瓠室诗话》卷二,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吴孟复说:“拜师之日,陈师命余作诗二首,即古人所谓以诗为贽;又备全红柬帖,只书‘受业吴常焘顿首拜’等字,即世人所说的门生帖。余拜了三拜,陈师以柬帖奉上,交揖后,即对坐。余亦坐其侧。陈师又以余作文一册呈袁师。”(18)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袁氏披阅后以为,吴孟复之作“气充词健,为诸门人之冠”(19)陈诗:《尊瓠室诗话》卷三,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第140页。。袁氏为陈三立入室弟子。陈三立之父陈宝箴在湖南任巡抚时实行新政,开启新机,影响后来历史既深且巨。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皆被免职。陈宝箴曾致书曾国藩切问,并附自作之文一册求教。曾氏撰《复陈右铭太守书》,从桐城义法角度,畅论为文之旨。陈三立以家学转授袁思亮。袁氏则以之授吴孟复。吴孟复说:“陈、袁皆兼承桐城诸老所传之义法,无门户之见。袁师把散原批改之作,授我阅读,叫我从中领会去取损益之缘故。我也常给散原写信,散原勉以‘锲而不舍,他日必可大成’。”(20)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
吴孟复在无锡国专时,听顾实讲授文化史课,用的教本为柳诒徵所撰《中国文化史》。在吴孟复就读期间,柳氏应唐文治邀请,莅临无锡国专讲学,以为清儒考证多出宋贤,令唐氏极为推服。柳氏年轻时候,曾在南京与陈三立对门,“时常亲炙,粗闻其诗古文绪论”。桐城派名家范当世常游南京,居亲家陈三立之寓,柳氏常去请教。范当世同门张謇对柳氏也极为赏识。柳氏曾得姚鼐纂《古文辞类纂》等书,“欣然若贫儿暴富”(21)柳诒徵:《我的自述》,见《柳诒徵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页、35页。。可见,柳氏之学也与桐城派脉联。吴孟复的从舅卢天白是柳氏和马其昶的弟子,尝云:马文简洁,柳文宏壮,各极其胜。吴孟复外公卒,墓志即由柳氏撰成,这是他读柳氏古文之始,时间尚在其入无锡国专之前。1949年秋,柳氏主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组的工作,吴孟复与焉。在朝夕相处中,他得从柳氏习文献之学,对其学问至为倾倒,执弟子礼甚恭(22)吴孟复:《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年纪念献诗》,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15页。。
就这样,吴孟复在众多师友加持下,感发兴起,皈依桐城之学。此后数十年,他在桐城派研究和创作领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取得诸多建树。他以自己的实绩,为走向终局的桐城派,奏出了最后的典雅纯正的乐章。
二、在义理、考据、辞章之间
吴孟复受桐城派师友熏沐,汲取桐城之学神髓,一生游走于义理、考据、辞章之间,在会通中力求创新。
桐城派学者信仰宋儒义理。他们所讲的义理,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敦品;二是洞明性理之奥;三是经世。他们在理论上谨守程朱对性理的辨说,少有别解。但在伪道学出没朝野、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他们的特别处,是对敦品、经世看得极端重要。姚鼐视躬行为己为人生第一义谛(23)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曾国藩将经济融于义理之内,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桐城派学者视义理高于考据、辞章。义理之内,在敦品、性理、经世三者中,桐城派学者又视敦品高于性理、经世。唐文治出入程朱理学,肩随姚、曾,论学最重义理。1934年春,唐氏在面试吴孟复时,问其为学蕲向,答云:“愿终身立足于考据之门。”唐氏听后怫然不悦,稍停乃曰:“诗文易作,文人皆能之。考据则惠、戴以后,门径已开,稍加读书,亦不难致。人之一生,难在做人。”(24)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进入无锡国专以后,唐氏教吴孟复:“立志为圣贤。命以‘希颜’为字。”(25)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1947年,唐氏在《赠吴生常焘序》中,以王阳明、曾国藩为范型,期待吴孟复追求三不朽,尤以做人气骨勉之。他说:“‘人生唯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有气骨而文章随之。”(26)唐文治:《赠吴生常焘序》,见邓国光辑释《唐文治文集》(三),第1905页。受唐氏教导,吴孟复终生重视内修,不敢稍越雷池。在学术研究中,他也最为看重研究对象的品节。在《屈原九章新笺》中,他强调屈原“以生命殉国家,光明磊落,大节凛然”(27)吴孟复:《屈原九章新笺》,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4页。;在《重建包公墓碑记》中,他赞誉包拯“清刚之气,公正之操,日星同曜,终古常新”(28)吴孟复、李汉秋:《重建包公墓碑记》,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二,第92页。;在《桐城文派述论》中,他将姚鼐拒绝拜入领班军机于敏中之门、马其昶反对变更国体等事特意表出(29)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98页、168页。;在《记李拔可先生》中,他说:“盖先生诗品之高,正由其人品之高;唯其人品之高,故诗品高也。”(30)吴孟复:《记李拔可先生》,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二,第98页。在《为李敬夫丈作传成,情有未尽,复成小诗》中,他称李诚“不忘忧国见平生”(31)吴孟复:《为李敬夫丈作传成,情有未尽,复成小诗》,见吴布整理《吴山萝诗存》,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32页。。这都是他看重品节的人生观的外现。1985年,唐文治百廿岁诞辰时,吴孟复抚今追昔,写下这样的诗句:“‘考据辞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为人。’回头多少崎岖路,始信先生教诲真。”(32)吴孟复:《追怀唐蔚芝父子(十一首)》其七,见吴布整理《吴山萝诗存》,第73页。
桐城派学者虽将考据置于义理之下,但在乾嘉汉学昌明的时代,少有人敢对考据心存轻忽。不过,桐城派学者虽不明弃考据,但擅长考据者却稀如星凤。就吴孟复而论,其最初的考据观念,并不是来自桐城派学者,而是由其在广益中学的国文老师段熙仲所授。段氏毕业于东南大学,是柳诒徵、黄侃的弟子,治学偏重考据。在课堂上,他讲解过《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清代学术概论》《廿四史》和《新元史》,讲解过吴派、皖派等概念以及江、戴、王、段的学术。吴孟复说:“我之所以有志于国学,喜欢读点并搞点考据,皆段先生之教也。”(33)吴孟复:《我的读书、治学与教学》,未刊。最终把吴孟复引上考据之途的,是柳诒徵。在上海文管会,吴孟复叩问为学门径,柳氏以其师缪荃孙之言答之,以为当以《汉书·艺文志》为标志的目录版本之学、以《说文解字》为标志的语言文字之学为基础。吴孟复闻听柳氏之言,豁然贯通,多年所学,如纲举而目张。从此,他对柳氏之教持之不稍懈。他平生撰写的著作主要有《训诂通论》(1983)、《古书读校法》(1983)、《唐宋古文八家概述》(1985)、《屈原九章新笺》(1986)、《语文阅读欣赏例谈》(1989)、《古籍研究整理通论》(1991)、《桐城文派述论》;校注点勘的著作主要有《刘大櫆文选》(1985)、《刘大櫆集》(1990),参与或主持编纂的著作主要有《汉语大词典》(1986)、《续经籍纂诂》(2012)、《古文辞类纂评注》(1995),等等,可谓硕果累累。这些作品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文学等多个学科,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方法是考据,而考据的立足点,便是柳诒徵当年指示的两点:知书、识字。1986年,在柳诒徵辞世三十年之际,吴孟复郑重撰下《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年纪念献诗》,对柳氏教诲感念不胜(34)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见《相麓景萝稿》,第7页。。
吴孟复在考据中,不仅坚持考据与辞章合一,而且主张“训诂出辞章”(35)吴孟复:《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年纪念献诗》,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一,第15页。,将辞章置于训诂考据之上。吴孟复所谓的辞章,主要是指古文之法。他说:“古文之法,不止为作文言之。盖古今人著书作文,其文外曲旨,往往在斯。程瑶田云:‘东原之治经也,以能知古人之文章。’(《修辞余抄》)又曰:‘所谓解字者,非徒认取字面,识其实义而已。盖将联属数字以成文理。而所以成文理者,又必有一二虚字空运于其间,以传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即得其指趣!’(《解字小记》)程君是汉学家,而亲受业于刘海峰,故言之亲切如此。故‘古文之法’,非仅为作文言也,亦是所以读书治学之法。知古人之文章,涵泳其传神之妙,以知其指趣,即辞章之功夫也。……而就读书治学言之,苟得此法,每能发前人所未发。吾尝以拟之如仙家之‘金丹’、禅宗之‘寸铁’,此在近代桐城诸君著作犹能遇之。即今日桐城教师之善教,其妙亦在此也。”(36)吴孟复:《〈桐城近世名人传〉序》,见陈所巨、杨怀志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第2~3页戴震、程瑶田都是汉学皖派大师,戴氏的经学考证成就非凡,得力于其深懂古人文章;程氏乃刘大櫆弟子,通晓古文之法,因此在解字时,强调从辞章角度涵泳文字,以得其实。近世桐城派学者握此金丹,在考据时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吴孟复的研究常常是考据、辞章兼施,异彩纷呈。钱仲联概括其著述特点:“沉浸浓郁,提要钩玄,考订精严,文词尔雅,是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善用以相济者也。”(37)钱仲联:《〈吴山萝诗文录存〉序》,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首。
在辞章创作方面,吴孟复诗文兼擅。其诗文的突出特色,就是以学问为宗。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是一个空前重视学问的时代,学者治学重心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流风所及,诗文各家虽风格迥异,却都以学问植其根。吴孟复谓:“清诗以学胜。”(38)吴孟复:《〈清文举要〉序》,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二,第49页。又谓:“清文之盛,由清学之盛。”(39)吴孟复:《〈清文举要〉序》,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二,第49页。桐城派学者的诗文虽独树一帜,但其总体倾向是由虚向实,讲究学问。吴孟复谨守桐城派家法,其诗文中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他曾这样总结写诗心得:“一曰起处用反笔;二曰以单行之气,寓于对偶之中;三曰虚字传神;四曰篇终接混茫。无一字无来历而又无一语为人道过。此查他山、姚惜抱不言之秘也。”(40)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见《相麓景萝稿》,第18页。追求无一字无来历,其诗如此,其文亦然。吴孟复的文有白话、文言两种,而以文言成就为高。在文言文中,吴孟复作有散体文、骈体文、骈散合体文三种,各体皆有所长,难分轩轾。桐城派强调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吴孟复服膺此论,其诗文创作的确做到了有所法、有所变。
吴孟复的诗作在学界享有盛誉。袁思亮说:“曲达而健,举阳刚阴柔之美兼而有之。”李宣龚说:“作者先治古文而后为诗,故其根柢槃深如此。”程千帆说:“诗格老而韵,气深稳而卷舒自如。此惜抱圣境也。”舒芜说:“大诗清空浓至,二妙并兼,其往复宕漾处,真宋贤胜境。”(41)《师友评语》,见《吴山萝诗文录存》卷首。马茂元是吴孟复衫鬓青青时代的挚友,二人惺惺相惜,乃有马氏姊归于吴孟复之事。尽管吴孟复与马氏姊中道分离,马茂元晚年仍然语于舒芜:“平生师友,诗才仍当以吴山翁为第一。我最佩服的还是他。”(42)舒芜:《致程千帆》(三十六),见《碧空楼书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自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之说后,桐城派内外诸多学者即将此悬为学问鹄的。唐文治在《送吴生常焘序》中申论姚鼐之说,并谓:吴生“笃守桐城派,精进不已。自吴挚甫先生而后,传人其在兹乎!”(43)唐文治:《赠吴生常焘序》,见邓国光辑释《唐文治文集》(三),第1906页。相期何其殷殷。自唐文治诲导后数十年间,吴孟复竭力将义理、考据、辞章打并一处用功,也多有创获。但时移世换,唐文治能够预见吴汝纶和他自己后继有人,却未能卜得广陵散至吴孟复而绝矣。
三、发覆见宝璧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肇开桐城派研究先河的,是刘声木、姜书阁。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补遗》(1929)、《桐城文学撰述考》及《补遗》(1929),为桐城派研究奠定了文献学根基;姜书阁撰《桐城文派评述》(1930)为桐城派研究建立了最初的阐释框架。自刘、姜之书问世之后,到1995年,桐城派研究领域最为卓越的学者是吴孟复。他钻仰先达,自铸新论,最先论述了桐城派与王学的关系、方苞与颜李学派的关系,最先论述了刘大櫆思想的启蒙价值,最先分析了桐城之文的小说化和诗化倾向,最先悟出毛泽东著作中包含着桐城派元素,等等。他的见解发前人未发之覆,为桐城派研究开辟了新的论域,推动着桐城派研究达致新的境界。
吴孟复以为,桐城学者最著名者为方以智。方氏之学渊源于其曾祖方学渐。方学渐所撰《心学宗》《桐彝》《迩训》等,皆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将方学渐列入《泰州学案》,与李贽等同列,史称“王学左派”。宋儒把伪《大禹谟》中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奉为二帝三王的心传,倡为“存天理,灭人欲”之论。方学渐独解“危”为“高大”,与宋儒异趣。四库馆臣称其“一扫虚无空寂之说”。其学与王学末流之空疏放荡者又自不同(44)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22页。。王学后来对刘大櫆、姚莹等皆有影响。
方苞是一位宗奉程朱的理学家,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45)《原集三序·王兆符序》,见彭林、严佐之主编,成棣编《方苞全集》第十三册《附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近三百年间,学者对此从无异论。唯吴孟复再三研磨后发现,方苞在程朱理学之外,也“学承颜李”(46)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1页、。清初,颜元、李塨崛起于大河以北,强调实学践履,以为程朱理学空疏无用。颜李学行有溢出宋明理学之外者,一时风靡南北,在儒学内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派系。方苞“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47)方苞:《再与刘拙修书》,见彭林、严佐之主编,诸伟奇、陶新民整理:《方苞全集》第八册《方望溪文集全编》(上),第350页。。年二十四,方苞受庙堂和时代风潮影响,才以程朱理学为指南。在宗奉程朱理学的同时,他因与王源、李塨交密,又对颜李学派有深刻理解。他以为,颜元与朱熹不过在诸经义疏与设教条目等枝节问题上有异,在性命伦常之大原和讲究事功方面并无不同,二者均为孔子之徒。方苞治学志在经世,立朝数十年,关心的是如何屯田西北、经略苗疆、控制台湾,如何经略畿辅水利、淮黄河工、漕运、赋税、禁烟、禁酒、备荒,等等,这与颜李学派的重视礼乐兵农若合符节。但比较而言,方苞以为,孔孟之后,唯程朱乃得天地之道,比颜元之学要高,因而视李塨、王源訾謷朱子为非。在上述认识指导下,方苞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主、颜李之学为辅的思想格局。也因为如此,他推重李塨、王源的人品、学问,与李塨、王源易子而教,而且临终前两年命在家祠左厢敦崇堂内崇祀李塨、王源等四友(48)苏敦元辑、李昌国和王永环点校:《方望溪先生年谱》,见王长林主编《桐城派名家年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5~46页。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1页、67~69页、208~209页。。尽管吴孟复的论述尚欠明晰,但他提出方苞学承颜李,对于学界认识桐城派道统及其演进具有重大价值。民国初年,徐世昌作为北洋政府总统,为迎接西学挑战,把颜李学派推向国家意识形态主位,并将其引入桐城派道统之中,在政、学两界引起巨大波澜。徐世昌的做法正是继轨方苞(49)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刘大櫆被姚鼐抬入桐城文统后,在桐城派内外,引起诸多争论,学者对其肯定者少,否定者多。桐城文统建立后,至姚门弟子,方苞、刘大櫆、姚鼐被视为一体,形成桐城派一脉文心传三世的叙事模式。但是,越到后来,刘大櫆越被轻视,学者论起桐城派,往往方姚并称。由于刘大櫆的失位,连继他而起的阳湖派诸家是否属于桐城派,在文学史上也成为疑案。唯吴孟复再三研磨后发现,刘大櫆思想超迈,“他的愤世嫉俗,敢于怀疑,有不少越出‘桐城’以至程、朱之范围”(50)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72页,他的“部分作品中,讲了一些方、姚不敢讲的话,有的竟与黄宗羲、唐甄、吴敬梓、曹霑、戴震颇为近似”(51)吴孟复:《〈刘大櫆集〉前言》,见《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第16页。。其被传统学者否定的因由在此,其独特价值也在此。关于天道,刘大櫆以为,“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也”(52)刘大櫆:《天道上》,《刘大櫆集》,吴孟复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与人的穷通寿夭无关,风水之说乃无稽之谈。关于理欲,他承认人们合理的欲望,以为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的“嗜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也。夺其所甘,而易文以其所苦,势不能以终日”(53)刘大櫆:《慎始》,《刘大櫆集》,第20页。,应该“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54)刘大櫆: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刘大櫆集》,第27页。。关于伦理,他以为,“君臣以义合,故曰‘合则留,不合则去’”(55)刘大櫆:《汪烈女传》,《刘大櫆集》,第202页。,对“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不能苟同。关于理学,他推戴王阳明之学,曰:“我爱新建伯,术业何崇隆。七龄矢志学古圣,富贵于我浮云空。径从良知见性命,震磕天鼓惊愚蒙。卒其所就继孔孟,唱和如以徵应宫。后来小生肆掊击,连接鸡雌排虎雄。擒濠立功在社稷,用由本出观其通。”(57)刘大櫆:《奉题学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韵》,《刘大櫆集》,第438~439页。他反对朱陆异同之论,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无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58)刘大櫆:《息争》,《刘大櫆集》,第16页。,主张息争。他也反对理学家好古而失之愚;反对理学家重男而轻女、重富贵而轻贫贱,以为“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贵者不能,而乞人能之……”(59)刘大櫆:《乞人张氏传》,《刘大櫆集》,第208页。;反对经义八股,以为八股文“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60)刘大櫆:《张俊生时文序》,《刘大櫆集》,第104页。。吴孟复据上述内容得出结论:刘大櫆“有些话,竟似出于李贽、吴敬梓、曹雪芹之口。所以,把方姚与程朱理学联系在一起,还是‘事出有因’;如果也把刘大櫆与程朱理学混为一谈,则未免冤屈已甚了”(61)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72~80页。。吴孟复站在当代高度,烛照刘大櫆诗文,揭示了其思想的独到价值,从而稳定了其作为桐城派三祖之一的经典地位。
吴孟复指出:“‘桐城文’是文艺散文。”(62)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1页。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桐城文的最突出特点是“把小说技巧吸收到散文中”(63)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前言》,第1页。。方苞首倡义法之说,以清真雅正标准衡文,最看重古文之体的雅洁。他那段经典性的表述是:“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64)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见《隐拙斋文钞》卷四,乾隆庚午(1750)毛贽跋本,第7页。为了雅洁,方苞首先排斥的,就是小说家言。归有光为桐城派所尊仰,闻一多却发现,明代文学的主潮是小说,归有光之所以成为欧阳修以后唯一顶天立地的散文家,就是因为他“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是沾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65)闻一多:《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见《闻一多全集》(一),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05~206页。。吴孟复接过闻一多的识断,对桐城派的创作下一转语:桐城派学者继承归有光之处,主要就是“把小说描写方法用入散文”;他们“在散文写作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现,采用一些白描方法,特别是注意特征性细节的描绘。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从开端、发展、高潮到结束,情节基本完整。特别是探监一段……有人物肖像,有心理解剖,有动作,有语言,通过这些,写出人物的形象,显示人物的性格。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这完全是小说的笔法’”(66)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40页。。桐城派上接《左传》《史记》,下承唐宋八家和归有光。《左传》《史记》和韩文、归文的写人记事皆用小说笔法,桐城派散文将小说笔法用入散文写作,可谓其来有自。吴孟复的发现说明,桐城派学者的理论和创作之间,并非完全吻合。
从“‘桐城文’是文艺散文”的判断出发,吴孟复以为:桐城派学者往往在古文写作中,“借助于比、兴手法”;“利用散行语言的特点,从多层转折中,做到委曲尽意”;词必己出,“用接近于口语的文字,写平畅简洁的文章,不肯蹈袭前人的一言一句”;往往以诗为文,“以诗的神韵特别是以‘不说出’写‘说不出’之妙,用入文中,使散文诗化”,等等(67)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14~15页、39页。。
必须郑重道及的是,吴孟复凭借在桐城派研究方面的渊深学殖和敏锐灵动的艺术感觉,很早就发现了毛泽东文章中的桐城派元素(68)王达敏:《毛泽东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曾国藩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的经典学者。他对桐城派的推扬,使桐城派长久牢牢盘踞于文坛核心,湖南学界尤其为桐城之学所笼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受到景仰桐城派的师长熏炙,数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倾向、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创作风格等都打上了桐城派烙印。但是,毛泽东在世时,他与桐城派的关系绝少引起学界关注。1969 年,吴孟复被遣送淮北乡下劳改。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匮乏、体力劳动强度极高、慢性肺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阅读马列毛著。在读毛著时,“他咬文嚼字,划段析句,后来竟然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发现与桐城派文章的相通之处”(69)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见《相麓景萝稿》,第10页。。无独有偶,吴孟复的总角至交舒芜也直觉到了毛著与桐城派祖师韩愈之文的渊源。舒芜的老友汪泽楷在湖南一中与毛泽东同学。他告诉舒芜:“毛泽东起床很早,宿舍采光不好,他起床后就站在宿舍窗口,就着光大声朗读韩愈文章。”舒芜说:“这同我的一种揣想很符合。我一向觉得毛泽东文章很有韩愈气味,可能他对韩文下过工夫,果然如此。”(70)舒芜:《汪泽楷教授点滴》,见《牺牲的享与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4页。在特殊的时代氛围中,吴孟复与舒芜当然无法对自己的发现作出阐述,但他们作为桐城派的行家,确定毛泽东的创作与桐城派的内在联系,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吴孟复对桐城派与王学左派、颜李学派关系和刘大櫆思想独特性的论述,彰显了该派尊奉程朱理学之外,在思想方面的多元选择。他对桐城派学者引小说元素入文的论述,解释了在晚清民国,该派何以能够产生出林纾、姚鹓雏和潘伯鹰等小说家的缘由。他对桐城文是文艺散文的论断,显露出五四新文学中散文体裁与桐城文的丝连。这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在学理上为桐城派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内在依据。
四、守望桐城的壁垒
桐城派是吴孟复和舒芜共同的精神摇篮。他们少年时代从桐城派出发,始则并辔而齐驱,继则分道而扬镳,各自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1980年,吴孟复和舒芜度尽劫波,在京华重晤,都已进入斜阳岁月。吴孟复赠诗给舒芜:“倾盖相逢各少年,都门重聚两华颠。”(71)舒芜:《吴孟复作〈唐宋八大家简述〉序》,见《舒芜集》(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但是,由于阅历、思想和艺术趣味的差异,关于如何对待桐城派问题,他们之间发生了连绵十余年的或明或暗的争论。吴孟复从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文革”中醒来,捍卫华夏传统文化,尤其捍卫桐城派;舒芜则痛定思痛,站在五四新文化派立场上,对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展开批判,尤其从各个层面对桐城派进行解剖。吴、舒之争,成为桐城派走向终局时代的一首哀歌。
关于唐宋八家。唐宋八家是桐城文统的核心。自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之后,桐城派学者多致力于研习唐宋八家之文,因而被视为唐宋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孟复因爱嗜桐城文,而及于八家,撰《唐宋古文八家概述》,以颂其功。此书有殊前哲处在于,他以语言为本位,论述八家的文学贡献。他认为:“‘八家’的所谓‘词必己出’,其实就是从书面语言中选用一些人们常见易懂的词语,也从口语中提炼出一些为普通读书人多能理解的词语,按汉语句法、章法、篇法,加以组织安排,做到‘文通字顺’。因此,就表现为语言的通俗性与自然朴素美,较充分地发展其尽意的功能。”(72)吴孟复:《〈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后记》,见《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33页。同时,他指出:“既知‘八家’之起弊,又知‘八代’之非衰,知‘八家’集‘八代’之成,然后可与论‘八家’之胜。”(73)吴孟复:《〈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后记》,见《唐宋古文八家概述》,第253页。书成,吴孟复请舒芜作序。舒芜在序中却着着实实对吴孟复的著作喝了倒彩。舒芜说:他不喜欢唐宋八家,也不喜欢后人编排出来的唐宋八家名目,因为,“‘八家’之首的韩愈,在《原道》里编排出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名单,其意即以继承‘道统’自命。同样,编排和鼓吹‘唐宋八大家’这个‘文统’的名单,其意亦即以继承这个‘文统’自命。而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总要攘斥异端,定于一尊,顺我者正,逆我者邪,如韩愈在《原道》里就杀气腾腾地宣布要对佛教徒实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他认为,吴孟复的这项研究“是内行人说内行话”,但对八家未免“偏爱”;他提醒青年读者阅读吴著时,应知道五四新文学家对桐城谬种的抨击,知道曾经发生过反对“八家—桐城”正统权威的严重斗争(74)舒芜:《吴孟复作〈唐宋八大家简述〉序》,见《舒芜集》(二),第367~369页。。吴孟复不同意舒芜对唐宋八家的指责,不同意舒芜对尊奉八家为正宗的桐城派的指责,因此在《唐宋古文八家概述》问世时,毅然将舒序黜落。
关于桐城派讨论会。1985年11月1日至7日,首届桐城派讨论会在桐城举行,舒芜、吴孟复均被盛情邀请。会前,舒芜就表示:“桐城派我不懂,也不喜欢。”(75)舒芜:《致左孝武》(一),见《碧空楼书简》,第101页。会间,他建议桐城举行方以智学术讨论会,以为“这比桐城派讨论会有意思得多”(76)舒芜:《致左孝武》(三),见《碧空楼书简》,第102页。,而且特意表示“我不是回来参加研讨会的,我是借此次会议回来走访亲朋故旧的”(77)杨怀志:《舒芜先生与桐城母校》,见陈半湾编《思想者的智情意——读忆舒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90页。,所以参加完开幕式就离开了。吴孟复则不然。他由女公子吴布陪同,兴致盎然地与会,提交论文之外,还赋诗十余首:《陪梦笤先生自合肥同车至桐城》《与梦笤先生、舒芜兄弟游浮山》《重至桐城参加文派讨论会赋此(三首)》《桐城晤舒芜》《论桐城派(八首)》。对于这次盛况空前的会议,舒芜的冷淡与吴孟复的兴会淋漓,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桐城谬种问题。自1980年起,吴孟复写下一系列研究桐城派的论著:《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色》(1980)、《桐城派三题》(1982)、《略论梅曾亮与桐城派》(1982)、《论刘大櫆与桐城派》(1983)、《简论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1985)、《刘大櫆文选》(1985),等等。在这些论著中,吴孟复不接受五四新文化派所作出的“桐城谬种”判决,对桐城派的勋业给予很高评价,引起学界关注和呼应。此时舒芜正试图回归五四,不惬于吴孟复等重审“桐城谬种”旧案,于1987年3月2日撰下长文《“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舒芜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王若霖、钱大昕、冯桂芬、蒋湘南、陈澹然和章太炎对桐城派的訾议,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傅斯年对桐城派的笔伐,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周作人对桐城派持续地挖根式的解析,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既是中国文学史的必然发展,又是作为当时中国改革运动一部分的必要的斗争,今天完全应该给以肯定,不应该否定”;“我们应该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广阔视野来观察问题,应该比前人更加痛感桐城派的‘道统’和‘文统’的反民主反科学的性质,更加深入地剖析桐城派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整套封建主义的结构。不管今天纯学术地讨论起来,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历史上却只有一种理学活生生地存在过,那就是鲁四老爷的理学,不动声色不沾血腥地吃掉了祥林嫂的理学;那就是冯乐山的理学,有声有色鲜血淋漓地吃掉了鸣凤的理学。桐城派所载的就是这个道。离开这个道,就不是桐城派,不是历史上现实地存在过的桐城派。所谓‘桐城义法’,完全是为这样的道学服务,适应于这样的道学的需要的”(78)舒芜:《“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续),见《读书》1989年第12期。。《“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写定后,舒芜并没有急于投稿。就在他沉淀之时,吴孟复又连续刊出《略谈柳诒徵先生的治学与教学》(1987)、《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1988)、《文献学家萧穆年谱》(1988)。舒芜面对吴孟复等学者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中国传统的回护,面对那场政治大波,决定发表《“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读书》1989年第11期、第12期)。吴孟复及其弟子杨怀志读了舒芜之文,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杨怀志立即针锋相对,于1990年1月24日写下《桐城派研究的回顾》一文,历数前人对桐城派的赞誉,指责舒芜数典忘祖(79)杨怀志:《桐城派研究的回顾》,油印本。。吴孟复则沉稳地校理着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刘大櫆集》(1990),抓紧撰写《桐城文派述论》(1992)。在《桐城文派述论》中,他论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兼斥“桐城谬种”之说,不点名地与舒芜争辩。
关于编纂安徽古籍丛书。1984年,安徽省成立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甄录校释历代皖人著述。吴孟复任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舒芜、马茂元等被聘为学术顾问。此后十年间,吴孟复为纂修这套丛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丛书草创阶段,吴孟复以自己熟稔的桐城派著述为基础,编制工作规划。丛书第一种1989年问世,至1991年,共出版14位作者的21种著作,其中,桐城派就有5位学者的11种著作入选,分别是马其昶撰《定本庄子故》《桐城耆旧传》,姚永朴撰《旧闻随笔》《文学研究法》,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方苞撰《方望溪遗集》,姚莹撰《康輶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寸阴丛录》。吴孟复还为《方望溪遗集》《识小录·寸阴丛录》《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撰序。对于恩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他撰序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书后予以倡扬。这些文字俯仰今古,感慨万千,充满真知灼见。对于幼时就读过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他推崇备至,以为此书著录桐城派学者,“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实为研究桐城文派最佳之工具”(80)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见《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第47页。。但是,吴孟复以桐城派为重心的编纂方针和已出之书不尽如人意的编校质量,引来舒芜非议。1991年12月7日,舒芜说:“安徽古籍丛书,我被列名为编审委员会顾问之一,实际什么也没有做。我这里看到几种,觉得校勘和标点较粗,可议处颇多;又选目偏重桐城派,我甚不以为然,即如《桐城文学渊源考》一书,几乎举全国文人尽入于桐城派,实不足据也。”(81)舒芜:《致左孝武》(十八),见《碧空楼书简》,第118页。
舒芜是一位思想家。他幼承家学,在桐城派的文化土壤中成长。接触五四新文化后,他信奉民主与科学,主张个性解放,离桐城派日远。1949年后,经过思想改造,他“要完全抛弃从‘人’出发、人道主义、人格力量这些五四传统中最好的东西”;“运用政治标准来把一切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想归入有害于革命工作一类”。他说:当时他没有觉察到,改造知识分子“所用的标准常常是接上了新说法的儒家理学家的伦理道德,乃至小市民小农民的修身处世标准”。又说:“我自以为学到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又说:他的进步,“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82)舒芜:《〈回顾五四〉后序》,见《舒芜集》(八),第366页、380页、275页、388页。。1979年后,他对过往经历进行反思,矢志回归五四。他说:“检点下来,我原来的几个思想基点之中,只有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学,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点,大致还能保存;其中有的例如‘个性解放’思想虽被我宣布抛弃了,有些淡化了,生锈了,但大致还能寻回来,磨濯干净。我只能就在这几个思想基点上,尽量做点事。”(83)舒芜:《〈回顾五四〉后序》,见《舒芜集》(八),第389页。在舒芜回归五四之路上,学尊程朱、文法韩欧的桐城派被他视为封建专制文化,受到狙击。
与舒芜不同,吴孟复是一位纯粹学者。他早年受国学湛深的师友甄陶,建立起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中叶,他在为姚永朴撰《七经问答》所撰后序中说:“世方废经蔑孔子,诐词邪说,横被天下,亘古未有。”(84)吴孟复:《自传》,未刊。这样的想法显与五四新文化思潮相悖。他出身大地主之家,又曾在旧军政机构和大学里做事,这成了他在后来的原罪。1957年,他在原罪之上,又添新愆。在救赎中,他虽历尽磨难,但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信仰从未动摇。1979年昭雪后,其职志就是以“文章报国”(85)吴孟复:《康衢颂十二首》其七,第47页。、“以涓埃报盛时”(86)吴孟复:《训诂通论·后记》,见《训诂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具体说来,就是以研究古典传统的实绩来润饰鸿业。对于遭遇的苦痛,他从不抱怨。国庆三十五周年时,他写下《十喜吟(十二首)》,其一曰:“三十五年惠爱深,我和草木共逢春。春光万里人人乐,我唱山歌给党听。”(87)吴孟复:《十喜吟》,见吴布整理:《吴山萝诗存》,第48页。也是这一年,舒芜、王以铸、吕剑、宋谋玚、荒芜、孙玄常、陈次园、陈迩冬、聂绀弩所著旧体诗词合集《倾盖集》出版。九位诗人,除陈迩冬曾是现行反革命外,其他八人都是右派。《倾盖集》所抒发的,正是从动荡年代走过的诗人的忧喜(88)舒芜:《倾盖集》,见《牺牲的享与供》,第277~278页。。舒芜本来也约了吴孟复的诗作,但其枯木逢春式的诗思因与该书格调不合,而被摒弃。吴孟复早已被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化。1992年8月20日,他说:“桐城之学之文,此文化之菁英,天下之公器,终必传世不废。且吾读书数十年,先后数更其专业,而桐城文心之妙,文法之奇,所以助读书作文者,久而愈见其为用之广。”(89)吴孟复:《〈桐城近世名人传〉序》,见陈所巨、杨怀志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第3页。说此话离其辞世已经不远,可视为其晚年定论。所以,当舒芜谴责桐城派时,他除了坚守桐城壁垒,实在别无选择。
百余年来,在西风东渐的大变局中,如何面对异质的西方文明,如何面对悠久的华夏传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桐城派是吴孟复、舒芜共同的精神之根。但是,后来,吴孟复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捍卫桐城派,舒芜站在五四新文化派的立场拒斥桐城派。他们之间的纷争,正是时代难题具体而微的展现。
五、岿然灵光
民国文坛主要由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组成。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影响有限,鲁迅说:当时“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90)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因而才有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的登场。此后至抗战军兴,新文学有长足发展,古典文学也有很大施展空间。1947年4月11日,胡适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会中,“对目前白话文退化情形慷慨陈词,希恢复三十年前精神,应请政府切实提倡白话文”(91)《白话文退化!》,见《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4月11日。。可知直到那时,白话文体写作还没有获得压倒性优势。就桐城派而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它虽再无五四前的赫耀,但也仍在万方多难中,在与新文学并峙、交融中,调整并寻找着新的方向,人才鹊起,成就卓出。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徐树铮主持的正志中学、周学熙主持的宏毅学舍、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专、张学良创办的萃升书院、梁建章主持的莲池讲学院、步其诰主纂的《四存月刊》、张家骝主纂的《民彝》杂志、陈灨一主纂的《青鹤》杂志、刘叶秋主纂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以及海内各大、中、小学校的国文教科书,皆是桐城派盘踞之所。吴孟复正是在无锡国专成长起来的桐城派嫡裔。
桐城派真正走向终局,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
在新的历史时代,桐城派失去了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单就文化环境而言,国家以白话文著作为基础制订的语文政策,收窄了以文言写作为特征的桐城派的腾挪空间。1951年1月,中央决定颁布指示,纠正各类公文中的文字缺点。这些缺点最常见的“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1月27日至2月28日,毛泽东对该指示稿予以修改,并在2月25日批示胡乔木:“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92)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1949.10-1952.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2~293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吕叔湘、朱德熙在三个月内撰成《语法修辞讲话》,于1951年6月6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语法修辞讲话》刊出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93)《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第3版。接着,吕叔湘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主持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于1960年出版了试印本,1978年正式发行,至今已修订印刷了七版。“《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以文言为主,从来没有人做过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94)张伯江:《吕叔湘:语言研究中的破与立》,见《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第11版。。新时代的国家语文政策,看重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价值,忽视文言文著作的意义。至此,在语文层面,由晚清至五四发动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终于取得完全胜利,而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终于走到了尽头。且1949年之后,毛泽东承五四传统的绪余,以阶级分析的眼光,视桐城派为地主阶级文化,对桐城派全面否定(95)详见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61.07-1966.09),第503页;毛泽东:《致康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6页。,这些都加速了桐城派的终结。
1949年至1979年间,在国家的语文政策和毛泽东否定性评价影响下,桐城派学者的文学创作已经没有合适的发表园地,学界对桐城派微弱的肯定之声也被强大的批判之声所淹没。关于肯定,马茂元说:“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文学流派,是它对于散文创作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鲜明的主张,而这一流派的作家都能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贯彻和充实这个文学理论和主张,从而扩大它的影响。”(96)马茂元:《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语文学习》1957年第10期。王气中说,桐城派“继承了中国以前的文论传统,加以总结、发展, 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97)王气中:《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1957年。。李鸿翱从古为今用的角度着眼,以为桐城派在当下依然“还有很小一部分, 是有其继承价值的”(98)李鸿翱:《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光明日报》1961年5月7日、14日。。钱仲联从桐城派学者的创作、评点及其古文与时文之辨等方面驳斥了桐城古文为时文变种之见(99)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这些肯定桐城派的学者多与桐城派有一定渊源。至于否定的文章则不胜枚举。“文革”十年,严肃的学术讨论完全停止。1975年,桐城派故乡的文教局成立桐城派批判小组,写出《桐城派是一个反动的儒家学派》(100)桐城县文教局桐城派批判小组:《桐城派是一个反动的儒家学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这样的文字,该是桐城派前贤在九泉之下所想象不到的。
1949年之后,那些漂泊海外的桐城派学者依然在孜孜以求。钱穆为学根柢在桐城之学。他早年对姚鼐、曾国藩高山仰止,以为“天下学术,无踰乎姚、曾二氏”(10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卷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他对桐城之学依然情有独钟,以为学文应从姚、曾所纂两书入(102)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5年,第307~308页。。其弟子叶龙因著《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而享誉学界。曾克耑受钱穆奖掖,任教于新亚书院,在课堂内外,竭力弘扬桐城之学(103)曾克耑:《述桐城派》《自叙》,分别见《颂橘庐丛稿外篇》卷三、卷三十八,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61年,第59~106页、1590~1576页。。李钜在台湾一边行医,一边撰写诗古文辞。因亲经乱离,其诗文沉郁顿挫(104)李钜:《李钜诗文集》,稿本,李建雄先生收藏。。贺翊新在台北两度出掌建国中学达十五年之久,哺育人才无数(105)钱复:《追忆建中校长贺翊新》,见《建中校友》;杨照:《大学应该比社会更自由》,《星州日报》2012年6月2日。。陈赣一到台湾后因文笔优雅而出任省政府秘书(106)吴琪整理:《少帅身边的黎川秘书》,见风雅黎川的博客,2016年3月1日。。周明泰在美国继续其戏曲研究(107)沈津:《周志辅和他收藏的戏曲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这些身在海外的桐城派学者虽然努力绍斯文之传,但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笼罩下,终不免落寞。随着他们的离世,桐城之学在海外也渐入杳寂。
1949年至1978年间,吴孟复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能钻缝窥隙,研磨学业。1957年,吴孟复在合肥教师进修学院成为右派后,离开三尺讲台,到图书馆从事古籍编目工作。爱书如命的他获此良机,干脆吃住在编目室,整日寝馈书丛,尽管肺疾已深,仍焚膏继晷地博览深研。这一阶段的阅读和编目,为其重见天日后的学术腾飞奠定了基础。1979年2月20日撤销右派处分后,至1995年2月1日逝世前,吴孟复的生命突然迸发出耀眼光芒。整整十六年间,他以浸润着桐城风格的诗文创作和丰赡的文献学成果为桐城派增光添彩;以深刻诠释唐宋八家和桐城派的著述把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以坚韧果决守望着桐城派的壁垒。就此而论,海内并世的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不能与其并驾,海外当代的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同样难以与其偶驰。由于大半生在蹭蹬和扰攘中度过,在学问的崎岖小路上,他拖着残病之躯,不畏劳苦,“三更灯火五更鸡”(108)吴孟复语,见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相麓景萝稿》,第16页。地攀登着,却并没有达到光辉的顶点。这自然不单是其个人的不幸。尽管如此,在当代学术从荒芜走向复苏的关键时刻,在桐城派经过数百年起伏跌宕而走向终局的时候,正是他以艰苦卓绝的奋斗,为桐城派赢得了最后的尊严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