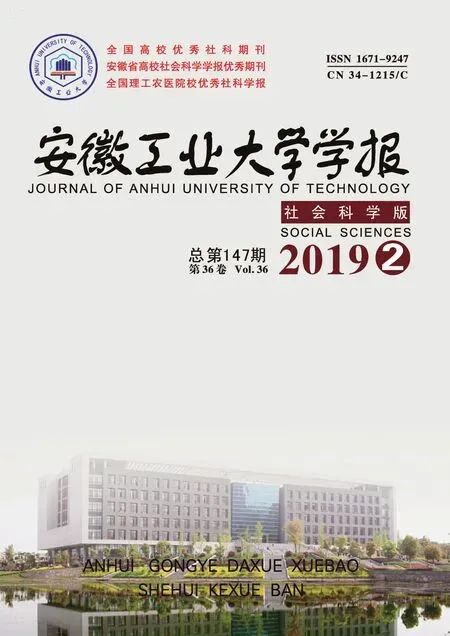从反叛到覆灭:《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反成长主题解读
李 健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2)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过度痴迷于守护儿童纯真、维护事物永恒和世界纯洁的虚妄梦想之中,试图通过延缓甚至反转儿童成长的自然进程来保持儿童的纯真和美好,他惧怕万物恒变,妄想以一己之力去维护事物的永恒与世界的纯洁。在小说的结尾,霍尔顿困惑依旧、抑郁如初,终因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而入院治疗。本文拟从“反成长”视角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题内容,旨在深化对这部小说中反成长主题内涵的理解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索,展现成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耽于幻想:虚妄的反成长之梦
霍尔顿受困于生活中的挫败与抑郁的纠缠之中,无法在异化疏离、荒诞扭曲的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于是,他试图躲避在自己编织的梦想之中,因为只有在此处他守护儿童纯真和事物永恒的堂吉诃德式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尽管,这种梦想本质上是虚幻且违背儿童自然成长规律的。霍尔顿的虚妄梦想主要体现在对儿童纯真、事物永恒以及守望麦田的理想的痴迷与渴求之上。
(一)对儿童纯真的极度痴迷
在霍尔顿眼里,弟弟艾力和妹妹菲比是纯真和美好的化身,他对已去世的弟弟艾力的过度怀念和对年幼妹妹菲比的过度保护体现了他对儿童纯真的极度痴迷。如科尔索所言,在文学中,青少年遭遇重大变故,如兄妹同胞的突然离世或同伴的自杀行为极易导致青少年难以言表的悲痛和对社会习俗盲目的抵制情绪[1]92。弟弟艾力因患白血病而突然离世给霍尔顿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愧疚感,即他潜意识里认为正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才导致了弟弟艾力的死亡,他保护儿童纯真的强烈愿望也来自于他对弟弟的这份愧疚感。弟弟虽去世已久,但霍尔顿认为弟弟比周围活着的人仍要好上一千倍,每当其遇到精神上或现实中的危机之时,他都会向弟弟祷告、交流[2]189。霍尔顿在纽约街头流浪之旅开始之际,这个孤独的反叛少年几乎无人可以倾诉,唯一可以与其心灵沟通的人是其妹妹菲比[2]75。霍尔顿也因菲比坚持同往而放弃了去西部山区的隐居计划。一方面,霍尔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给菲比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霍尔顿内心深处有着保护妹妹童真的强烈愿望,希望她永远不受时间与世俗的影响。
(二)对事物永恒的强烈渴求
霍尔顿对事物永恒不变的强烈渴求主要体现在他对博物馆的迷恋之上。在小说中,塞林格用了较大的篇幅描述霍尔顿对博物馆的钟爱与痴迷,当霍尔顿带着两个小孩在博物馆里参观法老墓和木乃伊时,他突然感受到了某种永恒的美好与宁静,甚至开始喜欢上了它们[2]224。在霍尔顿眼中,法老墓和木乃伊一如儿时的记忆一般永远待在那里,时间仿佛在他们身上停滞了,那份永恒的宁静正是他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在潜意识里,霍尔顿惧怕自己和外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为自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长大并一步步迈向他所深恶痛绝的成人世界而忧虑重重。在外在的现实世界中,霍尔顿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上的巨大压力与挑战,且在多数情况下,他都疲于应付,未能与外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只有在博物馆他才不用理会世俗的批判和人际交往的障碍,安静地享受内心的宁静与喜悦。霍尔顿对博物馆里法老墓和木乃伊的钟爱与痴迷,以及对简单、宁静、孤独的隐居生活的无比向往,体现了他对万物恒变的无名恐惧和对事物永恒的强烈渴求。作者塞林格通过笔下的霍尔顿表达了自己对宁静美好的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世界万物永恒不变的渴求,塞林格在盛名之际突然过上隐居生活的经历正是霍尔顿向往隐居生活的现实体现。
(三)对守望麦田理想的过于执着
霍尔顿认为腐化堕落的现实世界中已没有他能追求的目标,唯一可为之而努力奋斗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幻想自己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守护着在麦田里四处奔跑的儿童以防止他们跌落悬崖。此处,“麦田”象征着美好纯真的儿童世界,而“悬崖”则象征着堕落的成人世界,霍尔顿认为成长就意味着跳下悬崖,跌入肤浅、虚伪、冷漠、空虚和道德败坏的成人世界。霍尔顿“疯狂”的守望行为在本质上是虚幻且注定失败的,因为他上帝式的拯救行为与残酷的现实是相背离的。其一,霍尔顿本人也仅是个经验浅薄的16岁少年,他不具备拯救儿童、保护纯真的现实能力,也无法为其救赎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其二,霍尔顿的守望理想与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完全背离,“疯狂”的悬崖峭壁之下的成人世界虽堕落腐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其三,霍尔顿自我任命的守望者身份本身也深受质疑。在小说开始及结尾之际,霍尔顿曾两次求助老师的经历表明在其潜意识里并非真想成为一名守望他人的守望者,而是想成为一个被他人守望救赎的求助者。站在无边麦田的边际,霍尔顿才是那个最有可能跌落悬崖的无助者,他并不具备承担守望他人的能力,其自我任命的守望者一职仅是他无法摆脱自身困境的外化表现而已。从这个角度而言,霍尔顿并非一名真正的守望者,他仅是自己虚妄梦境中的守望者而已。
在传统成长小说中,守望者的角色一般由社会中的成人来担任,他们肩负着指引和监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责任。然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理应承担守望者角色的父母、兄长或老师集体失职,在物欲横流且精神贫瘠的社会背景中,追逐名利的物欲和现实生活的无形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个人事业的发展之中,忽视了对青少年的精神关爱和对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的营造,客观上造就了成人与儿童、老师与学生之间强烈的异化疏离。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中的成人本质上是已经放弃守望职责的守望者。
对小说中妹妹菲比角色的解读,文学评论界曾出现过不同的声音,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菲比是守望者还是被守望者的身份界定上。霍尔顿认为菲比是一个典型的天才儿童,她既如儿童一样纯真又如成人一般理智而负有责任感,且足够敏感细腻,能轻易看透事物的本质,菲比就曾当面指出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均毫无兴趣[2]187。霍尔顿一直以来把自己当成菲比的守望者,但当他把红色猎人帽送给了菲比时,守望者与被守望者之间的角色就发生了转换;带着红色猎人帽的菲比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此时的菲比俨然变成了霍尔顿一直以来苦苦寻求的守望者,而霍尔顿则变成了放弃守望之职的求助者。虽然菲比是使处于困境之中并决意离开城市喧嚣前往西部山区隐居的霍尔顿重返现实世界的重要人物,但菲比毕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她并不具备必要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去点化、救赎困顿之中的霍尔顿,从这个角度而言,菲比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临时守望者。
二、走向覆灭: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填补人民精神上的空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毫无生机、异化疏离和缺乏公正的精神荒原,这个时期的美国被称为“寂静的十年”或“怯懦的十年”[3]11-32。主人公霍尔顿的悲剧命运除与社会背景有关之外,主要根源在于其逆来顺受的性格缺陷、虚无模糊的抗争目标、挥之不去的死亡情结以及试图维护世界纯洁的虚幻使命。
(一)逆来顺受的性格缺陷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父母几乎都是缺席的存在,整部小说均未提及霍尔顿与父母之间任何直接的交流行为,母亲考菲尔德夫人唯一一次正面出现仅是当霍尔顿躲在妹妹菲比的房间,隔着衣柜听到母亲与妹妹菲比之间的对话而已。据霍尔顿表述,父亲脾气暴躁且有暴力倾向,经常因琐事而惩罚他,持续的惩罚行为导致少年霍尔顿怯懦、顺从的性格缺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化表现为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霍尔顿的性格缺陷和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在家庭和校园生活中多有体现。在家庭中,霍尔顿与父母关系冷漠,与哥哥日渐疏离,唯一能与其交流的只有未成年的妹妹菲比。在校园里,他经常被同学欺辱却不敢正面回击,小说中曾两次提及霍尔顿与同学打架,均以悲剧收场,但他借口因手不能握拳而刻意逃避性格软弱的事实;他喜欢一个名叫琴的女孩,却犹豫多次仍未有勇气向其表白;他的手套被同学偷走却不敢有任何反抗;他被学校开除却不敢回家直面父母的责骂等等。
文学评论中经常将霍尔顿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贝利·费恩相提并论。布兰奇认为哈克贝利是一个简单、智慧而富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他的言行举止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冒险精神[4]144-158。而作为现代人代表的霍尔顿却怯懦顺从、不堪一击,与哈克贝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霍尔顿本性善良而又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但他总是耽于幻想,无力反抗。怯懦与反抗在霍尔顿身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霍尔顿深受社会和家庭的冷漠之痛,但却出于自负而不愿直视其悲惨而孤独的现实处境,总是选择用逃离的方式来消极应对,被动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打击与挫败。霍尔顿的悲剧命运结局从其性格缺陷中可窥见一斑。
(二)虚无的抗争目标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生死抉择,体现了他内心的彷徨与痛苦。哈姆雷特的困惑在于虽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但缺乏为之奋斗的坚强意志,而霍尔顿的困惑在于既没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亦没有为之奋斗的勇气和决心。尽管他通过自暴自弃式的言行举止、假装趋同、谎话连篇以及反叛逃离等方式极力宣泄着心中的愤懑,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为之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霍尔顿看待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价值观念是简单而扭曲的,在他看来,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是两个对立的存在,世间万物仅是简单分为两个类别,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对即错。任何与成人世界相关的事物都是邪恶而虚伪的,是其极力反对和回避的,而与儿童世界相关的一切都是善良、美好而纯洁的,是其极力维护和推崇的。这种简单扭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得霍尔顿在反叛逃离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清晰、明确的抗争目标,一直是在与整个成人世界进行着盲目虚无的抗争,这种反成长的抗争方式严重阻碍了霍尔顿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正向成长,必将无疾而终。
(三)挥之不去的死亡情节
纵观整部小说,霍尔顿在其苦难的反叛历程中曾多次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甚至徘徊在生存和死亡的边缘。霍尔顿经常幻想自己在过马路时会突然消失,他对博物馆里的法老墓和木乃伊情有独钟,对死去的弟弟艾力异常思念,对众人在艾力坟前避雨的狼狈场景耿耿于怀;他还经常幻想如果再有一次世界战争,他一定会主动要求坐在原子弹之上,随之离去。据统计,在小说文本中“death”或“died”等表达死亡意象的词语共出现了25次之多,霍尔顿对死人或死亡的偏爱显示其潜意识里有着严重的死亡情节。弟弟艾力去世时,家人拒绝让其出席弟弟的葬礼,使霍尔顿无法以合适的方式舒解心中的巨大伤痛,在其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永久伤痕和无法弥补的遗憾,客观上加重了霍尔顿的死亡情节。每当霍尔顿身处困境之时,他都设法与已故的弟弟艾力进行“交流”。如当其被电梯工莫里斯敲诈后,他开始大声地向弟弟“说话”。当过马路时,他祈求弟弟不要让他消失。在纽约中央公园湖畔,他祈求弟弟不要让自己死去。霍尔顿的死亡情节反映出在其内心深处对关爱和尊重的渴望,他的父母对霍尔顿愈发漠不关心,但却为艾力的夭折而伤悲不已,这使霍尔顿在潜意识里认为死亡是换取父母和他人的关爱与同情和摆脱世间困难、伤痛的唯一方式。
霍尔顿的死亡情节在其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度恐惧感与抑郁情绪。“抑郁”一词在小说中共出现了31次之多,持续的抑郁情绪若不合理应对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饱受恐惧和抑郁的煎熬,霍尔顿最终并未主动选择死亡。同班同学詹姆斯·凯瑟尔因不堪其他同学的凌辱而跳窗自杀的行为让霍尔顿无比震惊,导致詹姆斯死亡的罪魁祸首未受到法律的惩处而逍遥法外的事实让霍尔顿最终彻底惊醒。詹姆斯自杀时正穿着霍尔顿的外套,在霍尔顿的潜意识里不自觉地把詹姆斯的死亡和自己的反叛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面对恶人没有恶报的残酷现实,霍尔顿开始担心自己与堕落腐化的成人世界之间的抗争也会如詹姆斯一样以死亡为最终结局,正因为如此,霍尔顿才假装融入了校园生活,和其他同学一样终日酗酒、抽烟、说脏话、谈性与女人。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痛恨自己肮脏的行为,渴望一个充满关爱、理解与尊重的理想世界,霍尔顿深受死亡情节的折磨,在内在正直善良和外在虚假伪装的矛盾冲突中一步步走向悲惨的命运结局。
(四)试图维护纯洁世界的虚幻使命
身为一个怯懦者和热切追逐理想的青少年,霍尔顿既没有选择为某个高尚的事业而献身,也没有选择安于现状、了此一生,他从反成长的守望麦田之梦中幡然醒悟,却又陷入了维护纯洁世界的新使命之中,试图擦除世界上所有的污言秽语。例如,在去往菲比学校的校长办公室的楼梯上,霍尔顿突然看见了“Fuck You”的字样,便随手将它擦去,但在下楼返回时,在另一个楼梯上他又看到了相同的脏话,他几次尝试均未能擦去,因为这次是被他人用刀刻在楼梯上的[2]222。在享受博物馆的宁静与美好时,霍尔顿看到墙壁的玻璃上也有人用红色的蜡笔写上了同样的脏话[2]222。刹那间,霍尔顿突然意识到不管他身在何处,这个世界早已被虚伪冷漠和堕落腐化的成人所玷污,完全找不到一片干净纯洁的地方。此刻,他终于明白即使给他100万年的时光,都无法除去世界上一半的污言秽语,自己试图维护世界纯洁的使命如同守望儿童的理想一般荒诞不经,永远无法实现。此时的霍尔顿对自我是极度否定的,对外在世界是极度失望的,对自己的未来是迷惘而恐惧的,这是压倒霍尔顿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之彻底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在苦难的流浪之旅中完全迷失了自我,导致了其精神崩溃覆灭的悲剧结局。
三、结语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成长的环境背景下,霍尔顿未能从迷惘困惑中走向觉醒回归,而是踏上自我迷失与幻灭崩溃的反成长之路。小说对这一人物的刻画揭示了从反叛到覆灭的反成长本质特征,体现了深刻的反成长主题,揭露了美国堕落腐化的社会环境给青少年成长所带来的困惑与痛苦。成长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应加大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力度,为其健康正向成长营造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