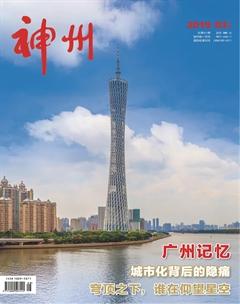城市化背后的隐痛
翟静萍
摘要:《极花》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女孩胡蝶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找工作的时候却被人贩子拐卖到西北一个闭塞没落的小乡村,成为了拐卖者的媳妇的故事。小说借半城市人“胡蝶”的“进入者”的视角,打开屹梁村这闭塞之地,不仅写出了胡蝶作为个体生命在特殊的环境中一步步被动地完成对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写出了她在社会大环境里的挣扎、撕扯和无助。贾平凹以城市化进程下日益凋敝的乡村为书写背景,用温情的笔触批判了人性之复杂,表达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日益颓败、凋敝的隐痛以及对城市化发展的反思。
关键词:乡村;城市;身份认同;人性;城市化
一、身份认同的曲折之路
《极花》讲述的是一位向往城市的农村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获救,最后又自愿回到被拐乡村的经历。这个结果令人无法接受,荒唐却又真实。曾经那么向往城市、厌恶乡村、被拐卖后在屹梁村遭受了种种暴行后、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乡村的一个女孩,为什么选择回到了破落的小山村呢?
主人公胡蝶出身农村,与众多进城者一样,如浮萍般地游走在喧嚣的闹市中。她随母亲靠捡废品维持生计,供弟弟读书。她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却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虚荣。她学着把长发放下来,学习城市姑娘走路,还私扣了母亲要邮寄给弟弟钱中的一百元染了一绺黄头发,最后又买了高跟鞋。一有空就在镜前照脸,给镜说:“城市人!城市人!”。即使是被贩卖到了偏远的乡村,她也忘不了城市人身份象征的高跟鞋,认为“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身份”,于是在被骗进窑洞的那天起,当黑亮给她脱去高跟鞋换上布鞋时,她一下子把布鞋踢飞了,宁愿打赤脚。身在城市的农村女孩胡蝶,内心怀揣着城市人的梦,却还是没有能融入进这所城市,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使得胡蝶虚荣、自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见了第一次外出找工作就遭拐卖的结果。
刚被拐卖到讫梁村的胡蝶性情狂躁,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厌恶和排斥,坚信“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也坚定表示“我肯定要离开这里”。但慢慢地,她开始发现“这个偏远龌龊的村子”居然也有像老老爺这样“浑拙又精明,普通又神秘”的人,怀孕后的胡蝶心理更是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怀孕后,她透过两个树股子突然看到了星,她感觉到自己和孩子都是这村子里的人,命运就属于这个村子,也就是这次看到星回去后她彻底地不再反抗黑亮,把那根放在她和黑亮之间的棍子拿走,主动要求和黑亮亲近。第二次心理转变是生下儿子兔子后,胡蝶抱着兔子往天上看,夜空中不经意星星就出来,两颗星已在看着胡蝶娘俩。之后胡蝶思考既然自己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之后的胡蝶开始真正接受并融入屹梁村,她称呼黑亮的爹为爹,又学会了“伺弄鸡”“做土豆”,更“学会了做屹梁村的媳妇”。
作家走进主人公的内心,细腻地抓住胡蝶所有的细微变化,从奋力逃生到适应、留下,胡蝶一步步学会做屹梁村的媳妇、孩子的母亲时,这个人物才变得丰满复杂起来,她平生第一次触摸到自身存在的某些依据。在这过程中,主人公逃离农村的过程实际上正是适应农村、获得归属感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生活,或是对农村产生了情感牵绊,而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体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星。从城市边缘人到黑家媳妇,再到兔子母亲,有了身份,有了情感支点,胡蝶作为个体的社会身份开始被认可,不再是在城市和乡村间游走的浮萍。
然而,被解救出来的胡蝶,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在城市,她无法安身立命。从媒体舆论到街坊邻里,人们肆无忌惮地评价着胡蝶的遭遇。络绎不绝的喧闹和探视,重复撕开胡蝶血淋淋的伤疤。亲人也并不理解和同情她的痛苦,弟弟觉得被拐卖的姐姐非常丢人。母亲想把胡蝶介绍给一个跋脚。在当地,她无法外出找工作,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本。
故事里的胡蝶从来没有像她的名字一样自由地飞翔过,不堪承受返乡后永不停歇的被评价与被窥视,加之迫切思念留在西北的儿子,她最终选择踏上返回被拐之地的列车。胡蝶最终在黑亮一家的感情中完成了身份与文化认同,控诉也化为了絮絮叨叨。胡蝶“被拐后”的经历,见证了小人物在城市化背景下,展示像胡蝶这样一种半城市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撕裂,见证了主人公实现个体认同的曲折之路,表达了心灵没有阪依和寄托的漂浮感和放逐感。
二、乡村生存之困境
“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很显然,贾平凹更为深切的关注点在于,呈现出在转型期中国和被社会所忽视的隐痛,这个隐痛就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城市文明挤压下,日益颓败凋敝的乡土文明,尤其是凋敝的乡土中隐含的文化与人性的撕裂,人性的复杂。
社会转型期,农村的财富、劳力、女人纷纷逃离农村,涌向城市。《极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乡土的赤贫留不住这里的女人,留守故乡的光棍汉只能通过贩卖人口来“娶”老婆,小说揭示了中国乡村在嬗变的时代下所遭受的人性的扭曲。胡蝶们的“离去”,对农村而言意味着生存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她们这看似自由的城乡流动背后,却是城乡发展的落差与失衡所致。这同样显现了城市文明对农村年轻人在伦理秩序、精神世界等方面的强烈冲击。而她们的离去却又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本就失衡的农村男女比例由此更加恶化,如黑亮所控诉的:“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这必然形成了当下农村剩男问题。这就是贾平凹所看到的“最后的光棍”“中国最后的农村”的危机。如有论者所言:“《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最后的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通过贾平凹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人”的精神变化、个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撕裂和挣扎,看到人的异化,也看到贾平凹对失衡的城乡发展中“人的失落”这一命题的思考,看到“乡村人”的喘息。
贾平凹在《极花》中直面无序混乱的乡土世界。在他笔下,道德、秩序、理性在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乡村“光棍”面前,轰然倒塌。乡村抵不过城市发展的血盆大口,被迫用最蛮横粗暴的方式,维持他们基本的生存。这并非是为人口拐卖开脱,而是展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存在。
三、衰败乡村之出路
《极花》出版之后,社会舆论便产生巨大反响,作品反映出来的拐卖妇女缓解剩男问题的倾向,引起无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剩男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必经历程,拐卖妇女绝不是符合道义、伦理的解决之道。争论也反映了当下我们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女权主义和乡村婚恋的冲突,农村剩男问题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冲突。
小说中的圪梁村可以被看作保存着前现代场景的乡村。在这块蛮荒之地,男人生存的动力是满足他们的消化器官和生殖器官的欲望,而女性则成为了繁衍后代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这块土地是作者的出生地,是作者心心念念隔断不了的所在。小说对农村男性表示了同情,也用温情的笔触批判了人性的复杂。贾平凹在这片日益凋敝的乡土上,寻找着乡土情感的回忆,重建着乡土的精神家园,替乡村人探寻着可期许的精神出路,充分彰显了作家的良心与责任。但作为作家,他只是呈现了这个时代中的痛楚,却无力找到消除痛楚的利剑。
即使乡土的秩序在新的时代面前不堪一击,但是贾平凹对其仍抱有幻想,他在写完《极花》后,想起两句古人的诗:“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一些问题由来已久,但总会有合适的时机,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贾平凹对最后的乡土,最后的守望,最后的人文关怀。乡土文明过去的荣耀,与现在的衰落;过去的淳朴,与现在的“肮脏”,是考量着中国转型期的沉重话题。
作为一部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小说,贾平凹借助《极花》将自己关注的大问题表述出来,这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学问题的定性,而是阐释了一座精神上的乡土孤岛,那就是我们无法洒脱地逃离这里,却也承受不了城市文明的压迫。
参考文献:
[1]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贾平凹.《极花》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文学评论,2016 (03):120-128.
[4]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 (06):66-69.
[5]韩鲁华.写出乡村背后的隐痛——《极花》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6 (03):62-71.
[6]侯玲宽.中国农村的隐痛表达——贾平凹《极花》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 (02):67-71.
[7]顾超.贾平凹《极花》:沉重的现实关切[N].人民日报,2016-01-29 (024).
[8]孔令燕.回不去的田園:《极花》之痛[N].光明日报,2016-05-10 (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