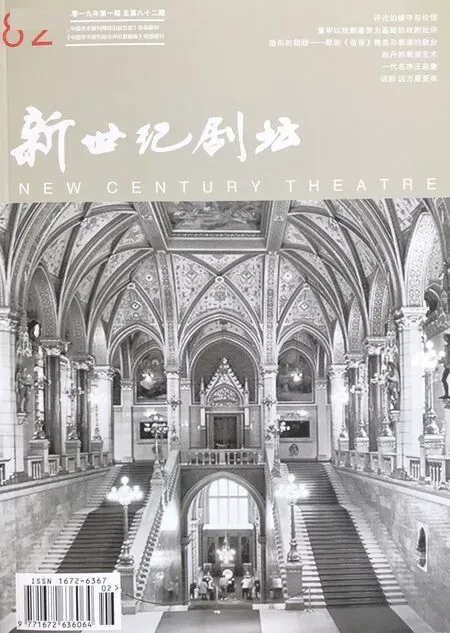一代名净王泉奎
常立胜
噌吰大净溯三山[1],
郎氏新声一脉传。
绝响萦怀犹脆亮,
遗音在耳忆清圆。
“刺僚”几度津门热,
“绑子”频博沪上欢。
一曲高寒人不见,
峰青一数一凄然。
这是1987年6月翁偶虹先生在王泉奎先生病逝后所赋的挽诗,以凝炼的诗文颂扬了一代名净王泉奎先生卓越的艺术成就。
王泉奎先生原名有珊,于1911年(宣统三年)的农历正月十四诞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当时家住在北京城的西便门。由其祖父靠经营小买卖及家庭小手工作坊置办起的一份家业,在其父亲一辈已渐中落。泉奎少年丧父,八岁便到宣武门外的广安菜市当了一名小伙计,后又到烧饼铺学徒。其父、兄都是戏迷,父亲能拉两下胡琴,长兄爱唱老旦。泉奎受父兄影响,也从小爱戏;当时常随其兄到家附近烂漫胡同“常熟馆”里的“娱乐雅集”和校场口内的“余暇寄友”等票房去清唱;兄弟二人合唱《遇后·龙袍》,兄唱李后,泉奎来包公,一时兴尽。
泉奎先生有一副清亮、干净的好嗓子。十六岁那年,一位名叫沈庄儿的盲老头儿走近他,对他说:“眼下北京的铜锤花脸一行已断门近二十年了,像裘桂仙、德子文这些名角都已老了,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不学戏呀?你的嗓音洪亮,学唱‘铜锤’,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个好角儿呢!”并表示愿意帮忙拜个师父。于是,泉奎先生的老母亲临时凑了四块钱,为儿子拜师置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王泉奎便由这位盲人引荐,拜在花脸名教师张春芳先生的门下正式学艺。张春芳系“长春班”坐科出身,与张春彦、李春林、荣春善(蝶仙)、李春才(洪春)等皆为同门师兄弟,后在杨小楼的“永胜社”做管事并广收弟子,课徒授业;张春芳先生的弟子皆以“奎”字排名,泉奎之名即为拜师时由张先生所起(名琴师汪本贞也是张先生弟子、艺名源奎,为泉奎师弟)。收王泉奎时,张春芳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惜爱泉奎之才,寄厚望于斯。张传授泉奎以金(秀山)派的纯正“铜锤”唱法,并结合王的嗓音条件,另借秀山之徒郎德山的清圆韵味加以启发、融化。生性聪颖的泉奎在张春芳先生“鞭打快牛”般的督教下,仅一年时间,即从第一出《高平关》开始,不断地学会了《断密涧》《探皇陵》《白良关》《探阴山》《锁五龙》《草桥关》《刺王僚》等多出铜锤花脸戏;之后张先生领着他去找杨小楼的女婿、永胜社的班主刘砚芳,通过刘先生吸收泉奎进入杨小楼的永胜社“效力”。刘砚芳拉得一手好胡琴,那天便亲自操琴为泉奎吊了一段《锁五龙》。听罢试唱,刘砚芳连声称好,对张春芳说:“行了,下个礼拜就上买卖吧!”泉奎先生在永胜社头一年“效力”,只挣八吊钱的车马费。从第二年开始才正式拿一场戏二块银元零二十吊钱的戏份。杨小楼先生那时较少唱夜戏,以在华乐戏院演出白天戏为多。
泉奎先生初次登台即是与徐霖甫先生在“华乐”合演《遇后·龙袍》。泉奎先生崭露头角之时,正值北京京剧舞台上铜锤花脸人才匮乏之际。此时,金秀山、刘永春、纳绍先、郎德山等已故,书子元、德子文、时玉奎、裘桂仙等老先生也都上了年纪,金少山远在上海,裘盛戎尚在坐科,“铜锤”花脸一行甚显颓势。王泉奎的脱颖而出,并以其洪亮、清脆的演唱很快博得了观众的欢迎与认可,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铜锤”大净求贤若渴的审美需求;年轻的王泉奎迅速走红,成为了受到人们格外注目的菊坛新星。杨小楼先生青睐于他,让他来配演《连环套》的梁九公和《安天会》的天王两个重要角色;尚小云先生更是极有见地地力携谭富英、王泉奎两位青年才俊合唱《二进宫》,三人同样的铁嗓钢喉,生、旦、净始终同唱一个调门,那又是怎样的满宫满调、声情俱佳,留下了多少的绝响佳话!1934年5月,富连成“大盛字”科的学生毕业后应邀赴上海演出,因没有出色的铜锤花脸,蔡荣贵先生便特邀泉奎加入,并将王泉奎的名字临时改作“王盛奎”,与富社学生李盛藻、贯盛习、杨盛春等一行同往沪上,合作演出了包括全部《捉放曹》、全部《击鼓骂曹》(含《群臣宴》《闹长亭》《鹦鹉洲》)在内的众多剧目。当事过六十年,李盛藻先生见到了泉奎先生的嫡孙王硕,仍向他谈起往事:“那是我们头一次搭伴离京去外地,一起演了不少戏,你爷爷那一次就唱红了,以至后来再到上海,剧院广告还在王泉奎的名字下面特注明:即王盛奎也!”自20 世纪3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王泉奎先生一直活跃于舞台,享誉三十余年。曾邀其辅弼的头牌老生演员就几乎囊括了同时代的所有名家:王又宸、言菊朋、孟小冬、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时慧宝、李盛藻、李少春、杨宝森、李宗义及李鸣盛等,其中与谭富英先生的合作长达八年之久。1938年冬,李少春自南方北上挑班,在北京新新大戏院贴演文武双出,声势巨大。谭富英为加强自己的号召力,就想到了以连演《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三折为全部《龙凤阁》来做抗衡。谭就此事商求于正与之合作的王泉奎,王起初对于连唱三折(谭只唱前、后两折,中间换二路老生唱《探皇陵》;旦角也只前、后两折戏;唯花脸是连唱三折且旧《探皇陵》中尚有大段的“数郎”[原板])在嗓音、体力方面有所担心,经谭的一再肯求,便凭着年轻气盛,一口答应下来。即于同年10月15日(李少春打炮戏后第八天)在吉祥戏院由谭富英与王泉奎、陈丽芳联袂上演了全部《龙凤阁》(即《大·探·二》),一时间九城轰动,万众争睹。从此,“铜锤连唱三折”之风盛起,开创了这出传世佳作演出的新形式、新局面。后居台湾的著名剧评家丁秉鐩先生在其《菊坛旧闻录》书中称:“由谭富英、张君秋、王泉奎三个人合演的《大·探·二》是最为标准的一份。”王泉奎秉承金派铜锤的传统唱法,又结合自身嗓音清亮的特点,经不断实践,载励载磨,演唱呈现出工整、严谨、流利、圆润的大家风范。30年代末,由当时北京的“国剧艺术振兴会”组织在新新大戏院举办了有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刘连荣和王泉奎五人参演的花脸大会,剧目为:一、王泉奎《大回朝》,二、刘连荣《下河东》,三、侯喜瑞《丁甲山》,四、郝寿臣《审七公堂》,五、金少山《御果园》,这无疑代表着当时京剧净行的最高艺术水平。时未满而立之年的泉奎先生能以青年之花脸翘楚身份名列于金、郝、侯之后,与诸大家同台奏艺,展示花脸艺术的最高成就,足以说明其当时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和已具有的相当实力与广泛影响。金、郝、侯三位都很赏识王泉奎的资质和表演。据泉奎先生生前所忆:有一次他与梅兰芳、金少山、奚啸伯同在光明大戏院演出,梅先生的大管事李春林先生把他拉到金先生面前说:“还不给三大爷(指金)磕个头!”金少山也笑着问:“你几儿个给我磕头啊?”泉奎虽未拜金为师,却在艺术上受到金的很大影响。他常为金配演《白良关》小黑、《探阴山》判官、《草桥关》马武等角色,俩人同台间,金如巨磬般的黄钟大吕与王似金钟般的清脆嘹亮交响辉映成了一道灿烂的风景线。金少山先生常对人夸讲泉奎:“这小子嗓子好,有出息,将来了不起!”爱才之意溢于言表。40年代,一次金少山与李少春、叶盛章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贴演全部《连环套》,金临时生病,改由王泉奎替演。素来挑剔的天津观众非但没有责怨,反对泉奎先生的表演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王泉奎与裘氏(桂仙、盛戎)两代也都处有很好的关系。王初登台时即常为年高的裘桂仙配演小黑、铫刚;裘在晚年嗓音不济,也常由泉奎顶替上场。40年代裘盛戎滞留沪上,演出缺少行头;每演《盗御马》,王泉奎都把自己从头到脚的服装借给裘用。裘先生曾对他的爱徒李长春夸讲王泉奎先生的演唱,并说:“王先生的嗓子好,一天能赶两包。”

京剧《盗御马》剧照,王泉奎饰窦尔敦
记得早年我去恩师宋富亭先生家探望,恰逢电视中播放山东某名净演出的《刺王僚》。先生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答:“不错。”不料先生说道:“一出场就不对!姬僚要有霸气,翎子怎么能晃来晃去?身份小了!”王泉奎先生的《刺王僚》造诣精深,久享盛誉,堪称其代表作。有人评价:“历史地看,无论纵向或横向地比较,王的《刺王僚》都是上好之作。”王泉奎演此戏,从上场引子、定场诗、通名及表白的念法,到大段[西皮]唱腔的唱功,皆体现着由穆凤山、金秀山前辈设计、开创的姬僚唱念韵味的独有特色。如在[西皮原板]第一句“弑君不比宰鸡牛”中的“君”和“牛”及第二句“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的“们”字上皆运用了鼻音拖腔的唱法,渲染出浓重的声腔特色。转[二六]后“真少有”三个字,在“真少”二字后做一小停顿,继以滑动的音节唱出“有”字,使整个行腔倍显俏皮、动听。该段中三处上行的颤音唱法则更为警人:如果说前两个分用在前后两处“打鱼的小舟”的“小”字上的颤音,只显示出了比另类唱法更见难度的字简腔奇的特色;而后施展在“冷气吹得难禁受”的“禁”字上的颤音,则听罢令人不禁寒噤,愈加惊赞其以腔传神、声情并茂的超凡功力。
王泉奎的《刺王僚》经其丰富的舞台实践,精炼成为了京剧铜锤花脸的经典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推崇和欢迎。演出全部《伍子胥》时,《刺王僚》为最后一折。即当挑班老生前面唱完了,接由傍角儿的花脸来墩底唱大轴,这无疑对花脸演员的艺术实力构成了严峻考验。王泉奎的演出竟能令有些观众在《鱼肠剑》将完时,等候戏院门口,愿以原价商购退票;大有嗜王艺者专为听“刺僚”而来。王泉奎墩底《刺王僚》的大获成功,尤其增添了他的艺术身价。
翁偶虹先生曾谈及40年代王泉奎与李少春的合作:“架子人物,世海专利;铜锤角色,泉奎专责。最受欢迎的《打金砖》又因泉奎饰演的铫期而大增荣光。”《绑子上殿》一折中,在刘秀唱完大段[二黄三眼]下场后,王之铫期遵传统路数,叫起[长锤],再唱大段[原板],以收“豹尾”之功。此唱难度极高,在末尾长达二十六个字的“垛字句”中,“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昼夜杀砍、马不停蹄”十六个字,泉奎先生唱来竟能一气呵成,最后“我还怕着谁来?”一句的拖腔,上扬下抑,禹浪三叠,尽得锦上添花之彩;翁赞之曰:“锵金戛玉,韵厚声清”并论道:“优美卓异之唱功,在于有力有气。有力无气则太浊,有气无力则太飘。气是先天之赋予,力是后天的磨励。”王泉奎的演唱体现出的深厚功力,于其身后,至今还难再见来者。王泉奎能戏甚多,演来皆有特色。他的《空城计》司马懿、《法门寺》刘瑾都是当行应工,出类拔萃,堪为一时之选。于“铜锤”角色外,他也兼擅架子表演,身段严整、边式,工架美观。他曾为盖叫天配演《恶虎村》濮天雕、为周信芳配演《乌龙院》刘唐、为杨盛春配演《霸王庄》黄隆基、为周啸天配演《定军山》夏侯渊及在周信芳与林树森合作的《战长沙》中饰演魏延,显露出了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王泉奎的表演恪守传统规范,却并非艺术的保守派。如随着不断地演出《大·探·二》,他就留意对剧中一些旧的服装、道具进行翻新改制。像徐彦昭怀抱的铜锤,原来只有个锤形儿,包上块红门旗就成了。泉奎先生观之简陋,便精心设计出了金色锤头、攀龙漆金锤把,在锤下再系上两个黄绸彩珠的铜锤新造型,此铜锤造型一直延用至今。再如徐彦昭戴的侯帽,又称“台顶”,从前两侧的耳子只是两块涂银的片子,粗糙而不显气派,对此王先生曾改过两次:先改成涂金挂穗子,仍觉小气,就又加大两片,再镶以点翠的图案,使之显得精美、大方;进而丰满、提高了定国公的艺术形象。
王泉奎于50年代初进入中国京剧院,是最早加入国家剧院的花脸名家之一。期间他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参与排演了多出新编剧目和经加工、整理的传统剧目,如《五台会兄》《敬德装疯》《智斩鲁斋郎》《十五贯》等,都是他经常演出的剧目。他于50年代曾多次随团出访,到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卢森堡、比利时、法国、英国、挪威、芬兰、瑞典、丹麦、冰岛、苏联等十数国家演出。他与言慧珠、沈金波等合演的《二进宫》等文戏同武剧一样受到外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被称为:北京opear(北京歌剧)。60年代中期,王先生还主演过《三让刀》等现代戏。
泉奎先生晚年曾应邀到中国戏曲学院授课,为学生刘琢瑜、郭永江及孟广禄等传授了《五台会兄》《遇皇后·打龙袍》等剧目,并参加了多场名家教授的示范演出。他与张君秋、马最良、高盛麟、李盛藻、王玉敏先生合演了《龙凤呈祥》、与陈大濩先生合演了《失·空·斩》、与王玉敏先生合演了《打龙袍》、与关肃霜、高盛麟先生合演了《龙凤呈祥》(带《丧巴丘》),还参加了《戏剧报》创刊30 周年的名家荟萃演出,再次出演了《龙凤呈祥》中孙权一角。此外,他还几次到天津小住,与老友、爱徒欢聚一堂,并向花脸新秀邓沐玮等传授了《断密涧》等戏。
纵观王泉奎先生一生,身为一代净行大家,声名赫赫,为京剧花脸表演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地位不可低估。他在继承金派表演艺术的基础上,结合着自身条件和时代要求,从峥嵘朴拙的旧有风尚中衍化而出,开创了洪亮、清脆、玲珑、圆润的崭新演唱风格,从而,使京剧铜锤大净的唱腔韵味得到了有益的进化与规范。深谙净道的翁偶虹先生曾写下警世之言:“十净九裘,世所公认。然歌喉天赋,应以天籁之声克展其长。倘无裘盛戎之韵,无裘盛戎之慧,矻矻摹学,岂止适履而削足?铜锤流派,繁花似锦,有识之士,当按图索骥,百家争鸣。”
注释
[1]翁诗注:三山指前辈名净穆凤山、何桂山、金秀山。郎氏指前辈名净郎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