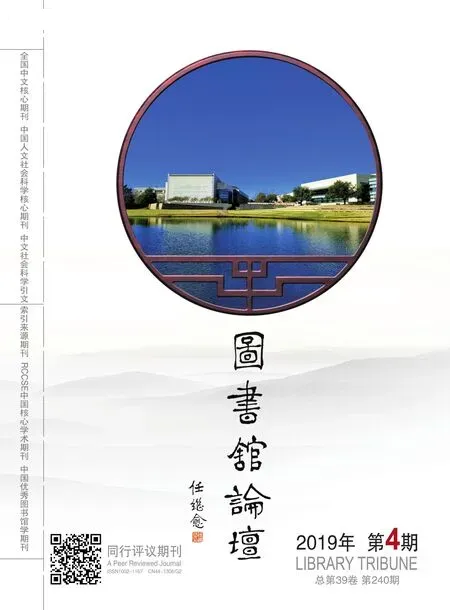《花笺记》在英国的收藏与接受*
徐巧越
木鱼书是明末诞生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俗曲文学,它是在粤语民歌的基础上借鉴各地说唱艺术的精华,形成了以七言体为主的诗赞系说唱体载。随着木鱼书歌唱体式的日趋成熟与民间出版业的蓬勃发展,这种俗曲说唱文学在清代独树一帜,成为岭南独具特色的代表性说唱艺术,其中最知名的作品便是“第八才子书”《花笺记》。
木鱼书的诵唱内容十分丰富,多以民间逸闻、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为主,更有不少借鉴了其它地域的民间文学题材,但惟独文词雅驯的《花笺记》“在中国文学及其他戏剧与小说中,还未能找到雷同故事情节和内容的”[1]21。这部俗曲唱本在过往的数百年里有近30 种版本发行,流传于世界各地,并有多种译本出版。大文豪歌德在读后更创作了《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十四首,藉此赞美中国传统的礼义美德。但是,由于中国学术传统一向不重视戏曲说唱等俗文学作品,又因中国自清末起一直处于战乱不断与局势动荡的阶段,许多古籍遭遇劫难,所以此前少人注意的俗文学作品大多流入海外的藏书机构。《花笺记》亦是如此,该书的版本虽多,但许多早期与珍稀的版本大多散落在国外的各大图书馆。面对这部木鱼书唱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况,梁培炽在《海外所见<花笺记>版本及其国际影响》也曾感慨:“至于更古老的版本,目前在中国国内似乎尚未发现,或不易见到了。”[1]22
最早提及该木鱼书海外藏本情况的是郑振铎,他在1927年发表的《巴黎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里便提到附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光曾序的静净斋藏板《第八才子书花笺》。而柳存仁则是最早提及英藏《花笺记》的学者,他在伦敦大学留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著录了英国博物院(大英图书馆前身)与皇家亚洲学会所收藏的旧刻本中国小说,偶有提及弹词说唱等俗曲唱本,汇集成《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此书就著录了大英博物院的考文堂藏板《静净斋第八才子书花笺》与皇家亚洲学会藏文畲堂藏板《绣像第八才子笺注》,后者随该学会汉籍的移交,在20 世纪60年代被转移至利兹大学的布莱泽顿图书馆(Brotherton Library)特藏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海外相关学者的开拓下,愈来愈多的英藏《花笺记》版本亦为学界所认知,其中不乏孤本与珍本。日本学者笠井直美在1996年发表的《大英图书馆所见通俗文学书抄——木鱼书为中心》便著录了考文堂与福文堂版的《花笺记》。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于1995年曾赴欧洲进行文献调查,期间便发现了牛津大学博德莱恩图书馆收藏的《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并据书中所夹信函推测此本为明末刊本[2]。稍晚,美籍华裔学者梁培炽作《海外所见<花笺记>版本及其国际影响》与《<花笺记>会校会评本》,系统的搜集了海内外罕见的《花笺记》藏本,并通过比对更正了郑振铎与柳存仁此前著录的错误。梁氏在专著中详细介绍了入藏于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挪威、丹麦、越南与香港等地区的十余种《花笺记》版本。梁氏的会校本虽存在一些校勘错误,但此书至今仍是关于《花笺记》最全面的版本著述。而杨宝霖在《<花笺记>研究》中,也对流入欧洲的几种《花笺记》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著录与考述,其中亦提及两种英国藏本,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近年来,随着域外汉籍与俗文学研究的兴起,愈来愈多的国内学者亦将目光投向海外的藏书机构,并在文献调查与编撰目录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花笺记》木鱼书唱本,完善了这部说唱作品的版本著述。笔者于2016年赴英国做文献调查,在英国的各大藏书机构共访得6 种不同版本的《花笺记》,其中不仅有前文提及的明末孤本,更有来自名家收藏的珍本。下文将在著录这些《花笺记》版本的基础上,介绍它们的入藏经历,分析这部岭南唱本在不同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变化,详述这部岭南木鱼书在英国的收藏情况与接受历程。
1 《花笺记》在英国的入藏与流传
《花笺记》是首部被译为英文的中国俗曲说唱作品。由于契合了当时欧洲的民谣热潮,它在19 世纪颇受西方学者的青睐,出现多种西文译本,仅英文便有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as)与包令(Sir John Bowring)的两种译本。鉴于它在欧洲学术界的受欢迎程度,也不难理解为何欧洲较知名的藏书机构皆有收藏这部岭南木鱼书唱本。据调查,目前已知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与利兹大学收藏有6 种不同的版本。参见表1。
据表1可知,上述的四个图书馆都分别入藏了两种不同版本的《花笺记》,由此可以看出这部木鱼书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在这些版本中,尤以牛津大学收藏的《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最值得令人关注。在发现这个版本以前,关于《花笺记》是否诞生于明末一直是学界试图解决的疑题。郑振铎在法国发现朱序本时便说:“原文中提到征战事,每多缺字,如‘奏旨征□’,则却□自,原本似为明末之作,缺字当为关于清人之事者,故入清时,不得不铲去这些违碍字样。”[3]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他也仅是做个推测而已。此后,梁培炽在谈及牛津残本时,因该本残缺不全又“字体潦草,渍漫不易认”[1]25等缘由,在判断此书是否为明刊本时,他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直至最早发现《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的李福清公开了夹在此书中的信件②,其诞生朝代才有了定论。从圣约翰学院的图书馆负责人科尔文(H.M.Colvin)于1953年4月22日写给大英博物馆费兰德雷希博士(Dr.Flenderleith)的信件可知,此书是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大主教在17 世纪初捐赠给圣约翰学院的汉籍。他从劳德主教的卒年断定,其生前捐赠的汉籍一定是明版,其中亦包括了此《花笺记》残本。这不仅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花笺记》刊本,更将整个广府木鱼书的诞生年代推前至明朝。

表1 英国藏《花笺记》之版本与入藏信息
此外,汤姆斯的译本Chinese Courtship 兼具中英两种语言的双语本,梁培炽将其中的中文部分归为一种版本。王燕作的《<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也认为“汤译本为《花笺记》保存下一个独特的中文版本”。汤姆斯翻译所依据的底本到底为何版本,学界至今未有定论。但经比对,汤姆斯译本应更接近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康熙五十二年静凈斋朱光曾序刻本与道光二十年(1840)翰经堂本。比如,在“兄弟谈情”一回,仅汤本与翰经堂本唱词为“我想人事得逢风月景”,别本均作“花月景”。又如,在“碧月收棋”一回,梁生请丫鬟碧月带向杨瑶仙表达爱意的唱词,汤译本与法藏康熙本均作“望娘指引蓝桥路,无敢忘恩负我娘”,别本则为“岂敢忘恩负我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汤姆斯在序言称“这部作品出现在明代”[4];而汤译本还保留“胡”与“番”等对异族及其政权的蔑称字眼,这在康雍乾三朝最为忌讳,故此种《花笺记》明显的带有明版的痕迹。而且,仅汤译本、翰经堂本与牛津大学藏明刊残本将“揖别夫人归馆去,二生携手绕栏杆”两句归入“姚府祝寿”章末尾,其它版本均放在“兄弟谈情”章的开头。另外,汤姆斯译本的许多细节与别本均不同,仅“棋边相会”一回,汤本就有6 处细节与别本相异。通过与《花笺记》的其它版本的比对,推测汤姆斯在翻译《花笺记》正文时,极有可能参考了至少两种以上的版本,而其中一种的版本体系与最早的明版本十分接近。
作为较早进入欧洲视野的中国文学作品,追溯《花笺记》文本的英传经历,能为研究汉籍的西传提供宝贵的案例。从上表可知,它们主要通过捐赠与采购两种方式入藏相应的图书馆,而早期收集这部岭南木鱼唱本的是英国的劳德主教和马礼逊传教士。劳德主教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图书中介处购得此书,他不认识中文,更看不懂书中的内容,但因《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内附有多幅带有东方特色的绣像图画,不仅具有艺术观赏价值,还能丰富其个人收藏。马礼逊在驻华期间肩负着编撰《华英字典》的重任,他大量收集中国的书籍,以全方位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与风俗礼仪,此书便是在此期间购得。以独特的东方书籍扩充个人收藏,通过由通俗易懂的俗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此二人的收藏动机亦反映出当时西人购藏汉籍的目的之一。
《花笺记》最早来到英国的是刊刻于明末的《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它的原收藏者劳德主教曾于1635年、1636年、1639年与1640年四次向牛津大学捐赠书籍[3],虽不知道此书是在哪一年被赠予,但最迟也应在劳德主教逝世(1645年)前入藏该校图书馆。此外,还有其它四种版本可明确是在19 世纪西传至英国。亚非学院的福文堂本原为马礼逊的旧藏,他在1823年回国时将驻华期间收集的汉籍一并带回;大英图书馆藏考文堂本的封底钤有馆藏印章,上面注明了入藏日期③;正如前文提及,入藏利兹大学的两种《花笺记》原为皇家亚洲学会旧藏。而基德教授(Samuel Kidd)在1838年编撰的《皇家亚洲学会中文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ctic Society)里收录了这两种藏书,它们的流传经历亦可由此推知。从17 世纪至20 世纪下半叶,陆续有不同版本的《花笺记》入藏英国的藏书机构,这亦侧面反映这部岭南说唱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不仅范围广,且持久性也较长。
《花笺记》是岭南木鱼说唱的代表作品,国内现存的版本主要以清末刻本和民国机器印本为主。相较之下,英国图书馆收藏的《花笺记》版本,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稀见版本更多,但它们长期都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英藏《花笺记》版本的刊刻年代普遍较早,除牛津藏明刊《绣像花笺记残页》外,其它版本亦保留了大量明刊本的痕迹,这些细节对研究这部作品的时代变迁、清代广东出版业的发展与广府文化的传播都有重要意义。
2 《花笺记》的版本差异及其缘由
自明末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地的民间出版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态。从清代至民国初年,《花笺记》因其生动的故事与朗朗上口的雅驯唱词,在岭南一带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因此这部家喻户晓的粤调说唱作品也被不同的书商翻刻发行。目前已知版本将近30 多种,传布世界多个地区。这部作品在被再版和翻刻的过程中,其版式与文字均出现了变化,这些差异亦见证了这部作品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演变。
朝代的更迭影响了民间书坊的刊行,出版商会随时局的变革对刊物作出调整,故出版于不同时期的同一作品,彼此间亦会有所区别。《花笺记》在不同朝代的刊本,其绣像的内容就有明显的变化:清刊本绣像的内容比较单调,如福文堂与考文堂刊本,其中的绣像仅以刻画主要人物的形象为主;而圣德堂版与文畬堂版《花笺记》插图描绘的多为“棋边相会”“归馆相思”“闺阁达情”等浪漫的爱情片段,图画背景也以富有生活气息的园林闺房等室内景致为主。而明刊本虽只保留了11 幅绣像,但展示的情节与内容比清刊本更为丰富。如图1至图2所示,不仅有描绘发生在朝堂庙室的场景,更有展示征战的图画,在清刊本中尚未发现与此雷同的绣像。据此,《花笺记》的清刊本有意抹去了明版原貌中所有与战争相关的痕迹,并淡化了政治色彩。

图1 牛津大学藏《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之“刘舅诉请”(左)、“梁生议计”(右)绣像

图2 牛津大学藏《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之“玉卿投江”绣像
此外,《花笺记》的版式在由明入清与满清倾覆这两个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它的版本大致可分为无评语的二卷版本与有钟戴苍评语的六卷版本,早期的刊本只有六十个章节④。此书的明刊本与其它清刊本有许多细节差异,尤以“胡”和“番”等康雍乾三朝所忌讳的字眼为最。比如,在“奏凯回朝”章节中,牛津大学藏明末残本的唱词为“胆又壮时心又恳,乱杀胡兵似斩泥。五千万胡兵都杀净,天明山上血成池”,其中的两个“胡”字在早清的刊本中均被剔除;而在民国时期发行的五桂堂机器版《花笺记》,它不仅删去了前两句,“五十万胡兵”也被改成了“五十万人”,参见图3。

图3 《绣像花笺记残页》(左)、考文堂版《花笺记》(中)、五桂堂板《花笺记》(右)之书影
清末民初,随着清廷的没落与分崩离析,原本指代异族政权的文字也不再受忌讳,因此后出的《花笺记》版本便将部分“胡”和“番”等字重新补入。即使未能补全所缺文字,也会依据原意改写。在清刊本中,“梁生被困”的前一章为“奉旨征□”,这因避讳而缺字的章节标题在五桂堂机印本中则被改为“领军平虏”。正如薛汕所言,“正是所缺欠的都是‘征番’一类的事,往往为‘好奇者’所猎奇,于是节外生枝”[5],因此,出版年份较晚的版本在“芸香报主”之后新增补了章节,如在以文堂藏板刊本中,新增的四个章节分别为“瑶仙问觋”“回话勾魂”“衷诉情由”和“衷情告别”;五桂堂版本则作“觅影寻踪”“沙场撮影”“表述因由”与“衷情苦别”;而省城广州翰经堂本更将新增的内容合为一节,以“瑶仙问觋”作为标题,故发行较晚的版本会出现六十四章节本与六十一章节本。而这些新增的文字远不如原文雅驯流畅,内容也以神鬼报应为主,与原作的中心思想迥然不同。补全缺字与新增内容都是书商为了满足读者猎奇心理所想出的对策,以此吸引眼球和增加销量,有些改动虽粗鄙低俗,但《花笺记》的这些变化亦体现出当时的时代境况:封建政权的没落与出版业走向商业化。
至于《花笺记》的作者为何人也,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考知。据说梁培炽在民间走访时,曾打听到相关传闻:撰写《花笺记》的作者因罪死于狱中,他当时只完成了这部木鱼唱本上半卷的创作,翰林院中的耆老在阅读这部未完之作后,深受感动,便按原作情节续写了下半卷。这虽是民间传闻,但并非全无依据。此书前39 回(第二至第五卷)主要以梁亦沧、杨瑶仙和刘玉卿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文字细腻优美,但从第40 回“奉旨征□”起,则笔锋忽转,浓墨重彩地描述梁生奉召出征、沙场平贼;第六卷的情节不仅转折突兀,文采也略逊于前文。钟戴苍在点评此书时,便多次提及此书有后人的添写与续作之笔。他于“花笺大意”的开篇便指出:“真乃因乎其所,不得不因,易乎其所,不得不易。非一味胡抄乱改者所可同日语也。”[6]卷二第二页其在“对花自叹”的总评里也写道:“此篇无甚新雅,声调亦平。与对月、化物等篇俱岂后人所添耶。”[6]卷四第八页直接指出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后人添写。而在“奏旨征□”的总评,钟氏更直言:“花笺记自此以下是续笔矣。余细相其用笔,真不复知有轻重,知有详略,只随笔卸去,有何多味。”[6]卷六第一页而他对这些后人添作与续写之笔并不认同,钟戴苍在“对月自叹”的尾批中感叹:“大殊词句亦俗,颇似续笔,天下后世才子必能同辨。”[6]卷五第四页而对“房中化物”章节的点评亦然:“大是败笔,当亦后人所添,真不是《花笺记》一色笔墨也。”[6]卷五第七页综上推断,《花笺记》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才华横溢的原作者并未完成原作,有后人在其故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添写续作,这些后作虽不如原作者的笔墨富有情感,但却让这部作品得以完篇。
此外,圣德堂版《花笺记》的封面上注明了“芥子园藏板”,而文畬堂版与考文堂版的封面虽修改了藏板信息,但版心的“芥子园”藏版记识却被漏铲。芥子园原是李渔在金陵的宅院,他后来以“芥子园”书坊的名义印刷与售卖书籍。在康熙至同治的两百多年间,芥子园书坊虽几经易手,却一直是出版界的翘楚。《花笺记》乃独具地方特色的粤调俗曲,能为南京著名的书坊芥子园所刻印,这不仅体现出这部木鱼说唱作品的独特魅力,更说明它在清朝的流传范围并不局限于岭南地区。而南京作为当时汇集文坛名流的文化中心,这部广东俗曲既在江南地区被印刷出版,不难猜测,它应曾广泛流传于该地区的文人墨客之间。
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花笺记》可知,这部作品曾随两次朝代更迭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由避讳少数民族政权到补全缺字与新增内容,其版本差异亦反映了民间出版业在改朝换代中的经营之道。细读钟戴苍之评语,亦可得知此作有添作与续笔,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部分版本中残留的“芥子园”藏板标识,说明此作的流传范围在清中叶便已拓展至江南地区,由此亦可一窥其风靡之盛。
3 《花笺记》的英译与接受
木鱼书《花笺记》是最早进入西方视野的中国俗曲作品之一。在《华英字典》的印刷负责人彼得·汤姆斯于1824年将这部作品译为英文后,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转译为各种语言,仅在19世纪,这部木鱼书便有5 种西文语言的6 种不同译本。迄今,在英国的各大中文藏书机构仍可寻得不同版本《花笺记》的踪迹。这部广府木鱼书在海外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汤姆斯于1814年9月2日抵达澳门,协助马礼逊编撰出版《华英字典》。当时广东地区的市面上已出现多个版本的《花笺记》,而马礼逊在字典中的“花”字下也援引了这部木鱼书,所以汤姆斯自然会注意到这部广府说唱作品。这位英国人把这部木鱼书作品视作诗歌,正如他在英译本序言中所言:“以往的翻译是不适于欧洲人形成有关中国诗歌的正确认识的,所以我在此尝试把一部18 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品《花笺记》译成英文,以改变这种现状。”[4]在此之前,黑格尔依据早期赴华西人的汉学研究总结出“中国无史诗”的结论,这个观点亦随着《美学》的出版而在欧洲广为传播。汤姆斯在其英译本的序言中指出,喜爱诗歌的中国人并没有史诗作品,但《花笺记》属于叙事长诗,而这种体例可以让诗人们“尽情地发挥而不是沉湎在平庸的推敲文字之中”[4]。此外,他还认为中国诗歌“缺乏那种使古希腊罗马诗歌作品成为杰出作品的美”,其缘由在于中国诗人在作品中对神灵的描写并未表现出西方诗歌对上帝的那般尊崇,“因为中国人不像我们一样偏爱丰富和崇高理念的矿藏——如《圣经》这样的宗教典籍,但这是其他民族至少部分拥有的”[4]。但对比其他民族的诗歌,汤姆斯认为中国诗歌内含丰富的意象、崇高的思想与大胆的隐喻,创作传统亦具有创新性。
汤姆斯的英译本《花笺记》以散文体的方式进行翻译,这与19 世纪英国主流的维多利亚时期规整韵律体相违背,故它在出版之初并未得到英国主流评论界的认可。《东方先驱》(TheOriental Herald)便批评汤姆斯译文的用词拙劣而缺乏美感,更毫不留情地挑出了19 个带有语病的句子;《评论月刊》(The Monthly Review)不仅认为这部译作的叙述缺乏生动性,更直称这是一部“反韵律的译作”(anti-metrical translation)[7]。即使如此,这个带有瑕疵的译本却让这部广府说唱在欧洲文艺圈名声鹊起,俄文译本(1826)、德文译本(1836)、荷兰文译本(1866)与丹麦文译本(1871)随之问世,包令爵士也在其基础上重译了这部作品。
汤姆斯虽是《花笺记》的首位西文翻译者,但他的职业只是一名印刷工匠,这与包令的身份有着云泥之别:后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是当时英国颇具名气的经济学家与语言奇才,更一度出任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长,先后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和香港总督等要职。不同于汤姆斯将《花笺记》看作长篇叙事诗,包令则把这部作品定义为“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花笺记》兼具韵律性与叙事性,钟戴苍曾评论该书为“歌本小说”。二人对这部木鱼书的文体认识虽各有公理,但包令对文体的重新界定,为其重译做了必要的铺垫。
包译本的序言肯定了汤姆斯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本逐行翻译的流行小说对学习中文的学生能起到莫大的帮助。”[8].vi对比汤译本,包译本的文字更为自然典雅,这也是译者所追求的“自然而流畅”[8].vi。汤姆斯在翻译时,刻板地遵循译文与中文原作逐字逐行对应,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文意断裂与文化隔膜等不可译现象,“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表面上是诗,实际上却并不讲究音律之美。勉强接洽起的文脉,自然也难以贯通”[9]。另外,包译本中附带了大量丰富的注释是其译作的特色之一。拥有深厚学养的包令在翻译此作时添加了大量的注释,部分章节注释的篇幅甚至超过正文,内容丰富,既是这位学者低调“炫技”的展示,更从侧面反映了西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正如包令对“镜花水月”所作的注释:
“水月”或月相渐亏,在中国通常被用作对光明的期待。在欧洲的修辞中,“相思病”往往与“黯淡的月亮”联系在一起,因为青年与少女总会习惯(在这样的场景下)互诉衷肠;而在中国,“皎洁的月光”则与热恋的激情息息相关……[8]5
他通过这个批注比较了“月亮”这一意象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差异。除了评释中国的专有名词与传统典故,他的注释还涵盖了政治制度、社会境况与民俗礼仪等方面,在包令看来,“任何能帮助深入了解中国本土民众日常生活的(信息)都应受到欢迎”[8].viii。对《花笺记》的全面阐释,不仅能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深层含义,并尽可能地再现原作之神韵。
除了借鉴汤姆斯的英译本,包令在重译《花笺记》时还参考了施列格的荷兰文译本,其中部分的讹误就是从荷兰单词转译为英文时出现的错译现象[9]。可是他在出版这部译介著作时,并未对施列格作出片言只字的致谢,这也成了他晚年受人诟病的污点。但无可厚非的是,包令的确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字典雅流畅而更具可读性的《花笺记》西文译本,扩展了这部岭南俗曲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范围,其注释更是19 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中国文化的西渐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首部被直译为英文的广府俗曲作品,《花笺记》 英译本的问世比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翻译、汤姆斯·帕西(Thomas Percy)编辑的《好逑传》英译本晚了63年,较德庇时翻译的《老生儿》刊行则晚了7年。前者是最早被翻译为西文的中国长篇小说,而后者则是首部被直接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戏曲作品。这些较早被介绍至西方的中国俗文学作品都宣扬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与礼义精神,这也是它们在西方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其内含的道德教化既打动了西方读者,更于无形中契合了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精神。《花笺记》亦是如此,歌德正是被其内涵之“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传统思想所打动,包令也认为这部木鱼书以华丽诗意而富有想象力的语言展示了中国文雅礼节与渊博文化的精髓。《花笺记》以梁生与瑶仙的“才子佳人”爱情传奇作为载体,宣扬了中国的传统礼仪美德,这既是此木鱼说唱作品长久不衰的原因,更是它被西方读者所认可的重要缘由。
4 结语
《花笺记》作为广府俗曲的艺术精华,是中华民间文化的瑰宝。这部木鱼唱本诞生于明代,在清朝走向鼎盛,不仅深得岭南百姓的喜爱,地处非粤方言区的金陵芥子园亦曾印行此书,其诸多版本见证了我国时代的更迭及印刷业的发展轨迹。
中国自古便有“戏曲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传统,民间的说唱艺术更不为文人所待见,因此《花笺记》虽有“第八才子书”之美誉,但国内可见之版本多为晚出的“改良”刊本与铅印本。值得庆幸的是,这部作品凭着其独特的魅力走向海外,是早期走向国际文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欧洲各大藏书机构都可寻得其踪迹。而这些散落在海外的古籍不仅版本丰富,其中的珍稀版本更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研究广府俗曲与地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界关注。笔者将英国所藏之《花笺记》进行梳理,通过比对版本之差异,探讨此作的历史演进及历程,由此一窥明清时期岭南民间艺术的发展生态。
从默默无闻的印刷工匠汤姆斯,到身份显赫的包令爵士;由逐字逐句的诗歌韵律式翻译,到典雅流畅散文叙事式再译;而对原作的注解,也从简单的释义演变成丰富详实的文化解读。这部木鱼书唱本在19 世纪的英国也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接受历程:它因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流传与文学盛名,引起了早期驻华英人的注意;而《花笺记》内涵的真挚情感与崇高礼德为欧洲文坛所推崇,由此成为在海外流传度最广的中国俗文学作品之一。
注释
①梁培炽在《<花笺记>会校会评本》著录牛津残页本时,谓此书“版面分四栏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现存全版之插图共十帧”。此处乃梁文讹误,据笔者目验,每行有二十八字,共有绣像十一幅。
②李福清只公开了两封信函,但笔者在访书时发现共有三封信件夹在书中。除文中提及的这封信外,另外两封都以交流此书的价值与修复为主题。
③有关大英图书馆的中国戏曲俗曲的具体入藏经历与版本信息可参见徐巧越《大英图书馆藏中国戏曲俗曲文献初探》(《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五辑,第439-465 页)。
④文畬堂、考文堂、圣德堂、福文堂与法藏朱光曾序本的目录皆漏刻第二卷中“兄弟谈情”一回,故目录只有59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