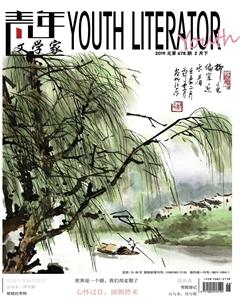浅析《白鹿原》中的话语冲突
摘 要:《白鹿原》文本中包含了两种叙事话语,民间话语和革命话语。两种话语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呈现,同时在文本中还有诸多交叉与冲突。陈忠实通过对二者的冲突、对比,展现民间话语对革命话语进行的某些松动。这与陈忠实的民间立场密切相关,两种话语的摩擦,表现出陈忠实书写的复杂性。
关键词:白鹿原;民间话语;革命话语;冲突
作者简介:袁玲(1992-),女,重庆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读,中国语言文学2016级研究生,现研究方向:当代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3
《白鹿原》陈忠实主要采用了两种话语形式,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构造了白鹿原这个复杂的社会。二者之间呈现着不同的叙事线索,在文本中冲突,体现了陈忠实的民间立场与革命立场的纠缠。两种话语的纠缠让文本充满杂语性。
一、民间话语的运用
陈忠实在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剥离”,试图将自己从前三十年的影响中剥离出来。“怎样理解集体化30年的中国乡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乡村……是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发生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对《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1]面对思想解放的潮流,陈忠实艰难地将左翼的思想集体化的记忆进行剥离,试图逃离左翼文学的影响,打开新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民间。《白鹿原》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左翼文学的写法书写农村,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反映白鹿原地区几十年的风云变化下的普通农民。陈忠实颇崇拜柳青,柳青《创业史》中的乡村描写以及对农村生活的判断和看法,一直让陈忠实对集体主义带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但是随着集体化的退场,陈忠实感到困惑。《白鹿原》正他革命立场向民间立场的艰难转向的记录。陈忠实在小说第一页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试图通过对白鹿原的书写,通过艺术真实来“记录”下白鹿原的历史。既然是秘史,自然与官方正史有着诸多差异,填补正史无法弥补的缝隙,这个缝隙就是民间。
文本对白鹿原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陈思和所说的民间藏污纳垢的特性。[2]小说开篇便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3]文中对这七个女人进行了叙述。所娶的女人或死于难产,或生各种怪病而死,或精神恍惚疯癫溺死,或撞鬼气绝而死,在陈忠实的描写中虽然有感叹荒诞的意味,但却很难看出陈忠实站在启蒙者或者知识分子角度对白嘉轩这种传宗接代的行为进行讽刺或者批判。这段描写中还夹杂着鬼神论、宿命论以及女人是生育工具等多种叙述,如白嘉轩的母亲认为女人就是窗户纸,破了再糊一层就行了。白嘉轩不断丧妻的噩梦终结于白嘉轩将祖坟迁到了“白鹿”出现地,白家香火终于得以延续。在启蒙视角看来,以上是需要批判的,但书中并未进行嘲讽,只是将其陈述出来,展示民间社会的通行法则以及价值取向,“延续香火”这只是白鹿原民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说采用了大量的民间叙述结构。对白孝文命运的书写正是民间叙事的产物:白孝文在鹿子霖的設计下与田小娥厮混、吸大烟、败光家产、气死原配,被逐出家门,正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败家子形象。而后白孝文到了保安团受到赏识,风风光光地重回白鹿原,得到了白嘉轩的原谅,重新拜祭祖先,这也是民间故事中浪子回头的桥段,白孝文这条线索基本上按照民间故事逻辑发展。再比如,鹿子霖作恶多端,在被民兵押到台下陪斗,在目睹鹿黑娃、岳维山、田福贤被斗的场景后疯癫,也体现了民间社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价值观。当然,这套价值观只在民间叙事中起作用,而在革命叙事中则毫无作用。
从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来看,书中并未简单将其归为封建迷信。民间信仰在启蒙者和革命者眼中是需要批判或打倒的,而在《白鹿原》却并非如此。象征白鹿原精魂的白鹿是神圣的,“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了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4]被神化的白鹿寄托着原上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是具象的:麦苗长势良好,害虫销声匿迹,病痛痊愈。白鹿不仅作为象征意义在远古故事中出现,而且出现在白家人的生活中:白鹿的出现终结了白嘉轩丧妻的诅咒,白嘉轩梦中的白鹿是女儿白灵牺牲的后的化身。白鹿不是遥不可及的幻象,而是影响白家荣辱兴衰的“实体”。书中对鬼怪的书写亦是如此。田小娥死后化为厉鬼,让整个白鹿原沾染瘟疫,甚至附身于鹿三呵斥白嘉轩。瘟疫的控制不是到了寻找瘟疫发生的病理原因,而是通过修建镇妖塔将田小娥尸骨压于之下,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却在白鹿原取得成功,因为这种做法符合民间叙述的逻辑。
《白鹿原》中蕴含着明显的民间立场,陈忠实通过对民间话语的运用,对民间习俗的书写以及对民间叙事结构的借用,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虽然陈忠实经受着内心的剥离,但是曾经的革命文艺教育,让陈忠实不自觉采用革命叙事。
二、革命话语的建构与松动
如果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一代人是民间话语的代表,那么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就是革命话语的承担者。如果说民间话语代表了稳定的民间社会,而革命话语就代表着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对百灵等人的叙述中可以觅见左翼文学的蛛丝马迹,如革命加恋爱模式、英雄人物的塑造。
首先,革命恋爱模式的运用。白灵、鹿兆鹏出生于传统农耕家庭,接受了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在省城接触到革命而后参加革命,但是家庭并不支持,所以他们反叛家庭,在革命中既坚定了信仰又收获了爱情,这是左翼文学常用的方法,将革命与爱情紧密相连构成叙事的动因与线索。书中通过鹿兆海、鹿兆鹏、白灵三者信仰的变化与爱情纠葛,展现出人物的成长与形势的变化。
其次,通过鹿兆鹏对农交会的领导,展现革命的正当性与曲折性。陈忠实生活的白鹿原地区,曾经发生过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中共成立五六年后就有了第一个党支部,革命者的塑造是有原型。书中写对地主的斗争是建立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他们大都是触犯过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的恶劣地主,如三官庙的辱人妻女的老和尚,抢人妻女的碗客,以及贪污征粮的以田福贤为首的九个乡约。但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样的斗争只能触动无根基无背景的外乡人,在制裁白鹿原总乡约的田福贤时却力量有限。地主重新掌握权力后,又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杀害了闹农协的农民。国民党的统治,无法撼动有根基的劣绅,从而展示了中共领导革命的正当性。这一段描写体现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既要组织农民的反抗,又要引导农民进行合理的斗争,还要防止地主的疯狂报复。
再次,通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塑造。白灵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后变“国”为“共”,逐步由一个热血青年转变为一名共产党员。鹿兆鹏则是一名思想成熟的英雄人物,领导农协,惩处叛徒,解放后继续参加斗争。鹿兆海更是一个悲情人物,爱情与信仰不能两全。三者形象与“十七年”时期塑造的无私奉献、勇于斗争英雄人物有某种呼应。陈忠实认为:“我有一种骄傲,一种激情,我要把我生活着的白鹿原上的革命者推到读者的面前。他们是先驱。他们对信仰坚贞不渝,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是这道古原的骄傲。还有,他们几乎无人知晓,遗忘得太快也太久了。”[5]但是对这部分人物陈忠实有着自己的理解,“不写他们的缺点,不仅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6]与传统英雄形象塑造不同之处,就在于陈忠实笔下的英雄人物正面且生活化。
最后,通过鹿兆鹏、白灵之口说出最重要的革命话语—阶级斗争。鹿兆海与白灵就农协事件产生了分歧,鹿兆海认为“鹿黑娃贺老大白兴儿尽是一帮死猫赖狗,凭这些人能完成革命?他们懂得革命的一分意思吗?[7]”鹿兆海认为共产党只是运用了一些乡村的边缘人,根本无法完成革命,但是白灵却说“你没听到贺老大怎么死的?你听过见过把人从高空蹲下来的蹲刑吗?共产党就要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8]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两人感情上的依恋,进而为白灵与鹿兆鹏的结合埋下伏笔。这段对话展现了二者分歧在阶级立场上的分歧,鹿兆海以地主视角看待农民革命,而白灵则是农民立场看待革命。通过二者的分裂展现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但是书中的革命叙述却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叙述。书中的革命叙事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某种松动。陈忠实受过延安文艺的影响,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又一直试图剥离意识形态影响的本本主义。他当时也关注国内外的各种思潮。“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主张,一种大胆得生活理念和道德判断,都会无一例外地与我原有的那些‘本本发生冲撞,然后便开始审视和辨识,做出自以为可信赖的选择。”[9]这正是他构思《白鹿原》的时候,不光他自己,白鹿原也面临剥离,白鹿原作为千年历史悠久古原,革命已经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发生。在革命叙事中虽然有我们熟悉的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但对英雄的书写却是不同的:书中英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不光有其政治话语的诉求,还有个人情感的表现。英雄的伟大不仅在于战斗中光荣牺牲,也可能死于同志的出卖。这也反映出陈忠实力图摆脱以前的革命叙事,对革命反思的深刻性,表现出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好人有好报这样的结局更多只能在白鹿村发生,而一旦进入现代社会以及革命中,这一套民间的话语便不可行,所以黑娃起义的革命果实被窃取,而鹿子霖却能恶有恶报。
三、二者的冲突与交锋
民间话语与革命话语虽然是两条线索展开,但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有着诸多交锋的。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同时存在造成了《白鹿原》文本的杂语性。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套话语间的摩擦。
在白灵、白嘉轩,鹿兆鹏与鹿子霖的代际差异中,展现出二者的摩擦。白灵、鹿兆鹏代表着新一代的革命话语,而白嘉轩、鹿子霖代表着乡土社会的民间话语,通过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而表现出两种话语的矛盾。白灵虽然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但是自作主张到省城念书,而后参加革命,因写了封信解除了与邻村婚姻与家里彻底闹翻。鹿兆鹏也是因为收到了新式教育,不满家里为其安排的婚姻,离开了白鹿原,成为原生家庭的背叛者。当县长被赶下台,国民大革命前夕,革命已经冲击了除了白鹿村的整个白鹿原地区时,白灵投身革命,白嘉轩试图阻止白灵。“他不偷不抢,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的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10]白嘉轩作为民间话语塑造的代表,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依旧奉行独特、自在的价值取向。白灵与白嘉轩的冲突,正是两种话语与价值观龃龉的表现,当民间社会无法容纳革命话语,他们只能选择离开白鹿原,寻求革命话语发生的场所。在老一辈遵守民间的乡规民约,新一代的人无法在这样的话语中确立价值。正是两套话语的不同,白灵们出走。年轻的一辈或牺牲或离开,而白嘉轩他们才是白鹿原真正的、永远的主人,或許只有民间话语能够真正地扎根于乡土社会。
二者冲突表现在革命对民间社会的冲击。鹿黑娃为首的三十六兄弟在白鹿原上掀起一番“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对白鹿原的乡村秩序造成了冲击。黑娃在“瞅着再在庭院正中的‘仁义白鹿村的石碑说:‘把这砸碎”[11]通过将白鹿村具有标志性的祠堂改为办公室,砸碎以前的乡约,革命试图进入这个民间社会。但是这样的介入还不具有彻底性,民间社会的传统还是被重拾。革命撤出民间后,白鹿原恢复了往常,砸碎的乡约碑文又被重新巡回、修补。《乡约》是贯穿整个白鹿原地区人民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间能靠自有的治理恢复秩序,但是革命仍在缓慢地渗入。白鹿原在缓慢地发生剥离。从第一次闹农协开始,就已经开始冲击着整个民间的文化心里结构。即使“这座沉积了两千多年封建理念的白鹿原,还有普及儒家思想的《乡约》也有近千根深蒂固的影响”。[12]
两种话语在书中的交替,展现文本的复杂性。书中对民间话语的运用与对传统革命话语进行了松动,展示了二者的摩擦,也体现了陈忠实立场的摇摆。陈忠实深受延安文艺以及柳青的影响,同时又处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他在剥离的同时,又恋恋不舍。《白鹿原》或许正是他试图寻求两种话语的平衡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58页.
[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3页.
[4]同上,28页.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84页.
[6]同上.
[7]陈忠实.《白鹿原》.1993年6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84页.
[8]同上,285页.
[9]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61页.
[10]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208页.
[11]同上,3页.
[12]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