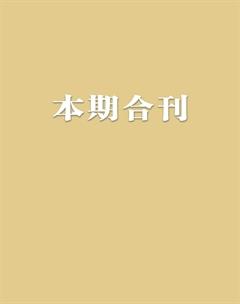建筑师下乡,盖房之前先谈理解



何崴 建筑师下乡,要让乡村重新找到自信
在上坪古村复兴计划中,何崴将自己的视线聚焦于猪圈、牛棚、杂物间、闲置粮仓这些看似简陋,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空间。对他而言,这些建筑虽然面积不大,但都位于村落空间的节点上,可以成为村落未来生活的支点。而建筑师在乡村的工作,本就不只是要改造空间本身,更是要重塑产业,重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最终,才能真的复活乡村。
上坪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溪源乡,历史悠久,大部分居民为“杨”姓,相传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人。村庄保有浓厚的耕读和廉孝文化,据传朱熹曾来此讲学,并留下墨宝。虽然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资源,但上坪村的情况与中国大部分传统村落一样,空有历史资源,却没有转化为服务于当地人的资本。
自2017年起,何崴带领团队参与了“上坪古村复兴计划”,并将空间改造的范围确定在水口、杨家学堂和大夫第等三个区域的11栋建筑物上。这些建筑虽然面积不大,但都位于村落空间的节点上,可以成为村落未来生活的支点。此外,它们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和代表性,可以为整个村落的未来发展加分。何崴直言:“建筑项目若想要切实有效地起到激活乡村的作用,其重点不在于外观奢华,也不一定一直好看,但它们必须是活态的,能持续自我造血,也能够为乡村输血。”
因此,在乡村建设的工作中,他选择重新回归前工业性“部落人”属性,用全局性的思维方式来工作,具体到上坪村项目,即立足改善空间环境的基础上,重塑产业,重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譬如在改造方式的选择中,三文建筑没有采用常见的“修旧如旧”的方式,也没有“赶时髦”地打造民宿,而是挑选了村中若干闲置的小型农业设施用房,如猪圈、牛棚、杂物间、闲置粮仓等进行改造设计。这些看似简陋,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空间,尽皆被植入新的业态,杂物棚被改造为供人歇脚的场所,废弃猪圈则成了慵懒酒吧,古村落原本匮乏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在这些空间中——补足。此外,在空间改造的基础上,三文建筑还将为村庄提供后续经营的指导,设计乡村文创产品以及相关的宣传推广,几乎承包了从产业规划到空间营造,再到旅游产品和宣传推广的全过程。
显然,何崴眼中的乡建不是一个单纯的建筑设计和建设的问题,它不同于基于大工业生产和分工的城市建设,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因此在从事乡建工作的过程中,也不能将规划、建筑设计、文化保护和发展、经营等问题孤立起来,分块处理。
而从建筑师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建筑师下乡一方面是为乡村带去信息和审美,一方面是做榜样,让乡村重新找到自信和自我审美。因此,建筑师进行乡建时,最重要的态度是“谦和”,谦和不是谦卑,谦和是谦虚和平和,是以一种朋友的心态,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去观察乡村,理解乡村,讨论乡村。
海峡旅游×何崴
你如何理解建筑师在鄉村复兴中所担任的角色?
首先,建筑师是建筑师,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其次建筑师也应该了解产业和规划,要在做建筑设计之前预想建筑完成后的身份和作用,建筑为谁而做,为何而做,怎么用,因此建筑师也要是产业的策划者,经营的参谋者;此外,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筑与地区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建筑师有时候还是文化保护者、挖掘者,要努力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地区文化;最后,建筑师还应该是传播者,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为乡村的发展发声,宣传乡村,为乡村带来资源和关注。当然,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建筑师还会扮演很多角色,这也就是建筑师这个职业的特点,综合、复杂,需要协调多方利益,从中找到一条通向彼岸的道路。
在城市与乡村进行建筑设计项目,有什么不同?
乡村的土地所有者、建造者和使用者是合一的。这更有利于建筑师、建筑设计回归它的本源。我想这也许就是近年来很多建筑师回到乡村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乡村从事建筑设计很多时候比在城市里面复杂、困难,成本和资金是一方面,沟通和不确定性是另一方面,要想做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认为建筑师下乡的趋势是否还会持续?
越来越多的乡村愿意和建筑师合作,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也不认为是一种趋势和必然。现在的盛景也许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和扶持,如果这些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没有了,乡村是否还会和建筑师合作,需要未来告诉我们。当然,我也不觉得乡村中一定需要职业的城市建筑师,毕竟乡村很多,懂乡村的建筑师不多;乡村相对并不富裕,而建筑师相对较贵。做好自己,守住初心才是建筑师该做的本分。
白毛 乡村建筑师是一种多元的角色
身为一名建筑师,近年来自毛带着一群年轻人在黔东南实践“新上山下乡造村行动”。这样的驻村生活,不单纯是个人价值的选择,更是出于乡村建筑师的“职业需要”。在他看来,理解一个地域的建筑形态,必然要先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乡村建筑师的工作,绝不只是造房子这么简单。
在無名营造社的自我介绍里,白毛加了一句话:与在地默默无闻的乡村营造人士共同劳作,尊重在地的营造智慧和营造习惯。这些“乡村营造人士”,是指村里的村民和工匠师傅,而他所说的“共同劳作”,包括但不限于与他们同吃同住,抽旱烟、喝劣酒,互掏心窝子。
自2017年夏天起,白毛带着無名营造社在贵州黎平县茅贡镇开始驻村工作,此后,他们先后参与了黎平县黄岗村和雷山县白岩村的总体规划与建筑组群设计,以及遵义市绥阳县光明村土窑文化再生项目。在他看来,建筑形态体现了在地的生活智慧,是当地人对风土环境的适应、民俗审美意识的反映,所以要理解一个地域的建筑形态,必然要先理解当地人的生活。
事实上,对地域建筑形态的研究,会在极大程度上帮助整个村落的媒介系统梳理。乡村是有性格的,不同的地域孕生出不同的村落,跟人一样,村落也有各自的属性特征。而建筑是适应时代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演变出不同的建筑形态,所以它的变化有一定逻辑,它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在驻村工作中,白毛更倾向于先去挖掘在地民俗建筑的营造智慧,厘清当地的建造智慧与习惯,由此,才能更好地帮助乡土建筑应对当下的问题。而驻村建筑师的工作,也绝不仅仅是画图设计、监督施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乡土建筑与现代时空之间嫁接桥梁,让近几十年来因各种因素而断层的乡土文化,能够适应当代,从而也才有了在未来延续的可能。
“我觉得建筑师在乡村,不能单纯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单纯将驻村工作看作是自己的职业抱负,还是得回过头来,认真思考这个建筑对当地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个建筑完成之后,它能活多久?”白毛坦言,当下有很多乡村建筑,在盖起来的那一刻,它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期待自己能承担一个更多元的角色,除了给老百姓盖房子之外,也能在力所能及的不同层面,帮助村落做更多事情,让建筑能够在这里真正活起来。”
而無名营造社近年来的驻村工作,对白毛而言,也像是一场“以自身为试验点”的乡建试验,用以探寻在如今的社会背景底下,中国年轻人是否能在乡村生存下来,在乡村里面生活、工作。当然,这场试验才刚刚开始,远还未抵达终点。“也许能为想来乡村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吧?”白毛笑道,“我相信,未来年轻人不仅会跟乡村发生很多工作上的联系,甚至会有很多人回流到乡村,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你认为建筑项目应当具备哪些要素,才能切实有效地起到激活乡村的作用?
我认为最直接的要素,就是如何把在地价值跟地域性格结合到新的建筑形态当中来。在乡村,建筑师的最终目的不是造一个很好看的建筑,而是要使这个建筑承载一定的意义,为乡村带来实际的使用价值,激活乡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所以在现阶段,我希望能以建筑为媒介梳理村落自身脉络,以建筑为窗口输送乡村在地价值。这其中有很多要素,包括在地建筑营造脉络、建筑空间所承载的在地生活系统、建筑所承载人文层面的民俗文化等等。特别是通过驻村工作,我发现建筑实际上能够缓解很多乡村现阶段的发展矛盾。现在很多乡村是以旅游为发展方向,那就必然会有很多游客进入到乡村,这些外来者和村民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多矛盾,所以我们新的建筑形态如何去连接在地与外来的两个群体,如何使他们之间能够发生一些良性的对话,甚至是通过这个平台产生一些价值的交换,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此外,乡村的激活需要很多外来的资源介入,那么这个空间形态如何去适应这些外来的新业态?这也是乡村建筑空间需要思考的问题。
你如何理解建筑师在乡村复兴中所担任的角色?
这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我对于自己在乡村工作的角色定位很模糊,对外我是一名建筑师,然而在工作中,建筑师的角色却是非常无力的,往往需要扮演建筑师之外的诸多角色。我现在努力在探索思考自己的立场和定位,或许乡村建筑师本就是一个特别多元复杂的职业,和我们常规理解的建筑师不一样,只是目前还没有人去定位乡村建筑师的职业属性。
近年来,关注乡村的建筑师日益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乡村愿意与建筑师合作。你认为这样的趋势是否还会持续?
会持续,中国偌大的乡村,实际关注乡村的群体还是非常少,真正在乡村工作的人士更少,真正为乡民工作的人士更是少。越来越多人士,尤其是都市创意青年群体率先进行乡村回流,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一種趋势和现象。
“乡村旅游刚刚起步,民宿却已抢跑出几个身位的距离。时至今日,当我们再谈乡村民宿时,关注的不再只是设计和景致,而是民宿背后所透露的某种精神需求。当然,曾经抢占先机的民宿主们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藏身秘境的民宿集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