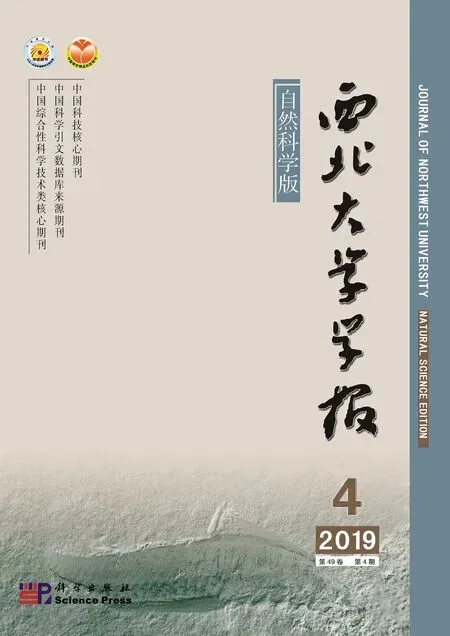城市绿地健康效益的群体差异及绿化投入影响研究
张丹婷,陈崇贤,洪 波,李树华,3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3.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解决居民健康问题已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开放性公共绿色资源,对提升居民健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城市绿地可以增加空气负离子浓度[1],改善空气质量,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2];另一方面,绿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可以有效缓解负向情绪[3],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状况[4-5],且多组数据显示绿地可以改善慢性疾病患病率[6-8],对提升老年人寿命[9],减少死亡率[10-11]都有着积极影响。
虽然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积极影响已被证实。但是,不同社会收入地位群体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机会有所差别[12],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差距也在逐渐扩大[13]。在此背景下,绿地带来的健康效益作为居民可以无条件享受的公共社会福利,是否也受到社会收入地位影响?这一问题对于居民健康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群体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绿化投入作为城市绿地建设的上层指标,对城市绿地水平及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14]。探究绿化投入能否通过绿地真正作用于居民健康并取得良好效果,以及上层绿化投入的增加能否弥补社会经济差距带来的健康差异,对未来城市绿地规划的目标设定以及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运用全国性健康与城市绿地数据,构建绿地与其居民健康效益的回归模型,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探究群体之间的健康效益差异。计算地区绿化投入力度,分析绿化投入对于居民健康的作用,并通过检验不同投入水平下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差异,判断绿化投入力度对于绿地健康效益群体差异性的影响。
1 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1.1.1 城市绿地健康效益 本文以城市居民健康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城市绿地水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表征城市绿地对居民的健康影响情况。居民健康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15]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受访人群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居民样本规模达17 000人左右,该数据库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中国居民的经济[16-17]、社会[18-19]及健康[20-21]研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居民健康水平通过CFPS中健康自评问题“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答案划分,该题项共设置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康、非常不健康5个量度。
城市绿地水平通过城区人均公园面积体现,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该年鉴共收录从2002年至今每年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市自治区,共684个城市的建设数据。
1.1.2 群体差异数据 居民健康水平与个体特征及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12],因此本文引入居民个体特征变量,包含居民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态、个人收入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变量,包含运动频率、抽烟、喝酒,共8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一同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中,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表征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变量,与自评社会地位一起构成群体社会性分级指标。以上群体差异指标均来源于CFPS数据库受访者个人资料。
1.1.3 绿化投入指标 城市绿化投入通过园林绿化投资额占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百分比体现,代表不同的城市绿化投入力度。两种投资额数据均来源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1.2 数据处理
1.2.1 变量数据 居民健康水平题项的原始赋值中,1表示“非常健康”,5表示“非常不健康”,为了便于分析表达,本文将选赋值与水平项倒置,使健康水平由1到5依次递增,即1表示“非常不健康”,5表示“非常健康”。
1.2.2 CFPS数据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绿地的健康效益,因此仅选取城市居民数据;在回归模型的构建中,除了绿化水平之外还纳入抽烟、喝酒等影响健康的生活习惯进行分析,因此仅选取成人数据库,剔除儿童数据。
删除不符合要求及有数据缺失的个案后,根据省份代码,在SPSS22.0中将《城市建设年鉴》中的城市绿化水平指标与从CFPS中提取的其他指标进行合并。最终匹配得到涵盖4个直辖市,21个省份,共600个城区的13 922个城市居民样本。样本主要变量统计性结果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分布特征表Tab.1 Main variab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自我评价“比较健康”的居民占全体样本的39.35%,比例最高;认为自身“不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居民人数较少。居民整体健康的全样本均值为2.956 8,介于“一般”与“比较健康”之间。整体而言,居民健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极端值较少。
2 研究方法
2.1 有序Probit回归
本文选用有序Probit回归建立城市绿化与健康的基础模型。由于居民健康自评选项为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康、非常不健康5类,赋值代表相应类别,不能简单视为连续性数字,在统计学中,该变量属于有序多分类变量。如直接带入以最小二乘法为运算基础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不契合,有损结论的正确性。借鉴Knight[22]和陈永伟[23]等的处理方法,运用适用于有序多分类变量且变量各取值分布不均匀的有序Probit回归模型。
2.2 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
本文群体健康差异的比较均使用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即非参数秩和检验。该方法用于非连续性变量分布情况的比较,检验两个独立样本是否取自同一群体,适用于比较对象为有序分类变量的样本。群体差异部分,通过居民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的平均值将所有城市居民分为高收入、低收入、高社会地位、低社会地位四类进行比较。社会投入部分,通过全国城市绿化投入力度平均值将群体分为高投入、低投入两部分。在此基础上,结合高、低收入组,进一步比较不同收入群体下的绿地投入力度差异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群体差异与绿地健康效益分析
3.1.1 基于全样本的绿地健康效益评估 将居民健康状况设为因变量,城市绿化水平设为自变量,居民个体特征及生活习惯设置为控制变量,通过有序Probit回归建立回归模型,评估基于全样本的绿化健康效益。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全样本模型栏。模型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变量容差大于0.1,符合多重共线性检验标准。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公园面积与居民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OR值为1.008 6,即人均公园面积每提升1个单位,居民健康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概率变为原来的1.008 6倍,证明在全样本层面,城市绿化确实能够带给居民正向健康效益。
在控制变量部分,年龄与居民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年龄越高,健康水平越低;女性的整体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在个人习惯方面,运动频率与健康呈显著正相关;一月中喝酒不超过3次的居民健康状态更好。关于个体特征的回归结果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2],证明对于绿地水平与城市居民健康的回归研究,所选数据库与受访者具有可信度。
在收入水平这一变量上,模型以最高收入水平为参照组,其余收入水平回归系数均小于0,OR值均小于1,表示收入水平越低,居民整体健康状况越差。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类收入水平都呈现出显著性,即在全样本条件下,模型本身已经呈现出了分层现象,有进一步探讨群体差异性的价值。
3.1.2 收入及社会地位分层效应分析 一方面,全样本回归模型已显现出收入水平分层现象;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收入差距确实可能间接造成居民可接触到的绿地在质量、数量、面积等方面产生差异,从而导致不同收入群体对于绿地资源的利用情况与对于环境的敏感度明显不同。因此,本文将居民收入水平,结合居民社会地位作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区分群体,分析城市绿化带来的健康效益群体间的差异性。
根据全样本收入水平平均值2.39及社会地位的平均值2.72将所有居民分为高收入、低收入,高社会地位、地社会地位4类,分别进行绿化水平与居民健康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城市绿化水平对健康影响的群体差异回归分析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group differences in urban greening level impact on health
续表2

变量 全样本低收入高收入低社会地位高社会地位 个人收入水平1-0.407 5∗∗∗(0.665 3)-0.072 4∗∗∗(0.930 1)--0.049 2(0.952 0)-0.372 0∗∗∗(0.689 4) 2-0.327 0∗∗∗(0.721 1)a--0.014 1(0.986 0)-0.271 8∗∗∗(0.762 0) 3-0.137 6∗∗(0.871 4)--0.124 3∗∗(0.883 2)0.068 9(1.071 3)-0.127 0∗∗(0.880 7) 4-0.062 3(0.939 6)--0.053 6(0.947 8)0.253 5(1.288 5)-0.081 7(0.921 6) 50a0a0a0a0a 运动频率 0.017 0∗∗∗(1.017 2)0.019 7∗∗∗(1.019 9)0.013 7∗∗∗(1.013 8)0.023 1∗∗∗(1.023 4)0.012 6∗∗∗(1.012 7) 抽烟情况否-0.028 3(0.972 1)-0.010 9(0.989 2)-0.050 4(0.950 8)0.015 9(1.016 0)-0.055 9∗(0.945 6) 是aaaaa 喝酒情况否-0.136 0∗∗∗(0.872 9)-0.181 5∗∗∗(0.834 0)-0.097 8∗∗∗(0.906 9)-0.142 1∗∗∗(0.867 6)-0.134 3∗∗∗(0.874 4) 是0a0a0a0a0a
注:表格内数值为对应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OR值;*,**,***分别表示该变量在0.1,0.5,0.01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由SPSS 22.0计算得出。
对比回归结果可以得出,4类人群回归模型中绿地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仅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人群在统计水平显著,结合回归系数绝对值表明,城市绿地对于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群体的正向影响均大于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群体。绿化水平的提升对居民健康均有积极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居民获得的绿地健康效益有显著差异,经济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得到的健康效益显著较少。
3.2 绿化投入与绿地健康效益分析
3.2.1 基于全样本的绿化投入影响评估 以园林绿化投资/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00%作为绿化投入力度指标,百分比越高表明绿化投入力度越大。绿化投入力度作为城市绿地规划的上层标准,是城市绿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导。本文通过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全样本分析,探究政府绿化投入力度是否可以真正作用于城市绿地,从而提升居民健康状况。
依据绿化投入力度平均值将全部样本划归为低投入组与高投入组,对两组居民的健康水平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处理结果见表3、图1。

表3 绿化投入分层对居民健康影响假设检验汇总Tab.3 Hypothesis testing of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differences on residents′ health
注:显示渐进显著性。显著性水平为0.05。

注:左侧组1为低投入组,右侧组2为高投入组。图1 绿化投入分层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Fig.1 Greening control stratification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表3显示,高、低绿化投入居民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图1中的统计结果,高投入组居民健康平均秩次为7 075.19,大于低投入组的6 820.11, 证明高投入组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显著优于低投入组。通过图1中的健康水平频率直方图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虽两组居民都呈现中位健康人群多,基数大的情况,但是高投入组中健康水平高(健康赋值为4,5)的人群频率较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分布较低投入组呈上移趋势。因此,绿化投入力度的提升对居民整体健康水平有显著积极影响,加大绿化的社会投入对居民健康提升有重要正向作用。
3.2.2 绿化投入与收入分层综合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绿化投入增加带来的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是否存在差异。分别以高、低收入人群为研究样本,对不同绿化投入水平下的居民健康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见表4、图2。

表4 绿化投入分层对不同收入居民健康影响假设检验汇总Tab.4 Hypothesis testing of health impacts of greening control regulations o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s
注:显示渐进显著性。显著性水平为0.05。

注:组1为低投入组,组2为高投入组。图2 绿化投入分层对不同收入居民健康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Fig.2 Greening control stratification on the health of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for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s
检验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保留原假设,高收入人群拒绝原假设,表明对于高收入人群,不同绿化投入力度下的居民健康有显著差别,而低收入人群则没有显著差别。高、低收入人群健康的分布频率图与平均秩变化与全体居民的健康变化相似,均呈现出中位健康基数大,健康水平整体上移的趋势。综合平均秩与显著性数据可以得出,绿化投入力度的升高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对于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存在差异,其仅对高收入人群有显著提升效益。
这一结果表明,上层投入介入后,不同收入群体的绿化健康效益仍存在显著差异。为探究绿化投入的介入能否弥补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健康效益差异,本文通过计算不同绿化投入水平下高、低收入人群的健康分布频率差值,判断绿化投入对群体绿化健康效益差异的影响情况。
分别计算高投入低收入、高投入高收入、低投入低收入、低投入高收入4类人群的健康分布情况,即每一健康程度人数所占该类人群总数的百分比;如图3所示,横坐标为不同健康水平,纵坐标及表格中数值为高、低收入人群在不同健康水平的人数频率差值的绝对值,代表不同收入人群健康差异。虚线代表低绿化投入地区人群,实线代表高绿化投入地区人群。

图3 不同绿地投入下高、低收入人群健康差异比较Fig.3 Comparison of health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nd low income groups under different greening control stratification
从图3可以看出,绿化投入的升高对不同收入人群既成的健康差异影响可分为3种。对于较差健康状态,绿化投入的升高减少了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对于中间健康状态,绿化投入的影响并不突出;而对于较好健康状态,城市整体绿化投入的提升反而加大了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整体健康差距。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绿化带来的居民健康效益回归模型,并以收入及社会地位指标为划分依据,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居民绿化健康效益差异。此外,通过引入绿地投入力度指标进一步探讨上层绿地投入的增强能否提升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从而弥补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产生的健康效益差距。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绿地对城市居民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高收入、社会地位人群获得的健康效益显著高于低收入、社会地位人群;另一方面,绿化投入的提升可以使城市居民健康分布情况正向上移,然而对于由于社会收入地位产生的既成健康差距,整体绿化投入的提升可以缩小不同收入人群在较差健康水平差距,反而扩大了其在较好健康水平的差距,加深了居民健康不公平性。
这些数据结果表明,虽然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因此接收到的绿地健康效益并不相同,甚至有显著差异;增加城市绿化投入使得经济收入较好的居民获得更大的健康效益提升幅度;对所有居民而言,健康都得到了提升,然而不同经济水平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更大了。
4.2 讨 论
本文数据表明,虽然绿地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绿地投入的增加反而扩大了健康的不公平性。针对这一矛盾,2017年Steffen[24]与2018年谭冰清[25]的研究都给出了实验支持。Steffen[24]以德国城市慕尼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Log-gamma回归模型,发现慕尼黑街区社会经济地位与临近公共绿地可用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高社会经济地位街区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街区周围公共绿地的空间面积与可达性都显著下降。谭冰清[25]以中国深圳市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与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发现深圳市绿地在数量、质量、可达性上均有较大差异,住房条件差的街道公共绿地数量普遍较少,住房条件好的街道公共绿地数量一般较多。
以上两个代表性实验都表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常常伴随着公共绿地使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绿地本身的数量、面积、可达性等方面。可以说,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本身就具有不公平性,城市整体绿化水平及其提升分配并不均匀,社会经济水平高的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城市绿化资源,并且,在整体绿化水平提升时获得更大的健康提升空间,进一步扩大了与经济水平较低居民的健康差距。
4.3 建议与展望
城市绿化水平与居民健康息息相关,绿地带来的健康效益对每一位居民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绿地带来的不公平性问题,在整体绿化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应注重绿地分布差异,不仅仅提升城市核心区域、发达区域的绿地水平,更要重视低社会经济地位街区的绿地发展,在规划源头尽可能地保障居民享受公共绿地的公平性,才能减少由于绿地带来的健康效益差异,避免由此引发的社会群体差距进一步增大。绿化投入作为城市绿化的指导性指标,对提升居民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绿化投入水平不应仅仅体现在城市整体的绿地投入,还应分区进行进一步推敲分配,在源头尽可能提升绿地本身的公平性,从而保障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居民健康,这一举措有助于在健康层面减弱社会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和谐。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数据选择上,剔除了儿童数据及乡村数据,会造成部分影响分析信息缺失;在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部分,本文将城市居民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没有深入区分城市间的差异,后续研究会关注绿地健康效益的城市差异,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城市群体的影响及改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