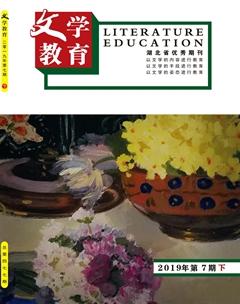论中医在日本的传播
万芳
内容摘要:中國传统医学技术于公元5、6世纪传到日本,对日本医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先后经历了全盘接受中国医学阶段、模仿中国医学阶段、运用中国医学阶段、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汉方医学独自发展阶段。汉方医学,即将中国传统医学精髓和日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发展成的医学体系。汉方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初现端倪、进一步发展、衰退、复兴阶段,尤其二战后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成为日本当代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医学 汉方医学 传播 影响
1.日本全盘接收中国医学阶段
中国传统的医学技术是和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大陆文化一起、于公元5~6世纪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历史上曾留下5世纪新罗医师为允恭天皇治病、6世纪新罗医师智聪将中国的医学书籍带到日本的记载。颁布于公元701年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上面就规定“朝廷设立典药寮,引进中国医学”。除了典药寮,朝廷还设内药司,进行医疗管理。同时还进行医学教育,由典药寮里的大学1或地方的国学担任;而医学教科书则全部为中国的医书。“根据医疾令,医生要学《甲乙经》、《脉经》、《本草(本草经集注)》、《小品文》、《集验方》,针生要学《素问》、《皇帝针经(灵柩)》、《明堂》、《脉决》、《流注图》、《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1]”。这一时期,中国医学东渐日本的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在世界医药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据日本宽平年间(889~895)藤原佐世(847~898年)所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到894年遣唐使废止为止,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医方书达160余部,共计1390卷之多[2]。当时中国医学书籍在日本的流传可见一斑。
除了引进中国医书之外,日本还引进中国的药材。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西北的正仓院里收藏有这一时期的珍贵药物的记载。《正仓院药物》主要分为两个体系,第一部分为了纪念殁于756年的圣武天皇、光明皇太后而供奉于东大寺大佛的药材,共有60种,记载在“种种要账(东大寺献物帐)”里,被称作“帐内药物”;第二部分没有药物由来的记录,被称作“帐外药物”。朝比奈泰彦于1955年重新整理并编撰的《正仓院药物》中记载了从公元710年开始日本从中国引入的药材图像,包括人参、远志、五色龙齿、冶葛、桂心、大黄等珍贵药材;现存的药材中,帐内药物有39种,帐外药物有24种。
2.日本模仿中国医学阶段
从平安时代(794~1129年)开始,日本就开始逐步进入对中国医学进行模仿阶段,主要表现为:开始模仿中国医书的体裁和内容编写日本医书。
平安時代中期的宫廷医师深根辅仁(?-?)为减小日本医师使用中国医书的难度,于日本延喜年间(901~923年)编撰《本草和名》,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药物(本草)辞典。这本辞典模仿唐朝的《新修本草》的范例,整理并收集了中国医学书籍记载的药物名字,并给药物注上和名(日语名字)和该药物在日本产地情况。《本草和名》引用了30余种中国古籍的药名,分为本草类、禽兽虫鱼类、谷类等9类共1025种品目的药名,其中矿物性药81种、植物性药509种、动物性药182种。
905年醍醐天皇敕令编撰、并于927年完成的法典《延喜式》,对日本运用中医典籍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凡应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难经六十日。其博士准大学博士给酒食并灯油赏钱。凡大素经准大经;新修本草准中经;小品明堂八十一难经并准小经[3]”。可见,此时的医学典籍已经通过法典形式统一为《太素经》、《新修本草》、《小品文》、《明堂》、《八十一难经》等。
这个阶段还有一部医书也展示了日本对中国医学精华的接受情况。写于984年的《医心方》是日本平安中期的宫中御医丹波康赖(912~995年)模仿中国医书的体裁,广泛搜集中国医学典籍,博采众家之长,用汉文编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医学书籍。该书三十卷,是一部颇具“百科全书”性质的医学书籍。除了广收科药方之外,还记载了针灸俞疗、本草食疗、服石辟谷、房中养性以及医德修养、治疗原则、服药方法等。
3.日本运用中国医学阶段
随着律令制的瓦解,日本进入了镰仓幕府(1185~1333年)时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已经从朝廷主导转变为民间的交流和僧侣之间的交流。由于僧侣和中国大陆文化接触频繁,医疗工作的接力棒由宫廷御医传到了僧侣的手中,医疗服务的对象也开始惠及到普通民众。如日本僧侣受中国僧侣的影响,在寺院里开设简易的行医场所,普救众生。最为有名的是镰仓时代真言律宗的僧侣忍性(1217~1303年)于1283年在镰仓极乐寺开设疗养院、施药院,对贫民、麻风病患者等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医疗救助。在以后的20年间极乐寺接纳了约46800人次的病患。
由汉文和假名混写的医书的出现在日本人运用中国医学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些汉文和和文混写的医书中,集大成者是梶原性全(1266~1337年)编写的医书《顿医抄》(1303年)和有林编写的《福田方》。梶原性全是一个生于镰仓武士家庭的僧医,在学习佛学经书的同时,也研习了大量的医学典籍,并积极向当时医学世家丹波氏2和和气氏3学习医疗技术。梶原性全摒弃了当时医药界流行的医疗技术作为家族秘方不外传的风潮,在开展医疗事业时将多年的行医经验著书立说,于40岁写成了《顿医抄》。此书共50卷,包含了预防疾病的养生知识、医疗伦理等。此书不同以外医学书籍照搬中国医药典籍的传统,梶原性全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医药和医疗术语。本书还附载了人体解剖图,这是日本医书第一次采用人体解剖图。
这一时期的另一本医书《福田方》则是由南北朝时代的禅僧有林编写,此书共12卷,用汉文和假名混写的方式撰写,涵盖了从中国汉朝到元朝约160种中国医书的内容。按科目和症状分类记载药方,涉及到本草、制药、针灸、养生等领域,同时也详细阐明药方所出典籍,是一本实用性极强的医学典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医学的最高水平,也是研究中国医学书籍在日本传播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4.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从室町时代(1336~1573年)开始,日本进一步消化中国传统医学,进入了中国医学的日本化阶段。这个阶段日本僧医到明朝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后回到日本加以推广,并结合日本实际情况编写适合日本的医学书籍和培养医疗人才。最有名的是田代三喜(1465~1537年)和其弟子曲直瀬道三(1507~1594年)代表的后世派或后世方派。
田代三喜是日本室町时代的僧侣、医师,曾到中国明朝学习当时最先进的金·元时期的医学,后将先进的金·元医学的精髓(如五行说理论)带回日本,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加以推广。其弟子曲直瀬道三先为僧侣,后因立志行医而还俗,为宣扬中国医学,设立医学校“启迪院”培养后继医师。曲直瀬道三积极引进明初至嘉靖年间(1368~1567年)的中国医学,编撰医学书籍《启迪集》(1574年出版),宣传医学思想、培养医学人才。田代三喜和曲直瀬道三都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将药物分为五性(寒、凉、热、温、平)、五味(辛、酸、甘、苦、咸),将人体内脏器官分为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将人类精神活动分为五神(魂、神、意、魄、志);主张诊疗时,通过各药材在五性、五味的调和,使得五脏、五腑各人体器官相生相克,从而到达人体生命活动的平衡。这种诊疗方式受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在日本称为后世派或后世方派。
中国医学日本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日本开始自行印刷出版医学书籍,加大宣传力度。当时有名的刊行者是中日贸易窗口的大阪堺港的医家阿佐井野宗瑞(1473?―1532),他首次出资刊行的典籍是明朝熊宗立的《医书大全》。《医书大全》1446年初次刊行,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雕刻印刷的医学书籍,较之手抄本,宣传力度很大,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甚大。1536年日本出版了第二部印刷医书《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勿听子”是熊宗立的号,可见此书的刊行也深受《医书大全》的影响。随着活字印刷技术经由朝鲜传到日本之后,大量的医书被印刷,据日本学者小曾户洋调查,“古活字版医书的刊行始于1596年,至宽永年间,据我调查就出版了不下于二百種,大半是中国新医书的翻印[4]”。这些中国医学书籍的大量翻印,改变了之前只能依靠从中国输入原书或手工抄写的现状,推动了医学书籍在日本的传播,提高了日本的整体医学水平,为日本独特的汉方医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5.日本汉方医学发展阶段
日本江户幕府4为了加强封建统治,从1633年开始发布第一次锁国令到1853年美国黑船打开日本的大门200年间日本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引进、翻刻中国医书的频率和数量减少,日本开始消化多年来学习中国医学的经验,出版了大量日本人独立注释的中国医书以及养生、针灸、本草等书籍。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医学独自发展,出现了汉方医学,即将中国传统医学精髓和日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发展成的医学体系。
5.1.汉方医学初现端倪阶段
5.1.1.古方派的出现
日本汉方医学独自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出现了古方派。古方派视中国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5为医学圣典,排斥传统中医理论中观念式的概念(如阴阳学说),重视将古代药学实践和医学实践作为理念,根据《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经验进行诊疗。首先倡导重视古典医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是名古屋玄医(1628~1696年),他是日本第一位对《金匮要略》进行注解的医师,被称作日本古方派的始祖;同时他结合行医经验,写成了《医方问余》等医学书籍。对古方派的医学思想进行实践的还有后藤艮山(1659~1733年)、山脇东洋(1706~1762年)、吉益冬洞(1702~1773年)等。
后藤艮山反对空泛的医学理论,主张重视《伤寒论》等古药方,是一气留滞说的倡导者,即认为百病皆因一气留滞而生,而顺气则为治疗之纲,提出食物治疗法和汤熊灸庵法(即通过针灸、熊胆、温泉等方式治疗疾病)。
后藤艮山的徒弟山脇东洋出生于医学世家,是位尊法眼的高僧,也是日本实验医学的先驱者之一。师从后藤艮山,翻刻了《 外台秘要》24巻。在浏览群书时,对传统医学典籍中所说的“五脏六腑”持怀疑态度,为了研究人体内脏的构造,于1754年对京都六角狱舍的死囚犯遗体进行解剖,并将绘制的内脏图记载于1759年出版的专著《藏志》里,此书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本解剖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吉益东洞博览古代医学典籍,提出“万病一毒说”,即“万病源于一毒,众药皆毒,以毒攻毒则毒去体佳”。他主张通过强效药剂治疗疾病。因此在他编撰的医书《类聚方》中药方只有200种左右。今天看来,吉益冬洞的主张和实践过于偏激,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大大提高了诊疗效果。这种重实践效果、轻理论的观念一直主导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
5.1.2.本草学的发展
除了医学实践,古方派也重视本草学的发展,而本草学的发展主要围绕对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进行和文注解以及模仿著书进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原益轩(1630~1714年)、寺岛良安(1654~1732年)、松冈玄达6(1668~1746年)。
贝原益轩是一个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也是博物学家。他从小体弱多病,故注重养生,且博览群书,喜欢四处游览,用眼睛、耳朵和手等感官亲身验证书中所看内容。晚年的贝原益轩专注于著书立说,将一生所学都传世后人。他留下了60部共270余卷著作,既有本草类书籍,又有训导类和养生类书籍,其中最有名的本草类书籍是《大和本草》。此书成书于1709年,仿照中国明朝李时珍的著作《本草纲目》(1607年传到日本)范例,记载了约1326种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的性状和功效。《大和本草》代表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生物学类、农学类书籍的最高峰,也是现存的唯一一部明治时代以前的生物学、农学类书籍。
寺岛良安是江户中期的医学家和考证学家。受中国明朝易医论的影响,认为只有通晓“天、地、人”“三才”才是真正的医家,仿照中国《三才图会》7,出版了日本第一部带图的百科书籍《和汉三才图会》。此书共150卷,按“天”“地”“人”三才分类,图文并茂,既有本草药物,又有绘图插图,药名用汉文和和文标注,药物性状则用汉文解说。
松冈玄达是江户时代有名的博物学家、本草学家。他不仅从小博览群书,还虚心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学习:向思想家、儒学家山崎闇斋(1619~1682年)、伊藤仁斋(1627~1705年)学习儒学经典,向医学名家浅井周伯(1643~1705年)学习医学,向本草学家稻生若水(1655~1715年)学习本草。松冈玄达一生留下许多著作,其最大的功绩还是对日本本草学发展的贡献。他协助江户幕府积极推进江户本草学的发展,并广纳弟子讲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并在本草学代表作《用药须知》中记载了320种日常用药材及每种药材的和文名字、产地、性状和功效。其弟子小野兰山(1729~1810)继承松冈玄达的衣钵,继续开展本草学的推广和研究,在著作《本草纲目启蒙》(1806年出版)中还增加了药材在植物阶段的各种性状描述及别名。
古方派和本草学的发展促进了漢方医学的发展,也奠定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基调:重实践轻理论;药方和药材的相辅相成。
5.2.汉方医学进一步发展阶段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汉方医学进一步发展,践行医师们开始总结古方派的实践和经验,一方面继续丰富和完善古药方的实用性,并通过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另一方面开始反省古药方的局限性,并开始探索与其他学科的互补和融合。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考证派、折中派、汉兰折中派的出现。
5.2.1.考证派
考证学派受当时中国清朝流行的考证学的影响,主张对儒学经典和医学经典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证,从而梳理出典籍中的经典药方,并通过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两种方式促进汉方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代表人物为多纪元简(1755~1810年)、多纪元坚(1795~1857年)父子。多纪元简出生于医学世家,是一名幕府医官,后入佛门,位尊法眼8。后在幕府管辖的汉方医学馆——跻寿馆任教,教材为经多纪元简注释过的《素问》、《灵枢》、《伤害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在教学和考证经典之余,多纪元简整理了历年历代关于脉象的各种学说,梳理出对于疑难脉象的诊断标准,写成著作《脉学辑要》;多纪元简一生博览群书,考证的古代典籍不计其数,他从考证的212本医学经典中梳理出近2400副药方汇总成药方集《观聚方要补》。其子多纪元坚继承父业,也是一名幕府医官,后也入佛门,先后位尊法眼、法印。在幕府医学馆任教时专著于古典医学书籍的收集、考证、复原,最值一提的是对仁和寺本的《皇帝内经太素》和宋版《外台秘要方》的新旧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尝试复原原版本。根据医学实践写成的《伤寒论述义》影响甚大,被后世不断重印。
5.2.2.折中派
折中派主张将后世方派的辨证论治诊疗法和古方派重视古药方的实用性结合起来,发挥古代药方的实用性。代表人物有和田东郭(1743~1803年)、原南阳(1753~1820年)。
和田东郭为折中派的泰斗,曾师从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冬洞,对古典医方尤其是《伤寒论》的医方尤为推崇,主张一切疾病的治疗要以古医方为主,不足之处则由后世方等补充。他的治疗法中庸、温和,得到世人的好评,直到现在日本汉方医学界仍然沿用。和田也曾入佛门,位尊法眼。但是和田东郭不喜著书立说,其医学思想主要散见于门人弟子的笔录里,如《蕉窗杂话》、《蕉窗方意解》、《道水琐言》、《伤寒论正文解》、《东郭医谈》等。
原南阳出生于水户一个藩医9之家,曾师从古方派的山脇东洋之子山脇东门(1736~1782年)、著名产科医生贺川玄悦(1700~1777年)。他从山脇东门处学到了古医法、放血法、经络针灸法等技术,从贺川玄悦处学到了通过按摩孕妇的腹部辨别胎儿胎位的方法。学成后,他继承父业,成为水户藩的一名医官,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原南阳在行医生涯中,不拘泥于医学典籍中的字句规范,而是根据患者的情况采取临机应变的诊疗方法。原南阳医生著述很多,有日本第一本军医书籍《砦草》,有对中国古医方的解读和理解的《伤寒论夜话》、《经穴汇解》也有以原南阳的室号从桂亭命名的书籍如《丛桂偶记》、《丛桂亭家藏方》、《丛桂亭医事小言》等。
5.2.3.汉兰折中派
汉兰折中派是伴随着荷兰医学在日本的发展而逐步出现的。17世纪德川幕府采取禁海令,实行锁国的政策。从宽永十二年(1635年)以后,日本只限长崎一港为对外贸易港,允许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通航。伴随荷兰船只到达日本长崎的除了经商人员外,还有为商馆人员服务的荷兰医师。之后的200年间,荷兰医师以每年1、2人的频率源源不断地来往于日本与荷兰之间。按照规定,这些医师专为商馆内的人员进行健康管理,禁止离开商馆给普通日本人诊疗或交流。但如果经过政府许可,荷兰医师可以在商馆馆长到江户参府10时一起去江户,与江户的学者们进行交流。日本的学者们被荷兰医学吸引,纷纷到长崎向荷兰医师学习。另外,担任翻译工作的通词也逐步对荷兰医学产生兴趣。一门新的学问——兰学应运而生。好学的日本学者们在消化、吸收汉学的同时,也开始对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数学、军事、天文学、历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接收中国文化一样,日本对荷兰文化的接收也是通过书籍开始的。1744年,日本第一本西方医学翻译书籍《解体新书》出版,此后大量的荷兰语或日译本荷兰医学书籍大量出现,促进了近代日本医学的发展。对西方医学在日本传播有重大贡献的当数德国籍医师Siebold(1796~1866年)和绪方洪庵(1810~1866年)。Siebold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医学世家,在德国名校维尔茨堡大学学习医学、动植物学、民族学等。1823年到长崎的荷兰商馆任医师,并开设医孰教授医学知识,积极推进西方近代医学在日本的传播。绪方洪庵为江户末年的武士、医师,曾向宇田川玄真(1770~1835年)学习荷兰医学,并游学长崎向荷兰医师进一步学习西方医学,后又在大阪开设医塾教授荷兰医学。绪方洪庵最大的贡献是引入西方的种痘法,为天花病毒的预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推广种痘法、预防天花病毒,绪方洪庵完成著述《病学通论》,这成为为日本第一本病学原理书籍。
汉兰折中派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代表人物为华冈青州(1760~1835年)、本间枣轩(1804~1872年)等,他们主张在给患者诊疗时,将汉方医学的药方和药材的优势与荷兰医学先进的外科技术结合起来。
华冈青州,江户时代研究汉兰折中技术的外科医生,曾向古方派医家吉益冬洞的长子吉益南涯(1750~1813年)学习汉方医学,又向外科医师大和见立(1750~1827年)学习外科技术。为了减轻手术带给患者的痛苦,华冈青州在中国古药方华佗的麻沸散的基础上,利用曼陀罗花、草乌头、白芷、当归、川芎等6种主要草药,研制出全身麻醉剂——通仙散,并利用通仙散于1804年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乳癌摘除手术。作为对世界外科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医师之一,1952年华冈青州被供奉于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外科学会的荣誉馆内。
本间枣轩,出生于日本水户的一个医学世家,年轻时曾向折中派的原南阳学习汉方医学、向外科医师杉田立卿(1787~1845年)学习西方近代医学技术。曾投身于华冈青州的门下学习外科技术,利用通仙散麻醉效果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大腿截肢术。本间枣轩一生成功实施了无数手术,他总结了这些案例的经验,写出了不少著作,传世后人。如《伤科秘录》、《后伤科秘录》、《内科秘录》。
5.3.近代汉方医学的特点
从以上古方派、考证派、折中派、汉兰折中派等汉方医学名家的医学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汉方医学是在对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的不断学习、反复推敲、坚持实践、总结经验中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的;药方和药材的发展促进了汉方医学的发展,也奠定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基调。近代日本汉方医学具有如下特点:①重视药方的实用性,并反复推敲中国古典药方与岛国现状的适应性;②重视本草学的本土化发展,注重中国古典药方中药材的岛国适应性,如注上和名、栽培地点等;③忽略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观念式的概念(如阴阳五行说),探索对经典药方实用性的改良。④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给古典药方引入新鲜血液,如兰学和西方医学。⑤汉方医学发展的重担往往落在寺院僧侣等汉学修养高的人群肩上。
6.日本汉方医学衰退阶段
到了江户末明治初期,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两大名医:尾台榕堂(1799~1870年)和浅田宗伯(1815~1894年)。
尾台榕堂被称为江户最后的古方派,本姓小杉,16岁时到江户拜当时的名医尾台浅岳学习古方医学,后继承其姓,改姓为尾台。尾台榕堂对吉益东洞极其推崇,认真研究《类聚方》中的古药方,并根据临床经验对古药方进行删减、补充,完成了著述《类聚方广义》。这部巨著到今天还被日本的汉方医学界广为好评。
浅田宗伯是幕府末年有名的医学家和儒学家,也是佛教高僧,位尊法眼。以精湛的临床医学技术广为人知,尤其以擅长诊疗传染病霍乱和麻疹而闻名。因此被幕府任命为御用高级医师,1865年受幕府派遣,运用汉方医学技术成功挽救了驻扎在横滨的法国公使Michel Jules Marie Léon Roches的生命。
但随着1853、1854年美国人佩里(Matthew Calbraith Calbraith P.1794~1858年)驾驶黑船在浦贺岛11登陆、强迫日本开港,尤其是1868年倒幕运动成功、明治新政府的成立,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如潮水般涌向日本,陪伴了日本一千多年的汉方医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存续危机。明治政府于1874年以汉方医学不是医学为由,取缔了汉方医学,认定西医为唯一医学。以浅田宗伯为首“汉方六贤人”12为汉方医学的存续而不断努力。1875年明治政府提出医师资格考试改革,提出将西医七科作为考试科目,为此浅田宗伯等人提出汉方六科为考试科目与之对抗;1879年为了更好推进汉方存续运动,浅田宗伯等人成立温知社,通过机关杂志《温知医谈》宣传汉方医学,为了推进汉方医师的培养成立了和汉医学讲习所(后改名温知医学校)……温知社的汉方救亡活动曾一度风靡全岛。但1883年,明治政府发布了“太政官布告”,规定如果没有取得医师资格的国家考试,就不能挂牌行医。为此,浅田宗伯等人向政府提出的“继续汉医学”的请愿书,请愿书于1895年在国会第8议会中被否决。至此汉方医学的存续救亡活动宣告彻底失败。温知社逐渐式微,不得已于1887年召开全国大会讨论是否解散温知社;温知医学校也因为负债问题面临关门危机;《温知医谈》也于1889年停刊。汉方医学陷入了灭亡危机。
7.日本汉方医学复兴阶段
尽管汉方医学被政府取消,汉方医学的救亡活动也宣告彻底失败,汉方医学曾一度停滞。但民间仍有一部分医师、药剂师、药材商为汉方的存续继续努力,保存了火种。代表人物是和田启十郎(1872~1916年)和弟子汤本求真(1876~1941年)。
和田启十郎1892年到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期间偶然在旧书店里发现了吉益东洞的《医事或问》,从此与汉方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进一步学习汉方医学,向一位名叫多田民之助的汉方医师学习古医方。和田启十郎行医经验丰富,先后开设诊所、医院,甚至作为军医参加了日俄战争。在多年的诊疗中,他发现西方医学中纯粹外科学的局限性和汉方医学在病毒治疗中的功效,并结合临床经验撰写著述,于1910年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锤》,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汉方医学的重要性,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汉方医学的功效性。1915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了第2版《医界之铁锤》,又添加了许多治疗实例。
汤本求真1901年毕业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从1903年开始挂牌行医,并兼任警察医。1910年因长女汤本俊子传染了疫痢而西医医治无效的事件导致了汤本求真对现代西医技术产生了怀疑。受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锤》的影响,汤本求真潜心于汉方医学的研究,并于1917年出版了《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1927年自费出版了《皇汉医学》第1卷,1928年出版《皇汉医学》第2、3卷。《皇汉医学》的出版,成为了日本汉方医学中兴的基础。鉴于此,汤本求真也被称为“汉方医学中兴之祖”、“东西医学融合之先觉者”。之后,日本的汉方医学开启了漫长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