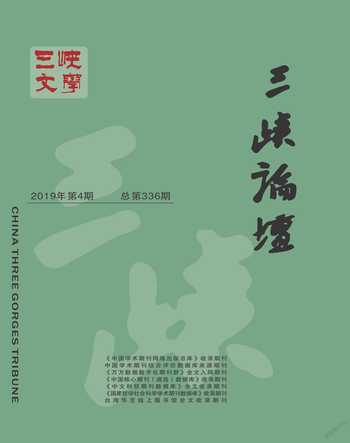新化山歌的“活态性”传承研究
刘建荣 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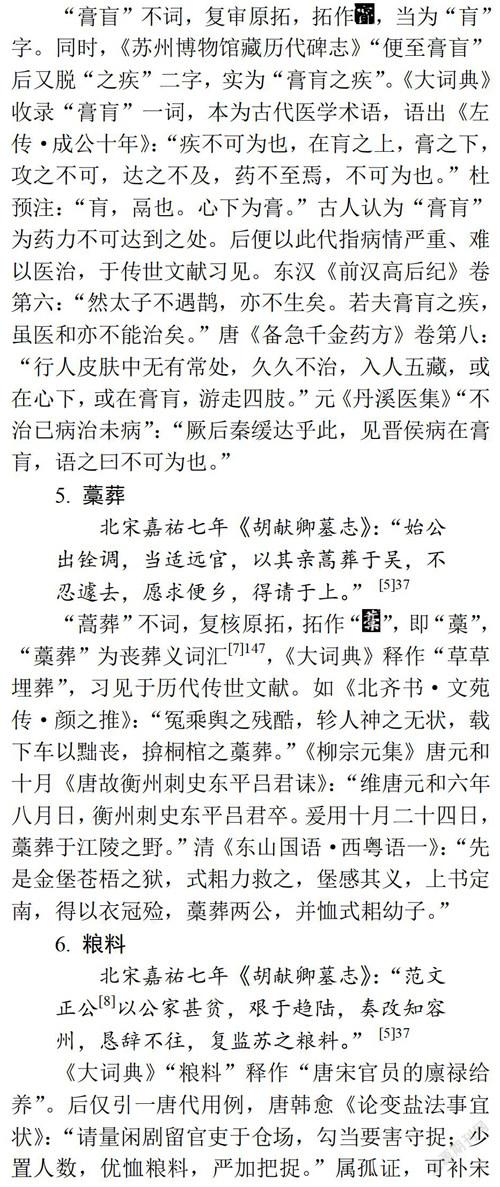
摘要:“活态性”传承是针对无法直接物质化生产的精神产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传承方式,坚持文化精神为传承核心,文化传承主体群为传承动力的传承方式。新化山歌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历经两种传承方式,实践证明都有一定的弊端。新化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活态性传承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其“活态性”传承应把握传承的关键环节、基础条件、发展手段,坚持文化基因的人文关怀、区域生态的整体保护、文化传播的现代转化,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传承、有人传承、可持续传承。
关键词:新化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46-06
党的十九大以来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发展人民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人民文化生活的尊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新化山歌是新化人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中酝酿而来,已融入新化人的骨髓中,保护和利用新化山歌对于新化人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对新化山歌的“活态性”传承进行探讨,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借鉴思路。
一、“活态性”传承的界定与特点
目前学界多从活态性传承方式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传承问题,但对于活态性传承的含义多有歧义,根据“活态性”传承的特点,需要对活态性传承进行全方位的认识。
(一)“活态性”传承的内涵
我国在2003年就着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发展策略,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索传承之道。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生产性传承与活态性传承。两种传承方式适用的对象是有区别的。2012年,我国文化部在“文非遗发〔2012〕4号”文件中指出生产性保护仅限于“传统手工技艺及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类项目”。意味着生产性传承方式是有局限的,是针对可以物质化生产,并产生经济效应的物质产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之相反,活态性传承是针对无法直接物质化生产的精神产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等。
活态性传承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传承方式。“内”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文化,这也是活态性传承的核心。强调寻求文化传承主体的内部力量,要求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创造性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表现形式、舞台张力。“下”是指活态性传承的中心是文化传承主体群。文化传承主体群是指承载相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与文化的传承共同体,拥有非遗文化在解释、表现、宣传上的主导权与决定权。这种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根植于传承主体在生产生活中培养的素养,也是与现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相互协调的结果。也就意味着活态性传承方式并不排斥政府的保护、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发展空间上正在由私密向共享发展、时间上由集约向碎片化发展。活态性传承是非遗文化内化的结果,必须避免因生产性保护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商业化、产业化、旅游化。
总之,活态性传承是针对无法直接物质化生产的精神产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采取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传承方式,坚持文化精神为传承核心,文化传承主体群为传承动力的传承方式。
(二)“活态性”传承的特点
活态性传承重在“活”,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非生产性。山歌等精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能批量生产、流通与销售的,也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不具有生产性能,具有非生产性特点,但此类山歌等具非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艺术加工形成的表演产品却具有天然的舞台渲染力与彰显力,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喜爱而传唱。
第二,主位性。主位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规范。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指出:“所谓主位立场是指从内在的、研究对象的角度理解文化。”如山歌主位性特点是指山歌源自群众生活,是群众生活的主体性反映,山歌传承需要尊重山歌主体的个性与生活样式,立足于传承主体群的自我意识与自我个性,体现传承主体的集体记忆、内心热爱与发展愿景。
第三,整体性。山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某一地域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生长的,因而,活态性传承不仅仅需要着眼于传承主体群,也应该重视传承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坚持从环境、制度、社会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整体性效应,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中体验山歌的词曲声韵。
第四,发展性。活态性传承就在于其在传承中赋予了每一代人的生活积累与创造性发扬,积极顺应历史人文环境的熏陶与经济社会的刺激。活态性传承是辩证“扬弃”。如山歌是一代一代先民祖祖辈辈口传身授传承下来的,继承一个地方山歌的独特韵律与体例,但又扬弃生产生活发展中淘汰了的内容,才能使山歌永葆生命力。
第五,開放性。如山歌的活态性传承不仅体现在山歌与生活紧密结合,因时因地因情因景等等而随心所欲、随口唱就,声韵、曲调、内容在不同情境中可高亢悠扬、幽怨回肠、欢喜流畅、俏皮幽默、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生活写照等,体现其中的灵活、活现、活跃、活脱以及开放、奔放,在开放互动中抒情会意。活态性传承就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交融互动、开放交流、融会贯通,因对事物的情真意切而感悟吟唱。
二、新化山歌的历时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各个群体或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传承积淀下来的。纵观新化山歌的艺术发展过程,“非物质”的新化山歌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传统的传承方式,口传身授的方式;一种是外界力量干预的传承方式,政府介入主导的方式。但这两种传承方式在现实的活态性传承过程中各有优点,亦有缺陷。
(一)传统口传身授传承方式
山歌是诉诸声音与氛围的艺术,人们鉴赏与学习的途径则依靠视觉与听觉的相辅相成。郑培凯先生提出“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是人类文明存在的三种方式之一。口传身授方式的本质是山歌诀窍的传授,是显性表演背后的隐形技巧。诀窍的传授使得新化山歌的多重角色达到精微与传神。山歌的演唱在新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新化山歌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表现在:第一,由新化县主办的“梅山千人山歌大联唱”,数万名齐声共唱,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新化山歌在当时广泛流行。第二,伍喜珍演唱的新化山歌《神仙下凡实难猜》,不仅在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中荣获一等奖,而且为毛泽东等众多领导人多次演唱,收获掌声连连,被评价为“蛮脆蛮甜”的山歌,促使新化山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播。新化山歌在全国打响招牌,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也达到高潮。一个师傅招收小规模的徒弟,亲自示范、亲自教学。徒弟在长时间浸润式学习中,以师傅为范本,学形、学态、学技。在现代化进程未影响乡村发展时,口传身授作为乡村山歌发展的主要形式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促进新化山歌的传承与发展。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大量新化农民外出打工,传统乡土文明构建模式被破坏,现代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等导致新化山歌的传承人难以为继,老一辈的技艺无人学习,口传身授传承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降低。
(二)政府介入主导的传承方式
由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自然传统的传承方式面临着一些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干预性传承是指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脆弱性或者后天的生态环境恶化等,导致其自然性传承功能障碍,因此需要借助某些社会力量的干预而进行的传承。政府力量的介入使新化山歌的传承具有了合法性,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新化山歌的发展环境,提供了人力财力支持。自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活动以来,新化县政府积极响应号召,开始以新化山歌为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5年,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化县委、县政府牵头组建了新化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拨付保护专项基金、组建行政工作人员,进行覆盖全县的入户入门式调查,并依照保护中心的五年计划,工作人员搜集整理山歌、歌谱千余首,扶助建立了15支新化山歌队伍,并尝试将山歌教育渗入学校科班教学,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新化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当年就初见成效,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中获得银奖。之后,新化县政府积极筹备资料、开展活动,2006年成功申报成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年成为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6年在中国武陵山片区山歌王大赛中凭借新化山歌《呜哇峒》,获得众多好评,一致认可。
(三)两种不同传承方式评介
新化山歌作为一种口头的艺术,其衬词与腔调无法用语言准确记录,也无法记录。口传身授是面对面的教学,手把手的辅导,有利于克服文化传递的障碍,但是,也具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具有效率低、扩散面小等缺陷,所需时间成本与学习成本过于高昂。山歌是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个人的传承有一定限度。历史已经证明,传统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方式,无法作为主导的传承方式。
面对口传身授传承方式在经济社会的式微,2005年政府作为行政强制力量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在保护力度与保护制度上都给予高度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环境、传承作品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在新化山歌传承现状调查中发现,为追求明显的保护成效,政府由主导型保护转变为包办型保护。长期以来“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也使得“为民做主”成为政府与民间双重的惯性思维,体现在非遗保护方面,便是政府的主导与包揽,以及民众参与的形式化与边缘化。政府以主流思想鉴别新化山歌的传承内容、传承形式与传承人员,山歌在内容上拒绝传统情爱与旧时劳动,强调演出形式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固定扶持有知名度的传承者,这样一来违背了山歌的固有特点——群众性,也挫伤了农民群众创作的积极性。故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化山歌成为官方民俗。新化山歌的价值也由文化价值转变为凸显政府绩效指标的政治价值与地方发展的经济大戏。
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是需要商榷与改进的。我们并不否定以上两种传承方式的作用,但是为促进新化山歌的发展则需要寻求最佳的解决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信息化时代的传承方式需要与时俱进,传承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
三、新化山歌“活态性”传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新化山歌的口传身授与政府干预两种传承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活态性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新化山歌采用活态性传承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首先,新化山歌采用活态性传承是可行的。第一,新化山歌属于精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生产性的特点,适用于活态性传承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做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第二,活态性传承的主位性保障传承实践。活态性传承“是主体的实现,在这种活动和过程中,体现着主体的参与和投入,贯穿着主体的作为。”活态性传承把新化山歌的发展回归于主体本位,传承主体群在参与中践行平等享受权利与传承发展义务,最大化地保护新化山歌的原真性与实践性。第三,活态性传承的整體性保护传承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天人合一”的公共产品,是环境、制度、社会三要素的共同产物。活态性传承尊重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一变量,主张从生态大环境入手,推动文化“内生力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基因,创造新文化,加速活态性自我生成。第四,活态性传承的生长性推动传承能力的发展。活态性传承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促使新化山歌成为人们精神娱乐与消遣的一部分。同时,活态性传承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众要素集结的产物是随生态演进而不断进化发展,需要在适应生态演进中倒逼传承能力。
其次,新化山歌采用活态性传承是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是通过活态性传承,使热爱山歌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量的参与到山歌吟唱之中,有助于增加新化人的向心力,振兴新化乡村文化;二是活态性传承具有开放性与发展性,可以促进新化山歌不断赋予时代的最强音,有助于推进新化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建设,升华人们的道德观念并外化为道德实践;三是活态性传承体现了山歌的主位性,可以充分表达新化人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以歌代说唱出新化乡村振兴的远景,形成远大的社会理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聚力量。总之,采用活态性传承方式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充分践行文化部“見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也是最大化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样态,最大化地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
四、新化山歌“活态性”传承思考
新化山歌的传承需要以传承人群为主体,也需要在内容上与形式上与时俱进。引入活态性传承,将活态性保护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寻求传承之道。
(一)传承关键:文化基因的人文关怀
坚持活态性传承的主位性。基因支撑着生命的基本构造与机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最终留存的文化基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作品与非遗传承人,两者是文化基因的物化与人化的体现。活态性传承的人文关怀是高度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野性与纯真的文化基因。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对可以谱曲的音乐文化作品给予文本式记录、对难以谱曲的音乐作品加以实物化保存,注重充分运用信息化的网络技术,形成有所传承、可以传承的文化基因内容。活态性传承的终极人文关怀是对现实中传承主体的关注。传承主体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义,是物质技巧与工匠精神的寄托者,是“活态性”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根据杨民康教授提出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狭义性”,将草根意识的非遗传承人在区域内纵向传承为主线,以求得在内容、形式、手段上的文化认同为主要目的。非遗传承人上承文化指要,不断开发自身文化的广度与深度,在与民间老艺人切磋技艺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也要下接传承新人,履行责任培养下一代文化承接人;发挥自身的文化魅力推广非遗的发展,开拓当地发展的文化空间。在传承祖宗技法与传统的同时需要有更多以辜红卫、陈福云等新化山歌代表性传承人,在原有生活积累的基础上,把握视角、选取题材、造词组句、自编自导山歌剧,借助谙熟于心的山歌脱口而唱。例如山歌实景剧《呼唤紫鹊归》、歌唱曲目《梅山山歌联唱》、原生态音乐实景剧《谁与茶缘》。在寻求突破原有山歌缺陷的同时,也需要牢牢地扎根在新化土地上,将山歌借助土地深厚的力量凸显山歌的俗与雅,以新化山歌的高亢曲调与民俗特质融入新化全县各乡镇的风俗民情,打造一支支符合当地特色的演艺队伍,创新推广及传承形式,促使梦开湖湘,唱响新化山歌。
(二)传承条件:区域生态的整体保护
活态性传承要坚持整体性保护。每个具体文化事项的文化内涵及其形态特征与相关地理、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其中最密切、必要的关系构成的空间位域就是生态壁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其发展需要、必要且直接在于地利、天时、人和,为此开展以物质文化遗产为目标对象的区域生态中环境、制度、社会的三维空间条件。
天人合一是这般的诗意地栖居,也是人的存在的本真维度和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本体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与续存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的,新化山歌产生于相对闭塞的山岭地带,旷野的自然环境与传统的生产生活是其产生的环境基础。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经济现代化转型不断加快,新化山歌的传承可以采取村寨为传承保护单位,利用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加之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发展山歌主题的旅游经济。环境空间具有自发与不稳定的特点,必须用制度空间加固。制度的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应坚持“客位观—局外人”的立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机制。在国家支持下,政府成立专业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抢救和保护机制具体化。制定新化山歌传承与发展的目标与方案,通过项目制的形式开展,培养专业人才进行专项工作,拨付专项保护基金支持工作的开展。并成立新化民间文学协会的领导小组,在多部门的配合下增强实施力度与波及范围。传承的整体保护也不可缺少社会空间的建构。应注意其原生地的文化生态,联合非遗传承人的单线培养模式,加强基础教育与艺术院校的山歌系统教育,借鉴西方音乐理论式教育模式,形成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山歌素养的山歌教育体系。同时,发挥文化馆(站)的山歌艺术普及工作,在激发兴趣的同时培养一批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新化歌者。借助环境、制度、社会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开展整体性保护,为山歌在当地的发展铺路架桥、保留并创新当地的高歌传统,继而培育当地良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
(三)传承发展:文化传播的现代转化
生态壁龛概念的提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空间构建的意义框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直接现实空间。活态性传承坚持开放发展性的价值取向,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融通和民族和合共生的大背景当中以生态保护和基因传承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寻求非物质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面对乡村空巢现象、山歌艺术的受众群体小等压力,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文化的传播路径来倒逼创新发展。在原有新化山歌的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增加现代表演元素、现代审美情趣。通过对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提升山歌魅力。加强新化山歌的宣传力度、提升表演效果是当下的主要任务。新化山歌的宣传发展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要充分利用和挖掘文化旅游、现代剧场、大型比赛和文化节庆四大平台资源,产生群策群力的产业园效应,促使新化山歌整合行业高端资源,形成文化高地。为此,首先需要将乡土化的山歌文化既融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在情景交融中达到山歌演唱有所想、有所感。利用文化旅游这一平台带动新化山歌的传承与发展。其次,新化山歌需要将乡土文化与都市气息相融合,形成现代剧场并予以推广。保持乡土气息的同时突破流动演出的弊端,通过修建固定的剧院与会场来提升影响力。再次,当地政府要组织新化山歌团队积极参与比赛。比赛平台能够为新化山歌对外推广提供渠道,特别是培育和推送经典山歌作品参加有影响力的大型比赛,有利于集聚人气成为舆论焦点。最后,充分利用新化的传统节庆,例如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梅山文化旅游节等,促使新化县生态旅游区、歌剧院、竞赛活动与抬故事活动等整合开发,以感受梅山风情、了解新化民风。文化活动铸造新农村的灵魂。通过利用文化旅游、现代剧场、大型比赛和文化节庆四大平台资源,不断通过外力的推动作用达到新化山歌的名字听的熟、打得响。
新化山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文化之林中,在其中包含着的是新化人对生活的热爱,寄托着的是新化祖祖辈辈的美好,憧憬着的是新化人对未来的希望。面对艺术的流逝与山歌的低谷,新一代新化人手持山歌古韵需要扬鞭奔腾、起航远行。通过比较新化山歌在历史上的传承方式,探索山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文明的大环境中发展之道。
注 释:
[1] 陈华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三联书店,1989年。
[3] 曹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4] 孙红侠:《桃李不言 一代宗师——王瑶卿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 陈沛照:《主体性缺失: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 杨民康:《论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广义性特征——兼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狭义性和广义性》,《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
[7]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8] 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
[9] 乔清举:《回归仁的本真存在:一个基于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创新思考》,《云梦学刊》,2017年第2期。
[10] 刘吉平:《基因传承:“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态保护》,《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1] 邱正文、刘建荣:《农民协会活跃农村文化——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新农村建设调研》,《学术论坛》,2011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