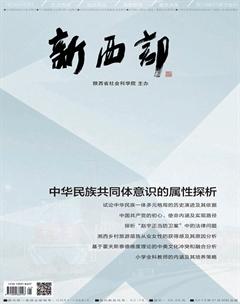论社会转型视角下公共意识的缺失与重构
【摘 要】 本文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两部著作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公共意识的缺失与重构问题。认为,公共意识的重构无论在经济发展到何种地步时,其重要性都不应该被忽视。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以及如何平衡处理人事的能力与处理技术的能力。
【关键词】 社会转型;公共意识;缺失与重构
每一次科技的发展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大进步,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愈发凸显,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还是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将对我们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精神文明产生重大冲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从协作的社会转向合作的社会,[1]在工业社会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是对于二者的辩证统一我们也是不可否认的,究其本质二者的关系就在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当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味的借助社会科技进步带来的先进技术追求个人利益,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个人资本的过度积累,必然会导致其信仰的缺失,忽视社会群体的利益,漠视社会普遍价值道德,将“披在身上一件可以随时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变成“禁锢自己的牢笼”。[2]
一、现实诱因: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
自二十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相继展开,社会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使复杂性和多元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认为风险在当今社会中随处可见,[3]而这些“风险”也正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从个人到社会包含多个不同的层面。正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样,社会普遍大环境的变化将会直接在人们的个人生活中加以体现出来,从某个人的价值观念也将窥探出社会整体的道德精神取向,社会的转型变化必然会对个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这些将会通过个体行动表现出来。
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必然經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这几个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阶段,其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相较于商业高度的自由流动性,农业则发挥着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在传统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大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人们仅仅追求使最基础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满足。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科学技术的更新完善,人们对于新事物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强,那些已经掌握绝大多数财富的人甚至会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财富以弥补自身在政治领域的不足。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层面时,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作,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加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社会分化加剧,业缘关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4]这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在冲击着基本的价值观念,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利他主义必然会有所褪色,转化为理性的利己主义。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在给人们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使人们的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在财富的冲击下,传统的真善美被弃置一旁,信仰缺失现象屡见不鲜,正如卢梭所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上边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5]
二、公共意识缺失的体现:韦伯与梅奥的反思
公共意识的形成是在社会长时间培养下慢慢积累而成的,是物质积累到一定层次在个人思想中的反映,是社会物质保障、上层建筑和公民参与多方互动的产物,大致上包括公共规范意识、公共利益意识、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6]对于公共意识的概念,学界莫衷一是,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概念,目前的主流观点是陈付龙、叶启绩所提出的“一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拥有的意识,二是指独立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三是指人们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认识和行为的自觉性”。[7]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的主流思想与国外哈贝马斯对公共意识范围的界定具有一致性,他认为“公共领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而言的,[8]公共意识只能出现于公共领域之中。在本文中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组织,并从公共规范意识、公共利益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三个维度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进行详细论述,并提出对现实的思考。
1、资本主义下的公共规范意识缺失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主要体现一种公共规范意识的缺失,由于经济的发展淡化了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作用。韦伯以问题为切入点,将聚焦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即规范意识如何从有到无。在路德提出的“天职”观中,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必须实现上帝的安排,在世俗活动中得到拯救;而加尔文宗用“恩宠预定论”取代了传统的“恩宠普遍主义”,[9]同样通过上帝的意志对人们的世俗活动加以规范,企业家和个人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劳动来获得财富。但是财富本就是极大的危险,具有永无休止的诱惑,[10]只有当个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对自己贪图享乐的欲望加以遏制的时候,它才能是符合道德要求的。[11]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做法极大的肯定了企业家获利正当性,当限制消费与获利活动目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出现信仰危机,产生抛弃旧理想的倾向。[12]宗教伦理对人们的约束和规范力量逐渐丧失,手段和目标的异化促使人们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最终使其成为禁锢个人的“铁笼”。 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依靠机器生产,已经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13]当初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精神变为纯粹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2、工业文明中的公共参与意识缺失
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同,梅奥在《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谈到的社会问题体现为公共参与意识的缺失,将焦点转至工业化所产生的结果,即在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中导致人性的冷漠。与定型社会中技术能力和人事能力的平衡相比,变动社会中的人事能力显然低于技术能力,因此变动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不愉快的人数量增加,社会团体的合作水平下降,工业化的进步破坏了历史形成的个人和社会的联系。[14]通过班克·威林观察室的实验对传统经济学理性自利人的假设予以否定,人们想要与同伴交往的本能很容易超过单纯的个人利益和逻辑思考,[15]在社会未解体的条件下,人们显然不是自利的,组织环境中的个人有参与合作的意识,只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被忽视掉了。为了证明这一初步发现,随后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管理者为了适应工业化的变化将标准化操作流程引入生产,通过物质刺激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却忽视了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员工没有自己的价值偏好,成为非人格化的生产工具;而员工则更为重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总是谈及自己的家庭和教会中的事情,[16]甚至因为要离开日常相处的同事和伙伴而拒绝提升。[17]管理者可以通过规章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员工对管理者的不满则通过缺勤、转业、发脾气外化表现出来,正如“昆厂劳工”例子中员工通过摔碗和对所供应的食物不满而表现,[18]这些都说明了忽视团体合作,缺乏参与意识的做法是存在局限的。
3、公共利益意识的弱化
无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反映的公共规范意识的缺失还是《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中体现的公共参与意识,究其本质均表现为公共利益意识的缺失。公共利益是现代公共管理的行为基础,[19]公共利益在宏观方面表现为实现更大范围内人民的利益,微观层面则指公平效率等,[20]与私人利益相对它具有公共性,但是在工业化程度逐渐加强、工具理性占据上风的当下,人们往往更重视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当传统新教伦理所提倡的理性的财富观出现歪曲时,原本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褪去剩下的世俗社会对财富的狂热追求,通过勤奋、节俭等美德获利的手段也随之不复存在。机器大生产使得个人普遍追求巨额财富,天职责任的观念也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联系,[21]每个人都仅仅成为获取财富的机器,虽然个人的财富得以积累,但是却导致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铁笼之中。工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处理技术的能力远远高于处理人事的能力时,就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不够,参与合作的意识缺乏,技术能力的增长甚至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组织来讲,员工之间不能很好的交流合作,情绪性缺勤转业现象频发,那么即使管理者通过高额的物质进行激励,也难以提高团队整体的效率,必然会使企业的利益受损。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宗教伦理规范的弱化和合作参与的淡薄都会损害公共利益的形成与积累。
三、社会发展走向何处:公共意识的重构及其反思
韦伯与梅奥都对工业社会中道德价值的丧失与人性的冷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毫无疑问,他们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价值信仰的淡漠确实是当下社会的现状也值得我们反思,但是他们二者对于社会未来的走向却持不同的态度,相较于梅奥,韦伯更为消极,他认为未来人们将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铁笼”中,而梅奥则认为应该通过有效的合作,要唤醒人们心中的合作参与意识,进而使我们处理人事的能力与处理技术的能力齐头并进。[22]在本人看来,更为赞同梅奥积极的态度,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会经历不同的时期,而在不同的时期中也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以及如何平衡处理人事的能力与处理技术的能力。
谈及各种公共意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人类历代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对价值规范的塑造以及信任合作行为,这也就说明我们曾经能够很好的协调经济与文化、人事与技术的关系,但是终究还是机器的生产在人的心中蒙上了黑纱。毫无疑问,我们对韦伯和梅奥所揭露的社会现实是痛心的,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宗教伦理对人的规范作用还是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都是当下应该学习改进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感到庆幸,前人已经准确的预见了社会的危机,也为此类危机的解决提出了大致方向,我们只需在充分认识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此加以改正即可,重塑人们心中的信任与合作。虽说我国所提倡的勤劳、敬业、合作等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工业文明”的孕育环境不同,其内在的价值目标也不相同,[23]但所包含的本质含义却大相径庭,而且在经济与财富的冲击下,这些精神意识正在逐渐被忽视,它们的发展前途具有一致性,公共意识的重构无论在经济发展到何种地步时,其重要性都不应该被忽视。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J].甘肃社会科学,2013(01)5-11.
[2]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2.142.
[3] 张康之.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生活[J].人文杂志,2018(08)110-118.
[4] 郑杭生.社会学新修精编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
[6]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公共意识/1067806? fr=a laddin.
[7] 陈付龙,叶启绩.民主模式、公共生活与公共意识[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01)81-85.
[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 张云平,刘建华.“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探析——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理论界,2014.05.83-85.
[10][11][12][13][2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22,127,135-136.142.142.
[14][15][16][17][18] 梅奥.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M].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64.21-22,57,89,92,94,133.
[19] 蓝志勇.公共利益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核心[J].中国行政管理,2006(06)21-22.
[20] 李玲玲,梁疏影.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邏辑起点[J].行政论坛,2018(04)70-75.
[23] 陈春萍,张志兵.韦伯“新教伦理”的实质探究与当代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63-67.
【作者简介】
赵梦涵(1997.12—)女,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