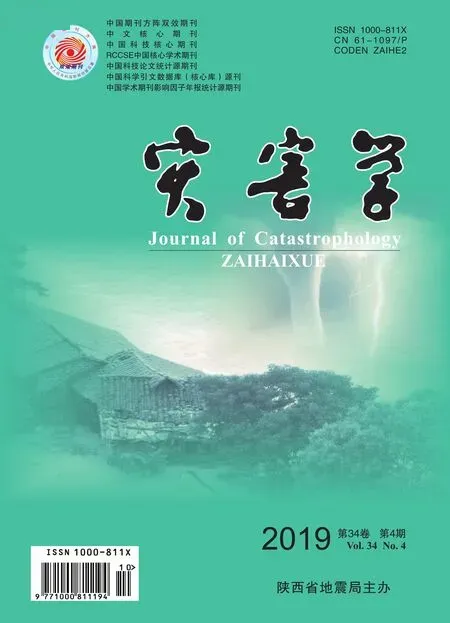风险元理论研究*
唐彦东,于 汐,李潇昂,乐怡筝
(防灾科技学院 应急管理学院 灾害风险管理中心,河北 三河065201)
在风险研究领域,围绕风险概念和认知引发了许多争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术界对于建构风险理论所持有的基本立场不同。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原有风险理论研究的范围,需要从更高层次的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风险理论。元理论(metatheory)由前缀meta和理论(theory)两个词构成,其构词方法源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一词汇。后来,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将“meta”与数学(mathematics)相连,创造出元数学(metamathematics)一词。自此以后,通过在学科、术语或名词前加前缀“meta”构成的新学科、新术语或新名词不断涌现,如元理论(metatheory)、元研究(metaresearch)元哲学(metaphilosophy)、元科学(metascience)、元化学(metachemistry)、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等等。“meta”可以加在某一学科名称之前形成一个与该学科相关的另一新学科,也可以加到某个一般名词之前而构成一个新名词[1]。
本文风险元理论揭示的是建构风险理论所秉承的基本信念、观点和立场[2]。开展风险的元理论研究,探索建立风险科学的元理论,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梳理,总结风险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现状,对风险理论自身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诸如研究对象、性质、起源、结构和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审视和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风险元理论是对风险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和再总结,是对风险理论的超越和提升,这对于从更高层面研究和解释现代社会经济面临的灾害风险、安全风险问题。
1 风险的种类
人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理解,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上存在不同类型的风险,这些风险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些客观现实,只是由于人们的同意或认可才成为事实,或者说,存在着一些由于我们相信其存在而存在的事物[3]。著名的托马斯公理指出,如果人们把某种状况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把这一理论应用到风险领域则成为,如果人们把风险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货币即是这类事实的典型例子。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是由于人类的货币制度保证其存在。与此相类似,风险领域也存在着至少部分人相信其存在而存在的风险,如不吉利的数字,不好的习俗。这类风险在本体论上具有主观性质,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我们把这类依赖于社会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条件而存在的风险称为虚拟风险。虚拟风险还包括社会禁忌和宗教禁忌等等。与虚拟风险相对应,还存在一些不依赖于社会条件而存在的风险,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风险。这类风险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观察者的价值观、态度等无关,不依赖于社会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在本体论上具有客观性,本文把这类风险定义为现实风险。
现代社会中,现实风险和虚拟风险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晰。人类社会在创造未来的社会实践中,为特定功能开发出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产品,如核技术、纳米技术、转基因生物等,这些技术产品也产生大量超过我们感知能力而认知的风险。这些风险在未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表现出实际损害之前,一直笼罩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不是一种可视的存在。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和增强抗病害虫能力,但部分人群相信转基因技术及食品具有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若未来科学能够证明不存在这种风险,则这种风险是一种虚拟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反之,若未来科学证明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则这种风险为现实风险。此外,有些风险认知可能既包括现实风险,也包括虚拟风险。统计数字表明,乘坐飞机比乘坐公交更加安全,但一些人依然认为乘坐飞机具有更高的安全风险,从而选择购买航空意外险,而对于购买公共交通意外险具有较低的意愿。一方面,飞机失事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现实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因素或社会环境造成的高估的那部分风险,具有建构性质,则属于虚拟风险。
2 风险元理论
哲学探讨的是人类知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充当着元理论的角色[4]。元理论内涵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逻辑)三个层面[5],本文更多涉及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风险元理论是关于风险理论的理论,是从哲学层面思考风险理论的根基。
2.1 实在论和建构论风险观概述
关于风险最大的争议可能是风险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或者说风险是实在的还是建构的。探讨实在论和建构论风险观,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风险观,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风险观。
本体论关于“是”本身,即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在本体论意义上,实在论和建构论是指实在的属性,研究的是实在的存在方式。如果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它是否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否意识或者认识了它,风险都是客观的,则对风险持有实在论立场。风险实在论认为风险的存在不依赖于内心感知或者经验判断,关于风险的认识建立在风险的客观存在性的基础上。实在论风险观的核心是风险不依赖于认识而客观存在,如果否定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则可能持反实在论立场、建构论立场,或者走上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道路[6]。与实在论把风险视为客观实在物的观点相反,建构论认为风险不是客观实在物,是由实践主体建构的认知判断,是由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社会建构物。建构论强调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风险。建构论者坚信所有知识都是主观的和再解释的,世界是我们所解释的世界,故风险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人的经验、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纯粹的客观实在。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或知识)的学说,是关于认识的本质和产生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认识论意义上的风险观反映的是风险判断的基本属性。若判断的真假不能得到客观的证明,则经常会认为该判断是主观的或建构的,因为判断的真假不单纯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依赖于陈述者的态度、情感和观点。“地震比洪水更可怕”这一判断是主观建构的。与此相对应,“昨天凌晨该地区发生了地震”则是客观性的判断。对于这样的客观性判断来说,评价其真假是不依赖于任何人对它们的价值判断和态度。认识论层面上,完全的客观性是很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的观察总是从某种视角出发,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并且处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
2.2 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风险观的组合
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实在论和建构论并没有对应关系,如本体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并不一定对应认识实在论,可以对本体论上的客观实在在认识论上做出主观的陈述。如在本体意义上,地震是客观的,因为地震的存在方式不依赖于任何感知者,而对地震的恐惧是主观的存在物,它的存在方式取决于主体的感觉。本体论上是主观的实在可以作认识论上客观的陈述。例如,“地震比洪水更加可怕”,这个陈述是关于本体论上客观的存在物的陈述,但对这一客观实在做出了主观的判断。
本体论研究的是实在的属性,认识论研究的是判断的属性,根据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属性,存在四种可能的组合。各种风险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划分详见图1。

图1 各种风险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划分
第一种组合是本体实在论和认识实在论。“昨天凌晨该地区发生了地震”这一描述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表现为实在论。在各种描述风险现象的形式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表现的朴素实在论视角[7]。在工程学、统计学、精算学等科技领域中,认为风险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为危害的可能性和后果,可以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客观地监测和计量风险,人们较多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识别和评估风险、风险的严重程度和评估结果的精度。在技术背景下,往往采用概率方法来刻画风险,风险被描述为期望损失。尽管持有这种观点的科技人员承认,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但依然倾向于把概率风险评估结果看成是真实和客观的。风险分析技术方法能够以合乎逻辑或者符合经验的方式评估预期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环境破坏情况,可以为决策者制定风险政策提供依据和标准,但依然受到社会科学的严厉批评。社会科学认为,技术方法对于工程决策也许是适合的,但不适合社会决策,它忽略了政治维度和伦理维度。当风险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单凭技术手段的解决方案就会力不从心[8]。忽视分析者所持有的价值观也是科技方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此外,概率方法也不是表示不确定性的完美方法。利用损失程度乘以概率来确定期望值实际上赋予这两个变量相同的权重,意味着当期望值相同时,小概率高损失与大概率低损失风险事件没有区别。然而,人们对这两类事件的偏好显著不同,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具有更大的威胁。
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技术或自然科学领域比较接近。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经济学研究中把破坏或不希望的结果转化为经济学中的效用。经济学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损害期望值的效用不等于期望效用,即人们并不根据期望值进行决策,而是根据期望效用进行决策。把期望损失转换成期望效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主观的满足感可以衡量所有类型的结果,包括象征性的、心理或社会影响;二是采用效用替代损失或破坏,个人可以根据满足程度进行主观衡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能回答“怎样的安全才是安全”这一问题。风险的经济学概念提供了2个主要的选择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若风险带来的收益的效用多于减少的效用,则风险是可接受的;二是在收益相同的备选方案中选择风险最低的方案。
第二种组合是本体实在论和认识建构论。“地震比洪水更可怕”,这一描述对客观实在的地震和洪水进行了主观的判断,持有本体实在论和认识建构论观点。Rosa[9]等认为,风险是世界的一种状态,在本体论上是一种不依赖于认识的客观实在,而在认识论上可以持有实在论或者建构论的观点,这依赖于知识主张的证据基础,认识风险是社会化的过程,因此,风险是科学实在与社会建构的混合物。Rosa[10, 11]提出分层次认识论-本体实在论(hierarchical epistemology-realist ontology)理论框架。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属于这一类别。批判理论认为,任何“事实”都经由了人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主观性、相对性和价值判断。批判理论把风险视为一种真实的现象。对于观察者来说,这些真实的风险并不总是显而易见,需要社会的集体话语来重新建构。
在本体论意义上,风险社会理论位于从实在论到建构论较大的变化范围之内。贝克[12]没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认识自己的风险社会理论,宣称自己既是实在论者又是建构论者。贝克[12]强调技术性风险,风险就是损害或危险的同义词,主张现代化的风险是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的不可逆转的威胁,是现代性的后果和本质,因此对风险更多地持有实在论观点,认为风险的实在性源于不断发展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拉什[13]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实在论范式,尽管并非如此简单。贝克[12]的风险社会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建构论倾向,他指出风险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明显界限的消失可以决定它的特性。因此,当我们说到自然时,我们却说的是文化;同样,当我们谈论文化时,我们也在谈论自然。吉登斯[14]则更多持有建构论立场,其风险社会理论侧重于制度性风险。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各个国家力图通过建立各种制度来防范风险,但另一方面,这些建立起来的制度本身反过来又成为风险的源头,制造出了新的风险。在认识论层面上,风险社会理论强调调解风险认识和感知的社会文化进程,表现出温和的社会建构论立场。
第三种组合为本体建构论和认识实在论
可以对主观的存在做出客观的判断,如地震以后我的恐惧感正在慢慢缓解。恐惧这一现象本身具有主观的存在方式,但这个陈述却表明一个主观认识上的客观事实,判断该陈述为真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第四种组合为本体建构论和认识建构论
我们没有必要对地震过度恐慌,该判断对主观存在方式的恐慌进行了主观的判断,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属于建构论。风险的系统理论、文化理论和治理理论都属于这种类型。
系统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持有温和的建构论立场。系统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为代表。系统理论没有把风险作为研究的客体,而是把它作为分析社会系统的工具、方法或者理论视角。根据系统理论,人类社会由自我指涉和自我再生的子系统构成。系统理论把风险理解为社会建构物,与社会子系统的特定理性有关。卢曼[15]并不否认被观察事物的存在,但他认为,风险更重要的不是一个客体或者事实,而是一种感觉或理解的形式,事件和损失具有时间上的偶然性而不是事实。卢曼[15]并不否认系统有可能产生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但他指出,每一个观察者都会受到社会系统的限制。
风险文化理论以道格拉斯、维达夫斯基和拉什为代表[16]。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危险已经达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危险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道格拉斯[16]把风险看成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危险进行的社会建构的解释和响应,认为风险概念本身是假设性和比喻性的,风险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人为色彩的创造物和思考方式。风险文化理论在本体论上持有温和的建构论立场,并且他的许多著作都试图解释某些危险被确认为风险而其他未被认为是风险的原因,认为不同的文化对风险进行选择,是由于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文化偏好,显示出特定的集体文化、信仰和价值,它们都是集体意识的反映[16]。风险判断是政治、道德和审美的过程。
福柯[17]的治理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持有激进的建构论立场。治理理论没有对风险主题给与特别的关注,但一些学者已经应用福柯的理念将风险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进行分析。治理理论认为,现实中不存在风险,风险本身的性质并不重要,治理性是社会监管和控制的方法。治理理论把风险与权力相联系,认为风险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和工具,是维持理性秩序而与知识合谋建构的结果。
3 风险理论连续统一体
把理解风险划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两种不同的视角,是一种传统的二元思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是对复杂世界的简单分解[18]。关于风险概念和理论的诸多争议就源于实在论和建构论的二元划分。风险理论连续统一体是把风险理解为连续变化的分布带,该理论的一端是实在论,另一端则是建构论,基于不同的观点,人们对风险的理解分布在从实在论到建构论的范围之中。风险理论连续统一体超越了实在论风险观和建构论风险观的二元困境。风险理论连续统一体意味着,尽管实在论和建构论两极根本不同,但理论连续统一体的每一部分与相连的部分没有显著不同。描述风险有多种视角,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以实在论和建构论为两极的连续统一体。
4 结语与讨论
在本体论立场上,风险理论表现为从激进实在论、温和实在论、温和建构论到激进建构论的连续变化。如果认为风险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现实,并且可以对风险完全进行客观的描述,则对风险持有激进实在论立场,风险分析的技术方法接近于激进实在论。若承认风险是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认为风险可以通过理性计算进行评估,然后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进行调解、感知和应对,则对风险持有温和的实在论立场,如理性选择理论和批判理论。温和的建构论认为,风险是客观的损害、威胁或危险,必然要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被调解,并且一旦脱离这些过程就无法被理解,系统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属于温和的建构论。激进建构论以治理理论为代表,认为没有什么事物在本质上是风险,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风险,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风险。
在认识论上,风险理论也表现为相似的连续变化。如果认为可以产生完全客观的风险知识,进而对风险可以进行完全客观的判断,则对风险持有激进实在论观点。在认识论上,风险分析的技术方法也接近于激进实在论;若认为认识风险会受到个人或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依然可以做出相对客观的风险认识,则对风险持有温和的实在论观点,如理性选择理论。依据知识的功能是主体适应于经验世界的组织,还是对本体论的客观实在的反映,建构论有激进建构论和温和建构论之分。离人类是创造者一端越近就越激进,离这一端越远,就越温和,到达一定界限时就不再属于建构论。激进建构论认为,现实不是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的经验世界,即我们所创造的世界[19]。在他们看来,独立的实在观念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抽象。没有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客观的、可理解与可把握的实在。客观实在是不可及的,我们对它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由人创造的,并仅仅主观地存在于人的大脑中,风险知识不能反映真实的风险,而更多的是风险的概念和思想。风险治理理论在认识论上持有激进建构论立场[19]。温和建构论则在主张主体的建构作用的同时,也承认知识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的一面,如风险系统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