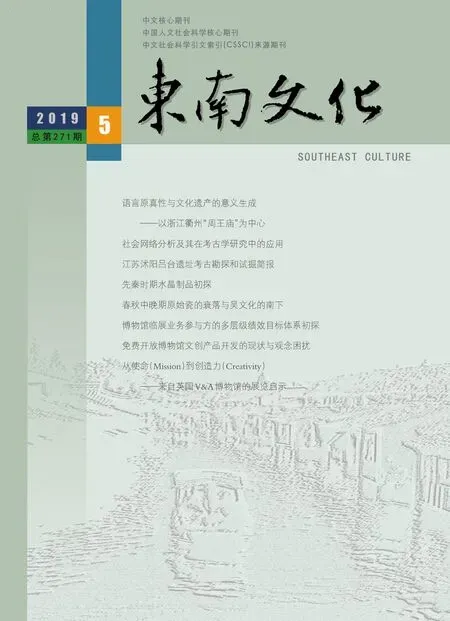镇江博物馆藏吴国早中期青铜容器的铸造工艺研究
田建花 张 剑 李 军
(1.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2.镇江博物馆 江苏镇江)
内容提要:镇江博物馆藏部分吴国早中期青铜容器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显著特征:存在浑铸且壁范垂直二分、直接在外范制纹和不设盲芯。吴国早中期,青铜器制作技术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技术的原始性和地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制和纹饰,形成了吴国青铜器鲜明的地方风格。
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江南吴国青铜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支。江苏宁镇地区作为吴文化最为重要的分布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土了大量吴国青铜器,丹徒烟墩山[1]、丹徒大港母子墩[2]、溧水乌山一、二号墓[3]、仪征破山口[4]和丹阳司徒窖藏[5]等都是典型器群和遗址。吴国青铜器既受到了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又融合了本地地域文化的特色,因而在其制作工艺方面也有着区别于中原与其他区系的一些特征。肖梦龙先生将吴文化的冶铸分为四个阶段:先吴、吴国前期、中期及后期[6]。本文将着眼于制作工艺探讨吴国早中期青铜器的相关铸造特征。
制作工艺考察主要是通过对器物上遗留的工艺痕迹(如浇注成形时遗留的范线、浇口或冒口痕迹、主附件的叠压关系,以及铸后加工痕迹等)的观察,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吴国青铜容器的铸造方法、铸型组合、芯撑设置、浇注位置等铸造工艺环节,以及补缀、修整、打磨、抛光等铸后加工过程,进行初步的判断和复原。
吴国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7],本次研究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专门针对早中期青铜容器,进行深入补充和细化研究。考察对象均为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器,亦属于保护修复的前期研究工作[8]。
一、典型器类的铸造工艺
1.鼎的铸造工艺
郭宝钧先生在研究器物的器型和制法时,曾将商代鼎类器的形制和铸法总结为两大类。二里岗时期的鼎形制多为“小耳、深腹、短锥足,底部圆形或分裆形,锥足多空。耳足分配,一般都是四点配列式,即一个足在一个鼎耳的垂直线下,其他两足,分列在另一鼎耳垂直线下的两侧”,铸法采用“三壁范过足包底铸法,即只有壁范三块,并无另外一块三角形的底范,它的底范实际上系由三块壁范的下边延伸部分,包折到鼎底中心,来代替三角形底范”。而到晚商时期,形制以“直耳、柱足、深腹、圜底的形式为主流。耳足配列为五点式,有两足在两耳连线的一侧,另一足在两耳连线另一侧的正中”,主流铸法是“壁范三块,分应三足相接,底范三角形,由侧边榫卯和三壁范扣合,由壁范负担重量,使底范悬空组成”[9]。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焊接、铸接、铆接等连接技术大量运用前,鼎的主流铸法仍承晚商。
吴国早中期青铜容器铸法往往有异于同时代主流铸法,结合形制,根据铸型组合方式的不同,青铜鼎的铸造工艺可分为二类。
(1)耳足四点配列式,壁范二分
以14393(丹司︰4)和14397(丹司︰8)鼎为代表。
两鼎形制基本相同,折沿,附耳,圜底,短锥足或柱足,足实心,器腹有两道弦纹,耳足呈四点配列(图一︰1)。观察工艺痕迹,其范线比较特别,整个器壁只在两耳之间腹壁中线处有两条垂直范线,如果将三足分别标记为足Ⅰ、Ⅱ和Ⅲ,则两垂直范线在上腹处为直线,延伸至下腹近底处分别折向足Ⅰ和足Ⅱ(图一︰2、3),与此两足外侧中部的范线相接。底部存有三角形范线。根据范线推断,铸型应是二壁范(二壁范衔接线类范线,不是完全垂直),一三角形底范和一芯范。这类鼎耳、足对应形式类商早期的情况,是耳足四点配列式,足Ⅰ和足Ⅱ在一耳垂直线的两侧,足Ⅲ对应另外一耳。但是壁范纵向二分且不规范、有底范的设置不同于早商,早商大部分情况是壁范垂直三分,无底范,采用“壁范过足包底铸法”。
14397(丹司︰8)鼎与14393(丹司︰4)鼎虽形制和基本铸法大体一致,但对足Ⅲ的处理有所不同。14397(丹司︰8)的足Ⅰ和足Ⅱ是和器体同一铸造单元浇铸而成,足Ⅲ是补铸的。器整体都磨砺过,表面很光滑,应是磨过后才补铸足Ⅲ的,因为补铸块包裹的器体部位是被磨砺过的,而如果补铸了再磨砺的话,补铸块边缘的器体则无法磨砺到位。另外,足内面对应位置也可看到相应的补铸痕迹。14393(丹司︰4)的足Ⅲ并非后补铸的,而是利用二分壁范和和三角形底范一次浑铸而成。
14393(丹司︰4)鼎和14397(丹司︰8)鼎的足Ⅲ均对应一耳,类商早期的情况。对于三足圆形器,在尽量减少块范的情况下,为了脱范(脱模)方便,必须考虑到耳、足的位置和设置,所以沿用了商早期耳、足的对应关系,因此两耳分别置于二块壁范的正中,型腔由壁范和芯范形成;对应耳的足Ⅲ包于一壁范,足Ⅰ和足Ⅱ包于另一壁范。14393(丹司︰4)鼎的足Ⅲ有两条范线,由其中一壁范和底范形成的,14397(丹司︰8)鼎足Ⅲ是另外补铸的,范线与壁范和底范无关;两鼎的足Ⅰ和足Ⅱ上都有三条范线,由底范和两块壁范共同形成。因为壁范二分且包足,芯范不易控制,器壁厚薄不均,总体器壁较厚,个别地方较薄。
14393(丹司︰4)两侧对称位置有两孔,疑为原垫片位置。浇口和冒口应在三角形底范和壁范的范缝处。
(2)耳足五点配列式,壁范垂直三分
以14390(丹司︰1)、14392(丹司︰3)、14394(丹司︰5)、14396(丹司︰7)、14399(丹司︰10)鼎为代表。
之所以依据耳足配列方式分类,是因为不同的耳足配列方式往往体现着不同的铸型设计。14390(丹司︰1)的器型与14393(丹司︰4)和14397(丹司︰8)基本相同,仅尺寸较大,但耳足配列关系是“五点配列式”,因此其铸型与14393(丹司︰4)和14397(丹司︰8)完全不同,而与14396(丹司︰7)、14394(丹司︰5)、14399(丹司︰10)和14392(丹司︰3)相同。遗留铸造痕迹均是三条垂直范线分别对应三足,且与足外侧范线连成一直线,底部有三角形范线,因此铸型应是壁范垂直三分,另有一块三角形底范。
14396(丹司︰7)和14394(丹司︰5)均蹄足,半球形腹。前者沿耳足有兽面,后者附耳足上无兽面。但两鼎均是耳足五点式配列,郭宝钧先生曾谈到,这种基本形制是沿袭西周后期鼎形来的[10]。因工艺不够成熟的原因,足的芯范并非盲芯,是和底范一体的,所以造成的效果是,足的横截面是非闭合圆环(图二)。器腹纹饰应是在外范上刻划阴文,后浇铸形成。器体外表面被磨砺过,非常光滑,但底部三角形范线区域内和内表面都不曾磨砺。虽然进行过表面后加工,但仍能分辨出壁范三分的范线。浇口和冒口在底范和壁范相接的范线处。
14392(丹司︰3)、14394(丹司︰5)、14396(丹司︰7)、14399(丹司︰10)鼎的足均无盲芯,采用与底范相连的小芯范,因为芯范设置随意,每个芯范大小和形状不同,所以足的壁厚和形状也差异明显。14396(丹司︰7)鼎的芯范相对足而言较大,于底范相接部位较小,因此足壁较薄,还有大部分芯范存于足中;14394(丹司︰5)鼎和14399(丹司︰10)鼎的足芯范较小,于底范相接处较大,所以其足壁很厚,截面近四分之三月形;14392(丹司︰3)鼎足的芯范相对较大,与底范相接处也较大,其足壁较薄,足的横截面为半环形。
2.簋的铸造工艺
纵观商周时期的簋,壁范多四分。但是吴国的簋,如15040(3︰1266)百乳簋、14407(丹司︰12)簋、14402(丹司︰13)簋和14404(丹司︰15)簋等,壁范设置较为特别,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域出土的簋差异显著。
15040(3︰1266)百乳簋,侈口,束颈,腹较鼓,圈足有较高直裙,双兽耳有钩形小珥。腹饰斜方格底的乳钉纹,乳钉小而密集,乳突平坦,且行列稍有歪斜,与口沿及颈部纹带不平行。地纹为菱形纹,颈腹间一条圈点纹边饰,与腹部乳钉纹同属于圆形类纹饰,两者同施一器,互相呼应。该器在形制、纹饰上皆与中原西周早期器相近,但又稍有区别,中原器一般乳突长而尖,以云雷纹为地纹。故该器应是一件具有地方风格的仿铸器。在簋耳中线及其上下相接的颈部和腹壁处,均可看到明显的连续的范线痕迹,耳内部对应位置亦有范线;而在两耳之间的腹壁处,却观察不到任何分范痕迹(图三),所以此器壁范应是沿簋耳二分的,并且在两壁范相接处分别修凿簋耳轮廓纹饰,留出其空间,不设盲芯,使簋耳与器体浑铸而成。器体纹饰均是阳纹,菱形底纹的高低和宽窄参差不齐,乳钉亦有大有小,排列也不规整,其应是直接在外范上刻凿和修整形成的,并非由中原地区常见的模印法所形成。器体外表面无纹饰处和口沿处都进行过磨砺,纹饰处未经处理。圈足上有两个铸疮,浇口和冒口应是设于圈足处。颈部两耳上方有补铸痕迹,底部也有。
14407(丹司︰12)、14402(丹司︰13)和14404(丹司︰15)簋形制大体相似,大小和细部略有不同。三器均为典型的南方青铜簋,侈口,束颈,腹较鼓,圈足。铸造工艺类15040(3︰1266)百乳簋,均是壁范沿耳二分,一底范,一芯范,浇冒口在圈足处。
3.尊的铸造工艺
尊在中原地区盛行于商和西周,春秋战国时少见。吴国境内的情况有所不同,不但西周常见,当西周晚期后,尊类器在中原大地渐渐退出舞台时,吴地的尊则以新的面貌展现出独特的风姿,具体表现为器形增大,腹部更加扁鼓、膨出,饰纹也更为繁缛。吴地尊的铸造工艺也有其自身的特色。以14407(丹司︰18)和14409(丹司︰20)两件棘刺纹尊为例来说明。
两尊皆为侈口、高圈足、扁鼓腹,颈、足饰密集的锯齿纹、几何纹,腹饰带有纤细而密集的棘刺纹,颈、腹、足间界以圈点纹。这种腹部扁鼓、饰纹独特的三段式棘刺纹尊在当时属于吴境的上海松江[11]、安徽屯溪[12]、江苏武进淹城[13]等地均有发现,另其器型亦见于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14],其密集的锯齿纹等纹饰特色亦见于广西恭城地区[15],迥异于中原商周青铜器而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
两尊器体无纹饰处已磨砺处理过,所以口沿和圈足上均看不到范线痕迹,但在颈部和腹部的纹饰带中可看到两条相对应的垂直范线,所以壁范纵向应是二分无疑。值得注意的是,14407(丹司︰18)在颈腹相接处整齐地断裂为两部分,几乎呈水平面断裂,颈部断茬非常平整,近乎于铸造面(图四),腹部却相对参差,所以推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其上段(口颈部分)先铸,中下段(腹部和圈足)铸造时,通过嵌铸方式将上段与中下段连为一体。这样就能理解为何会出现此种断裂,并形成这样的断面。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在其他尊上发现此种分铸和嵌铸连接痕迹,所以是否偶然现象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型范设置和铸造质量,此类多段式的尊如果不是分铸,则一般都存在水平分范。
两尊纹饰均阳纹,且不规整,应是直接在外范作纹所致。
4.盘的铸造工艺
以13760(水乌岗M2︰3)盘、6812(3︰270)盘(申子墩出土)和14410(丹司︰21)盘为例来说明。
13760(水乌岗M2︰3)盘,大口浅腹,圈足附耳,耳很薄,不设盲芯。两耳之间的器壁正中有两条垂直范线,其壁范应二分。二附耳分别在两壁范的正中,耳对应的腹壁部分无纹饰,有与耳尺寸相同的方形范线,说明耳的型腔是直接在外范上形成的,芯范和外范之间设有一楔形块,使附耳仅底端和器壁相连。另外,此盘耳与器壁之间有一水平方向的铜梗(图五),将二者连接起来。此铜梗并非装饰需求,而是泥范分型铸造的产物,即在楔形泥块上设置一水平方向的孔洞所导致,这一孔洞最重要的作用是增加浇道,以防附耳产生浇不足现象。同样,盘器壁纹饰并无完全一致的单元块,应是在外范上直接制作形成的。综上所述,其铸型应是二壁范,一圆形底范,二耳部楔形块和一芯范。
6812(3︰270)盘和14410(丹司︰21)盘的形制同13760(水乌岗M2︰3)盘,纹饰有差异。工艺也同13760(水乌岗M2︰3)盘,但缺少连接耳与腹壁的铜梗。
5.卣的铸造工艺
以13759(水乌岗M2︰2)卣为例,此卣盖已缺失,卣口沿和腹部截面均呈椭圆形,腹下垂且鼓,圈足有直裙,提梁两端为直角羊首,颈部有凸弦纹和圈点纹,圈足上方有两周圈点纹。卣的提梁和主体一般而言都是分铸的。卣体正面不见垂直范线,环耳处垂直方向有对称范线(图六),因此器体壁范应是垂直方向沿环耳二分,另有一底范,一芯范。器物底部有一道铸疮,疑为浇冒口。推测其制作顺序是:先铸好器身及环耳,在环耳周围裹泥并修制成兽首之芯范,芯范在环耳中心的部位需要穿凿一水平方向的孔洞,作为提梁底端穿过环耳之横梁的型腔,再将提梁和羊首型范置于相应的位置处,并使其型腔与横梁的型腔相通,这样铸造好提梁和羊首的同时,也将提梁与器体连接在一起。
另外,在提梁中部可看到铸接痕迹,说明提梁是分两半分别铸造的,这可能是为了使提梁和腹部的连接更容易完成。
6.甗的铸造工艺
以17400(大青M1︰1)甗为例,此甗两绳纹耳外撇,圜底,短蹄足,颈部饰方雷纹和弦纹。壁范垂直三分,三角形底范,但器壁范线并不对应足,三范线都在相邻两足的中间位置(图七)。两耳置于其中的二壁范中,但不在壁范中间,而是比较靠近范线。器壁不曾磨砺,所以并不光滑。就器型来看,此类甗的型范设置除了垂直分范,可能也存在着水平分范。
7.鬲的铸造工艺
以16082(丹港︰7)雷纹鬲为例,此鬲平折沿,沿耳直立,口沿下饰两周方雷纹和一周凸弦纹。腹壁较直,腹下分裆,成三袋足。器壁三条垂直范线直通足底(图八),说明壁范三分应三袋足,另有三角形底范,一芯范。此器制作粗糙,器壁很厚且不均匀。从器物内外表面及断裂面看,孔洞(砂眼)非常多。耳的内表面有纹饰,外表面无纹饰,且在耳下方、器的口沿处有一道和耳同宽的范线,推测是在芯范上直接制作耳的型腔,而不是通常的在外范上设耳范铸耳。
大部分吴国青铜容器表面都进行过磨砺处理,较为光滑齐整。此器上的范线粗且突出,似未进行修整处理。
二、与其他地区青铜器铸造工艺区别
吴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特色,在青铜器上亦是如此,铸造工艺方面与同时期其他地域铜器的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浑铸且壁范二分、直接在外范制纹和不设盲芯三个方面。
1.浑铸且壁范二分
纵观青铜时代的圆形器,尤其是三足器的型范设置方式,壁范垂直二分的工艺并不盛行,主流的仍是壁范垂直三分或四分。就目前来看,江苏仪征破山口铜器群[16]、溧水乌山墓铜器群[17]、丹徒母子墩铜器群[18]、丹阳司徒庙铜器群[19]、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群[20]以及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铜器群[21]和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墓铜器群[22]中均普遍存在壁范垂直二分的现象。前三者均是西周吴国铜器群,均属壁范垂直二分且器体与耳、足等附件浑铸的状况,后三者是战国铜器群,均属壁范垂直二分但器体与附件分铸后再铸接或焊接的状况。笔者认为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此类器的壁范垂直二分在西周时属吴地的一种工艺传统,后随着楚灭吴,在其他地域也有所使用。不同的是,随着分铸法和连接技术的成熟,壁范垂直二分与分铸法相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可铸造出更加精美的器物。
壁范垂直二分虽减少了外范数量,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不利于三足器器足的设置和浇铸,尤其是足和器体浑铸的情况下,需要简化足部的造型和纹饰,但如果分铸后再连接,则方便可行;二是纹饰制作受到制约,如果要在器物上形成阴纹,就需要从模上翻制纹饰,这对于垂直二分的壁范是很不容易成功的,因为在其脱模时,分型处的纹饰很容易损坏。相较而言,直接在外范上作阳纹更具操作性。
吴地尊多是扁鼓腹,这也与其壁范垂直二分关系密切。圆形器物若壁范垂直三分,壁范脱模时较易控制,截面容易形成较为规整的圆;壁范垂直二分,则壁范分型处容易在脱模时受损,而做成扁腹,使截面呈椭圆则可避免此种问题。
2.直接在外范制纹
吴国早中期青铜容器上的纹饰多为阳线条构成的几何纹,如梯格纹、折线纹、棘刺纹、尖叶勾连纹、矩形纹、云雷纹等,相较于中原地区庄重规整的多层浮雕装饰,吴国青铜器的纹饰更为随意。究其原因,乃直接在外范上制纹所致。而同时期中原地区则普遍使用模印法。因此,在很多器物上都可观察到直接外范制纹的特征,例如纹饰不对称,同一器物上同类纹饰大小、高低、线条粗细各不相同等。
制作阳纹,要么直接在外范上刻凿,要么使用模印法。对于无底纹的单层细线条阳纹而言,显然在外范上刻凿更加容易。模印法可节省劳动,提高效率,且器物纹饰较为规整,但是对型范制作者的技能要求较高。另外,从脱模的角度考虑,壁范垂直二分的工艺也限制了模印纹等规整纹饰的发展。吴国早中期,青铜器制作处于起始和发展阶段,技术尚不成熟,不能支持完成规整庄重的中原纹饰。所以,文化传统和技术虽源自中原,但仍有强烈的地方风格,故大体形制虽似中原,但细部不尽合拍,技术也稍显落后。
3.不设盲芯
一般而言,器物上比较厚的部位,例如耳、足、鋬等,为了防止铸造缩孔等缺陷,在铸型制作时需要内置泥芯,铸成以后,泥芯被完全包裹于器物中,不能从表面看见,故称作盲芯。盲芯技术的应用从殷墟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纵观吴国早中期本地风格器物,很少发现器物的耳、足等附件使用盲芯,这与同时代其他地域器物群有着显著区别。
不设盲芯,耳、足等附件的壁厚就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控制。所以,吴国早中期本地风格器物的附件或者薄或者小。例如,鼎多为小型立耳,立耳型腔是直接在内范上形成的,盘多为薄型附耳,附耳型腔多在外范上形成,耳和器体的型腔之间增加通道以防产生浇不足现象;又如,鼎足或者矮小,或者细长外撇,又或者横断面作外圆内空的半环状,少见厚重闭合性的足。
三、结论
总体来说,吴国早中期青铜容器在铸造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青铜容器皆浑铸,分铸技术应用不普遍;(2)纹饰多阳纹,且随意不规整,应是直接在外范上制纹所成;(3)圆器不圆,主要是壁范垂直二分的工艺造成;(4)不设盲芯,附件多薄或者小。吴国早中期,其青铜技术尚处在未使用分铸法来简化器身和附件的阶段,所以泥范的分型制作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足、耳等附件的设置,在保证浇铸成功的前提下,才考虑满足功能和审美需求。技术的积淀和提升会促进形制和纹饰的创新发展,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力状况下,尤其是区域技术的初始阶段,技术的不成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形制纹饰有所限制。
[1]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2]肖梦龙:《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3]吴大林:《江苏溧水出土的几批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3期。
[4]王志敏、韩益之:《介绍江苏仪征发现过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5]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6]肖梦龙:《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7]a.华觉明、肖梦龙、苏荣誉、贾莹:《丹阳司徒青铜器群铸造工艺》《丹徒母子墩青铜器群铸造工艺考察》,肖梦龙、刘伟主编《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b.华觉明、肖梦龙、苏荣誉、贾莹:《丹徒母子墩青铜器群铸造工艺考察》,肖梦龙、刘伟主编《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8]本文所提及的文物及其编号中,五位数数字是器物的馆藏总号,括号内编号是馆藏分号,以往文献中均未见考古编号,因此本文亦未提及。
[9]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页。
[10]同[9],第71页。
[11]陆耀辉:《上海广富林遗址出土棘刺纹尊的铸造工艺研究》,《上海工艺美术》2019年第2期。
[12]安徽省文物局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13]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16]同[4]。
[17]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4—55页。
[18]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19]同[17],第67—69、75—86页。
[20]田建花:《淮阴高庄战国墓青铜器群制作技术研究》,《华夏考古》2013年第1期。
[21]同[9],图版玖肆。
[22]同[9],图版玖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