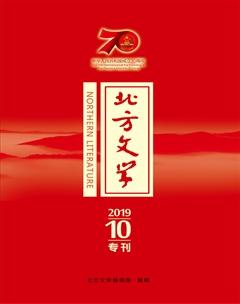追寻那份无悔的纯真
拂去岁月厚厚的封尘
敞开心的世界记忆的闸门
一幅幅一帧帧
不能忘却的画卷
引领着我 默默地前行
追寻 我生命的那份纯真
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
那份无悔的忠贞
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临近的日子,我心中总是回旋着孙楠这首《追寻》的旋律。七十年的共和国正年青,七十岁的我却老了。老人总愿意怀旧。这70年是怎么过来的?拂去岁月封尘,敞开记忆闸门,那一幅幅一帧帧历史的画面不由得显现在眼前:
那是1949年的风雪之路,也许就在开国大典后的日子,亲戚传来口信,说父亲在外县当了邮电局长,让我和母亲快去。于是,那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我和母亲坐上亲戚赶的马车,从家乡的老屯出发,开始告别母亲在土地上刨食我在地头抱着空碗哭号的日子,寻找温饱的新生活。
那时的天很冷,母亲用棉被把我包裹得很严并紧紧地抱在怀里,我还是被冻得哭号不止。母亲哄着我说:“别哭了,别哭,就要见到你爸了!”亲戚使劲抽打那匹老马,终于在天黑时,我们驶进了一座灯光暗淡的小城。父亲把我们安置在一间废弃的日本旧浴室里,他把冻僵的我放在新砌的火炕上,电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父亲的热吻让我感到了甜丝丝的温暖。第二天母亲用从街边捡来的破砖搭了锅灶,就开始了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小家族的创业史。
父亲任职的这个县邮局,大约有两个投递员、两个话务员、两个线务员,他经常的任务就是做他们的替补。所以他总是很忙,下班也晚。母亲一直等父亲下班才开饭,饭后就喜欢听他唱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啊,延安,你这雄伟的身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完歌,父亲给我和当时还不识字的母亲读书,都是革命故事,有关抗联的故事、长征的故事,最早都是听父亲讲的。我上小学之后,父亲也给我读小说,有当代的,也有古代的。听父亲读小说,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始是我和母亲听,后来妹妹和三个弟弟一起听,听到最后的,总是母亲和我。一个因热爱进步文学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父亲,就这样开始用文学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思想启蒙,对我来说也是文学的启蒙。
上小学时,我到了齐齐哈尔,这座文化深厚的古城,让我感到了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因为我说话声音洪亮,经常被老师点名领读课文。后来老师又让我在班会上给同学讲故事。学校组织汇演,我代表班级表演朗诵。当时得了一块石膏做的奖牌,乐颠颠地跑下台,结果和另一个上台领奖的同学相撞,把奖牌撞成两半,后来母亲用胶布把它粘了起来,我才破涕为笑了。因为多次搬家,这块奖牌早就没了踪影,可我从小到大的所有奖状,母亲都保存着。
我因这点儿表演才能还被老师派去“战斗”。当时,反右斗争开始了,我们一个老师说,现在农业生产不咋的,土豆长得不如鸡蛋大。学校召开批判大会,老师找了一个大土豆和一个小鸡蛋,让我上台和那位老师辩论。我把土豆和鸡蛋都举到他的眼前,问他:“你说是土豆大,还是鸡蛋大?”他指了指土豆。然后我无话可说地就下台了。老师说,你应该接着批判他,为什么说假话,攻击社会主义。我说:“我妈买的土豆,也有比鸡蛋小的。”这也许就是我生命中最初的纯真。
后来我还参加过报捷活动。那时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哪个单位建小高炉了,老师领着我们敲锣打鼓去祝贺,我们这帮小学生高喊:祝贺,祝贺!然后朗诵祝捷词,场面特别热闹。大跃进出奇迹。我妈领着大院的家庭妇女还办了一个生产电器原件的工厂,没等我们去报捷就黄了。
1961年9月,我戴着纽扣般大小的齐齐哈尔“优秀小学生”奖章被保送到市实验中学,那是所省重点校。特别值得记忆的是俄語老师教学有方,给每个学生起了个俄罗斯小孩子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瓦利雅”,从此我特别喜欢俄语学习。还有一件事,我们全体住校生有一半学生前十天就吃完了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的定量口粮,最后学校团委发出号召,全体住校生把所有剩下的粮票集中起来,每天喝两次粥,保证不饿倒一个同学。我是把自己剩下的粮票捐献给同学,背着行李回家了,然后每天走读的。来回有三十多里路。回家的时候,有时走不动了,就坐在道边休息。那时,有小孩儿提着水壶卖水:“一分钱管够!”我喝饱肚子,接着走。那时母亲在郊区农场打工挣的饲料豆饼和每天分的一把青菜,让我和弟妹们填饱了肚子渡过了难关。
后来,我们跟着父亲搬到哈尔滨,随行的队伍有爷爷奶奶,还有我和妹妹弟弟五人。我们这一家三代挤进两间小屋。父亲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校长兼书记,住和其他职工一样的房子。我转入离家很远的一所普通中学,当时学校正在学雷锋,我因表现突出而入了团。那时,我把雷锋的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上,郑重地抄下那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在1968年的那个动荡的5月,当时的我是哈尔滨一中的高三毕业生,我和五名同学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上山下乡闹革命。我们选择了离黑龙江最近的哈青农场(后编入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们渴望参加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战斗。当时我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毕业前,我被选为出国留学预备生,突然而至的“文革”,使这都成了泡影。
1968年5月28日,我们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而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在这一年的12月),列车几乎是推开送别的人群驶出车站的,开始是慢吞吞,以后便呼啸着奔跑了。这时,一个女孩子跟着启动的火车奔跑,先是慢跑,后来就是狂奔了。火车消逝在远方,她停下来, 伫立在人群淡去的站台,默默地流泪。她是我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战友,现在的老伴。当时,我们一起报了名,在迁户口时,母亲突发心脏病,她被学校劝阻。勇敢和坚定可以冲破所有羁绊,她终于在几个月后的11月7日悄悄地登上北去的列车。她在黑河坐着敞篷的汽车,顶着风雪跑了二百多里路到达我们独立一营,当时她成了冻得说不出话的“雪姑娘”。她也是一中的学生党员,高中毕业时学校党组织动员她把“北京医大”的高考第一志愿改为“国际关系学院”,那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院校。下乡后,她做过饭,养过猪,教过学,当过家属队指导员。返城后,她真的去搞“国际关系”——在市政府外事办工作到退休。
开始我的处境比她好,先在农工排当副排长,后被抽到营部搞清查。父亲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四个下乡的兄妹刚下乡时,父亲亲自给我们写信,几乎每月每人两封,后来突然改为留城的三弟给我们写信了。开始,他说父亲出差了。后来我一再追问,终于等来父亲从“牛棚”寄出的信,他说,他已经被专案组定为“走资派”,让我们和他划清界限,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据母亲说,他写这封信时痛哭流涕,说我会把孩子的前途耽误了!还好,我们营的教导员说,你好好争取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他说,你还有能力,去报道组工作吧,再不能搞清查了。父亲的信也救了我,如果继续在清查组,也许会干出逼死人命的事。我们这个知青的农场,为抓苏修特务,还把一个知青和一个种菜的“二毛子”老太太逼得自杀身亡。
在哈青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但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后来营里从红色草原农场买了一匹叫“草上飞”的枣红马,成了我的坐骑。那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个鼻青脸肿,但最终被我驯服了。每当我骑着马,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会让每一个女知青动心。我最愿意跑营部到一连的那条路,因为路上有可能和她邂逅。我看到她在天低云暗荒草萋萋的草滩上,追逐着猪群,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曾十分美丽的脸庞上写满忧伤。我呼喊她的名字,远远的我看出了她坚强的微笑。我当时很后悔,后悔让她跟我来到了这大山深处的莽原之中,后悔她放弃了已经在学校安排好的工作。
我的稿子最早发表在《黑河日报》,那个四开的小报是我文学和新闻的发祥地。我总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送稿的情景。天刚亮,我就从大山深处的营部出发,坐在敞篷的嘎斯车上,一路饱览兴安山川的优美和壮丽。我们的车先到黑龙江边,然后顺着江边公路东进,对岸树丛中闪动着军人的身影和隐蔽的炮车,珍宝岛战役打响后,江两面都在准备打仗。傍晚时分,我们的汽车开进了炊烟袅袅的小城瑷珲。闻着淡淡的硫磺味的煤烟,看着一片片低矮的房舍,我竟像第一次进北京那样激动。
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进江畔《黑河日报》那座不大的院落。院里有座灰楼,楼梯是木制的,悬在楼外,踏着颤动的楼梯,我走进那座灰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中年人,把一摞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面前,那是我趴在连队的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问了我们报道组的一些事。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这些稿子能发吗?”他说:“再研究一下,争取发一篇两篇。”记得我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基础不错,以后多写。”后来我知道,他叫杜广洲。再后来他当了《黑河日报》总编。二十年后,我当了黑龙江日报社社长时,每次到黑河总要去拜见我的这位恩师。
从瑷珲回来第二天,我们营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我和报道组的哈尔滨知青吕永岩(现沈阳军区副军职作家)抓紧写准备打仗的稿子,但总不相信真能打到我们这儿。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孙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正在过江,营部全体马上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套了,那些“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我和小吕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又消灭了昨天家里寄来的红肠。天亮之前,我们背着打印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一起撤出驻地。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汗水湿透了,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做饭,孙协理员高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我代表营首长向大家表示慰问!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倒到他的脸上。
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组名震兵团,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2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六连因和林场的土地纠纷被迫搬迁,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原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厢板的时刻,原木向下滚落,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原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金学和在营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连队的,干过许多好事,显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又派来师报道组的大手伊永文(现黑龙江大学教授)与我合作,这篇经过多人之手的长篇通讯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同时还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
按照部队的传统,推出典型的报道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连表扬都没得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要我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树都放绿了,紫色的达子香开得正茂盛。小吕和我的女朋友都来送我,他们竟掉了泪。我说,一个月我就回来!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兵团战士报》乏善可陈,但对经济工作,对农业生产的突出报道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李先念批评兵团的生产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兵团首长很着急,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推进发展。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我们报纸连续发表学习大寨的“社论”,由“第一支笔”李惠东(后任黑龙江日报社副总编)操刀,在写到“六论”时,李老先生积劳成疾(主要是抽烟太多),突然昏倒在办公室,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只好接过李老师的笔。我又写了几篇“社论”。后来怕写社论累死人,我以“梁丰”署名写过许多鼓吹以农以主多种经营的小评论,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扬。他还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好一番鼓励,还亲自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后来我也自以為是“专家型记者”了,全兵团的许多生产数字、农业政策,我也可随口说出,在以政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记者中也是“凤毛麟角”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祖国相连的。“文革”的灾难终结于1976年10月的阳光中,两千七百万知青的命运得益于邓小平的一句话:“让这些孩子回家吧!”1976年的12月,我们十个知青被招工到哈尔滨日报社,当时报社编辑部的干部已经青黄不接了,刚恢复工作的江村总编,派得力干部到兵团选人。于是我们十个哈尔滨知青,抖落一身黑土,又兴奋又惶然地走进报社大楼。这十个人中我三十岁,蒋巍二十九岁,江总编破例把我俩定了锅炉工,每月三十六元,其他八个人定为印刷工,每月比我们俩少三元钱。
我们是12月26日那天到报社人事处报道的,副总编邹本业叫我和蒋巍去友谊宫为报道人代会的记者们帮忙。一位老同志把几张已经排好版的大样交给我们,让我们熟悉报纸出版流程。我和蒋巍不知深浅地在大样上挑出许多错别字,还改了几个标题,还发现了放错位置的刊头。没让我们吃上一顿会议餐,就被打发回报社了。下午,我俩被叫到总编办公室,江村和邹本业两位领导都在,桌子上就摆着那几份我们改过的报样。江村望着我们紧张的样子,笑着说:“我和邹本业看了你们改的大样,很好嘛!谁说你们是生荒子,我看比我们有的编辑强!”他接着说:“我和本业商量了,你们俩不用下报社印刷厂锻炼了,明天就上班,宏图上评论部,蒋巍上政教部!”
当时,我和蒋公子像得了彩票一样高兴。当然,我们没有让重用我们的领导失望,很快就成了哈尔滨小有名气的记者。在哈报工作的期间,我们俩各得了三次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大奖(有一篇是我们俩合作的),所写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当记者采访时发现的。一个地方报社出了两位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我们也没有在报社终老,我1983年10月被调到市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之后又到省作家协会、省文化厅和《黑龙江日报》任职。才华横溢的蒋巍走得更远,他先在市文联当主席,后来调到中国作协当司局级干部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哈报给了两个年轻人最早的信任和尊严。遗憾的是,在哈报工作时,我们从来没去一次锅炉房,白领了锅炉工的工资呀。
其实我和蒋巍这两个青年记者是被裹挟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去的,作家被压抑了十年的激情终于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解放思想”的火种点燃而喷发;一些曾被埋没和压制的人才,被新时代推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往往是时代■望者的记者,最先发现了他们,为他们唱出了壮丽的人生之歌。饱经“文革”的严寒,对改革春风的温暖特别敏感。作为新时代的受益者,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无论作为记者还是作家,我们站在破浪前行的时代大船的甲板上,■望光明的远方,感受扑面而来的风雨,我们是不能不歌唱的!
比如我写的报告文学《她在丛中笑》,记录了在“文革”极左思潮横行的时候,一个街道小厂的党支部书记陈秀云,在工厂没有产品面临倒闭的情况下,启用了当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工程师安振东;安振东冒着风险研制煤矿防爆整流器,陈秀云写下字据:我为研制组长,出现问题由我负责。这个产品救活了一个工厂。陈秀云又为安振东解决了住房,在上级还没有为右派平反政策时,她和支持她的上级七年跑了五千多公里,陈秀云和厂子其他领导光往老安工作的唐山和齐齐哈尔,就跑了十二趟,寻找推翻安振东的“罪证”的证据,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上为他翻身,为他后来当上我省副省长和全国九三学社副主席创造了条件。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光明日报》在转载时,还在一版头题发表评论说,有更多陈秀云这样的优秀干部,才能使更多安振东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得到重用。后来陈秀云和安振东一起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人物”,成为当时中央推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好典型。
这之后,我又写了狠抓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伊春市委书记杨光洪,坚持共产党员优秀品格、全力推进企业改革的大庆石化总厂厂长杨久礼和抵制歪风树立正气、关心群众疾苦的青年干部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张毅,这几篇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文学前辈刘白羽先生在1992年第16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寄希望于跨世纪人》中说:“贾宏图同志近几年报告文学所显示的一个很重要也很有价值的特点,那就是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从《大森林的回声》《人格的力量》到《跨世纪的人》,他描写的对象都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都集中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怎样坚持和发展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反对腐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所不同者,《跨世纪的人》在所描写的几个人物的精神品格的同时,更突出了开放意识,从而显示了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深化和突破。”刘白羽还在文章中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更多如同贾宏图这样跨世纪的文学艺术家,以自己的诗情画意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像恩格斯早就期望的那样,反映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把现代最革命的思想表现出来,以推动历史的前进” 。
也许我创作的多部报告文学有一篇是可以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那就是发表在1989年第5期《当代》杂志上的中篇报告文学《解冻》。这篇文章的创作,起源于1988年冬天在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和几个俄罗斯朋友的相遇。我用还依稀记得的俄语向他们问好,随行的翻译告诉我,他们来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来和哈尔滨联系经贸事宜的。
他们终于过来了,看来黑龙江真的解冻了!接着又从黑河传来当地干部用一船西瓜换来对岸三千六百吨化肥的故事。于是我直奔黑河,又去绥芬河,采访了上百人,带回关于黑龙江两岸的两国人民“敌对——友好——再敌对——再友好”的有血有泪有哭有笑的故事。然后,我又在哈尔滨采访了与俄罗斯有过深刻交往的人士,他们告诉我这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建的与中东铁路共生的城市与俄罗斯血脉相连。与原苏联“结束过去,面向未来,共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经过近一年的采访,这篇报告文学终于在11月于北京面世。这是中国第一篇记录中俄重归旧好,开始经贸往来的报告文学。也许因此,它荣获“中国当代文学奖”和“改革开放30年30篇优秀报告文学奖”。在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报告文学集《大纪录》中,《解冻》入选其中。这也是我一个与祖国一起成长的作家献给共和国七十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更让我欣慰的是,最近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为新自由贸易试验区,规划中涵盖的哈尔滨、黑河和绥芬河的三个片区,正是我三十年前报告文学中记录的黑龙江对俄开放的三个热点城市。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远离大海的北方大省黑龙江终于被推上沿边开放的前沿。
星期日孙子又回我家玩儿,因为我这几天感冒了,他问我:“老作家,你身体怎么样了?还能写文章吗?”
“我身体很好,正在写文章呢!”我指着电脑里的这篇文稿说。他笑了。
十岁的孙子是我们这个与共和国同时创业的小家族的第四代傳人。他一定会继承家族的传统,献给祖国一生无悔的忠贞!
责任编辑 韦健玮
——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