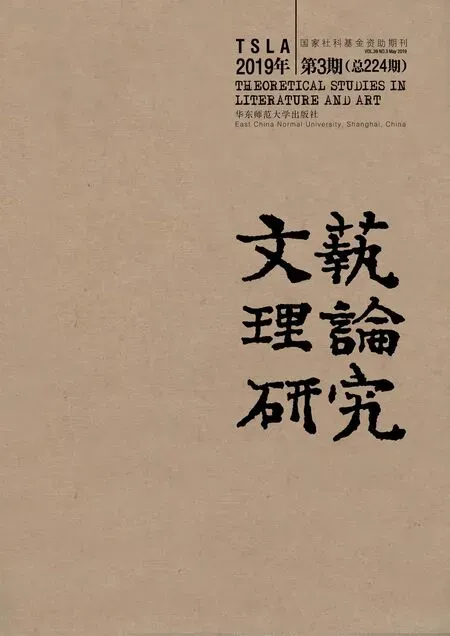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丁文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阿多诺针对现代性、美学、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述与思考,在批判理论的后续发展中继续引发理论家不断再解读,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三代理论家哈贝马斯、维尔默、霍耐特均对阿多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再阐释,可以看出阿多诺在批判理论思想脉络中具有重要意义。阿多诺的学术贡献在于以非同一性作为思考方法,不仅进入理论根基对启蒙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剖析,而且开创性对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和受众的心理学机制进行研究。美学在阿多诺的思想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包含了真理内容,乌托邦的想象只能建立在与现实社会相断裂的审美领域。
论及阿多诺,不能忽视奥斯维辛事件对他的思想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在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在当前中国学界,以奥斯维辛为视角研究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探究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Prisms
34),代表性成果包括:赵勇指出,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的论述体现了二律背反的逻辑。一方面,由于奥斯维辛在伦理维度的剧烈冲击,以及文化工业对艺术的侵蚀,提供欢愉的艺术不再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以策兰、贝克特为代表的“反艺术”则通过提供痛感,开拓艺术创作的另一种可能。单世联指出,阿多诺认识到西方艺术与文明传统参与了奥斯维辛事件,艺术必须自我革新,并批判旧传统及心灵的物化现象,保罗·策兰的诗歌被认为是成功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考察受难记忆问题与阿多诺美学思想的关系,不仅需要关注阿多诺针对“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论述,而且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的同事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的神学思考一直抱有强烈的兴趣,有必要结合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记忆问题的学术脉络,重新理解本雅明的神学思想遗产在阿多诺美学思想中的位置。阿多诺不仅切身体验了以奥斯维辛为标志的德国纳粹集团所发动的反犹行动的迫害,而且也试图将兼具社会历史以及神学视野的受难记忆纳入现代性批判规划,从记忆的视角出发研究阿多诺的美学思想,思考阿多诺如何将受难记忆纳入审美乌托邦的规划,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将是,在阿多诺的美学论述中,理想的艺术作品以何种方式包含了受难记忆;受难记忆如何促成审美乌托邦的生成;审美乌托邦的规划又是如何回应、转换具有神学政治学色彩的记忆诉求。
一、阿多诺美学论述中的受难记忆
一直以来,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命题在学术界与文艺界引起持续争论,二战结束之后,阿多诺在不同范畴的著作中不断对“奥斯维辛之后”这一命题进行回应与思考,“奥斯维辛之后”构成了理解阿多诺美学思想的重要切入视角。阿多诺痛斥奥斯维辛事件是“对百万无辜民众的行政主导的杀害”(Critical
90),并从哲学角度反思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构成西方现代文化根基的同一性思维模式在现实情况下的极端演绎,纳粹统治者将犹太人视为一个违背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纯粹的物体或者概念,在集中营中予以劳役乃至集体杀害。正因如此,阿多诺认为战后艺术存在的合理前提是深切悲悼奥斯维辛事件,并对启蒙现代性思想思潮进行彻底的反思。不仅奥斯维辛事件构成了阿多诺审美反思的现实触动,阿多诺深受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从神学政治范畴出发关于受难历史的书写与救赎方面的论述,启发了同为犹太人的阿多诺对受难与救赎的思考,这是理解阿多诺有关艺术与苦难问题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思想交往始于本雅明建基于神学的著作《德国悲悼剧的起源》,阿多诺看到了将著作中的神学方法论挪用于批判统治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此后阿多诺代表社会研究所与本雅明围绕“拱廊街计划”发生了三次学术论争,阿多诺在一定程度误读本雅明的基础上认为其背离了早期的神学思考。阿多诺的批评集中在本雅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包括社会政治范畴的乐观主义倾向的乌托邦构想,以及让社会材料的意义在列举中自动呈现的分析策略。阿多诺认为神学作为方法论有必要停留在理论反思层面,而非在社会现实范畴将单子论和弥赛亚救世论直接运用于建立布莱希特式的社会主义政体。换言之,阿多诺将本雅明理论中的神学要素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方法,但反对在缺失社会总体状况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将神学直接运用于文化阐释或政治动员,阿多诺试图将本雅明神学救赎所包含的政治构想转化为限制在审美范畴的文化批判与乌托邦想象。
首先探究本雅明针对受难历史的思考与早期阿多诺思想的关系,本雅明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围绕受难记忆论述悲剧时候写到,“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不再是被指控者的罪行,而是无法言说的受难证词。”(The
Origin
109)在本雅明的论述中,尽管“无法言说的受难证词”被由神谕支配的命运秩序所遮蔽,对受难证词的救赎构成促发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并反抗诸神的契机。对本雅明这本神学色彩浓厚的著作,阿多诺在多封来往书信中均给予正面评价,尤其对于“史前史”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知道我同意你在论述悲悼剧的著作中最大胆的片段”(Bloch et al. 112)。阿多诺在《自然历史观念》一文中借鉴了本雅明的方法论,“‘含义’说明自然的要素和历史的要素没有相互融合在一起,相反,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中最历史地呈现为自然标志之处,自然要素就表现为历史标志和历史。”(“自然历史” 243)他尝试通过将寓意本真欲求的“自然”与寓意理性规训的“历史”这两个对立概念相互融合,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理论概念——自然的历史,在坚持理性的必要性的同时,将一直受到由理性所主导的现实秩序所排斥的本真欲求予以重新言明。阿多诺认为需要借鉴本雅明的观点对卢卡奇使用的概念“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进行重新阐释,“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包含了尚未受到启蒙现代性塑造的完整原始经验,不仅包含了本真的感性欲求,同时也包含了理性历史展开过程中对自然的残酷征服,而日益走向物化的心灵将失去对历史记忆的感知与洞察能力。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并非一种均质、空虚的线性时间理念,根据相关研究,“痛苦和记忆既是自然史的必然性,也是个人生命史的构成要件”(黄圣哲 72)。再参见赵静蓉对文化社会学关于记忆问题的梳理,“文化记忆的核心是记忆,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之后的一个结果”(12)。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与当代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文化记忆”及其运用具有亲和性,参考他在以辩证法为主题的课堂演讲的论述,“辩证的社会理论的任务必须始终包含拒绝根据一种仅仅静态的潮流,把没有保持同步、落后的事物视为一些仅仅是落后的、在当下反对改变与变化的事物。”(An
Introduction
145)有待重新阐发的“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正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进步叙事话语中被视为“没有保持同步、落后的事物”,阿多诺认为辩证的社会理论不应该仅仅立足单一的线性发展的维度,而需要拯救储存在个人或集体潜意识以痛苦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记忆,并在进步叙事话语有异化为极权主义危险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重新阐发其价值,与本雅明将社会革命建立在以救赎受难记忆为核心的神学维度的方法论具有相似性。《自然历史的观念》被苏珊·伯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视为贯穿阿多诺学术生涯的纲领性论作,认为非同一性与否定辩证的逻辑虽然在当时还没有系统明确地提出,“然而两者的实质在30年代早期阿多诺的理论中已经很明显”(Buck-Morss 63)。阿多诺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结合身受纳粹迫害被迫流亡的经历,在后续的学术思考中对“自然的历史”做进一步的阐发,“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及其寓意也内在于阿多诺的美学思考中。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多次直接运用“记忆”或相近名词讨论艺术问题,阿多诺的论说文(essay)式的写作方法几乎拒绝进行任何概念界定,因而需要对阿多诺在美学范畴关于记忆的论述进行归纳、提炼。“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在阿多诺关于自然历史的论述中作为促成呈现真理内容的契机而存在,阿多诺在遗著《美学理论》用记忆的概念进一步论述两者在现代艺术中如何促成真理内容的发现和审美乌托邦的生成。阿多诺通过反问句式,把对受难记忆的表征作为战后艺术得以存在的根基,“但是,艺术作为对历史的书写,如果艺术摆脱了累积的受难记忆,那么艺术将成为什么东西呢?”(Aesthetic
Theory
261)与“石化的历史”和“陈尸所”的概念相延续,阿多诺的记忆概念可以从“受难”这个关键要素出发进行阐发。具体来说,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不仅需要同时在内容选择与价值取向两个方面和推崇肯定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相隔离,而且通过艺术形式将现实中的异化状况与被遮蔽的社会对抗转化为艺术表达,从而在保持艺术自律的情况下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与批判,艺术在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保持自律的姿态却因此反而更有效地介入现实,起到了见证历史并具有表征隐匿在现实中的自由潜能的作用,“累积的受难记忆”构成了真正艺术作品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阿多诺把发掘受难记忆视为进行非同一性思考以及动摇现存统治机制合法性的契机,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指出了统治机器试图通过抹杀受难记忆并营造虚假的幸福愉悦的现象,“阻止对由其产生的苦难的承认,是统治机制的构成部分,在幸福的信条与在远在波兰建设的灭绝的集中营之间存在着线性发展的关系,每一个我们的国民能够使自己确信不会听到痛苦的尖叫。”(Minima
63)对“累积的受难记忆”的反思不仅仅控诉当代资本主义对受难群众的压迫,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向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同一性逻辑。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论述,“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9)支撑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石是由理性同一性主导的启蒙现代性,理性走向异化的过程既是主体膨胀并进而无限度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统治集团将征服自然的手段毫无保留地运用在征服、乃至消灭同类的过程,异化的启蒙通过同一性的抽象逻辑将所有个体转换为工业时代可以统一支配、可替换的物,奥斯维辛事件则是纳粹将无法纳入其所确立的伪平等逻辑的群体予以集体清除的过程,因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切实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启蒙现代性从兴起、发展到异化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艺术对累积的受难记忆的表征,将是对社会统治体制及其内在逻辑进行辩证否定与批判。正因如此,阿多诺所论述的艺术中的记忆,是代际累积、又被启蒙现代性的叙事话语所遮蔽的受难记忆。二、记忆的构型:星丛结构
受难记忆是以何种方式内在于艺术作品中?在阿多诺看来,将受难记忆直接置入作品中并不适宜,他不仅忧虑受难历史可能被文化工业转化为用以谋取利益的煽情题材,也警惕特定的政治集团将记忆用作社会行动的动员,从而削弱甚至取消了反思的深度。参见阿多诺阐述自己与贝尔托·布莱希特在艺术生产问题的分歧,相比于布莱希特主张艺术需要以政治教化的方式直接介入现实的主张,阿多诺反对将作品视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与教化的载体,“然而,对自律艺术的强调本身事实上就是社会政治性质的。当前政治的畸变,境况的僵化没有在任何地方开始缓和,促使精神前往无需成为群氓构成的地方。”(Notes
93)真正的艺术因为自律而不具备任何直接的政治功能,这一特点恰恰构成了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自律艺术因为不直接介入现实而得以避免被社会的交换法则所同化,也避免了堕落为商品而被迫向群氓的趣味做不同程度的妥协,从而得以抗拒统治意识形态对历史记忆的遗忘。因此在阿多诺的美学论述中,记忆并不会作为直接书写的对象存在于自律艺术中,不会鲜明地直接体现作者的意图或某种总体性理念,而是以碎片的形态隐匿于作品的审美形式中,避免被制造为通过迎合、欺骗的手段控制受众的政治宣传品或文化消费品。阿多诺先后以“余像”(afterimages)“伤痕”(the trace of the damage)等名词描述记忆在艺术中的碎片式的存在形态。记忆之所以能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因为阿多诺把艺术作品视为一个“无窗的单子”,单子形态及其内部结构将有助于记忆在艺术作品中得以保存与再呈现。究其原因,在阿多诺的论述中,艺术作品作为单子,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艺术作品之间相互封闭,看不见外部世界,然而艺术作品能在紧闭的结构中表征外部世界事物”(Aesthetic
Theory
179)。单子是一种辩证的构型,一方面是因为“无窗”的特质而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离,有助于艺术作品幸免于社会统治机器的强大同化功能,为保留非同一性的自主感性经验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并非与社会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虚幻想象,而是作为“引力的中心”成为汇集人类共同拥有的丰富经验的仓库,尤其包含了不符合统治机器根本利益的事件与情感体验。同时阿多诺又反对天才决定论,艺术作品的语言构成于“集体性的潜流”(Aesthetic
Theory
86),真正的艺术是“集体性的潜流”的表达,是置身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对涵盖社会历史与当下现状的时代精神的间接性回应,艺术所储存的丰富人类经验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包含了主体及其所属集体在面对历史与现状的见证与反思,艺术作品的生成是社会性的过程,因此艺术所储存的人类的丰富经验就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忆。自律艺术因为其自身单子的构型而与异化的社会现实相互隔绝,其所包含的人类经验无需因应物化社会中统治阶级或文化消费者的需要而被篡改,因而构成记忆的被统治者的受难经历将在艺术中得到保留。再看记忆的具体构成形态,不同类型与不同发生时段的记忆事件是如何构成艺术的内在历史。参照阿多诺关于艺术作品的意义如何生成的论述,“艺术作品本身并非如历史决定论所设想——似乎艺术作品的历史仅仅是与真实历史中艺术作品的位置保持一致——在生成中被吸收。相反,就像存在物一样,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发展。”(Aesthetic
Theory
85)阿多诺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不认为艺术内部具有“内在时刻的连续性”,这意味着阿多诺不认为内在于艺术中的多重记忆会构成时间连续体或等级严明的系统。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将时间连续性与黑格尔构造的世界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而支撑着世界历史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同一性,走向异化的理性同一性体系对溢出既有历史发展秩序的异质事物进行规划性清除,在认识论层面导致了主体理性反思的缺失以及想象力的贫乏,现有的统治模式因此被构建为大众自愿接受的唯一选择,阿多诺则将“不连续性”视为终结这种异化社会状况的武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反转,最重要的强调落实在洞察事物的不连续性,事物不再慰藉地结合为任何精神与概念的统一体”(Negative
319)。回到美学范畴,假如艺术作品建立在“内在时刻的连续性”这一基础上,将导致其审美意义局限在理性同一性预先确立的体系之中,艺术作品将被视为意义恒定的完成物,对抵抗整合意图的异质性进行压制与消除,将外部的社会秩序以复制的方式引入作品内容,并对其合法性予以再确认,进而阻碍艺术所包含的个体性契机,阿多诺称之为“顺从的艺术”(Aesthetic
Theory
154)。阿多诺反对这种模式,而是以“迸发”(explosion)形容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生成情况,尽管艺术作品会构建一个建立在内部虚假统一基础上的“形相”(imagine),然而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发展”,其内部不同的记忆事件以“沉淀”(sedimented)的方式构成艺术的内部历史,诸记忆事件与经验现实之间构成多元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对立冲突的现象同时存在,记忆事件在形相试图整合内部诸元素过程中表现出对抗、不协调的姿态,并且在艺术作品生成的动态瞬间得到保留,并最终通过审美幻象的“迸发”摧毁与异化社会达成妥协的形相统一体,促使接受者受到震惊从而实现意义的再生产。综合诸记忆事件的存在形式以及意义再生产的模式看,记忆的构成形态就是阿多诺常用的哲学概念“星丛”,这个概念来源于本雅明,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星丛构型最终通过语言言说真理进行具有神谕性质的启迪,而阿多诺则将星丛概念进行世俗化的挪用,在否定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中,诸记忆事件在艺术作品的单子结构内部以星丛的构型存在,与理性同一性构建的完美体系相冲突,生成形相统一体所涵盖范围之外的过剩意义,从而激活艺术所包含的否定性潜力。三、受难记忆与乌托邦契机
纵观阿多诺的哲学论述与大众文化批评,阿多诺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操控型社会,根据安德鲁·鲍伊(Andrew Bowie)的说法,“对阿多诺来说,一个被商业化所控制的世界增加了固定的方式成为准则的程度,并因此鼓动对现状的消极接受。”(167)大众被当做无差别的物体完全纳入自上而下的管制体系之中,这是一种整体社会化的统治策略与透明性的管理方式,个体即使在闲暇时间也主动自觉地遵守统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与指引,将自身的行动、思考均局限在由资本力量主导的职业伦理和消费逻辑的范围之内,丧失了想象替代性社会模式的能力,阿多诺称之为“户外的监狱”(the open-air prison)(Prisms
34)。阿多诺以绝对悲观的态度看待几乎任何社会改良或政治运动,救赎的希望被寄托在审美乌托邦,以星丛的构型积淀在艺术品中的记忆,又是如何内在于审美乌托邦的理论逻辑?简要概述阿多诺构建审美乌托邦的理论逻辑,阿多诺将真理性内容赋予真正的艺术作品,真正的艺术作品建立在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批判意识与客体优先性的双重认识基础之上,通过与现存社会秩序相互分离的方式使作品得以逃离统治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从而得以保存人类丰富的感性与社会实践经验,因而艺术得以超越异化的社会现实,具有表征真理性内容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逾越既有主流话语预设的哲学体系与社会秩序,具备重新想象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潜力,即对“使不可能事物变得可能”(Aesthetic
Theory
107)“非存在物的美学实现”(109)的探索。对于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规划,可以引用两位左翼学者所做的评论作进一步分析,理查德·沃林认为,“在其探索过程中,由于阿多诺千方百计地把艺术作品首先看作哲学真理的手段,艺术作品之整个实用方面——它们在塑造、了解和改造历史上存在的个别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一受到了忽视”(127)。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认为,“由于末世论——感觉论的乌托邦,历史真实与和解状态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法度量,于是人类试图跨越这一距离的实践变得毫无意义。”(17—18)沃林与维尔默的论述类似,他们均肯定评价了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的重要论述基础,即艺术需要通过维持自身与现实状况之间的持续对抗的关系,从而展开艺术的批判与救赎功能。他们也相似地指出阿多诺所建构的审美乌托邦体现了绝对怀疑论的取向,审美救赎的美好承诺实际上并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或部分实现,因此批评阿多诺忽视了艺术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实用性功能,认为艺术所具有的交往潜能有助于促成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对话,进而产生积极的政治意义。沃林与维尔默对阿多诺关于审美乌托邦设想的概述与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大体上遵循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阐发批判理论的思路,尝试将建立在绝对否定性和审美救赎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代批判理论转化为民主社会体制下一种以政治改良为诉求的理论话语,有助于提高批判理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适用性。然而,沃林与维尔默对阿多诺美学思想的解读主要着眼于如何因应议会民主机制改造批判理论,导致普遍存在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学说中的审美乌托邦价值因为学理论证逻辑不够严密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性理由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阐发。然而,参考阿多诺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现实中没有解决的对立作为形式的内在问题返回到艺术中。正是这种方式界定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而非客观元素的介入。”(Aesthetic
Theory
6)阿多诺并非完全认同康德将审美与功利完全分割的美学观点,艺术与现实的断裂是为了通过这种断裂关系实现对现实的更有效的介入,避开主流社会意识对艺术的控制。正如沃林与维尔默所论述,阿多诺将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愿景寄托在与现实处境完全断裂的审美领域,在阿多诺的思想语境中这种断裂来源于艺术的单子结构,艺术作品凭借无窗单子的构型得以置身于异化社会之外,从而形成针对异化现状的绝对批判立场。另一方面,阿多诺又认为,“包含了单子构型的艺术本身指向了对单子构型的超越”(Aesthetic
Theory
180)。对艺术作品进行不纳入外在概念的内在分析,事实上却能更精确地理解社会境况,因为单个艺术作品的特殊审美经验,本身就具备普遍性的意义。诚如有法国学者指出,“阿多诺则相反地深刻批判了这种把当下转换为未来利益的‘抽象的乌托邦’。乌托邦理念吸引阿多诺,更在于其批判现存秩序的能力”(Wezel 30)。需要进一步思考以星丛构型内在于单子结构中的历史记忆,是否存在着作为中介发挥隐秘勾连审美乌托邦与现实的功能,实现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与重构,从而回应沃林与维尔默的质疑,并为重新审视第一代批判理论的遗产提供了契机。针对真理内容如何存在于艺术作品这个问题,阿多诺指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是对由每一个或所有作品所引发的谜的客观性解答。通过对艺术如何解答的追问,谜指向了艺术真理性内容。这仅仅只能通过哲学反思才能实现。”(Aesthetic
Theory
127-28)真正的艺术负有提供真理性内容的承诺,真理性内容以谜语的方式存在于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中,作为一种等待救赎的内容需要在以客体优先性为基础的阐释中被揭示出来,直接表现为对建构于自恋基础上的幸福假象进行否定。阿多诺在回应西方的衰落这一问题时候谈及,“能够抵制西方衰落的并非复兴的文化,而是包含沉默地被包含在衰落图景中的乌托邦”(Prisms
72)。这体现了阿多诺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否定性反思,他认为奥斯维辛的悲剧否定了现代性文化塑造的正义形象,重新想象与当下构成断裂性的乌托邦,需要建基于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的历史记忆之上。至于历史记忆如何促成审美乌托邦的发生,从阿多诺的该段论述谈起:
但是,艺术作品存在这个事实表明了非存在物(nonexisting)的可能性。艺术作品的现实性证明了潜在性的可能性。作为艺术所渴望的对象,非存在物的现实性通过回忆(remembrance)在艺术中发生变形。回忆是和非存在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回忆对象不再存在。(Aesthetic
Theory
132)阿多诺认为理想的艺术作品并非仅仅是创作者欲望的表达,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艺术作品并非只能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历史叙述以复制的方式纳入艺术中,而是相反地试图利用艺术的幻象特质,将超出主流历史书写之外的内容重新赋予意义,隐蔽地演变为艺术作品中的谜语而得以保留,从而为艺术作品表征现实存在模式之外的潜在性图景提供了可能。阿多诺在这个推论基础上认为,由于艺术作品具备表征社会历史进程中被遮蔽的“非存在物”的潜能,现实需要反过来摹仿艺术。而促成社会历史进入艺术作品的途径是创作者的“回忆”,根据阿多诺对艺术生产的论述,尽管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强调艺术生产与创作者所归属的群体、面对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艺术活动必须建立在“不能压制的、异于常态的独特主体”(412)这个基础之上,因此“回忆”是具有反思理性的自主主体运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将社会历史转换为艺术作品中有待揭示的谜语。由此可见,进入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并非一种由官方赋予其客观性权威的档案式文献,而是自主主体关于社会历史的独特记忆,正因如此,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具有超越既有意识形态框架的可能。
阿多诺所言的“回忆”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乡愁,在哲学思辨范畴,阿多诺认为,“对于超验的回忆需要立足毁灭才能得以保留,否则将变得不再可能;永恒并非呈现为如此,而是通过易毁灭事物的衍射而呈现”(Negative
360)。在社会批判范畴,阿多诺认为,“从保留下来的事物中欺诈地清除了被杀戮的事件,我们无权者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是回忆。”(Critical
91)阿多诺将回忆视为被统治者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性行动,回忆植根于统治机器不断试图清除的受难记忆,受难记忆作为对以奥斯维辛事件为代表的杀戮事件的见证,从被剥夺政治权利和话语权的受难者的立场控诉了统治机器权力来源的不道德性,从而为中止现有的社会机制的连续性并重新想象乌托邦创造了契机。对于如何以回忆为方法,促成乌托邦的生成,可以具体从三个层次予以理解。在第一个层次上,理想的艺术作品是一种无窗单子结构,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绝,回忆是主体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的行动。对社会历史的回忆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幻象,成为了艺术作品中的记忆事件,凭借着艺术作品的无窗单子结构的特点,保留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经验,避免了外部统治意识形态对思维习性与想象模式的形塑,因而记忆保留了生成与当下世界既有模式保持间距的非同一事物的可能性。在第二个层次上,参考阿多诺的说法,“然而,真理性内容不只是借助作品本身得到设定,而且也间接地通过作品对历史的参与和确确实实的批判得到设定。艺术中的历史含义不是人工制作的:这样,正是通过历史,艺术才从作为纯系虚构的产物中解脱了出来。在艺术作品中,真理性内容乃是历史的结晶。”(Aesthetic
Theory
133)这需要参照阿多诺对艺术的构成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予以解读。艺术拒绝以复制的方式全盘接受概念体系对当下现实、人们经验的独断解释,而是通过回忆将过去的社会历史与当下相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下的现实将不再是黑格尔设想的世界历史模式下线性进步关系。存在于艺术作品内在结构中的记忆将和现实构成相互并置的关系,这即是星丛的关系,历史记忆将不再是当下现实的低级状态或不完满的事物,而是在星丛关系中的相互并置关系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过去的社会历史将为理解当下现状的起源、发展,以及构想全新的另类发展模式提供潜在可能,这是艺术作品介入现实的尝试。以艺术作品为载体的记忆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介入现实,艺术作品中的记忆凭借自身所具备的超越主导当下社会的同一性思维模式的能力,通过借助艺术幻象呈现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的异质事物,实现了艺术对经验现实的间接性参与,这是对当下统治秩序的否定性批判。在第三个层次上,再探究社会历史的构成内容,主要是与启蒙现代性发展走向异化过程相伴随的受难记忆,尤其以奥斯维辛的记忆为代表。根据阿多诺的论述,“但是,因为对艺术而言,作为尚未存在物的乌托邦被黑暗遮蔽,被保留在回忆的所有调解中;对可能事物的回忆与现实中对可能事物的压制相对立;这是对世界历史的灾难作想象性修复;这是在必然性的魔力下没有出现以及可能从来不会出现的自由。”(Aesthetic
Theory
135)这是对艺术如何间接介入现实的进一步论述。“世界历史的灾难”作为艺术需要处理和反思的对象,内在于艺术所储存的社会历史中,艺术理当回应在后灾难时代与日益完备的非人化社会中如何生存的问题,通过呈现历史记忆包含的绝望和抵抗,激发大众进行非同一性思考的潜能,而不应该沦为向大众提供替代性满足的麻醉剂。总结来看,艺术通过回忆的手段对储存于自身的社会历史进行反思与再评判,得以洞察隐匿在现代性规划描述的美好远景背后的苦难与压迫,艺术进而借助自身具备的表征潜在事物的能力,构建具有自由属性并且独立于同一性哲学的必然逻辑的审美乌托邦,受难记忆构成了触发艺术救赎的契机。
四、艺术救赎对记忆诉求的转化
在阿多诺的美学论述中,包含了人类共同经验的艺术需要置身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之外,借助主体回忆的方式重新呈现、审视被进步叙事所遮蔽的受难记忆,引发对启蒙现代性进行辩证思考,进而具备想象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潜能,这是一种建基于审美幻象和艺术形式的审美乌托邦。既然促成审美乌托邦生成的契机来自于艺术对记忆的救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救赎完全实现了历史记忆的诉求?从这个角度做追问,我们需要继续思考阿多诺美学思想中艺术救赎对记忆诉求的转化问题。
关于阿多诺构建审美乌托邦的有效性问题,兰伯特·祖德瓦特(Lambert Zuidervaart)针对阿多诺将真理内容赋予自律艺术的论述做了得失评价:
阿多诺方法的优点有两个方面。其一,这样避免了将真理与艺术现象相分离,反之坚持了真理彻底由现象所中介。其二,这样抵抗了哲学学者读解艺术时添加进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的任意真理的诱惑。但是伴随这样的优点的是双重的缺点。阿多诺不仅将自律艺术特权化,特别是自律艺术品作为艺术中真理所在的位置,而且他将哲学特权化,特别是否定辩证法哲学,作为对艺术真理最权威的阐释者。这两种倾向均使艺术真理成为少数人的秘密。(124)
祖德瓦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建立在自律艺术对真理内容进行表征的基础之上,以否定辩证法作为审美反思过程中首要的哲学框架。尝试将祖德瓦特的论断引入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效度问题的讨论,在否定辩证法的哲学框架内,受难记忆的诉求如何被转换进入审美乌托邦?
受难记忆的诉求可以从阿多诺的该段论述谈起:
“换言之,进步的道路包括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特定的人类团体发现自身被驱逐,根据这些团体的起源与意识形态,他们显然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但是这些团体突然恰恰丧失了其自身历史与意识形态所指向的资产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An
Introduction
144)“特定的人类团体”正是受难记忆的主体,阿多诺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反思并没有局限在反犹主义范围,而是通过反思启蒙在祛魅之后自我神话化的逻辑如何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根基,将奥斯维辛视为启蒙现代性走向异化之后具有必然性的极端化事件,而容易被忽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发展和进步名义对历代被统治阶级进行剥削与控制,因此“特定的人类团体”涵盖了现代性思潮兴起以来被压迫的所有阶层,他们是社会历史维度的记忆主体。阿多诺从非同一性的视角出发,将针对世界哲学体系的认识论批判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指出黑格尔关于世界哲学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性体系,以反思性精神为基石的启蒙理性异化为聚焦如何更有效地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理性逻辑,统治集团进而将具备异质性的个体等同于可以量化的无差别的物体,也纳入精确计算和管控的经济体系中,这个经济体系演化成为资本主义政权的社会管理形式,这是一个建立在同一性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体系,人们被塑造为无差别的个体纳入到追求利润效益的线性历史的必然性进程之中,直观现实就是“现今的工业工人阶级和普通工人都不能被认为具有能力在面对支配性的生产关系时候承担对抗性的立场”(Petrucciani 25)。再回看阿多诺的该段论述,这些“特定的社会团体”参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进程,承受了资本集团在土地、劳动力等领域的经济剥削,以及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生控制,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各个阶段的物质积累、武装革命做出了贡献与牺牲,他们本应获得公平分享物质成果的地位,并切实享有现代性思潮所许诺的政治愿景。然而,在偏离了以个体的启蒙觉醒为初衷的现代性叙事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总体性的进步被视为需要普遍遵循的世界精神,而某些社会团体的特殊个体必须与世界精神保持一致,他们不仅在生存的时代受到劳役与剥削,而且这些与世界历史自我描述的进步、和谐的景象相违背的受难历史,在后世同样没有得到认可与呈现,换言之他们整个社群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驱逐。因此,受难记忆的诉求将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及其背后的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历代受难者需要得到当下社会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给予承认。
在阿多诺构建的审美乌托邦中,通过回忆的方式将受难记忆作用于当下,实现艺术以间接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乌托邦是通过何种机制转换受难记忆的诉求?埃里卡·韦茨曼(Erica Weitzman)指出,“对阿多诺而言,紧随着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动机的暴力,以及面对一个以主体堕落为仅仅是劳动者——消费者为特征的社会,艺术的即时享受是对错误意识和政治愚蠢行为的检测,是滑向暴力与堕落本身的平面。”(185)再联系到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说法,“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108)大众沦为纯粹的“劳动者——消费者”,这意味着大众作为劳动者不仅仅延续了世代受压迫与剥削的命运,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制作和传播即时性、无深度的大众文化产品,大众对政治与社会的严肃思考在消费过程中被“伪艺术”提供的快感享受所取代,大众体验快感的过程实质就是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断再确认的过程,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对大众的压迫与控制因而得到隐瞒,统治体制因此得以延续对大众的管控。正因如此,阿多诺论述的审美乌托邦不仅保留了苦难历史,而且回应以及转换历史记忆的诉求。正如前文所引用的祖德瓦特的观点,否定辩证法构成了阿多诺通过艺术阐释真理内容的哲学方法论,参考阿多诺的哲学思考,“为苦难发声的需要构成了全部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作为客观性由主体所承担;主体最主观的经验和主体的表达被客观地传送”(Negative
178)。阿多诺该段论述是在探讨思想如何才能有效抵抗既有意识形态法则对主体意识的控制,受难记忆得以被客观表达,体现了客体优先性的否定辩证法原则,表现为对预设的总体性法则和既有的思考习性进行抵抗,阿多诺因此认为受难记忆正是真理内容的重要构成,而受难记忆得以被有效地表达的最恰当、最有效的形式就是能够与现实的社会体系保持距离的自律艺术。换言之,受难记忆构成了艺术具有真理内容的前提。那么,艺术又是如何在文化政治的维度进一步转换记忆的诉求?针对艺术介入的目标,阿多诺指出,“介入的目标是转变处境的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在这个程度上介入倾向于成为美学的本质范畴。”(Aesthetic
Theory
246)至于艺术有效介入的方式,阿多诺则认为,“即使艺术的形式特征在政治范畴不能轻易阐明,尽管如此艺术中的一切形式具有可延伸至政治的实质含义。新艺术所真正地希望的形式解放,所有社会解放转为密码来保存,因为形式——尤其是所有事物的社会性联系——在艺术品中表征了社会关系;这是解放了的形式让现状憎恶的原因。”(Aesthetic
Theory
255)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内在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质,受难记忆的诉求如何转换需要从审美乌托邦包含的内在性与社会性的辩证关系上理解。一方面,艺术的真理内容具有逾越内在审美结构的文化政治诉求,受难记忆触发的审美救赎并不会止步于艺术表征,而且包含了批判造成受难历史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而利用艺术的虚幻性特质对潜在乌托邦进行构想;另一方面,阿多诺构想的审美乌托邦的社会诉求,却又是通过将自身完全局限在艺术形式范畴予以实现,通过与现实相断裂的艺术形式层面的激进改变表达否定性的政治取向,即表达实现一种幸福生活的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性体现了阿多诺审美乌托邦思想的毫不妥协性与激进性,因此被祖德瓦特批评为“使艺术真理成为少数人的秘密”。换言之,受难记忆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承认历代受难者地位与价值这两个方面的诉求,最终在审美乌托邦的论述中被转化为一种以绝对否定性为特征的认识论话语,借助艺术形式的变形表征外部世界的不人道,通过预示幸福的承诺没法实现的前景展开社会批判,却不涉及任何具体形式的社会革命或改良实践。同时又因为这种审美认识论话语建立在跨代际的受难记忆基础之上,因而具有从伦理维度出发重建主体性的诉求。阿多诺在反思本体论与存在论哲学时认为,“这个事实是主体变成一种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的目标性、功能性的语境,缓和了主体所承受的苦难。”(Negative
667)阿多诺将本体论与存在论贬低为“命定的辩证法”,认为两者引导主体对既有统治秩序表示顺从,并进而遵循启蒙现代性的发展主义逻辑为统治者对历代受难者的压迫事件进行美化与辩护,这将导致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当下不断被重复确认,个体的主体性日益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审美乌托邦的否定性论述意图批判一切虚假的幸福,受难记忆构成的真理内容通过艺术形式启示大众,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包含的压迫历史的回忆,瓦解了工具理性的神话,促使大众反思苦难及其背后以总体性为运作准则的社会机制,在同一性思维模式清除主体性精神的背景下,重塑具备自发行动能力以及自我反思性的独立主体意识。总体而言,在阿多诺的视域下,受难记忆的诉求在审美乌托邦的视野下被转换为一种伦理维度的认识论话语,在涵盖文学、大众文化、音乐等领域的广义文化维度,通过悲悼历代受难者和反思导致苦难的思维逻辑和社会机制,进行以重建主体性为目标、以否定性为思辨方法的意识形态批判。阿多诺在审美乌托邦对记忆诉求的转换策略,有必要与本雅明做对比,本雅明构造了“辩证意象”的理论概念,称之为“停顿的辩证法”(The
Arcades
462),辩证意象是由过去对于无阶级社会的期待与当下的生产力大发展构成的梦幻二者之间以闪现的方式构成、产生,这是针对支撑启蒙现代性的线性发展逻辑的中断,中断的瞬间是弥赛亚现身的时刻,这将是社会革命的发生并进而建立全新政治契约的契机,历代受难者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将在神学乌托邦中得以实现。本雅明将受难记忆视为神学救赎发生的前提,并将记忆的诉求转化为直接的实践行动,通过社会革命制定全新的政治契约。在实践层面阿多诺则与本雅明鲜明持相反立场,阿多诺反对将记忆的诉求转化为任何形式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而是将记忆的诉求彻底局限在认识论话语领域,通过以贝克特的创作为代表的“反艺术”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中介,将悲悼先辈受难者的伦理关怀通过艺术形式转化为对当下社会制度的批判,重塑具有遵循客体优先性原则并具备自我反思精神的主体性。结 论
如何评论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对记忆伦理的纳入与转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其一,在批判理论范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集团以大众文化为工具,在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与享乐欲望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人们的知识构成与情感结构的塑造,个体因此在以柔性手段为主的统治模式下往往以自我规训的方式遵循既有的行为法则与思考模式,这是主体性死亡的境况。个体只有在面对阿多诺所推崇的自律艺术的时候才可能重新恢复自主感知能力,走出对统治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认知界限,在受难记忆的基础上实现独立主体性的再生成,这是阿多诺所期待的乌托邦时刻。从这个角度看,阿多诺《美学理论》所展现的视野大幅超越了现代主义美学或者形式美学的范畴,强调艺术作品需要以审美形式表达苦难,借鉴本雅明的神学方法论思考救赎记忆对当下的意义,将记忆的诉求转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并重塑主体性,受难记忆构成了审美乌托邦以间接的方式关注、介入现实的中介,这是在“伦理——政治”的维度回答了奥斯维辛之后艺术何为这一时代命题,也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重要遗产。
其二,在如何理解奥斯维辛事件的范畴,一直以来战后欧美学术界对于如何反思奥斯维辛的灾难提出了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阿多诺将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受难记忆纳入审美乌托邦的构想中,展现处理奥斯维辛事件的另一种思路。阿多诺将奥斯维辛事件置于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予以理解,将奥斯维辛的屠杀视为工具理性发展极致的必然结果,因而奥斯维辛事件并非现代性进程的逆流,而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同一性逻辑。正因如此,阿多诺没有把奥斯维辛事件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纳入批判现代性的视野之中。一方面,阿多诺将奥斯维辛事件和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进程的压迫事件共同视为需要艺术表征的“世界历史的苦难”,将对奥斯维辛悲剧的反思引申到对历代先辈的受压迫命运的悲悼,从伦理维度拓宽了奥斯维辛事件的思考广度。另一方面,阿多诺创造性地在理论层面提出将受难记忆转化为自律艺术的形式,而非成为艺术作品所书写的内容,这是因为他忧虑受难历史会沦为文化工业用以牟利的素材,或成为非理性的政治动员的材料。而大众在体验以策兰、贝克特为代表的“反艺术”的审美形式过程中将受到震动,从而将以更主动的姿态读解艺术所表征的苦难,这是批判统治意识形态和想象乌托邦的契机,也是从审美政治的维度对奥斯维辛事件的拓展。
注释[Notes]
① 参见:赵勇:“艺术的二律背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一种解读”,《外国文学评论》3(2015):178—96。
② 参见单世联:“‘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文艺研究》7(2015):15—2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orno,Theodor W.Aesthetic
Theory
.Eds.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Trans.Robert Hullot-Kentor.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2.- -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Ed.Christoph Ziermann.Trans.Nicholas Walker.Cambridge and Malden:Polity,2017.- -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Henry W.Pickfor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
.Trans.E.F.N.Jephcot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 - -.Negative
Dialectic
s.Trans.E.B.Asht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 - -.Notes
to
Literature
.Vol.2.Ed.Rolf Tiedemann.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 -.Prisms
.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泰奥多·W.·阿多诺:“自然历史观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张亮译,张一兵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3—46页。
[- - -.“The Idea of Natural History.”Register
of
Critical
Theory
.Trans.Zhang Yibing.Ed.Zhang Liang.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2007.233-46.]Benjamin,Walter.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John Osborn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8.Bloch,Ernst,et al.Aesthetics
and
Politics
.Ed.and Trans.Ronald Taylor.London:Verso,1980.Bowie,Andrew.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and Malden:Polity,2013.Buck-Morss,Susan.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New York and London:Free Press,1977.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Horkheimer,Max,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Qu Jingdong and Cao Weido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黄圣哲:“历史作为自然史:论阿多诺的历史理论”,《哲学与文化》4(2016):59—75。
[Huang,Sheng-jer.“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On Adorno’s Theory of History.”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2016):59-75.]Petrucciani,Stefano.“Adorno’s Criticism of Marx’s Social Theory.”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Praxis
:Beyond
Reification
.Surrey and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5.19-32.Weitzman,Erica.“No Fun:Aporias of Pleasure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The
German
Quarterly
2(2008):185-202.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Wellmer,Albrecht.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ism
:Criticism
of
Reason
according
to
Adorno
.Trans.Qin We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3.]Wezel,Lucie and Jean-Baptiste Vuillerod.“La Réorientation Matérialiste de L’esprit Crit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TW Adorno.”Le
Philosophoire
1(2017):19-50.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Wolin,Richard.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Frankfurt
School
,Existentialism
,Poststructuralism
.Trans.Zhang Guoq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0.]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Zhao,Jingrong.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Zuidervaart,Lambert.Artistic
Truth
:Aesthetics
,Discourse
,and
Imaginative
Disclos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