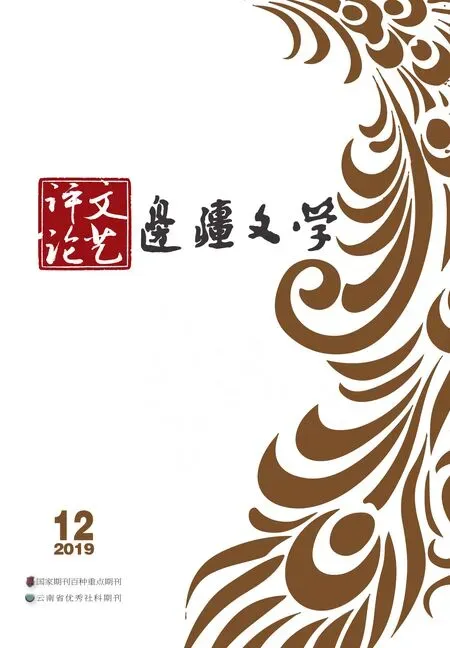除渣与去蔽
——关于文学与民间记忆的思考
刘川鄂
1.民间记忆可以丰富历史,但不能取代历史
民间与民间记忆,已成为近十来年文化、文学界的热门话题。陈思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民间”概念,提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民间”概念的出现和受追捧,体现了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受挫后知识分子寻找新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努力。虽有泛滥之势,但似乎有学术层面上“去政治化”的功效。
但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民间热”情形要复杂得多。当下中国经济腾飞,国人自我感觉超级膨胀。部分文化人越来越注重本土化,越来越强调地域性、民族性。有人鼓吹汉文化的伟大复兴,有人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签发文化复兴宣言,有些文教管理机构和学界人士发倡议编教材要中小学生尊孔读经。“民俗、民间文化热”“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等,也有这样的背景支撑。也正是在复兴中国文化浪潮的背景下,文坛兴起的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和“中国经验”热,包括诗歌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民间”写作、“民间”诗刊。由于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得部分国人急于从文化上证明自己,便出现了把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混同于民间文化的倾向。所谓的“民间”立场、“民间”精神,俨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文化“真理”与畅通无阻的艺术评判标准。
我同意陈思和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三大格局的划分,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它们相互独立又不断变动。90年代民间理论的最初倡导者们立意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话语霸权改为对话姿态。但我认为,中国启蒙话语空间始终狭小,从未“霸权”过。官方文化利用民间文化排斥精英文化倒是普遍情形。民间文化在许多时候与官方权力话语结成同盟,其中还保留了大量旧文化残渣。
作为一场以精神价值重建代替直接的社会改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价值进行了多方面审视,其中也必然包含对民间文化的审视。民间文化中保守和落后的一面在李大钊、鲁迅等笔下受到淋漓尽致地批判,这种批判在今天仍然是有力量的。“审父”的新传统薪火相传,仅文学领域而言,无论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还是40年代工农兵文艺运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热,还是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潮;无论是前半个世纪的“张恨水热”,还是后半个世纪的“金庸热”……当然还有世纪转型期的“民间热”。表面上看,“民间”始终处于潮流状态,但其间或隐含或彰显的对“精英价值”的贬抑倾向、“反智情结”,一直受到知识界的质疑。其“泛民间化”和“圣民间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一直受到知识界的警惕。
在世纪转型期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论者看来,走向民间和认同大众,不论这种认同最终指向的是以传统农村文化形式为主体的民间俗文化还是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都市大众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性受到伤害。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在彻底融入“民间”之后便会失去自身的立场。完全认同“民间”的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侏儒化”。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实境和语境绞织的当今中国,许多陈旧观念和传统文化依然扭曲着自由人性,以“民间”的名义否定启蒙、否定知识分子自身价值在现实中危害甚大。
近年来,关于民间记忆的论著也成热点。有人写作《野史记:200年来中国的一些民间记忆碎片》在网上发布。陕西合阳县农民侯永禄,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以《农民日记》为名出版。很多媒体从体制、军事、经济、外交等总结1949-2009年这段历史。比如《南都周刊》选择用私人生活史的视角管窥时代的变迁,以“小我”观“大我”,志在留存某些属于民间的历史和记忆;一本题为《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的书,有感于中国历史常常缺乏小人物出镜,正书有余,侧记不足,后人在了解历史时缺乏最基本的参照,也使历史缺少了很多应有的生趣,专门选取记忆深处的那些民间往事,也不失为“民间记忆”的参照文本。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总结中,也有不少鲜活的“民间记忆”论著。《1978-2008民间记忆》从春节联欢晚会、高考试题到《少林寺》,关注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关注这30年的歌曲、民谣、小说、影视、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更关注民间视野中呈现出的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事件;同样写近30年,《新京报》打破多数报刊营造喜庆气氛的应景式报道模式,通过“民间”视野反映大事件,解读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征程。尽管这些论著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某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民间记忆,丰富多彩、鲜活生动,已构成后人了解现当心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珍贵文本。
民间记忆相对于官方记忆而言。显然,这些“民间记忆”文本,具有不同于“官方记忆”的文体价值和超文体价值。当然,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此不惶多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重提并强化民间记忆,是中国公民生活空间扩大、言论自由度提高的体现。
我认为:记忆是一种泛历史,除了官方和民间记忆,还应有史家记忆,即现代历史学家客观理性的记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中国古代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与此相关,证明本王朝的合法性的方式是通过修史证明前王朝的非法性,充满了有意无意地误释和过度阐释,大量“民间记忆”被遮蔽,留存的则被改造和合流。从“史官”到“史家”,剥离其依附性,独立客观记载和阐述历史,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史家记忆是现代民主制度建设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化的产物。美国学者费正清领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学者许纪霖、陈达凯合著的《中国现代化史》等著作,尽可能以客观、中性的史家立场阐述近现代中国历史,其价值是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不可取代的。不能用民间这个大箩筐把知识精英和所有大众都装在一块。
民间传说、民俗是民间记忆的载体,它扎根于社会生活,以心口相传的形式绵延至今,反映了普通民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比如,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许多同类故事在众多民族众多地域(包括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美洲等地)都普遍地流传着,而且有些故事与在我国流传的故事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例如多日并出、射日射月、再造日月、洪水泛滥等故事,与流传在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美洲等地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如出一辙。显然,这些故事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带有蒙昧时代的印痕。作家的创作不是形象科普读物,但无论如何也不宜对愚昧迷信唱赞歌。再如,充斥着时下中国荧屏中韩剧中,经常出现胎梦的场景,这也是民间记忆在现代传承的方式之一,是韩国文化的一个侧影。深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文化浸淫,香火的延续也成为韩国民众头等人生大事,这自然深埋每个人的心底,转化为一种心理诉求。这种心理诉求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得到释放和安慰,胎梦就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人们通过胎梦,仿佛得到了上天的一个允诺,从此可以放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孩子,这种心理暗示的效用是巨大的。这样的心理暗示无疑能给人巨大的安慰,从而使其成为一种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成了为韩国民众所信服的社会信仰之一。民族的心理构成有着古今的贯通性,而梦作为预示性的先见被韩国民众广泛接受并传承至今。
民间习俗和民间传说化作的民间记忆,成为民间文化价值观,普遍存在善恶报应观、侠客崇拜和清官崇拜、穷人聪明富人愚蠢的精神胜利法、神秘风水观和各种反科学的禁忌、忠孝节义价值观等。它蕴含的独立、自由、理性、民主等现代价值观是极为有限的,自“五四”以来就遭到知识者的批判,今日“民间文化”的提倡者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应对。
民间记忆可以丰富历史,但不能取代历史,更不可以取代史家记忆。仅就历史记载而言,民间记忆是鲜活的,充满了原生态的质朴,但也可能是狭窄的有害的。有渣滓,知识分子要“除渣”,有蒙蔽,知识分子要“去蔽”。
2.作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
民间传说、民俗是民间记忆的载体,它扎根于社会生活,以心口相传的形式绵延至今,反映了普通民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民间记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很多优秀作品都从民间记忆中获取灵感,并赋予民间记忆以鲜活的生命,让民间记忆重生。如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于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汉民族神话叙事史诗《黑暗传》之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有关汉剧的传说故事之于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等等。
张炜一直醉心在“民间世界”里,他说:“我以前说过: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和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后一代人会把他视为不朽者,就像他依附的那片土地山脉,那个永恒的群体。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是他们发声的器官。”自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也被认为是具有真诚而朴素的民间写作立场的作家。他努力拨开官方记忆对民间的某些遮蔽,夸饰民间社会中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力图勾连民间精神与当代人格的相通之处。《檀香刑》显示了莫言在民间文学上的自觉求索。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很坦率地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语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他说,他的创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是“撤退得还不够到位”。《檀香刑》引入“猫腔”的韵律及调子,便是一种独创。
可见,民间和民间记忆是他们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即使是重要的,也不是唯一的。如果不加甄别,就会审美失范。《檀香刑》从头到尾对酷刑的描写,特别是赵甲500刀凌迟处死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的描写,长达20页。如此着墨渲染酷刑,宣扬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对暴力美学的过度欣赏,与他对民间记忆的盲信相关。《檀香刑》显现了莫言和中国某些作家在思想能力上的缺陷和在精神向度上的偏差,迷失于“古代”而放弃了“现代”,混迹于“民间”而放弃了“审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有区别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指向庙堂的威权和象牙塔的清高,其低姿态是有意义的。但是作家从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是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民间,也并不能否认和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心理上将自己放在一个和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并不是说他可以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批判和消解作家以往的精神贵族心态,也并不是要放弃文学在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如果忘记这一点,在“民间写作”的旗号之下,就可能掩盖着一场精神的大逃亡。
作家不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民间记忆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和想象力,但伟大文学之伟大与是否表现民间和民间记忆并无必然关系。事实上,很多作品即使是民间题材作品也并非一味认同民间记忆,某些指涉民间记忆的文学倒是对民间和民间记忆有所审视和提升的。在这方面韩少功是个自觉的清醒者。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在民间记忆里他们是刑天的后裔,但“鸡头寨”却是个愚昧落后的所在。显然,韩少功在这里不是迎合,而是否定了民间记忆。带着思想审视民间、挖掘民间记忆中的人文含量,是韩少功超于莫言之处,也体现了审视民间与“圣民间化”之区别。《马桥词典》集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115个日常用词,糅合了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表现了儒家文化如何融入民间惯常的思维方式扭曲人性,道家文化如何进入民间生活方式并强化为民间记忆形成了保守的人生。在对马桥的民间记忆的解构中,在对每个词语的文化审视中,揭示民间在历史发展中的负面影响。《马桥词典》“每个故事中都浸透着韩少功特有的沉思风格”。“作品处处展示出叙述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思”。“马桥人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本书是一部杰作”。“贯穿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对当地方言在官方语言影响下所发生变迁的分析。……这本书充盈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内涵。”从这部作品所获得的国际声誉来看,其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俯瞰民间审视民间而非仰视民间的结果。
如果说“泛民间化”是某些知识界人士的“说理策略”,那么“圣民间化”则是创作界的一种偏识和误植,值得辨析。跟很多“民间热”的反对者一样,我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的岗位置换到“民间”,降为“民间记忆”的打捞者和赞美者。因为民间也是鱼龙混杂的、民间记忆中也有污泥浊水,民间文化形态中所蕴含的独立与自由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很多作家、知识分子来自于民间,但他已部分地从民间分离。源于民间、高于民间,此乃作家之为作家、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不由分说地“倒向”民间,既不能救人,也迷失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不能在摆脱了官方记忆图说者的角色后,又盲目地在民间记忆中乞灵丹妙药。
3.对民间记忆的审视与提升
一味认同民间和民间记忆,写野史、写世情民俗、写民间秘史,写风俗展览,缺乏审美价值评判,是当下创作界“民间热”及与之相关的“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中国经验热”存在的带倾向性问题。可见,当下中国作家面对民间记忆,确有审视与提升的必要。
恐怕当代中国很少有作家能认识到,我国的每一处地域文化和“民间记忆”都有它的限制,都有其负面性。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我们的汉语里包括方言里,在我们各民族各地域里,在我们的民间记忆里,有不少与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适性价值不相兼容不可通约的愚昧落后的东西,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有着三千年太监制度的民族、一个让女人缠足九百余年的民族、一个强行让男人蓄辫子二百多年的民族,它有很多反人性反人类的文化毒瘤,有很多负面的“中国经验”和“民间记忆”。越强化它,越夸耀它,就可能越病态。
比如:“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早已入选了经典的孝顺教科书而家喻户晓成为生生不息的民间记忆。虽经新文化运动打伐多年,但在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复苏,很多省市以弘扬“孝文化”为文化强省(市)之重头戏,一时大有孝文化泛滥之势。孝本是指未成年人和青壮成年人对已衰老的成年人的尊敬和奉养,这作为一种对弱势人的关怀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等级化的道德律令,是在一种不平等的身份和心态中进行的,它往往以下一代的牺牲为代价,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关怀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利于现代个体人格、公民意识的培养。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政之本,弟子曾生说:夫孝为放之四海皆准之理也,正是这几句格言让中国男人跪了几千年,低头了几千年。也由于这几句“政治学原理”培育了千万个政治白痴。“孝”这种古代文化资源,明显带有负面价值,不可能进行现代性转换。对于《孝经》这样一部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书,有人还主张让小学一年级学生诵读学习,成为世世代代的民间记忆。
中国人以“孝”为人伦之本,以“忠”为君臣之本。“忠”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地服从,是愚忠。它不是建立在对真理、信仰的忠诚基础上的上下级关系,更没有平等互爱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忠诚不可化约;民间对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津津乐道,视为男人之男子汉气度的典范。民间充斥着忠义名义下的侠义精神、江湖豪气故事,它明显不利于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现代法治制度的建立。至于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更是对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妇女的绝大不公,扭曲人格、漠视快乐、没有平等、更危及生命。在自古到今的民间故事中、在美景传说中、在旅游文化的宣扬中,类似的褒扬汗牛充栋、不绝于耳。打“孝文化”牌、不加分辨地弘扬“忠义”“侠义”文化,完全是历史的倒退,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眼光、现代的价值观去正视它,反思它,不留情面的解剖它,挖出它的毒瘤。
在作家与民间关系上,鲁迅仍然是当代作家的榜样。鲁迅认为“刚健、清新”的某些民间文学作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他对绍兴民间记忆中“无常”与“女吊”两个鲜活的鬼形象的喜爱,体现了他与“下等人”生命意识接通的底层情怀,和对权力体系的彻底反对的反抗意识,与先驱者的启蒙理性和反封建向度相契合。而他对“女吊”的喜爱则体现了“精神界之战士”的反抗精神和独特的生命哲学。民间文化是鲁迅对封建正统文化进行评判的镜子,但也是他批判的对象。《狂人日记》直陈包括“吃人”的民间记忆中的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祝福》中揭示了“捐门槛”的民间记忆如何更深地导致了祥林嫂的悲剧,《阿Q正传》中未庄老百姓把“自由党”记忆为“柿柚党”有着无比丰富的历史含量和痛彻的批判。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对构成民间重要记忆的《二十四孝图》的批驳淋漓尽致,在诸多杂文中对民间负面文化的批判也是鲁迅的显著特色。他启示后来者,对民间记忆,要理性地甄别、清醒地审视、自觉地提升、坚定地超越。
1930年,闻一多把刚落成的武汉大学新址由“罗家山”和“落驾山”改名为诗情画意的珞珈山,这一改,否定了民间文化的世俗色彩,去除了代表皇权文化的专制意味(民间记忆中也有大量皇权文化印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面对民间社会和民间记忆仍有启迪意义。对那些早已化为民间群体意识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民间记忆,21世纪的中国作家应保持清醒的警惕。当代作家、知识分子当学鲁迅、闻一多,你的使命不是打捞,而是审视。不是认同,而是冒犯。
【注释】
[1]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2]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3] 参见网络论文《民间与知识分子:一场论争折射出的思想中国(一)》,出处不详。
[4] 孟云剑杨东晓胡腾:《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中信出版社2009年。
[5] 陈煜编:《1978-2008民间记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6] 该报道将结集成六卷本的《日志中国》丛书,目前已出版四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
[7] 冯天瑜:《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8] 参见王红旗孙晓琴:《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3年8月。
[9] 吉黎霞:《民间记忆的现代传承方式——以韩剧胎梦为例》《电影评介》2007年21期
[10] 张炜:《写作是迎送时光的方式》,《济南时报》2007年6月15日
[11] 陈离:《是“民间叙事”,还是精神逃亡?——从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说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2] 何也:《韩少功〈马桥词典〉在西方引起关注》,《羊城晚报》2004年3月6日
[13]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岀版社1981年版,95页。
[14] 参见刘希:《压抑,释放和狂欢——鲁迅民间记忆中“鬼世界”和“死后想象”》《作家》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