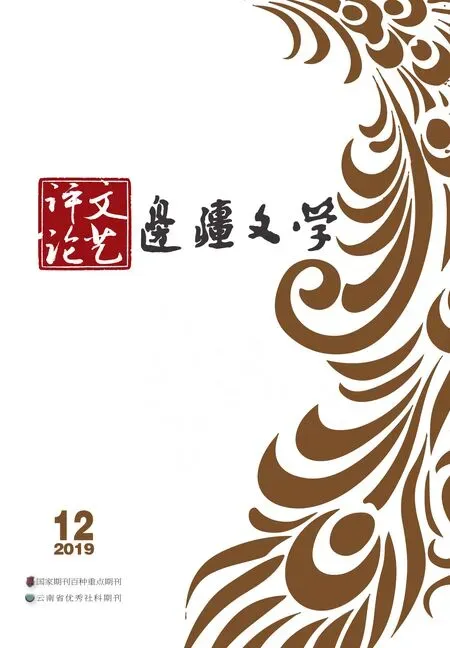重新认识父亲
——读邵丽的短篇《天台上的父亲》
何微
邵丽的短篇小说新作《天台上的父亲》发表于《收获》的2019年第3期,小说讲述“我”的父亲欲自杀及跳楼自杀之后,“失父”在家庭内部引发了儿女们的生活动荡和情感挣扎,并开启了一场“寻找父亲”的心路历程。以父亲自杀作为故事主线,文本自带尖锐度和敏感性,而作家深切而丰满的人文关怀更是灌注其中。从小说技艺层面来说,《天台上的父亲》能够称得上是一部精工的作品,这种精工来自于小说的结构,小说分为九个部分,小说始终以第一人称“我”,即父亲的二女儿为叙述窗口,并采用大量自由直接引语,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内心情感均有交代,进行多线索交叉叙述。作家以其高超的文字整合能力将家庭网络连缀出来,让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却又自持烦忧,映射出一个多子女传统家庭的精神内核形态——形散而神凝,整体文本散发出一种“复调”对话的魅力。
关于“父亲”的叙述
对“父”这个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又部》中作如下解释:“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可大致理解为,手里拿着棍棒教育子女守规矩的一家之长,即为父。故此,父亲便被赋予了传统固守者和旧有秩序维护者的文化隐喻色彩。父辈权威深深地压抑着子辈,这种固化的尊卑秩序结构在父亲与儿女之间形成一条隐形的深壑,两岸的人各有怨怼和期待,却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平等和谐的沟通,心结难解。 无论是冰心笔下小诗里那如大海浩瀚,如山坚固的父爱,还是朱自清的《背影》中塑造的那位笨拙地翻过车站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关于父亲的经典叙述,总显出类同的静默、难解、沉重的调性。
在《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对于儿女们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在“我们”兄妹三个的童年时代,父亲是完全缺位的,并且后来这段父爱缺失的历史,成为整个家庭秘而不宣的禁忌话题,没有人谈论它,“那样对他会有一次结算,但那是他作为一家之尊不能接受的”, “只是我们和父亲之间,这种隔膜,再也不可能擦干净了”。读者能够轻易窥见,在儿女们与父亲之间其实缺乏真正的水乳交融的亲情联络,仅存着冰冷生硬的血缘捆绑,这样的亲情没有一丁点以理解和包容为基础的“爱”在其间,以至于在父亲退休罹患抑郁症之后,最懂他的人、最牵挂他的人不是同一个屋檐下的儿女们,却是他的挚友和他曾经带过的下属。直至父亲自杀后,父系权威伴随着父亲的肉身消亡而失效了,在沉痛混杂着解脱的“失父”情绪中,儿女们反而获得了某种重新认识父亲的契机,并进而生发出想要走近父亲内心世界去看一看的情感渴求。父亲死后,子女们一面通过回溯各自的记忆,一面在母亲和旁人的叙述中展开对真实的父亲的追认和寻找。
被母爱书写遮蔽的“父亲”
在传统的家族叙事中,“父”与“母”作为同样重要的伦理角色,反映在文学中有不同的能指,往往也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大众对于文学作品中“父”与“母”的期待与想象更是完全不同。甚至在反封建年代,赞美“母爱”的文本也成为青年一代反父权专制的策略之一。于是形成了这样的书写传统,即较之于坚固恒久的伟大“母爱”书写,对父亲与“父爱”的表达往往因为“母爱”光环的遮蔽而显得更为单薄、内敛、含蓄。小说虽然命名为“天台上的父亲”,但正如前文所述,其实父亲对于子女们来说,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父亲或许只是笼罩在父系权威之下一个有名而无实的身份符号,而希声的母亲则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她是谐和父亲与子女关系的那味良药,也能成为关键时刻撑起家庭的中流砥柱。
在这篇小说中,“妈妈”在小说的后半段从叙事边缘逐渐移转到读者眼下,于是,一个外表柔顺而内心坚韧刚强的母亲形象慢慢明晰起来。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恰逢中秋节,“妈妈”组织了一场家庭聚会,然后她向始终走不出“失父”阴影的儿女们坦白了关于他们父亲自杀的关键细节,“他去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只管让他走吧,看到底会怎样。”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知晓一切的“妈妈”,决定默然扛住一切,既成全了父亲,也让儿女们得到解脱。这个颇具“反转”意味的结尾,无疑构成了凸显“妈妈”理想形象的高光时刻,顺其自然将叙事的情感浓度推至高潮,显露出“妈妈”这一角色所包蕴的复杂厚重的情感力度,且一下子就把前文所铺垫的儿女们各自悲痛、自责,混杂着解脱的情感表达,如掸灰一般轻轻掸开了。无论“妈妈”所作的坦白是事实,还是善意的谎言,都并不重要,它似乎为父亲自杀这件事画上了句点,只为将笼罩在“失父”阴影中的家庭从消沉中打捞出来。如此的举重若轻,让笔者不自觉地联想到诗人里尔克著名的《秋》里有这样一句:“然而有个人,用她的双手,无限温柔的捧接万物的坠落。”母亲交代了她伟大的成全,是整个小说极为出彩的桥段,但同时有个重要的文本细节不能忽略:母亲在坦白之前,将一块弹片拿给哥哥看,这弹片是从父亲心脏旁边取出来的,曾差点要了他的命,于是父亲将它珍藏起来。每当家庭遇上困难的时候,母亲想不开,父亲便会拿出这块弹片激励她,“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是父亲支撑着母亲,共同携手挨过生活的难关,“要不是这,我真活不过来,哪还能把你们几个养大”?可见,父亲曾是这个家庭背后的精神脊梁,可在他生前儿女们却无从知晓。在“父爱如山”的文化传统和书写定式中,儿女对“父爱”的体认往往停留在父权的压制层面,而忽略了父亲那“润物细无声”的付出,其实润泽着家庭中的每个人,这种对“父爱”在认知和事实层面的错位,实属传统家庭土壤催生出的悲哀和缺憾。
寻求理想的“父亲”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四种“自杀”类型,包括自我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失范性自杀和宿命性自杀。而失范性自杀不同于“自我主义—利他主义自杀”,它取決于“社会如何规制个体的方式”,而后者取决于“个体依附于社会的方式”,进一步解释,“自我主义的自杀产生于人再也找不到生命存在的基础;利他主义的自杀则是因为这种存在基础对人而言超越了生命本身;而失范性自杀源自人的活动缺乏规制及其随后的痛苦”。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的父亲,由于退休脱离体制,失去了熟悉的生活重心以致陷入重度抑郁,即是典型的失范性自杀。父亲固然是死于抑郁症对他灵肉的摧毁,但同时在父亲生前并未施予他足够理解和包容的家人们,难道就能够完全免于良知与道德的诘问吗?在得知父亲意欲自杀之后,儿女除了对此感到困惑、恐惧之外,就只会笨拙地采用强制性手段(轮流监视,锁门)防范惨剧发生,却没有人尝试走进父亲隐秘的心灵世界看一看,也没有人愿意去倾听一个失意的退休干部有何个人意愿和情感诉求。与此同时,抑郁的父亲承受着不被家人理解的巨大孤独,最终万念俱灰,从天台上纵身而下。父亲为何自杀?也许孤独正是元凶之一。明明子女监守父亲,是为了保护他,结果反而加剧了父亲的孤独,最终恶化了事态,这便是一个异常真实的巨大讽刺。
“久病床前无孝子”,正如这句古话所揭露的冷峻事实——以血缘关系的强制捆绑和父系权威支撑起来的子女“孝道”,终会被病痛或是漫长的时间等现实因素击溃。在进步知识分子们高呼“破除传统封建教条”已足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一切思想和现实器物都被打上了“现代性”的名号,但是在这个男性中心社会中,多数的传统家庭仍然被父权思想的巨大惯性所统摄。贤良的母亲依然背负着“女主内”的社会期待,她们顺从、坚韧;不可违逆的父亲依然是强权和威严的代名词,他们沉默、孤独;而子女们仍深深感到那个代际鸿沟的存在,多数传统家庭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相较于幼时温情的港湾,更是一个知世后想要急切逃离和反叛的牢笼。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人与人相处中最可贵的理解、尊重和包容,无疑成为了稀缺品。基于此,鲁迅曾经提出的那个问题毫不过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今天同样需要继续追问,健康理想的家庭关系应是什么样?我们如何做儿女?如何做一位合格的伴侣?这些是值得所有人去思考和探求的问题。
邵丽这篇《天台上的父亲》,无意从哲学层面去严肃探讨“自杀是否正义”,但作者将“自杀”放置到普通家庭的情境中,且牵涉每一个人,如同把所有角色置于四面镶满镜子的房间,让读者可以辩证地审视“自杀”“失父”,亲子关系等颇具借鉴意义的现实难题,使得小说具有书写人生经验与构建社会伦理的双重品格。在小说结尾,听闻了母亲所谓的坦白之后,“我”认为这是对生者与死者最好的交代,小说以一句“的确如此,也不过如此”收尾,道尽了儿女对无法躲避的失父之痛的苦涩的认可。以女儿的视角为窗口,通过多方对话的复调叙事技巧,高扬母爱之伟大的情节作为助推,从侧面充分显影出子女对父亲既怨恨、歉疚又满怀依恋的复杂而微妙的情结,最终完成了对“父爱”的某种肯定和追认。在力图还原一位“真实的父亲”的同时,隐含作者似乎同时在寻求一位“理想父亲”。在传统的亲情羁绊、家庭伦理规约和尊重个体生命的选择之间,邵丽试图努力探寻几者融合的可能。新式文明社会的到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或许意味着人们将呼唤更为平等和包容的相处之道,以理解和尊重为前提的亲情关怀。所以,如何使僵化的亲子关系“破冰”,如何重新认识父亲,如何化解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教育所中面临的在场却又缺席的尴尬困境,作者通过小说发出了迫切且有力的叩问。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靠自己向生活交出圆满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