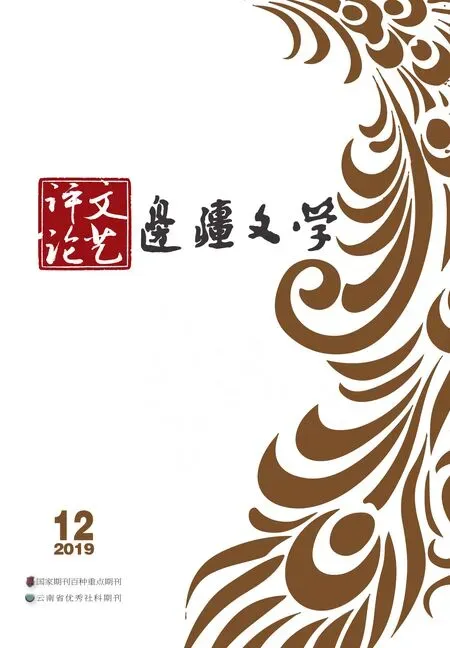描神绘形的语言魔力
——读余文飞诗歌兼谈其小说
杨荣昌
余文飞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多年来,他一直在基层生活,最初当小学教师,后来调到县城从事文艺组织和编辑工作,环境均没有脱离乡村和县城。这种通俗意义上的“小地方”写作,没有限制他的视角和思维,反而让他在一种紧迫感不太强的氛围下,从容悠游地阅读和思考,精心修炼文字的魔法。无论是写诗还是小说,都讲究创作的审美性,把作品当作艺术品营构,显示了鲜明的文体自觉。余文飞写了大量的诗歌,结集为《闲适的浪花》。这是一本勃发着青春心绪的作品,要么是个体的呢喃细语,要么是青年思考者对于社会现象的激愤与反思,均体现其写作立场和观察方式。众所周知,诗歌写作最能见出一个人的语言功力,在短短数行的艺术创造中,诗人的思想底蕴、文化涵养、语言修为,甚至人格节操都将尽显无遗,无法藏拙。这本诗集中,可见出诗人对于语言艺术的自觉修炼,诗歌想象奇特,用语活泼生动,有着灵动自然的艺术风格,显现出年轻写作者普遍的成长路径。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伤,可以促使诗人更加贴近这个世界的生命体温,激发出来自个体内部的某种感应能力,而敏感且善于表达,显然是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相比较那些抒发个人心绪、浅吟低唱的作品,余文飞接通了人类共通性情感的诗歌似乎更有感染力。在《闲适的浪花》中,有一组关于汶川地震的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视角的别致,语言的妥帖,情感的真淳,让人不由得为之感动。如《孩子,别哭》:“孩子,别哭/大地的颤抖惊扰了你梦中的小鹿/它们跑远了/驮着你的爸爸妈妈走上去天堂的路/他们不时回头看着你笑呢/他们在向你祝福”这是以成年人的口吻安慰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通过讲述一个童话般的故事,慰藉颤抖而受伤的幼小心灵。《爱人,请闭上眼睛》则转换了表达的对象,“爱人/再看你一眼我就离去/你用灵魂从地狱赎回我的生命/我绝不能让微弱的呼吸/辜负你一腔真情”。面对挚爱之人的离世,内心的伤痛无以言表,但是逝者远矣,生者还当坚强,无尽的悲伤只能压在心底,以故作洒脱的姿态面对亲人的远行。《来,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走吧!》继续转换着视角,这是孩子的呼唤:“爸爸,妈妈/您们咋都不说话/没什么好难过呀/还能有什么放不下/我们一生彼此牵挂/现在不都还在一起嘛”。诗歌以一个家庭共同走向死亡时的口吻来叙事,温情溢满文字,读者为之鞠一把泪。三首诗歌均书写生离死别,却以不同的表现角度,看似平静如水的语言,呈现了诗人的无尽悲伤。到了《我的眼睛模糊了,中国》,悲郁的情绪才得到了正面的宣泄,“大地的墓碑訇然洞开/我的那些数以万计的父老乡亲/甚至没来得及揉一下眼睛/问清楚是咋回事情/他们的天空骤然黯淡下来”。相信在这场引发全民诗歌热潮的写作中,诗人们大都来不及做艺术上的精心打磨,也难以再用隐喻、象征、通感等惯常的艺术手法表情达意,面对一个巨大而裸呈的灾难,唯有情感的真实是诗歌艺术的核心。可见,诗人并非没有能力呈现这个世界,也不是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麻木地闭上眼睛,他们需要的,是写作契机的出现。当重大的现实事件发生时,诗歌往往是最迅速、最直接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是为何像《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无名作者的诗歌会风靡网络,感动无数人的缘故。在刚刚发生的四川木里火灾中,30名消防官兵壮烈牺牲,四川的几位彝族诗人组织了一批诗歌,《凉山日报》文学副刊也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纪念专版,组织书写迅速,又普遍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我在自媒体转发这组诗歌时曾说这是本年度最好的诗歌,尽管不无夸张,却是满怀真诚的赞美。这说明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被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撞击了,它是面对巨大灾难时迸发的人间大爱,关于崇高、奉献、牺牲等词语的内涵再次被我们品味。在人类的共有性难题面前,作为时代良心的作家和诗人,不应缺席。
余文飞的诗歌语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即使锤炼诗意也不会玄乎高蹈,而是让每一个字和词都找到意义落实的地方。他的底层视角使得诗歌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这种悲伤不是靠呼天抢地来表达,而是始终保持冷静与节制,甚至不无黑色幽默,如《工厂卖掉了》《一个下岗工人》等,在略带戏谑的笔调中呈示出底层劳动者的荒唐遭遇,让人欲哭无泪。关注底层,是承认今日中国之复杂面貌,在高歌猛进的时代浪潮中,还有着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它们同样构成“现实一种”。这显示了诗歌写作的一种伦理,面对众声喧哗的文学潮流,是对社会底层苦难采取熟视无睹地轻盈掠过,还是扎入他们的生命深处,去感知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疼痛感,这是考验诗人的伦理选择。有论者曾精辟地指出:“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余文飞的这类诗歌不回避社会难题,也不懂得投机取巧去迎合权势的需要,而是将自己对于底层的痛感与悲悯用诗歌的方式呈现,在表达上采取客观而置身事外的叙述,任由情感自由漫涌,诗人隐身于文字背后,叙述自发生出力量。
对语言的把握还体现在他的小小说写作中。要在简短的篇幅中剖开一段横截面,需要有谋篇布局和较好的语言把控能力,不容许有丝毫的“注水”行为。小小说的简短与精炼,常有画龙点睛之功效,应是小说文体的基本训练。余文飞的中短篇小说集《牛抬头》取材于市井乡野,人物多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言语、行为,或庄谐杂出,或形神毕肖,贴着地道的云南地方色彩,以寥寥数语便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由于篇幅所限,这类小说无法展开更宏大的叙事格局,只能在深度与准确度上下功夫。这更考验作家对于社会的思考与判断,要么展示一种人性之复杂,要么显现社会之诡谲,读后让人会心一笑。小小说写作需要有扎实的写景状物、描神绘形的修炼,在更长的篇幅拓展和更丰富的世情百态的刻画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这些小说对于细节的雕镂能力是值得赞赏的,作者精心琢磨笔下的文字,与诗歌创作对诗意的凝练一样,让每一个字词都找到意义落实之处。由此观之,不妨把小说创作看作一门手艺,一门可以修炼与提升的技艺,它同样强调工匠精神,需要严谨细致的雕刻之功,一个细节的失真极有可能瓦解读者对小说的信任。而对于文字的苛刻,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文化自律。
诚然,作为读者,我们通常不满足于看社会的横断面,而是渴望在更纵深的历史维度与社会广度中,找到精神寄托之所,或者观照人生命运之路。也因此,学界常以长篇小说创作作为文学历史发展的高标。优秀的长篇,不是短篇和中篇的简单累加,而是应在结构、逻辑、气韵上的连接贯通,形成浑然一体的整全性构架。缺乏了整体感的长篇,是有缺憾的。就文体特征而言,短篇靠细节取胜,中篇以故事见长,长篇则应该写出人物的命运感。有了大量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实践经验,余文飞写出了长篇《马过河》,以故乡一个类似沈从文《边城》中风景秀美的山村为背景,展开他对于社会万象的解读。小说的细节依然精彩,语言富有生活的质感,但过度的注重叙述的生动性,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作家对于更宽广的社会画面的构造冲动,缺乏了长篇应具有的厚重感。希望余文飞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有所突破,创作出更有力度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