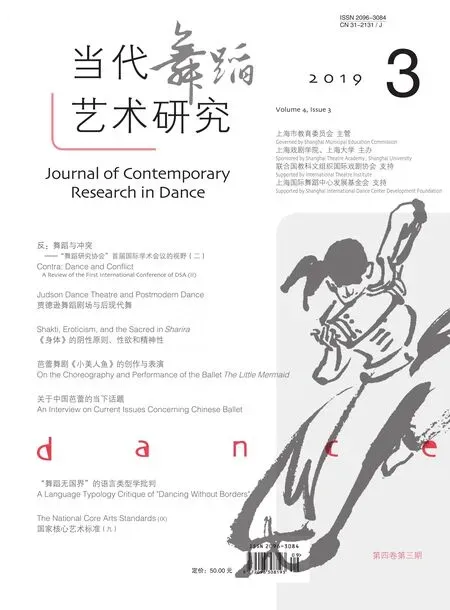关于莫高窟思惟菩萨的舞蹈创作
李婷婷 李 倩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直至晚清等十余个历史时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 000多平方米,彩塑2 400多身。敦煌壁画以呈现佛教文化、表达佛教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菩萨形象数以万计,几乎窟窟都有。莫高窟是世界上保存菩萨画像最多的佛教石窟,这些菩萨形象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因而被称为“敦煌菩萨”,并成为敦煌艺术的一大重要审美典范与艺术符号。
敦煌不仅是古代乐舞艺术的“博物馆”,同时也为当代的舞蹈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当代的舞蹈工作者,如何在不违背历史审美、贴近原型的宗旨下,将静态壁画中的舞姿形态、风格样式以及深层的意象,用舞蹈语汇进行活态创作?现以双人舞《思惟菩萨》①为例展开探讨。
思惟像是在5——6世纪的中国佛教艺术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思惟”从字面理解为思索、思虑;在宗教文化中,其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具有特定的宗教含义。在思惟过程中,世界万物都可集于内心进行思考,思考时排除万虑,达到空无所空的境界而集中心神。禅思的结果也是以思惟观想达到排除万虑、进入禅定的状态。
敦煌莫高窟第71窟洞窟北壁绘于初唐的“西方净土变”中的思惟菩萨图(见图1)②,是敦煌壁画中极少见的双菩萨思惟像,属于为佛陀和弘扬佛法作供养的菩萨类。两尊菩萨半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长发及肩、典雅端庄,其慈眉善目的面部神态以及倾头冲肋而弯曲的肢体形态,体现出典型的菩萨之美。位于图像上方的菩萨冲肋移颈、倾首立耳,似正聚神聆听佛法;位于图像下方的菩萨则右手托腮、低目颔首、支颐沉思,更体现出聆听的专注与投入。两尊菩萨的面部神态和肢体形态表现出了一种思修的境界与时空,这是静与境的完美结合,也是实与虚的交融体现。

图1 敦煌莫高窟第71窟思惟菩萨图临摹画
双人舞《思惟菩萨》以敦煌壁画中的菩萨形象为舞蹈语汇来源,根据壁画原型进行形态模仿,以艺术想象进行加工创作。由于壁画中只有少许姿态可供参考,因此,如何能充分地将静止的壁画形象“复活”,并凸显其艺术风格风貌,彰显形象独特的超俗气质,体现“象外之境”是舞蹈创作的难点。
一、展现特有形态,凸显作品主旨
在佛教文化中,造像作为传达宗教理想的重要艺术形式,其姿态、手印、服饰等都有很强的程式化规则,表达特定的宗教含义。因此,在塑造双人舞《思惟菩萨》的艺术形象时,遵循图像中具有特定含义的手形、姿态,有利于凸显作品主旨。例如,作品以佛教思惟像特有的“结跏趺坐”“头部侧倾”“曲肘支颐”等典型肢体动作为参照,展现具有特指含义的动作形态。又例如,在作品表现菩萨听法、思量及顿悟等不同阶段的情绪时,下肢呈现半跏趺坐(菩萨坐)、半跏趺倚坐、箕坐等坐相;躯干呈现微微前倾,头向左侧倾倒,左臂曲肘置于左膝之上,右臂曲肘托腮,敛目垂视,力争相对准确地把握敦煌壁画中思惟菩萨的禅思形象。此类姿态多次出现在作品的不同段落、不同空间、不同方位,以呈现思惟菩萨的沉思状态,强调并深化作品“思”的 主旨。
二、提炼符号语汇,营造佛法意境
佛教中不同的手印代表了不同的意义,是传达宗教含义的一种符号;其各自独有的样式,也是诠释佛法的哲学符号。思惟像是表现菩萨禅修思惟的形象,其造型的关键特征是“思惟手”。思惟菩萨呈现思惟状时,会出现侧头就手之态。“稍屈地水指向掌,余三指散,舒三,奇杖,稍侧头,屈手向里,以头指指颊”[1],这便是“思惟手”。在双人舞《思惟菩萨》中,用舞蹈展现思惟菩萨的思量状态时,多以“思惟手”表达主题意蕴,体现思修状态。在佛经中提到,当大众聆听了佛陀的说法后,经常出现欢喜、踊跃、油然而生的肢体语言。因此,该作品还运用佛手式、垂手式、合掌印、莲花式、听法式、接法式、悟法式等多种手部语汇来表达相应的内涵。例如,在作品第一段表达菩萨思惟时,肘部回折、弯曲,拇指捏于中指第二关节处,食指向上微翘,五指自然弯曲,托腮支颐,运用缓慢的运动节奏和静止的造型形态,呈现菩萨的思修状态,营造菩萨空、静、思的内心情境;在作品第二段表达菩萨辩法时,多运用佛手式、听法式、合掌式、捧托式等手形进行快节奏的交替变换,通过手形在急速节奏中的不断转换,来表达菩萨内心博弈的状态;在作品第三段表达菩萨悟法时,双手捧托仰视,用手部形态将内心接纳佛法的状态外化;在作品情绪达到高潮时,为表现菩萨觉法、悟法,则运用双人动作与姿态的配合,一人在前双手捧托接法,另一人在其身后,双手呈莲花状,缓缓升起,呈头顶生莲,寓意为思修得果,大智慧油然而生;在作品结尾,两人单手相交形成一朵盛开的莲花状,在缓慢步态下顺时针旋转,以体现“佛法”“智慧”“轮回”,从而达到通过符号语汇来营造意象空间的目的。
三、注重以气生韵,传递象外之境
古人认为,气的运行产生了天地万物和四时晨昏,而舞蹈则可催动阳气导发万物。在《思惟菩萨》的创编过程中,编导强调以气韵的顿挫、绵长等变化为身体舞动的内在核心,做到心为本,气为源,及全身,形成身体各部位点与线、收与放的律动,让气息赋予舞蹈生命。该作品主要运用了顿挫延绵和短促有力这两种呼吸方式。第一种呼吸方式气息深沉,发于丹田,自下而上延绵贯穿于胸腔,以气带韵,身体连动随之,最终达于头顶,随后下沉于胸口并顿挫发力,身体随气而微顿静止,再延绵下沉至身体松弛,气空、力弱而动作柔和。以此呼吸方式表现了思惟菩萨禅思冥想的瞬息静态,虚造佛国天境玄妙空灵的境域空间;在深沉延绵的气息中刻画菩萨端庄、深沉、恬静、高洁的气质,营造天地相和、人神互通,体现虚幻思惟与真实肉身合二为一的境界。第二种呼吸方式则气息存于丹田,经快速短促地挤压腹腔,使气息有力地呼出、吸入,带动身体形成相应精干有力的动作及韵律。通过急缓错落的气息表达思惟菩萨从听法到辩法再到悟法的不同思修状态,体现思惟菩萨内心的博弈过程及其后的蜕变与升华,并在酣畅淋漓的吸与呼中表达思修觉悟的状态与心境,从而使静态壁画形象犹如生命复苏般地鲜活起来,以气带韵,以韵达意,最终在作品中真正 “复活”。
四、强化以眼传神,塑造佛陀气质
眼神是生动细腻地传达内心情感的一大媒介,因此舞蹈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画龙点睛之“神韵”。敦煌莫高窟第71窟的思惟菩萨图以敛目垂视的神态呈现出菩萨的超凡脱俗、沉静冥思,这一神态既是具象形态的定格,又使意象空间无限延展。作品以此为依托,将定格的思惟神态进行艺术想象与加工,多运用垂视、斜下视、环视、仰视等眼部多方位神态的转换;收与放的交替配合,虚与实的视线变化,将内心情境转换于眉眼之间,表现出时而温婉柔静、时而肃穆明亮、时而深邃神秘、时而坚定平和的神态。通过不同眼神与肢体动作之间和谐统一的配合,力图塑造出菩萨脱俗气质的“神”,并将具象的“形”与虚幻的“境”融为一体,使观众眼中的思惟菩萨形象与思惟菩萨心中思修的佛法境界合二为一,从而在“神”的交流与感悟中产生情感互通,达到形神相容,即“神”(指眼神、神态)“形”(指菩萨形象)一体的审美境界。
五、扬“对称”之长,彰显传统之美
中国艺术中的对称正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体现。在敦煌壁画中彰显和谐对称的壁画图像比比皆是,无论在构图、数量还是形式、队列、形态等方面都流露出和谐的美学思想。莫高窟第71窟的思惟菩萨图亦然,图像中两尊菩萨倾首凝思,无论是头部倾倒的方位、表现思惟状态的手臂,还是下肢盘坐的形态等,无一不是表达两尊菩萨之间和谐一致的融合状态,从而投射出令人愉悦的和谐之美。作品依托于此,以表达“和美”为原则,利用不同的双人造型、空间调度、动作语汇、节奏变化来营造听法、辩法、悟法三个段落的不同情绪。在对称中树立听法悟法时心境的和谐,再运用不对称的造型队列和瞬息多变的节奏,来体现两尊菩萨之间的辩法状态,从而体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结 语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博采众长,是“丝路”多元文化艺术在交融和发展中产生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文明强大的文化基因,传承千载,影响至今。本文认为,以敦煌壁画为题材的舞蹈创作,亦是多元艺术形式的融合、独特审美的彰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此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除了要展现壁画中菩萨原有的姿态、形态和神态之外,更要在立象的基础上追求“象外生境”,使观者能观其形,临其境,思其道,并能在作品中感知永恒意蕴。
【注释】
① 双人舞《思惟菩萨》以敦煌莫高窟第71窟思惟菩萨图为创作题材,根据敦煌舞语汇及敦煌壁画中的原有造型进行菩萨形象的塑造,并运用空间调度和节奏变化来表现菩萨听法、辩法、悟法这3种不同的状态,从而展现两尊菩萨在佛国天境聆听佛陀说法以及遇佛得度的意境。该作品于2016年首演于西北民族大学,编导为李婷婷、李倩。
②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源: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10000_10000&sec=1564739736&di=1f95e528d7 b16c79e1bb80f493b56907&src=http://photocdn.sohu.com/20121225/Img3614591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