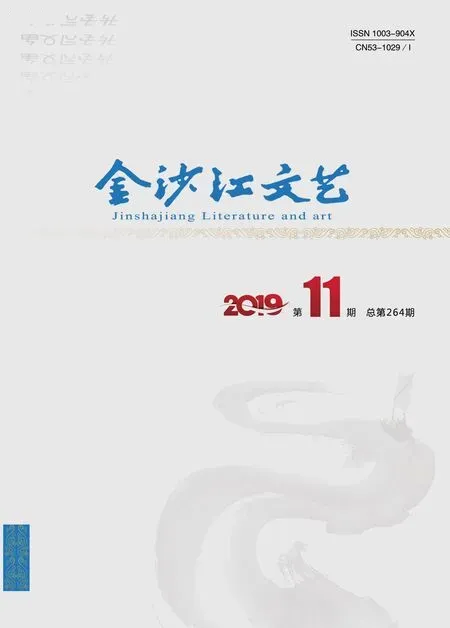橡胶林过冬
◎艾 吉
橡胶林在中越边境线上的金平县勐拉坝,一大片,是国营橡胶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省内外的农垦工人(包括大量的知青),一颗红心为祖国和时代的召唤热情澎湃,带着青春的梦想,怀着真正的“生活在别处”的神奇,在这个炎热、肥沃、适宜橡胶生长的美丽的边陲,扎下根来。浇灌狂热的心血,橡胶也似乎懂得为革命无私奉献,几年功夫就撑起了森林般茂密的浓荫。本来就让人销魂的傣族居住的勐拉坝,又增添了一道让人流连忘返的“仙境”。时间一久,胶场成了家园。走进人群,就像参加语言“博览会”,各种口音,各种声调,呜哩哇啦,几哩咕噜,软的,硬的,生的,熟的,绵长的,简明的,唱歌不像唱歌,交谈不像交谈,摸头不着脑,左耳听,右耳出,仿佛到了陌生的遥远的异国,然而又使人胸中涌起无限亲切,这是我生活的这块土地的家门口,那些远方的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如今跟我们已经融为一家人。
我生性爱四处转动,尤其爱跑进大自然,傻乎乎的其乐无穷。
我到勐拉坝,在无数次惋惜地错过橡胶林后,1997年的冬天下定了去住上几天的决心。
友人南马辞去公饭——在橡胶厂(准确说是制胶厂)干活命的事儿。他妻子的父母一家子就在那里安家。他们也是闲下来的农垦工人,说着我听来有些吃力的外地话。之前,南马来信告知我,那里如何如何,一大堆空洞美丽的词,描绘得远离尘嚣和世俗纷扰,生活中四处可见的愁眉苦脸跟这儿无关,引人尽早上钩的。他承包厂里的养猪场、鱼塘,随便交点承包费。这不失为一种断绝退路后先站稳脚跟的方式。制胶厂在勐拉坝边上橡胶林里面,跨过藤条江几步便到。
我到时,老朋友穿着高筒水鞋,正在清扫猪圈。我跟他约好了大体时间,却没有告诉他具体的时间。一步入胶林,我听见了鸭子“嘎嘎嘎”地高叫,是唯一听得见的动物的声音。此刻是白天三点钟,阳光蔚蓝蔚蓝的,因是坝子,稍稍出汗,衣服会粘扯粘扯皮肤,这种天气和时辰,估计鸟们在午休。看见我的卷头发,在微风中缓缓飘浮,身上是一只老掉牙的脏包包,正在忙碌的老朋友有些慌张有些不好意思地喊了一声“阿吉!”接着搓了搓手掌心,跑过来握住我的手,“杂种,你还活嘎!”平常本来就穿烂便宜的衣服,眼前的老马,更显得没落,“难民西装”看来很长时间没有洗了,皱皱巴巴,像从酸菜罐里捞出来,他也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喜怒哀乐,老老实实地表现着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的身份。“好久没跟你搞死了(喝酒),哥弟要好好的搞他几下”。这是他的性格。我很高兴他保持着革命意志,把我们之间一下子又拉得近近的。
好长时间不见老马了,我也歇不歇惦记他,我们曾经是“一条战壕里面的战友”,经常来往于彼此的落脚点(家),整天整天地喝酒吹牛,吹牛不上税,东拉西扯,鸡毛蒜皮,要严肃有多严肃,要俗气有多俗气;把一些人抬到天上,把一些人骂得狗屎不如;时而以为自己了不起,时而又自悲得仿佛到了连屁股也没有遮挡的破布。特殊的是,那些年很少听到“市场经济”这头狮子的吼叫声,大家过得相对平静,肚子填饱了就有浪漫和激情的心境。饥寒交迫固然也能成就文学,但衣食足后身心自自由由的写作,也许更能让作品生辉。在这个高山连绵起伏、河流纵横交错的边地,我们的存在和写作,当然像一只小蚂蚁的活动,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却依靠着固定的衣食的保障,爱着朋友,爱着文学,爱着许多许多。老马的家,比他还老,两小间,外加更小的一间厨房,家里进来贼,拿不走值钱的,都是书,花了万元以上,这样舍得花钱买书的,真是如珍奇动物越来越稀罕了。贼是不读书的,所以不会偷书。我这个人穷惯苦惯了,对吃住的态度随便得很,地上铺一张蓑衣就可以打发。老马家的书架脚、厨房的凳子,便成为我的“安乐窝”。那时,他的工作环境应该说是很叫多少人淌口水的,可以不分上下班,可以懒散、清闲、到处走动,只要不违法乱纪,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无所事事般的状态下,写些作品,活跃创作队伍。以老马等为领头的金平文人,曾经让外人刮目相看。我喜欢他那时写下的一篇篇富有边地色彩、性格、声音的作品,当我还在机关里炮制千篇一律的“指出、强调、希望、要求”等等枯燥无味的公文,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已经羡慕他的名字和作品。
老马是厌倦这种平静的生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突然丢掉了十拿九稳的铁饭碗。我是听别人告诉的,再后来又听别人说他去干实业了。所谓实业,是实实在在的事业,或是其它鬼东西,我弄不清,但他要靠自己养活了,死活都得凭个人的能耐。
“老马,你杂种悠闲得很嘛”!我拍了拍老朋友的肩膀,心里盈满了无法言语的感动。生活真是变化得不可思议。这里的房子宽敞、结实,看来年代还不久远,标准的猪圈式样,可养上百头猪。先让我特别注意的是鱼塘。鸭子们全在堤上,有单腿站立、头塞进翅膀打瞌睡,有公鸭母鸭追逐调情,有见不得别的爱情嫉妒而扰乱和谐秩序的,有扮绅士踱来踱去散步的。鱼塘的水浑浊,微风吹来,一阵阵腥臭味骚扰鼻子。因为位于背阴处,显得十分宁静,我不知怎么回事,或许是它的树荫衬托出的让人的身心放松的感觉,倏然间想到德国作家施托姆笔下的《茵梦湖》。那样优美、清澈、古朴的湖也许只是艺术的想象,即使存在,也可能荒芜、破败不堪。鱼塘当然也不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在乱哄哄的尘世边,仍然处在大自然的童年,童话般晶莹剔透,有意无意地抗拒着俗人的踏入和玷污。老马的鱼塘,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塘,他的生活的圈子一下子缩小成这么一塘水,他要靠它保证吃喝拉撒,他要每天照顾好那群鸭子,也要把鱼喂大,不能让它们死掉,它们是他的命,没有它们就要他的命。
冬季不是橡胶林忙碌的时候,不需要人们操心,橡胶白生生的乳液慢悠慢悠地顺着刀刻的树皮沟滴进勒紧树身的瓷碗。年轻人差不多都到外边寻找另外的活干,只有老人守在家里,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煮饭、洗衣服、料理菜地上,这里摸摸,那儿擦擦,闲下来了老骨头散漫地站着蹲着坐着,回忆往事,讲现在的种种世态。
老马的岳父岳母没有什么大病,还动得,住在只有一层楼的石灰土墙的几小间房里。最小的女儿一家跟他们搭火。俩老都是从外地来的,几十年了,还说着家乡话,听来是有些别扭,但听得懂。父亲是退休工人,话不多,终日一处不去,呆在胶林,每天很早就起床,穿着一双高筒水鞋,帮他打扫猪圈,喂猪,喂鱼及其它杂活。累了抽阵烟筒,烟雾从咕嘟咕嘟回响的竹筒里青灰青灰的窜出来,遮住老人家的面庞瞬间后飘散,老人家惬意地舒口长气,间或咳几声嗽。中午和晚上两顿饭,老人家都要喝上几小盅酒,饭桌上坐好长的功夫。那几天我不喝酒。我进胶林的根本目的是“暂时忘记尘世”,求得身体的放松,心灵的宁静。在风景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十分有必要的。好在我的朋友喜欢喝酒,跟老人作伴,他喝的多,老人喝的少,五十度的透明物下肚,相互高兴,话题自然哩哩拉拉。朋友不再像往昔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跟以往那样的政治、文学、理想、奋斗、激情、官场、腐败、愤世嫉俗、孤独、梦幻、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等等的话题全然没有了关系,偶尔会扯到国家大事,还有身边发生的一些风波,血气稍稍热起来,发点牢骚,这只是偶尔,他和老人关心的是猪如何、鱼如何、鸭子如何,一样一样地细细算帐,这个月可以卖多少钱,成本合多少,一年下来又会盈利多少。母亲耐心地等他们下饭桌,这其间靠在凳子上默默听“话”,说到某些方面时插上一两句。我真真切切地想到,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可贵的,如果他能始终不渝地理想下去;而理想主义者需要吃饭、穿衣、住房……他充其量还是俗人。当他的理想有一天被现实粉身碎骨,他的结果,不外乎自我毁灭投胎还俗,此外的路是没有的。当年充满抱负和虚荣心,在许多场合必开口闭口自己是“作家”的我的朋友,眼下的平淡乃至平庸,把自己放在微不足道的蝼蚁般全为了营生的位置,生命再真实不过了。
我喜欢这种家庭生活的氛围。老的会做老人,小的会做后辈,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我初来乍到,却凭着跟老马的缘,马上就和这一家原本素不相识的外来人,融成一块了。在这里,我是松脱的,没有心灵的包袱,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的底层,就像树木的根部,缠绕着泥土和地气,它不是空中的虚无飘渺,它用不着做假,它也做不了假。老马向家人介绍我是干什么什么的。很高兴的是,他们不会往深处想我是写文章混几口饭吃之类的话题。“是朋友才会来家里面。”“朋友来了是喜事。”“多个人只增加一双筷子。”这种朴素的为人处世的感情,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处处体现着。在乡野贫民的家庭,在陌生人路过也要喊人家来家里坐的少数民族清水洗净的环境,我从小耳濡目染以诚相待、以心换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我住在鱼塘边老马平时“办公、住宿”的房子里。晚上吃完饭后,他们一家子还在聊天,天色尚早,我就在藤条江边的沙滩上散步。
我从地图上知道,这条河发源于我的故乡覆盖原始森林的阿姆山。森林的奶水哺育的清澈透明的小河,经过四个县的长途跋涉,了解无数的山头、峡谷、田地、村庄,七八个民族,无数的风土人情后,到达这里,已经是饱经沧桑。然后,走向越南,再投入太平洋的怀抱。它的身世,它的经历,让我这样肤浅的人是会深怀无比敬畏的。
也许是朝日与这条河相偎相伴,我没看见一个当地人在河边散步。这给了我极大的空间,爱怎么想怎么做,都是靠自己的情绪。我的情绪当然好得不能再好了。藤条江虽为江,它的影响绝对比不上红河,却也是我们的大地上屈指可数的几条算得上的江河之一。平常见它的机会很多,但只是在它的身边路过时瞄瞄。真正贴近它肌肤的这是第一次。不管是不是勉强称作母亲河,它就像我们自己的血液,默默滋润着我们,给予我们灵性与坚韧,给予我们不屈与拼搏的精神。在这样的河流面前,只消度过一小时或几分钟,人就会洗涮掉矫情和浮躁,人就会变得厚重和刚强。
虽然是冬天了,由于河道陡峭而狭窄,干瘦的河水又急又猛,终日被不讲规则的水乱劈乱抓的石头,极有艺术性的怪模怪样,既面目狰狞,又可亲可近。我跟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担心突然从水里伸出凶险的舌头,把我卷走,吞没。其实这是玩笑的说法。河水只管往前赶路,它是不能停留的,天命使它不顾一切地赶路,蔑视任何艰难险阻。
沙滩,是藤条江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另外一种杰作。经它随意创作而成的鹅卵石(是天鹅下的蛋吗),在沙滩上丢得满地都是,像这样东西,像那样名堂,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我偶尔捡拾几颗,但捡捡又觉得一颗比一颗漂亮,舍不得也得舍弃,干脆一颗都不拿走,怕得罪满地的卵石。沙滩本身,是柔软的天鹅床。天鹅倒是不见,翠鸟等鸟们控制不住兴奋时,却在沙滩上空翩翩起舞,画出一道道颇有规律的线条。我想在沙滩上睡一觉,但怕被人看见难为情,于是只好用写草书似的脚印,把飘浮的孤影胡涂乱抹在沙滩上。
非常遗憾,那几天晚上没有月光,让我情不自禁地抒发“在那洁白的沙滩上……”黑暗仿佛锅盖扣下来,视野渐渐混沌,晚了,我夹一股涛声回房间。
屋子虽不破烂,却完全是没有时间料理卫生的打工农民式的。开门,一股股腥臭味滚进来,让人头昏,胸闷,心翻。但不要多久我就适应了。这是我所非常熟悉的生活。出门在外,四处浪迹,漂泊无定,还能有这样的房间住,我心满意足了。就是地上有一张蓑衣,我也知足而乐。夜间只有我一人守着偌大的房子,显得格外空旷、冷清。鸡鸭们睡得早,睡眠质量高,有谁梦中惊醒尖叫一两声外,享受着天国的静谧。猪却不是那么规矩了,或许是几头住在一格卧室里,无意中碰着谁都不得,或许是引起了久已忘记的性欲在相互摩擦中醒过来,这一阵你哼,过一阵我叫,要命般,我来不及蒙上耳朵,噪声把耳朵割紫割裂。但不要多久我也习惯了。跟这些家伙同宿,比正人君子相处要安全、放心得多。在落满灰尘的老掉牙的桌子上,放着几本文学和饲养家畜家禽的书。老马似乎在忙完活后偶尔翻翻。文学是残存的梦还在他的脑子里闪着几粒星火吧,其它书则是他的正道了,尽管未必能帮他发财。
我无事可做,因为无事,每晚读书读到神经麻木,不知道是哪一刻睡下。这里的冬天真好,它不是寒风刺骨的冬天。它其实跟季节意义上的冬天毫无联系。睡觉盖不盖被子都无所谓。读书是我的本行,说读书人一点都不值得自豪,但又一点都不必要自卑。读书是听死去或活着的人说话,好处是你跟他们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不必看他们的面孔,不必和他们生活在一块。你只消听他们说得好听爱听的话,而你用不着开口。有些人,哪怕他是无名小卒,话常常说到你的心坎,你就跟他经常保持朋友感情;有些人,大名鼎鼎,如果尽是废话,你可以把他踩在脚下,置之不理。市场经济的大浪,卷进了最偏僻的旮旮旯旯,人们都被钱惹红了眼,没钱就不如一泡狗屎。我躲进胶林过冬,不是在有意悲壮地做抗拒什么的英雄行为,我喜欢过走出别人的影子与眼神的自己选择的生活,那跟富贵与贫穷无关,跟孤独寂寞无关,纯粹是个人心灵的事。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读书也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它出于心灵的某种需要,就像大地需要青草、树木、高山河流,天空需要云彩、日月星辰。
当老马问起“你不想改变这种活法”时,我就不觉得有头发丝细的异样的心情。对我来讲,这种活法谈不上“诗意”,也算是“自在”了。
橡胶林绿荫的时候,再怎么美,跟大自然随意摆设的树林不可同日而语。
橡胶林别具一格的情调,只有在冬天才会毫无遮拦地表露出来。冬天的橡胶林,落光了叶子。地面铺满了金黄色的枯叶。在外看来是光秃秃的单调枯燥的林子,是世界上最适宜散步的地方。可以说,冬天到橡胶林,要说有目的,唯一的目的是散步。我们一群人曾经从公路边看见满地黄叶时,有人讲笑话,如果爱情倒在叶子上翻滚美死了。我来,哪敢有如此的浪漫。我只为自己。过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山上之外的冬天。
我起得很早。老马和他的岳父一早就要照管家畜家禽,他们一来,跟着而来的说话声脚步声,便把我弄醒了。他们开始为生计忙。抹抹脸,我开始为散步忙。
整个胶林到处是路,只消闭眼睛走出去,不必怕摔倒,摔倒了也用不着担忧受伤。偶尔遇见很少的鸟觅食和寻找伴侣,还有边溜达边警戒的松鼠,看不到行人的影子。风没有事,懒得起床,正在睡大觉。陪伴着自己的,就是轻悄悄的脚步踩醒黄叶的那点声音。散漫,零乱,细碎,像作贼偷偷摸摸,又像说含糊不清的梦话。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这时,我跟一片枯叶一块土坷一只蜘蛛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没有深奥的哲学探究,没有眩目的艺术思索,没有复杂的人际纠缠。像渐渐皱皱巴巴的树皮那样,我只是走在时间背后,以一团被叫作艾吉的血肉,去贴近给我最初生命的大自然。
我一直走下去,凭感觉走下去,不分方向。有时稍稍累了,坐在落叶上,或躺一会儿,更多的时候,像一个乡巴佬进城,贼眉鼠眼,东张西望,不知道怎么个看法,只觉得太美,全身的神经都被牵动着。叶子飘落下来,我像儿童追逐蝴蝶,朝旋转的片片黄色跳跃,接着,高兴得如寻觅到食物的鱼。由于忘记了回头,为我,家里总是延长吃饭的时间。
有天早上,我顺着山坡走上去。那座巨石挪起的山直插云天,那时,太阳踩滑了,从山头滚下来。四处乱泼的金粉,点燃胶林,平坝和高山,被熊熊的金黄的火焰吞噬,然而又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无声无息。突然,我听见一阵清脆的鸡鸣声,在我前面的炊烟袅袅的树林传来,随之,是模糊、零碎的人声。我不想打搅人们,只好奇是些什么人在那里生活。等我走出胶林时,发现芭蕉树下有几户山民,正在烧火煮饭,女主人在竹片围成的家出出进进,男劳力在门口抽烟筒,或做些出门干农活的准备工作,孩子跟狗站在一块转动,啼叫的公鸡则在柴堆上雄赳赳地为心目中的母鸡挣分数。这样的日子,似乎跟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并无两样。虽不一定男耕女织,但热锅上的蚂蚁般焦燥不安的世态,几乎没有波及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程序,依旧慢腾腾地遵循、运转着。自己的汗水,喂养自己的生命,并不因为把他们丢在山高皇帝远的角落。他们在简朴的知足中,迎来送往凡是人皆避免不了的淡淡或浓浓的哀愁。
这活跳跳的场景,尽管这样的景象在我安身立命的这块土地上,只要翻过一座山,走一条歪歪扭扭的土路,便会置身其间,它依然又一次激起了我的羡慕。总有一天,我想,最好的归宿是像鸟,在林子随便安个巢,填得饱肚子,暖得了身子,就别无所求了。
但现在,我无异于在说梦话。
从老远八远就鼻子闻到了陌生味的狗,见我傻乎乎地站在村边,“哇哇哇”地撵过来。可能这儿很少经过生人,众人的眼睛顿时全跟着狗往这边奔跑。我站着不动,还隔着一截路,狗和人都看来我不像偷鸡摸狗的,人劝狗“回来,回来,”狗摇晃尾巴“唏唏唏”地回头。真是人淳朴,狗也善良。如果我走进村里,他们肯定会主动邀进家门,以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感情掏心掏肺。
好像刚刚走进橡胶林,满目新鲜,满心惊喜,殊不知一个星期就溜过去了。临走前,我约老马散趟步,他被事务缠绕,还没有观赏过胶林的冬天风光呢!我说,你别只懂得赚钱,在别处,你出钱也买不到这种意境。那群吃吃睡睡的猪、鸭子拖他的腿。老马苦笑,跟它们一样,他忙忙碌碌也为了吃吃睡睡。我相信的是,日后,他会到我走过的落叶上,走走看看,闻着冬天和我的气息,会心地笑笑。
时光仿佛橡胶林旁边的藤条江,那么飞快地流走了好多年。老马和我都老去,只有往事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