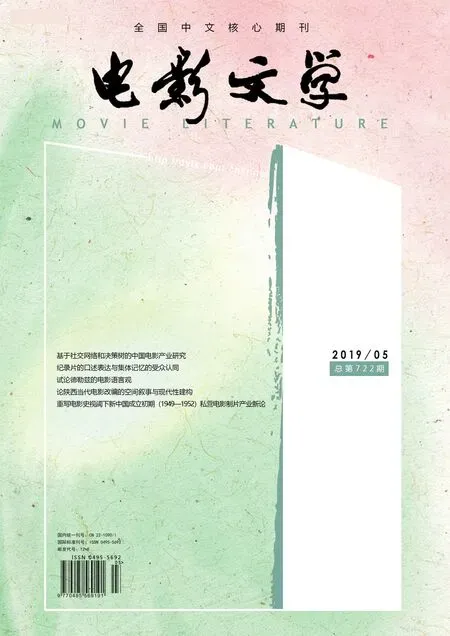叙事的寓言化与纪录性
——《幸福的拉扎罗》解读
赵春霞(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
《幸福的拉扎罗》2018年5月在法国、意大利上映,2018年10月在中国平遥影展上映,是意大利80后女导演爱丽丝·洛瓦赫(Alice Rohrwacher)继《圣体》《奇迹》后的第三部剧情片,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21世纪电影胶片慢慢被数字技术取代,人们渐渐习惯了数码技术制造出的视听奇观。但是,爱丽丝·洛瓦赫却近乎固执地坚持用胶片拍摄电影,这是一个“电影作者”对艺术的独特追求。《幸福的拉扎罗》延续了上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用寓言化的叙事方式和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对现实生活进行解构,折射出导演对社会、阶级、成长、人性的反思。
一、寓言化叙事
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20世纪以后成为西方重要的书写方式,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寓言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一种特权,在中心离散的时代,在自我意识分裂后,只有寓言是产生多种组合的问题方式,拒斥单一模式,本身就有‘复调性’。”[1]寓言叙事用隐喻和象征的方式使故事具有复杂性和多义性,《幸福的拉扎罗》因其寓言化叙事,人物形象脱离“能指”层次,具有抽象的“所指”,象征性的意象使作品具备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一)拉扎罗的“能指”与“所指”
《幸福的拉扎罗》中人物形象因寓言化叙事性获得了超越自身的丰富内涵,成为一种意蕴丰富的影像符号,传达出导演对社会、生活的宗教与哲学思考。“符号就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所构成的,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2]在影视作品中,能指大多是具象的画面,而所指是抽象的思想。拉扎罗是影片的主人公,他的外在造型、行为习惯构成表达面,即能指;他的内在思想以及启示意义则构成内容层面,即所指。
影片一开始用画面、台词以及人物造型等展现出拉扎罗的与众不同。他的眼睛明亮清澈,情绪平静如水,总是毫无怨言地干着别人让他干的一切工作。在收割烟草这一段落中,呼喊拉扎罗的声音此起彼伏,随着众人喊他的频率越来越高,剪辑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拉扎罗在烟草地里不停地往返奔跑,最后画面中只剩下绿绿的烟叶。即便如此,众人依然排斥他、欺负他。拉扎罗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依然幸福地不求回报地付出着。他掉下悬崖,苏醒时已是25年以后,村里的人已经回到现代社会,容颜老去,靠坑蒙拐骗艰难度日。但是,拉扎罗容貌依旧,他到处寻找自己的兄弟唐克雷迪,在得知唐克雷迪的穷困潦倒是因为银行后,他竟然要求银行把钱还给唐克雷迪,最终被众人打死。无论在与世隔绝的因诺拉诺,还是在自由开放的现代都市,拉扎罗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听从他人的召唤,毫无自我意识。
在众人眼里,拉扎罗是一个“傻子”,但是,导演却在拉扎罗身上寄托了人类救赎的希望。拉扎罗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他不求回报地奉献,生活平静而幸福,多年保持着不变的容貌,看似游离于故事之外,被周围的人疏远漠视,却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默默地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拉扎罗因其无欲无求的牺牲精神获得了心理上的永世安宁,也满足了他人的欲望与懒惰。导演把拉扎罗塑造成一个拯救世人的上帝。但是,值得讽刺的是世人却有眼无珠。因诺拉诺有教堂,村民们做礼拜、唱赞歌,小孩到女爵家听圣经。他们崇尚上帝,但是,拉扎罗任劳任怨地为他们驱使,做着他们向上帝祈求的一切,他们却麻木不知、冷漠以待,这就是虚伪的世人。
(二)象征性的意象
狼是《幸福的拉扎罗》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它具有隐喻和象征性。“叙述因素和隐喻因素——这是一般和个别在电影艺术形象中彼此对立、配合和相互联系的两种不同的途径,两种不同的原则。”[3]《幸福的拉扎罗》中影像层面讲述了拉扎罗的故事,声音层面则通过旁白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狼的寓言故事。圣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寻找狼,体力不支倒在雪地里,饥肠辘辘的狼跟踪而上,在圣人身上闻到了好人的味道,没有吃他。狼的寓言故事是影片叙事的缩影。
狼在影片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狼的嚎叫。拉扎罗和唐克雷迪站在山坡上,唐克雷迪带着拉扎罗模仿狼叫。第二天,警察解救了因诺拉诺被伯爵夫人奴役的村民。第二次是拉扎罗掉下悬崖后昏迷不醒,一只狼慢慢地来到拉扎罗身边,闻到了好人的味道,拉扎罗苏醒过来。第三次依旧是以声音形式。老年的唐克雷迪与拉扎罗重新表演了一次年少时的狼嚎,屋子里的村民也模仿起了狼嚎,这一瞬间,原本已经老去的村民突然变回了当年的样子。当灯打开,村民又成了老年的模样,但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因为贫困而愤世嫉俗、悲观绝望,开始乐观面对生活。第四次狼出现在银行,拉扎罗请银行把钱还给唐克雷迪,众人却以为他要抢劫银行。拉扎罗不解众人为何高举双手,向旁边一看,却见到狼出现在身边,悲悯地看着他。导演在拉扎罗纯真的眼神、狼的眼神以及众人对拉扎罗的咒骂与殴打之间交叉剪辑,形成一种对照和反讽。狼最后跑到大街上,逆流而行。
狼与拉扎罗一样,都是救赎者的象征,狼对拉扎罗形成救赎,而拉扎罗则对世人形成救赎。狼在四次救赎之后,失望而走。而拉扎罗却被民众活活打死。影片通过两个叙事层面中的故事对社会进行了质询与控诉。
二、影像的纪录性
爱丽丝·洛瓦赫于2006年执导首部纪录片《意大利生活》,开启电影之路,之后五年,她一直拍摄纪录片,直到2011年,首部剧情片《圣体》上映。纪录片的拍摄经历使她形成了一套具有个性风格的电影语言,并延续到剧情片中。这使爱丽丝·洛瓦赫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作为技术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4]它反对刻意雕琢画面,反对用专业演员,主张“扛着摄影机到大街上去”“到围观的群众中去寻找演员”“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事件”。这些都影响到爱丽丝·洛瓦赫的创作,她大量任用群众演员,并采用手提摄影的方式,使影片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纪实感。她认为“技术完美”无聊之极,《幸福的拉扎罗》在“技术缺陷”这一领域走得更远。
(一)客观冷静的画面风格
《幸福的拉扎罗》画面客观、冷静、内敛,有一种粗糙而强烈的颗粒感。这与导演爱丽丝·洛瓦赫的美学追求息息相关。她坚持使用Super 16mm的胶片拍摄电影,虽然在某些室内和夜间场景中,Super 16mm的影像清晰度不佳,颗粒感强,但这正是导演需要的具有饱含情绪的影像。在后期制作的调色阶段,爱丽丝·洛瓦赫避免使用调色工具使影像过于完美、过于标准化,而是尝试保持Super 16mm“渲染缺陷”的效果,甚至利用数字调色的优势增加画面阴影的亮度,使照明亦有“缺陷”。这些“缺陷”使影像不平滑、粗糙,却在另一层面获得了一种真实感,使爱丽丝·洛瓦赫成为一个“电影作者”。
影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因诺拉诺,第二部分是在现代都市。第一部分中,叙事节奏较慢,讲述村民们被伯爵夫人奴役终日劳作的故事。爱丽丝·洛瓦赫较多使用长镜头,且全景、远景较多,摄影机不厌其烦地跟随着拉扎罗的步伐,展现因诺拉诺的荒芜与贫瘠,让观众沉浸在与世隔绝的近乎静止的社会生活中。第二部分中,叙事节奏相对较快,讲述拉扎罗在现代都市寻找唐克雷迪的故事。爱丽丝·洛瓦赫控制长镜头的数量,多用中近景、特写镜头,且运动镜头较多,多用手提摄影来展现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和拉扎罗对现代社会的不适感。
无论因诺拉诺还是现代都市,爱丽丝·洛瓦赫的影像风格都有别于当前流行的近乎精雕细琢的影像风格。在物理层面,她坚持使用胶片拍摄,选择柯达VISION3 250D彩色负片7207拍摄白天的外景戏,用柯达VISION3 500T用于拍摄室内戏和夜戏,以呈现出客观冷静、粗粝原始的画面风格。在思想层面,爱丽丝·洛瓦赫想通过技术材料与技术手段给故事提供一个物理时空,并借此表达自己对社会、人性、宗教等的认知与思考。
(二)主客观结合的叙事视角
《幸福的拉扎罗》的摄影师海莲娜·勒瓦使用ARRI416 16mm摄影机拍摄,这款机器小巧轻便,她可以轻松地在各个场景进行操作,便于手提拍摄。在《幸福的拉扎罗》中,主要有三种拍摄方式。第一种是肩扛拍摄,以客观视角跟随拉扎罗,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第二种是将摄影机放在摇臂上拍摄全景或跟随镜头。当拍摄多人画面时,摄影机慢慢靠近拉扎罗,把他框在人群中,以此来凸显他的渺小、卑微;当拍摄拉扎罗单人镜头时,用仰角拍摄,造成拉扎罗形象被放大的假象,寄托着导演对拉扎罗的主观感情。拉扎罗在众人之间默默无闻,毫无存在感,自己独处时却像一个深邃的思索者。第三种是让摄影机明显与故事保持距离,采用俯角、大景别的拍摄方式,模拟上帝视角,注视、观察着拉扎罗。
这三种叙事视角在影片中转换频繁,有时未免出现视角混乱的现象,有些画面分不清到底是摄影机的客观镜头还是剧中人物的主观镜头。比如,拉扎罗跌下悬崖后,一个航拍的长镜头,既可以看作是一个搜救直升机的主观镜头,也可以看作是下一个画面中农妇的主观镜头,接着是农妇观看直升机的客观镜头。但是,爱丽丝·洛瓦赫是“技术缺陷”的坚定拥护者,用这种缺陷来表现她心目中的真实。
虽然影片视角转换频繁,但还是有着一定的逻辑性。影片前半部分较多地采用了拉扎罗的主观视角,通过拉扎罗的眼睛交代了因诺拉诺的生活,亦凸显出拉扎罗对因诺拉诺的熟悉感,在因诺拉诺,拉扎罗是一个凝视者。影片后半部分较多采用了客观视角,现代社会对拉扎罗来说是陌生的,他不了解这里的一切。在现代社会,拉扎罗是一个被凝视者。他穿着短袖行走在雪地里,清澈单纯的眼神在现代都市本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异类。
《幸福的拉扎罗》用寓言化的叙事、纪录性的画面给观众讲述了拉扎罗的故事。拉扎罗已经上升成一个影像符号、一种艺术象征,甚至成为对文明的一种反讽。在远离文明的因诺拉诺,拉扎罗虽然处于最底层,是众人驱使的对象,但至少没有人恶意伤害其生命。在现代社会,拉扎罗成为一个累赘和负担,返回现代社会的村民求生艰难,没有余力顾及挣不来钱的拉扎罗。复杂混乱的现代社会无法理解拉扎罗的清澈与单纯,甚至使拉扎罗丢掉性命。拉扎罗是上帝的象征,他以生命为祭礼来唤醒现代人的纯真与良知。
——艾玛·莫拉诺的117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