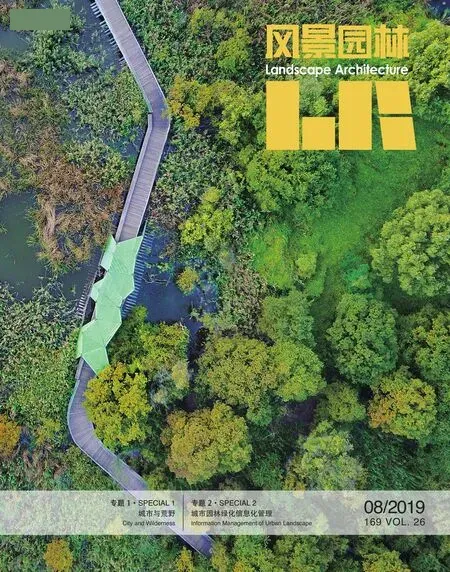村落生态单元及其景观模式的营造智慧—以青藏高原秀日村为例
康渊 王军
今天的传统村落保护,其本质是在保护什么?以“乡境”营造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建设,其实质又是在建设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建立在如何看待乡村本身的基础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村落曾是古典园林追求的“审美原型”[1],中国古典绘画、诗歌、散文多以村落景观作为描摹的对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维的《辋川别业》等描述村落景观的意境已经沉淀到了中国人的文化深处,如同地下伏流的泉水长久地滋润着中国的人文精神[2],而西方园林中现代意义上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来源之一便是英国“乡村景观”[3]。可见人类关于居住环境的理想景观部分来源于村落生存模式。彭一刚[4]认为村落具备审美的艺术形式,因其与人们的真实生活相连。俞孔坚[5]提出“桃花源模式”的村落结构是中国人心中理想景观模式之一。村落何以能够成为人类居住审美的原型?Appleton[6]强调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行为表明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与被感受的环境之间基本上等同于其他生物与其栖居地的关系。在原始、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维持栖息地系统的循环与演替。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形成了亲密的关系与深厚的情感,这种关系奠定了今日人类居住环境的审美基础。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种群延续依赖于栖息地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维持适当的平衡关系[7-8],生态系统稳定的栖息地也意味着人类种群生存的延续。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大自然中,村落作为人类栖息地,对自然人来说包含了所有美好的生存理想。环境审美的生物学基础认为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环境就是美的[9]。因此回归人类生存的本能来理解人类的审美,能够发现人类文化中对村落的审美偏好是一种基于原始的生存记忆,被深刻地烙印在人类审美基因的深处。对人类来说,村落的美正在于它是茫茫大自然中生命存续的机会,也因此成为人类不断赞誉、深入描绘、孜孜追求的理想模式。这个理想模式包含的深层含义是人类对生命存续的憧憬与赞誉,如美画卷和诗意描绘只是这个模式的浅层表达。人类追求的村落模式其实质是追求一种健康有序的生存生态系统,村落生态单元即是这种系统在空间层面的表现之一。由于构成村落生态单元资源环境的禀赋差异,不同的村落生态单元会表现出不同的景观模式,蕴含着不同的营造智慧。目前,学者们对村落生态单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景观要素的分析上[10]71-73。笔者从生态学的角度构建村落生态单元的概念,认为村落生态单元稳定平衡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往往蕴藏着深刻的营造智慧,并以青藏高原秀日村为例进行阐释。
1 村落生态单元
1.1 村落生态单元的概念与特征
村落是以乡村人群为核心,建筑设施为重要栖息环境的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单元是指可圈定的动植物生存空间[11]。村落生态单元是以人群为优势种群、伴生生物为主要生物群落[12],在人类种群适应和改造自然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独立、完整、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范畴。有别于纯自然环境的景观斑块,村落生态单元是一个融合自然、人工和社会各要素的复合生态系统。
人是村落生态单元的核心,在人的主导下村落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发挥其作为生态单元的功能。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自我调适能力和反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和推动着村落生态单元的进化[13]。村落生态单元的进化如同细胞的分裂,当一个村落单元发展到一定规模,物资产出和人口便会达到饱和,为确保二者的平衡,过剩的人口就要析出以另辟新地,新的村落单元随之产生[10]71。
1.2 村落生态单元的结构与功能
村落生态单元的景观模式是通过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来体现的,村落生态单元包括居住景观、生产景观、文化景观3个子单元。其中居住景观是以人群及其伴生生物栖息为目的营造的人工生态系统[14],包括村内一切为村民生活服务的建筑物与构筑物;生产景观是村落生态单元得以维持、发展的支撑单元,它能够为村落生态单元提供资源与能量,其内容包括农田、牧场、林地、果园等;文化景观是村民及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宗教、习俗等价值观念,基本表现为非物质形态。居住景观、生产景观及文化景观3个子单元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形成的空间形式即为村落生态单元的结构。
村落生态单元是一个多功能综合体,人类是功能的主体,其主要的功能为居住和生产及文化功能[15]。居住功能的基本实现单元是建筑与院落,聚落则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居住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人类有着不同的栖居需求,也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结构。如藏族的上寺下村、穆斯林的围寺而居等。生产功能指村落中居民的食物生产系统,主要包括农业与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功能的空间结构依赖于地域环境、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以及居住地人群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其典型的结构有山地梯田型、草原牧场型、河谷农田型等。文化功能是满足村落生态单元中人类种群精神需求的功能,主要包括宗教、娱乐、社交、体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功能投射到空间层面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族的寺庙、拉则台(藏族插箭活动的场所)、赛马场、锅庄舞场等。
2 村落生态单元的营造智慧
2.1 结构、功能及营造智慧的关系
在相同的环境中,何种景观结构更有利于村落生态单元功能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村落生态单元的结构并不是一蹴而就地被规划出来的,它来源于当地人的生活,来源于不同的土地和土地上自然和人文的过程,并继续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当结构与功能关系失衡时,使用者—村民会根据其生产、生活和文化等功能需求不断地修正,以使景观结构持续满足其功能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修正中,村民积累了丰富的营造经验。因此笔者认为村落生态单元稳定平衡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往往蕴藏着深刻的营造智慧。
2.2 解析村落生态单元的营造智慧
村落生态单元的营造智慧是通过营造其单元的结构以促进和优化功能的实现,即促进村落生态单元中生产景观、居住景观与文化景观3个子系统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的良性循环,以实现村落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并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和文化功能。在实际营造中,村落营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些功能,然而营造的对象只能是村落景观结构,功能无法被直接营造。营造目的和营造对象的差异给研究提出如下问题:如何判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失衡关系?哪些结构能更好地实现并促进功能的实现?在资源约束与人口速增的双重压力下,村落生态单元的生产景观、居住景观与文化景观3个系统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循环,不断地改变着村落生态单元的结构。当村落生态单元3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正常时,其生态系统的结构趋向稳定,村落生态单元的功能发挥正常,二者之间关系平衡;反之,村落生态系统结构受损,村落生态单元功能紊乱,二者关系失衡。与此同时,村落生态单元本身与外界进行着信息、物质、能量的流动与转换,如生产经济与外界交换形成的商品流、学生接受村外教育形成的文化信息流、各类工匠与外界的联系形成的技术流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转换推动着村落生态单元生生不息地发展(图1、2)。

1 村落生态单元结构与功能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village ecological unit

2 青藏高原理想山地村落生态系统模型Ecosystem model of ideal mountain village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3 秀日村区位图Xiuri Village location
3 秀日村村落生态单元及其景观模式的营造智慧
3.1 秀日村基本概况
秀日村属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藏族乡(图3),位于黄河一级支流尕楞河上游海拔3 000 m的高山山顶凹地,村民共59户,324人①。“秀日村”是藏语发音的汉字写法。“秀”的发音在汉语中是侧柏、圆柏的意思,“日”的发音是山的意思,秀日即为长满松柏的大山之意。秀日村为典型的半农半牧村,从20世纪70年代起,该村开始修筑梯田种植农作物,至今约有梯田120 hm2②。该地海拔高、热量不足,可种植农作物有限,多数村民以小麦、青稞、土豆和油菜种植为主,春种秋收,一年一季。其村周边有草山2座,面积约200 hm2,分别是村落西南的夏吾草山和村落西北的才毛吉草山。
3.2 “农牧共生”与“方位种植”的生产景观模式
3.2.1 “农牧共生”的生产景观模式
秀日村民利用山体缓坡修筑梯田种植农作物;利用田间谷地、坡地放牧。在空间上营造出梯田与牧场“结构嵌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两座大型牧场(夏吾草山与才毛吉草山)环绕村外梯田(村落西南和西北的梯田)布局;2)村落四周的五大梯田相互组合形成了众多田间牧场,其中每一个梯田内部仍然是一种牧场与梯田相互嵌套的关系,即草山牧场围绕并渗透到梯田景观之中,形成一种牧场与梯田紧密嵌套的结构关系(图4、5)。
秀日村梯田与牧场在结构上紧密嵌套的关系是“农牧共生”景观模式的典型表现。一方面,梯田的经营依靠畜牧业牲畜的帮助,如牛耕地、驴驮运等;另一方面,牧业的发展依赖农田产出的粮食、秸秆等食物。其梯田结构反映并促进村落农业与牧业在功能上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体现了传统村落中高效、节地的生产景观营造智慧。
3.2.2 “方位种植”的梯田营造智慧
“方位种植”的梯田营造智慧是指村民根据不同方位的梯田能够获取热量的多少决定种植不同热量需求的农作物种类的智慧。具体表现在:1)根据日照时间与梯田周边的地形关系,西南方位的宁古梯田能够获得热量最多,村民在这里种植对热量需求较多的小麦;2)东南方向的梯田坡度大、有山体遮挡,能获得热量略少于西南,村民在其阳面种植小麦、阴面种植热量需求少于小麦的土豆;3)东北方向的东日马与安杰农梯田坡度较小,但梯田方向与日照方向相反且受到村落高地的影响,其获热量能力受阻,村民在这里种植对热量需求不高的土豆和油菜;4)西北方向的赛果梯田获得热量能力最差,村民种植对热量需求较少的青稞与油菜。
秀日村民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根据每一块土地自身禀赋的不同,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因地制宜的种植方式很好地实现了土地的使用功能,客观上促进了村落梯田景观结构的多样性与景观视觉效果的丰富性,使村民获益的同时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景观资源。这一方式是村民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试错后呈现出来的关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智慧,也是山地环境中人类对资源高效利用的一种方式(表1)。
3.3 “田居一体”“循环再生”与“有机生长”的居住景观模式
3.3.1 “田居一体”的居住景观营造智慧
居住景观与生产景观之间依靠人类的调控实现物质能量流动,播种季节居住景观内的有机物、化肥、种子运至农田,收获季节农产品、秸秆运入居住景观中。这种循环流通对村落生态单元的系统稳定起到控制作用。在结构上,生产景观包围并扩散至居住景观内部。其中包括梯田与牧场在内生产景观围绕居住景观分布,居住景观内部以人居为单元的庭院仍配置有菜园林地等生产景观。这样生产景观与居住景观就形成了“田居一体”的紧密结构模式(图5)。

4 宁古梯田内“农牧共生”的景观嵌套模式Ninggu nested pattern of terraced landscape (featuring symbiosis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4-1 田间谷地牧场The pasture of valley in field4-2 田间平地牧场The pasture of flatland in field4-3 田间坡地牧场The pasture of sloping in field

表1 秀日村梯田种植特征分析Tab.1 Analysis of plan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erraces in Xiuri Village
该结构不仅实现了生产景观为居住景观的核心物种—人类提供资源能量的功能,同时实现了生产景观作为居住景观的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功能。即结构上居住景观依附于生产景观,功能上居住景观是生产景观的“汇”,生产景观中的大部分有机质都流向居住景观,富集的有机质在居住景观内循环流通,以更好地实现居住的功能。
3.3.2 “循环再生”的院落景观营造智慧
院落景观是指院落及其周边衍生环境系统。在结构上包括庄廓院、打麦场、草房、草垛、水窖、菜窖、柴堆、粪堆、菜园、粮房、牲畜房等一系列空间要素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的空间形式。这些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庭院空间背后反映的是村民在庭院单元建立的一套循环再生机制。
院落中农业的废料被作为喂养牛羊的草料,牛羊的粪便被晒干作为人类的燃料,燃尽的灰烬被用作梯田的肥料,肥料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形成新的作物。整个过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循环与再生系统。从本质上分析,发生在秀日村庭院空间的生态演进是一条由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循环再生机制,正是这种由村民智慧主导的再生机制促使村民与环境和谐共生,村落单元生生不息,破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
3.3.3 “有机生长”的空间繁衍智慧
空间繁衍智慧是指村落生态单元的空间增长方式③。在公元843年,唐朝和吐蕃王朝之间发生“西南战役”,吐蕃宰相阿尼何瓦带兵从拉萨前往今日的秀日村附近,参加对抗唐朝的战争。战后,宰相留在今日的秀日村镇守吐蕃边疆,在唐羊形成了最早的秀日村。后宰相在秀日村生育三子,唐羊不能满足发展。大儿子好么从秀日搬至今日合然村,二儿子牙木留在秀日村,开创了今日秀日村,三儿子哈么从秀日村搬至今日的建设塘村。
约200年前,唐羊人满为患,村民搬至今日秀日村西北的康乔囊。民国时期康乔囊无法满足使用,遂搬至今日秀日村中间的桑吉片区(平地)。从桑吉片区析出的人口先后搬迁至今日的桑高片区(高地)和扎德拉(洼地)片区。此三片区形成了今日秀日村居住景观单元。伴随人口的增加、村落生态单元不断向新土地析出人口。秀日村从一个家族的单元不断分裂,成长为3个村落单元的空间结构,其中每个单元又按照自身的驱动方式不断生长,呈现有机生长的衍生模式(图6)。
3.4 “信仰至上”与“万物平等”的文化景观模式
3.4.1 反映“信仰至上”的居住景观结构
秀日村文化景观对居住景观结构与功能有着广泛的影响:1)秀日寺分布在村落附近的神山,与居住景观的垂直关系表现为“上寺下村”的结构,与居住景观水平关系表现为“寺远村近”的特征;2)村内配置白塔、玛尼房、本康等宗教建筑;3)村落周边置五色经幡、玛尼堆等宗教景观;4)庭院内造炜桑炉、佛堂,种暴马丁香④等佛教植物。秀日村中心与核心位置均以宗教景观营造为主,宗教信仰是村民生活的重心,体现了“信仰至上”的特征。文化景观影响居住景观的结构布局,居住景观结构实现了文化景观的功能。
3.4.2 反映“万物平等”的景观保护智慧
秀日村文化景观“万物平等”的宗教观念在生产景观中表现为生产景观营造体现出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关系。村民不轻易破坏山体林地的地表景观结构,在特殊节日开展转山祭祀活动保护草山。春耕时期举行祭田活动,展现珍惜梯田、爱护牲畜、保护动物等行为,这些物化的宗教思想在功能上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促进了村落可持续的发展。

5 秀日村村落生态单元结构分析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units in Xiuri Village

6 村落生态单元的空间增长方式The spatial growth mode of village ecological units
4 讨论与结论
从生态学的角度构建村落生态单元的概念,认为乡村营造的实质是营造以人类种群及其伴生生物居住生活为核心,居住景观、生产景观和文化景观为内容的生态系统,该系统包含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出发,认为村落生态单元的使用功能不能被直接营造出来,而要通过一定的结构营造才能获得相应的使用功能。因此在给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单元结构利于功能的实现、功能促进结构的修正,成为评判营造智慧的重要依据。
以青藏高原秀日村为例,论证了梯田与牧场的嵌套结构促进其农业与牧业共生功能的实现,方位种植的景观结构实现其高海拔种植农业作物的生产功能;田居一体的居住景观结构促进了村民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紧密联系,不同庭院景观的结构通过循环再生机制实现了人与伴生生物的居住、生活功能。村落主体功能变化与人口规模的扩大推动其村落结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变化,开创了秀日村新的村落单元结构;寺庙、白塔、玛尼等营造实现了村民信仰至上、万物平等等文化功能。当前乡村建设在中国各地火热开展,乡村转型迫在眉睫。在这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冷静而审慎地看待村落在漫长的时间演进中形成的营造智慧与建设经验。对秀日村传统营造智慧与建设经验的探讨也是一种对待乡村发展的态度。
致谢(Acknowledgements):
感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晖老师的启发与鼓励;感谢风景园林专业博士研究生杨雪与李冰倩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Notes):
① 2017年10月笔者于秀日村调研中从村主任完么行青处获得数据。
② 秀日村历史的内容来源于秀日村才果书记从藏文经书的记载中口述翻译,由作者记录并整理得到。
③ 同上。
④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温低,菩提树无法栽培,佛教信徒用暴马丁香代替菩提树,又称西海菩提。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图1、3、5~6均为作者自绘;图2改绘自《应用生态学报》期刊中“基于理想生态系统模式与三维景观指数的徽派村落空间特征解析”一文中理想村落生态系统模式;图4为作者自摄;表1由作者自制,其中数据由笔者于2017年10月于秀日村调研中从村主任完么行青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