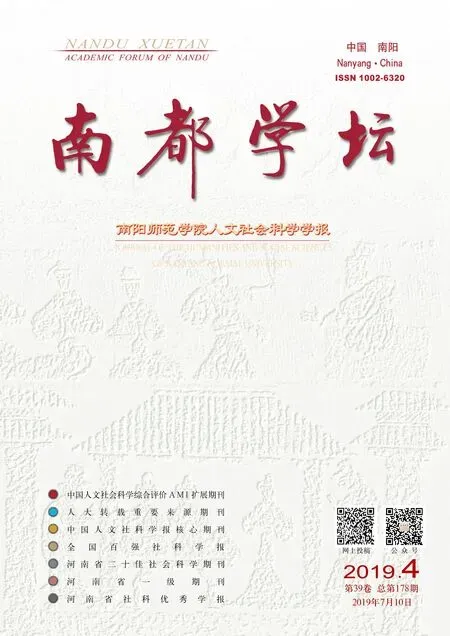唐代官营养马业的盛衰
丁 君 涛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我国地域广阔,草场资源也比较丰富,“我国草原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祁连山(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缘一线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1]107,内陆很多地区也分布有草山和草坡,很多地区宜农宜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宜农宜牧区的畜牧业逐渐被农业排斥,畜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农业逐渐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北方一些地区降雨少、地域广阔、人口稀少,适宜发展畜牧业经济,特别是草原长期生活着强大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有着实力强大的骑兵,当中原王朝趋于衰弱,军事力量不强时,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南侵。为了防备北方少数民族及维护自身统治,中原王朝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论语》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其强大的作战能力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恩格斯就曾高度评价骑兵在古代的作用,认为“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2];严耕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优良的养马场对于国家实力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3]。因此足兵就必然需要装备大量的马匹,只有拥有大量的马匹才能够建设一支强大的骑兵和维护政权的稳定。为此,历代政府都通过各种手段以解决国内的马匹需求,其中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自行发展养马业,完善自身的马政。
一、唐代官营养马业的管理机构
唐建立之初,北部和西北方向面临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特别是突厥。强大的少数民族长期侵扰边境地区,突厥更是深入唐疆域的核心地区,使得唐政权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政府非常重视官方养马业的发展,制定了非常细致的法律规定等,设置或保留了完善的养马机构,以促进养马业的发展。
唐代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养马业管理机构,在中央有太仆寺、驾部等,分布全国各地的机构有监牧,这其中对官方养马业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的是监牧系统,监牧分布范围非常广,贞观初年主要在原州及其周围,此后面积不断扩大, “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 (《监牧颂德碑》)。这一地区地域广阔,降水量也较少。“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东北大兴安岭经通辽—榆林—兰州一线直至西藏拉萨附近,斜贯国土全境,这是我国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大体为我国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1]22,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发展放牧业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唐代的马政管理机构是在继承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政机构在唐五代逐渐经历了许多演进和变革,其总的趋势是权力逐渐集中,逐渐皇权化。唐前期的太仆寺、驾部、尚乘局是唐代中央常设机构,这三个机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促进了唐代官营养马业的发展。太仆寺的长官称为太仆卿,从三品,“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4]479。其职责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中央宫廷皇帝及王公等人的乘骑、畜产品的供给;二是对于各地监牧籍帐以及属官的考课等。监牧隶属于太仆寺,属于基层的畜牧业经营机构,“监牧,贞观中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掌其事”[5]。监牧作为基层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其下属还设置有牧尉和牧长,专门负责马匹等牲畜的放牧、对畜群进行分级管理,以及对人员的奖惩等工作,马、牛都以120头为一群进行放牧,全国共设置有65个监牧,可以说监牧是唐代养马业兴衰的关键。驾部主要负责“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4]162-163,其所管辖的传驿系统拥有大量的马匹,驾部管理政府的畜力和车乘的配给,当然也包含马匹的使用,特别是传驿等交通用马。
牧场所养的马匹相当一部分要由马政部门接收,中央的太仆寺、尚乘等都接收一部分,但是闲厩使出现之后,马匹的养育、调度等权力逐渐集中到闲厩使的身上,“今内别置闲厩使,其务多分殿中及太仆之事。至于舆辇、车马,则使掌其内,监知其外,游燕侍奉,皆不与焉”[4]323。随着其权力不断扩大,到开元中叶,闲厩使成为单一的最高马政长官,闲厩使地位的上升反映了马政权力的集中和皇权化。晚唐时期,还出现了飞龙使,飞龙使管辖范围原本只限于飞龙厩,多由宦官担任,随着宦官势力的壮大,飞龙使逐渐取代闲厩使,皇家马政机构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国家马政机构。
二、晚唐监牧的南迁
晚唐政府由于失去了陇右等地的牧场,为了重新兴盛监牧系统,逐渐将监牧南迁,德宗贞元年间,“会(柳)冕奏:闽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马,置牧区于东越,名万安监,又置五区于泉州,悉索部内马驴牛羊合万于游畜之。不经时,死耗略尽,复调充之,民间怨苦”[6]880。有学者认为在福建养马并不合适,“出于无奈的唐王朝竟在福建养马,这实在是养马史上的笑话”[7]97。但是福建实际上也是一个产马地,只是质量和数量都远不如北方,“福建素来产马,至今闽南沿海各县农民仍养有约七千匹,但外省人几乎不知该省有养马之事”[8]。唐代这一地区实际也养有马匹,只是养马的区域很小,质量也较差,属于小型马,“仅福建滨海数县,在唐朝已有马群牧养,不过产量有限”[8]25。因此唐政府在此地设立监牧有一定的道理。
此后又在蔡州、襄州、银州等地设立监牧,多数牧场大都不算成功,如元和年间,“十三年(818),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819),又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地四百顷”[6]444。等到文宗大和四年(830),裴度就任山南节度使时,“白罢元和所置临汉监,收千马纳之校,以善田四百顷还襄人”[6]1100。元和十四年建立临汉监,在大和四年又予以废除,中间不过二十一年,从马三千二百匹,逐渐减少到千匹。可见监牧内迁后存在很多实际的困难,效果并不好。
晚唐时期,监牧内迁不得不面对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地理条件和农牧争地。养马业的发展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马匹的成长,除了需要大量的粮草,还需要开阔、平坦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史记》曾经对养马区域作了一定的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9]3254-3262。可见在龙门、碣石以北,陇西、天水、上郡一线面向西北一带,是我国主要的放牧地区,这一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因此我国养马之地主要集中在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干旱少雨,地势平坦,草场丰富,适合畜牧业的发展,“以后从汉初到唐朝约1000年间,国家马政建设的中心就着重在今日陕西、甘肃一带”[8]27。对于唐政府而言,河西、陇右地区是最为重要的牧场,“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发展了以陇右牧群为骨干的巨大牧场群,分布在中国西北方一个巨大的环形区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养马场”[7]35,但是,晚唐时期,河西陇右一带长期面临吐蕃的军事威胁,唐失去这一优良牧区后,不得不将监牧内迁。其内迁的区域,往往农业发达而畜牧业发展有限,如襄阳和泉州等地,在蓄养大批马匹以后又管理不善,常常大量死亡。原本河北地区适合养马,但是河北藩镇长期是中央心腹大患,这一地区自然不可能成为唐政府的养马地,淮北一带虽然也适合养马,但是这一地区的藩镇也时常不听从中央号令,唐同样无法在此地养马。唐后期比较成功的监牧主要在银州等地,银州刺史刘源就曾请求在其辖地建立监牧,太和七年十一月,度支、盐铁等使奏:“以银州是牧放之地,水草甚丰,国家自艰虞以来,制置都阙。每西戎东牧,常步马相凌,致令外夷浸骄,边备不立。臣得银州刺史刘源状,计料于河西道侧近,市孳生堪牧养马,每匹上不过绢二十匹,下至十五匹。”[10]1147这一地区的监牧发展非常顺利,不到四年时间,就从三千匹发展到七千余匹,“开成二年七月,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刘源奏,伏准太和七年十一月敕,委臣于银州监置监城一所,收管群牧,自立务以后,今计蕃息孳生马。约七千余匹”[10]1147。而且其牧地不断得到扩展,这是唐后期比较成功的监牧,此外离长安等地比较近的一些监牧也得到了保留。
困扰唐后期官营养马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牧争地。中唐以后,内迁监牧就面临征用土地以设立牧场的问题,必然需要处理农牧争地的问题,唐代的统治者又多以行政手段获取民田作为牧场,引起了地主的反对,“其数益多,出于远界须有凭倚,今访择得绥州南界,有空地周回二百余里,堪置马务……是臣当管界内空地,并非百姓见佃田畴,今请割隶……如实无主,使任监司收管”[10]1147。可见银州刺史在试图扩展其牧场时,都需要确保这一土地无主,以免激起矛盾。
临汉监征地四百顷,按照唐代土地的产量计算,将农田转变牧场并不合算,《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载,元和中“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余、水运使……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共耕种土地一千九百五十顷,每年收粟二十万石,合每顷大约产粟一百零二石。当然也有更高的,《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载,贞元八年(792)嗣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治荆州,今湖北江陵),在江陵东北七十里重修古堤,整治废田,“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一钟大约合粮六石四斗,一般而言,襄阳地区的善田产米应该在每亩二石以上。善田四百顷,产米八万石,以文宗开成元年(836)二月和籴粟麦,贵籴每斗六十文,平籴每斗五十文,贱籴每斗二十五文。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粮价水平,以平籴时的价格作为当时通常的粮价水平。平籴时,粟每斗五十文,按照唐代粟、米比价计算,则开成元年(836)的通常米价约为八十五文每斗。一石米八百五十文,米八万石,折合八千八百六万八千万文钱,以每匹绢大约一千文计算,大约有绢六万八千匹。唐代后期向回鹘买马价格为每马四十绢,照此计算,大约可以换得马一千七百匹,远多于临汉监所养的千马。因此在内地养马并不划算。不仅在襄阳地区设置监牧不划算,晚唐所管辖的很多地区都不划算,文宗大和二年就因经济上的不划算废除了海陵监牧,“海陵是扬州大县,土田饶沃,人户众多,自置监牧已来,或闻有所妨废。又计每年马数甚少,若以所用钱收市,则必有余。其临海监牧宜停。令度支每年供送飞龙使见钱八千贯文,仍春秋两季各送四千贯,充市进马及养马饲见在马等用。其监牧见在马,仍令飞龙使割付诸群牧,收管讫分析闻奏”[11]。文中“若以所用钱收市,则必有余”一句证明在农业地区,特别是赋税重地设置监牧养马得不偿失,这也正是很多监牧设而又废的原因。
在传世文献中论述较多的监牧主要有沙苑监、万安监、银州监、临海监、龙陂监等,许多监牧设置不久就予以废除,实际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主要有沙苑监、银州监、龙陂监、楼烦监等四监,据学者推测晚唐的马匹不会超过十万匹,“贞元二十年(804)前国家监牧养马不过四万匹。元和至大和二年(828)是中唐后监牧养马的高峰,恐也不超过六万匹,难望唐前期之项背”[7]97,因此元稹所说“臣闻平时七十万马”,“如今垌野十无其一”[12]。随着中央政府的监牧一蹶不振,地方藩镇的养马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武宗时期,昭仪节度使刘从谏“畜马高九尺,献之帝,帝不纳。疑士良所沮,怒杀马,益不平”,“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13]1355,从文中可以看出,潞州地区的养马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水平了,能够通过养马业每年获得钱数百万,在一定范围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优良的品种,被称为“津梁种”,刘从谏向皇帝进献的马匹可能就属于这一品种。不仅昭仪节度使在其辖区大力发展养马业,其他的节度使也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在自有辖区养殖了大量马匹,以河北三镇养马的规模最为庞大,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在拥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等十余州后,“复取曹、濮、徐、兖、郓,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马,岁不绝,赋繇均约,号最强大”[16]1346。靠近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所在区域适合发展养马业的,地方藩镇都积极地进行养马等活动。
三、唐前期对于官营养马业的投入及成就
唐初期官方养马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统治集团的重视、选贤任能、管理得当、积极引进优良马匹,以改良马种,“它们已与大批不同品种的马匹杂交。如703年向唐朝宫廷奉献的大食纯种马、由吐蕃人于654年奉献的小野马,同时还有霍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基什、喀什、买卖城、弭秣贺、库塔尔马、犍陀罗、于阗、龟兹马、贝加尔湖的黠戛斯马等”[13],大量马种的引进,明显提高了唐代养马业的发展水平。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获取了大量的马匹,这一点也促进了其养马业的发展,贞观四年(630)对突厥的作战中就“获杂畜数十万”;贞观九年在对吐谷浑的作战中也获得了大量牲畜(“获杂畜二十余万”),同时还有以朝贡等形式获得的大量马匹,如薛延陀在贞观十七年“献马五万匹”,以这种形式获得的马匹也充入监牧中,在绢马贸易中买到马匹,很多也进入监牧系统,但是更多的马匹则来源于贸易,“陇右地区的马场基本上都是通过绢马贸易获得的良马充实建立的,麟德年中,陇右牧马蕃生达七十多万匹,后经战争损失,由于绢马贸易的补充,开元年间有四十三万匹”[14],另外,政府长期大量地买马也促进了唐代前期官营养马业的发展。除此以外,唐代前期养马业的兴盛更得益于政府对于养马业的持续投入,古代养马的成本较高,而且要占用大量土地,马匹的养殖成本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承受的,只有官僚、贵族、地主和部分养马专业户等才养有大量的马匹,一般居民很少备有马匹。
正因为养马业需要高额的投入,唐代前期经济实力强大才能够支持庞大的监牧运行,从而保有大量的马匹。唐代的马匹每日耗粮数据如下记载,“诸尚乘马,秋冬日给蒿一围,粟一斗,盐二合,春夏日给青刍一围,粟减半”[4]331,同在长安的太仆寺典厩署所管辖的马匹每日耗粮数与尚乘署一样,“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如此计算,一匹马每年消耗粮食在三十石左右;军马的耗粮标准是“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个月十八石”[15],监牧和驿所的马匹也消耗大量的粮食,出土文书中也有大量关于驿所粮食消耗情况的记载,《唐天宝十三——十四载(754—755)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该文书就记载了长行坊下属各管驿匹食用料的记载,其中马匹的食料,如某馆“九月一日,郡坊马肆拾匹,内贰拾陆匹食全料,送旌节;拾肆匹食半料,共食麦三硕三斗。付健儿兹秀元,押官杨俊卿”[16]252-253。从文中可以发现,全料为1斗,半料为0.5斗,不同的马在不同的情况下食用的口粮数量都有所不同,细马数量较少,“廿五日,郡坊细马伍匹,食麦粟伍斗,付兽医曹驼鸟”。唐代政府为了保有大量的马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有关马事的劳动者数量也极为庞大,马事劳动者每年消耗的粮食数量也非常多,据学者马俊民等研究认为,“开元末共计马数七十五万八千匹,年耗粮一千零九十一万石……养马业全年消耗一千一百三十四万二千石”[7]47,而且唐政府发展养马业,并不以谋利为目的,“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出卖马粪,非佳名也,乃止”[17]。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得官营养马业维持下去,除了政府的大量投入,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采取开拓大量的营田、屯田、向民间征收等措施。
唐前期政府拥有大量田地,有足够的实力开拓营田、屯田等,监牧八坊[注]唐代监牧下属的八处养马之所。都拥有自己的营田,以做到自给自足,减少政府的负担,负责马政的官员同时也掌管大量的营田,牛仙客、王鉷等都兼任支度营田使[注]主管营田经营的一个职位。,八马坊拥有营田一千余顷,长行坊就有自己的营田小作可以补充粮草,《唐上元二年(761)蒲昌县界长行小作具收支饲草数请处分状》[16] 252-253就记载了蒲昌县营田的情况,现转录如下。
1.蒲昌县界长行小作状□
2.当县界应营易田粟总两顷共收得□□叁千贰百肆拾壹束每粟壹束准草壹束
3.壹千九百肆拾六束县□□□
4.□拾捌束上,每壹束叁尺叁围。陆百肆拾捌束□□□
5.陆百伍拾束下,每壹束贰尺捌围
6.壹千贰百九拾伍束山北横截等三城□
7.肆百叁拾束上,每壹束三尺三围。肆百叁拾束,每壹束三尺壹围。
8.肆百叁拾伍束下,每壹束贰尺捌围。
9.以前都计当草叁千贰百肆拾壹束具破用,见在如后。
10.壹千束奉县牒:令支付供萧大夫下进马食讫。县城作。
11.玖伯束奉都督判,命令给维磨界游奕马食。山北作
12.壹千叁百肆拾壹束见在
13.玖百肆拾陆束县下三城作 叁百□□□束北山作
14.右被长行坊差行官王敬宾至场点检前件作草,使未至已前,奉
15.都督判命及县牒支给破用,见在如前,请处分。谨状。
16.牒件状如前谨牒
17.上元二年正月 日作头左 思 训等牒
18.知作官别将李小仙
从此件出土文献来看,蒲昌县长行小作拥有的田地大约有两顷,土地较为分散,分别在县下三城作和山北的三城作,收集的草共有3241束。唐为了保有大量马匹等牲畜,在全国各地都设置有此类小作等田地,如柳中县城长行小作、柳中县界长行小作等,在高昌、交河等地这一类的小作非常普遍,正是这样的小作极大地减轻了唐政府养马业的负担。
除此以外,官方还建立了向民间征收草料、马匹的制度,在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出草账》就记载了向民间征收草的情况,少者交草一束,“范龙才壹束”,多者数十束,“龙兴寺贰拾肆束半”,“崇圣寺拾肆亩肆拾玖束”[16]23-25。这种税草的行为在唐代极为普遍,“贞观中,初税草以给诸闲厩,而驿马有牧田”“唐前期的税草,为地税的附加税,据亩征收。建中以后,税草制仍存而未废,这时的税草成为两税的附加税”[18],通过向民间征收各类资源也为唐代养马业减轻了负担。
唐代前期养马的牧场规模庞大,拥有的牧丁多达数十万,官方养马业正是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养马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唐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正是由于唐政府细致的管理和持续的投入,唐代养马业从五千匹马起步,逐步发展壮大,“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唐代正是自此建立了自己的监牧制度,至高宗时,马匹数量达到了七十万六千之多,“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9]443-444。这七十万六千匹马仅仅是监牧所拥有的马匹数量,实际这一时期唐政府在军队、驿站、闲厩以及其他机构还拥有特别多的马匹,特别是军队和驿站,唐代军队的马匹数量非常多,北庭翰海军拥有的马匹数量就有四千余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云“北庭瀚海军马四千二百匹”,另外驿站自身拥有的马匹也不少,仅西州长行坊,所管辖的马匹在千匹以上,《大唐六典》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如此多驿所,需要的马匹数量也是极为庞大。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9]444。政府各类机构中总计拥有的马匹数量远多于监牧中马匹的数量,整个官方养马业不仅仅依靠太仆寺、监牧等机构,军队、驿站等用马大户也从需求的角度推动了养马业的发展。
天宝末年,安禄山因任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等职位,乘机挑选大量马匹至范阳,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士兵前往平叛,陇右空虚,“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9]444,吐蕃入侵后,大量马匹损失,许多优良的牧场也落入吐蕃的控制之下。此后,唐政府又多次试图重建官府监牧,德宗贞元时,“会(柳)冕奏:闽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马,置牧区于东越,名万安监,又置五区于泉州,悉索部内马驴牛羊合万余游畜之。不经时,死耗略尽,复调充之,民间怨苦”[9]880。由于自身军事力量的削弱,境内藩镇割据,互相争斗,周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使得朝廷的监牧破坏严重,朝廷虽然一度将监牧地向其他地区迁移,但是由于农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与农业激烈争夺土地,监牧此后发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马匹的供应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与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
四、结语
总体而言,在安史之乱以前,国家实力强大,政府掌握了广袤的牧场,这些牧场为监牧和民间养马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养马业的繁荣为军事实力的强大奠定了基础,军事上的强大又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因为前期养马业的日渐繁荣,唐代才能够拥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同时,由于官方对民间马匹贸易的管理较为宽松,马匹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显得非常活跃。随着中唐之后国家实力的衰弱,养马业的规模日渐缩小,大量的监牧在内迁后都面临农牧争地、环境不适宜等困难,官营养马业不断萎缩,整个国家缺马的情势也日渐变得严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