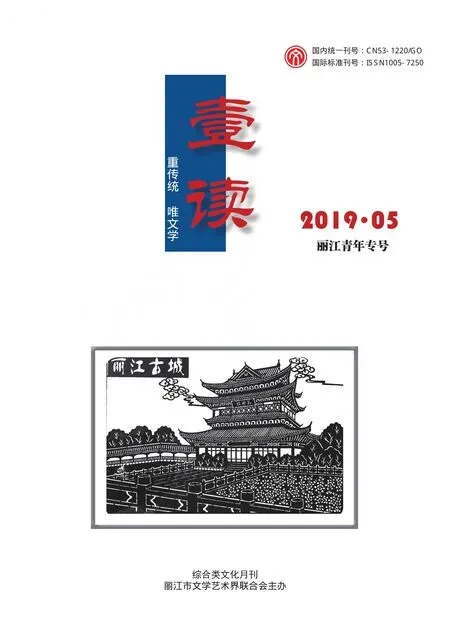有话可说
——读三篇丽江小说
◆宋家宏
丽江的小说我读得不多,但是知道丽江有深厚的文学传统,不断出现有作为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丽江的诗人和小说家往往很低调,似乎不大注重宣传自己,只是静静地写自己的作品,突然就出现让人感到惊异的作品和诗人、作家。本期我所读的三篇小说,让我感到惊异,又让我感到有所不足。评论的出发点在于“对话”,与作家的对话,与作品的对话,说过之后其实也就烟消云散了。重要的是所读的作品能不能刺激你想说话,有话可说;然后实话实说,写出你想说的话,这就是评论了,表达了你自己,足矣,并不希望承载更多的任务与责任。这几篇作品让我有话可说。
一
《我马玄黄》是东巴夫的中篇小说,东巴夫是一位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过去我也读过他的作品。乡村世界的风俗民情、世道人心是东巴夫经常关注的内容,这次他把自己的笔又一次投向了这个熟悉的领域。首先吸引我的是小说的篇名,篇名来自《诗经·卷尔》:“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大约说的是:骑马上山岗,人困马乏,我姑且斟满这杯酒,免得心中常常悲伤。小说以此为篇名,他有多深重的忧愁要向我们传达?
作家把他的故事设置在正月里的乡村,在外谋生的谢观返乡过节,意外在乡政府谋得一份差事,这份差事很是令人羡慕,在乡政府工作,不久他就可以去文化站,这是他喜爱的工作。这份差事来得也太容易,乡长告诉了村长,村长又告诉了谢观的父亲,然后他就站到了乡长的面前,可以说得来全不费工夫。谢观感到他的命运似乎可以由此改变,他成了“官家人”,父母因此而在乡民中有了脸面,村长的女儿也喜欢上了他。开篇一幅欢乐的景象,似乎没有忧,也没有愁。
东巴夫一如既往地写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却在不经意间把一个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世道人心静悄悄地揭示了出来。
如今的乡村,祭天,已经没有多少庄重的气氛,只是一个家族里的仪式而已。仪式已极为简化,过去有一百多项,现在简化到只剩下烧香磕头两项,烹饪却干得如火如荼。所谓正月里的“祭天”,只是族人们最后聚在一起吃肉喝酒。神权,曾经长久统治乡民的精神空间,如今神权的威势早已消失殆尽。只有乡长才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为所欲为,而无所畏惧。他的话决定着别人的命运,那怕是国家给予乡村五保户的救助金,也变成了他个人的恩赐,他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可以多给,也可以少给。所有的人都认可了胡乡长权力的威势,胡乡长可以为所欲为,理所当然地为所欲为。包括村长在内的乡民们对乡长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村长在他的面前卑躬屈膝,对自己在乡长面前的卑微表现,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他怕在可能成为他女婿的谢观面前丢了面子。
一个沉重而死寂的乡村世界。由于作者对乡村生活与人物心理极为熟悉,很轻松很随意地就把这个深重而死寂的乡村世界活脱脱地呈现给了读者。
一个醉鬼打破了这种死寂。这个醉鬼是骆果,骆果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五保老人,骆果是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他脾气很大,当村长领着要在乡政府谋一个差事的谢观战战兢兢地站在乡长面前时,骆果正与胡乡长吵架:“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一个五保户国家都敬我,我还怕什么!你们不把国家发下来的生活物资救助金发给我,我就放火烧山,让你们都丢官帽儿!”我们已经从生活里、从小说中见过不少乡村的泼皮无赖,他们蛮不讲理,得寸进尺,人见人怕。骆果是这样的人吗?扬言要“放火烧山”,他的强势与蛮横,似乎属这类人无疑,胡乡长也怕他三分。谢观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乡长要他去盯住骆果,不要让他去放火烧山。胡乡长干什么都无所畏惧,却害怕丢了乌纱帽,骆果如果真的放火烧了山,他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骆果却是一个极为清醒的“醉鬼”,喝醉时说的是最清醒的话,没醉时说的是“放火烧山”一类的醉话,似真似假,让人搞不明白。他希望谢观这样的人去了乡政府工作,能把乡政府治好了。“乡政府需要一些年轻人来使力,它现在不好,你现在去了,你就把它治好,它不就好了!你就算去对了,唉!我们这些老不死的就算讨了好了。”他说他要放火烧山,那只是吓唬胡乡长一类人的话,还真把乡长吓着了,其实他不会去放火,“我要给你说点真话,就是这个话,我不会去放火,我能去放火吗?我在这个村住了大半辈子,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自己的……我放火烧了,乡政府吃不到什么苦。吃苦的是谁,可不还是我们这些老百姓!你以为我蠢啊!我不会放火,但我不能告诉你们啊!就让你们心里悬着怕着!胡力那小子怕什么,这山烧了,他就要丢乌纱帽,这个政策我是知道的,我就要吓唬他!弄得他不安逸!”他很清醒,他知道太多的事,他粗通文墨,要是在旧时代,他就是一个乡村秀才。正是这样识文断字的人,内心才会感觉到痛苦。读了点书,他不能随波逐流了,却又没有学会与时俱进,攀附权贵。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不能改变胡乡长的强悍,他更不能改变前任村长当三年村长就开上了豪车路虎,他似乎知道这是哪来的钱,但是他无力改变,他连自己应该得到的国家给予五保老人的救助金也不能足额得到。因此,他很累,“我马玄黄”,他只能以酒浇愁,小说写出了他的内心的痛苦。小说还写到了骆果内心痛苦的另一原因,他年轻时候成全了兄弟骆桑,却孤独了自己,老了才发现那本来是自己的家却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守公厕的差事就让他内心得到了解脱,——他可以不回那个本应属于他的家了!
骆果这一形象,在我们读过的小说中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形象,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粗通文墨,他保持了传统社会读书人的那一点正直与担当,却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格格格不入,甚至与他的兄弟一家也格格不入。他的痛苦来源于他作为读书人的清醒,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读书人共同的痛苦吗?
谢观也是一个读书人,他与传统文人没有骆果那样深刻的渊源,小说中的他虽然没有趋炎附势,与孤独老人骆果还保持了一份温情,但他在求职,为谋得一份差事,也必须听命于胡乡长。他的命运与这个清醒的醉鬼的命运却联系在了一起。骆果因酒醉而死,谢观也丢了工作。不是因为他应负什么责任,而是乡长不需要他盯住那个要放火烧山的醉鬼了,乡长一句话,谢观被解聘了。这是小说开篇谁也想不到的,但是小说结束时这个结果却并不出乎意外,胡乡长本来就可以为所欲为。似乎不合常理,却合乎小说的内在逻辑。谢观的精神价值观是漂移的,他最终会走向何方?时间与社会将雕刻他的灵魂。
小说中还写了另一个读书人,文化站的杨大泉站长,这个曾经的中学校长,如今也是一个醉鬼,他在小说中补充了骆果的形象,他是骆果的后继者,从骆果的醉死,读者可以看到他的将来,从骆果痛苦可以窥见他的心路历程。
那个名叫乌衣的出场没有意义。搞纳西文化田野调查的人与这篇小说的主体内容毫无关系,至少我看不出关系在哪。一部中篇小说往往集中写好一两个人物,其他都只是陪衬,出现是为了写出主人公的背景。成为背景人物,他要形成某种气氛而存在,这个气氛要与主人公有关系,成为刻画主人公的一部份,如杨大泉站长。春花的故事占的篇幅不少,但没有深入进去。从开始到最后都只是一个影子而存在,读者知道一点她的故事,到最后也没有比开始更多。这个人物存在于小说中是为了什么呢?这部中篇小说如果去掉一些多余的旁溢邪出,文字更加简炼,叙事更为紧凑,把骆果形象浓缩在几个画面中来表现,可能一个稍长些的短篇的篇幅就可以完成。
二
《远与远方》是一篇让人读来想落泪的小说。一个倔强的女孩,一个不屈的灵魂,命运却让她屈服,她最后的选择充满了心酸与无奈。
如果小说写了一个没有梦想的女孩,浑浑噩噩地嫁给了一个她本不该嫁的人,可能引起我们轻微的叹息,而不会引起我们深重的悲悯。小说写了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几经挣扎,最后屈服于命运。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她的梦想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她的挣扎,对命运的反抗,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这些都被无情的命运毁灭了,因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更可悲的还在于,她的梦想并不伟大,在一些人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只不过是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做一个“国家的人”。国家的人,这个词在农村里曾经广泛地被使用,用得令人寒心,原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因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长久地被漠视。他们一出生就先天地低人一等,不是“国家的人”。改变社会地位,挣脱以生俱来的乡下人身份,成了他们的梦想。大姐是她的榜样,刘老师是她的偶像,他们都经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改变了既定的身份。她经过艰辛的努力,却因一两分之差,与上大学失之交臂,因而不能改变命运与社会地位。乡村青年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小说从80年代就不断出现,是一个撞击许多人心灵的题材。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形象,小说也有了一定的经典性。
作者用一个梦,预示了女孩如果留在理发店可能的结局。嫁给山西的矿工,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她已经丧失信心,只有心酸与无奈。只有刘老师对她还有信心,希望她保持着梦想。
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没有说话,读者从她的行动中可以体会到她的心理,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叙事者与叙述对象等距离的立场,女主人公妹妹的身份,她在为“二姐”的命运鸣不平,叙事中充满了同情与悲悯。也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只能写她眼见的行为与语言,作者只能通过主人公的行为与语言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不能直接去写人物的内心,这其实成为更有难度的写作。小说写得很朴素,没有故弄玄虚,平淡直白的语言,包含深情。
如果说,读完之后还感到有所不足,在于对女孩的心理开掘不够深入,过于平铺直叙,对她的选择中痛苦的挣扎没有写得更有力度,而这是她内心最为丰富的地方,也是最为动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她应该有过非常痛苦的挣扎。如何写出她的挣扎中的痛苦,把一个人心理的挣扎写得惊心动魄,确实需要作者的艺术功力。它需要更丰富的情节与细节,更主要的是对女主人公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体验。她与母亲的关系有明显的冲突,小说已经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下去。而这是女孩内心冲突最无奈之处。女孩是个有梦想的人,但她无力自己完成她的梦想,作为未成年人,她只有依靠母亲来完成,而家庭的现状由不得她长久地依靠母亲,她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
母亲内心充满了矛盾,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在付出艰辛,另一方面必然地情不自禁地要为自己的付出有抱怨,沉重的经济负担必然让母亲有怀疑,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给女孩巨大的心理压力。小说对母亲的心理与性格的刻画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更丰富更动人的细节与情节来突显。母亲的性格与心理刻画不足,也就使读者对女孩的心理压力体会不够。
还有,女孩如此心高气傲,她与乡民们是有冲突的,乡民们对她的落榜,一些人充满了快乐的嘲笑,这也是必然的,这是给女孩心理压力的外部环境。小说也只是点到为止,写得没有力度。
在结构上如果加强第一次落榜后更为丰富的描写,就可以对第二次落榜她的选择,有更为合理的逻辑。第二次落榜即使简略地写,读者也可以从她第一次落榜后的遭遇中体会到她选择的必然性。
三
《瑟几谷人家》的作者很年轻,年轻得让人羡慕。她的文字却非常好,“阿意朵用手掰开一大块粑粑茶,放进煮沸的水,加一点盐巴,再加上一点猪油,这味道在身体里沉淀,身体的记忆会在第二天的早晨醒来,这茶就勾住了你。”类似的文字在作品中大量存在,这是许多人写了多少年也写不出来的文字。
但我不想说好怕文字,这位年轻的作者写起纳西人的风俗民情也是得心应手,随手拈来皆成文章。小说的第一部分就是非常密聚的风俗描写,一个接一个。很少有小说像这样以风俗描写作为一篇小说的开篇的主体内容。作家们往往是在写其他生活内容时,作为生活内容的一个部分自然地展示出风俗民情。但是这篇小说不同,作家把风俗描写作为小说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90 后的作家,把纳西人的风俗习惯写得如此生动、鲜活,实在是一个奇迹。不仅说明纳西族的与众不同,纳西文化有强大的力量,在现代化进程如此强悍地推进的过程中,纳西文化依然鲜活地生存在纳西民间。还说明这位作家有很强的观察、感悟能力,这是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必要条件。
一些小说写到民情风俗,特别是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往往成为增加读者阅读兴趣的附属性描写,这些描写与小说的故事进程无关,为了吸引读者,甚至走向搜奇寻异的歧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那些“采风写作”的外来者笔下,也出现于写自己生活的少数民族作者笔下。他们以为这可以吸引读者,这样写可以获得亲睐。
《瑟几谷人家》中的民情风俗却不是外在于故事的附加物,它与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内心价值,人物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是构成人物性格冲突的重要内容。作为奶奶的阿意朵与阿了母女在一系列生活问题中形成了冲突。学校要教普通话,孙女回家想讲普通话,奶奶则不允许,她固执地认为讲普通话就影响了讲纳西话,甚至冲到学校去顶撞老师。但在今天的时代发展、社会交流越来越广泛的环境中,不会讲普通话,怎么生存于世呢?作者以非常风趣、幽默的笔调写出阿意朵与儿媳、孙女在是否刷牙问题上的冲突,这是一种生活习惯,阿意朵从来没有这种习惯,而孙女从小就受了文明的教育。阿意朵从不刷牙,但她在向祖先献茶时却是诚心诚意的。老了老了,她不忘老规矩,一天三回,献饭,献茶,献酒。她是善良的,在向祖先献祭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在她颂福的范围里,但这样的一天三献,在孙女看来繁琐,无聊。
如果一篇小说醉心于描写民俗风情,而忘了由此开掘更为深入的内容,那么,这篇小说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瑟几谷人家》进一步揭示,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与旧有的思想观念融为一体,与旧的生活习惯,甚至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朝代,纳西人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盛行,它就是民情与风俗。阿意朵深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她的一生都在为生一个儿子而努力,十三个女儿耗尽了她的心血,终于有了一个儿子。阿意朵一方面是这种旧的思想观念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坚定的捍卫者。这是她与儿媳与孙女发生冲突的重要内容。阿意朵的妈妈住在大女儿家,却不忍心忘记命运不好的小女儿,她要关照受苦的小女儿,大女儿夫妻心怀不满,常给她气受,她受不了他们的气,最后上吊死于树林里。阿意朵却没有能力照管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是女儿。
旧的民情与风俗还与贫穷、匪患合为一体,阿了爱听奶奶讲抗击土匪的故事,惊心动魄,而且与土匪周旋、从土匪身边逃离,并让两个土匪死于非命的人,就是自己的奶奶,就是给她讲故事的人,这实在太令人惊异且有魅力了!但是,阿了决不想回到那个时代。
小说作者站在时代发展的立场,对旧有的民情风俗必将消失有清醒的认识,奶奶的木楞房注定是要消失的,旧的风俗民情也是要消失的。她似乎是在为它的消失唱挽歌,但这曲挽歌的抒情部分又非常弱,太过清醒的认识使得文学要表现的复杂性丧失了生存的空间。而风俗民情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与时代隔膜,它们中的一些要素还会与时代同步发展,在新的时代开出艳丽的花朵。这是一个民族得以保持其特色的重要原因。但哪些民情风俗会与时代同步,并得以丰富和发展,这需要时代的检验。作家理应站在文明发展的前列,作出自己的判断,给予那些能与时代同步风俗民情肯定与鼓励。这一要求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过于苛求了些,但我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这几篇小说皆有扎实的生活底子,作者所写皆与自己的生活阅历有密切关系,不是坐在书房里编造出来的,从所用细节即可看出作者的生活积累。但如何在丰富的生活积累基础上腾飞起更为丰富的想象?也许是每位作者都面临的问题。毕竟,小说是想象的艺术,在想象的艺术中更能穿透人物的心灵世界,给予读者更深透的感悟,也是每一位作家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