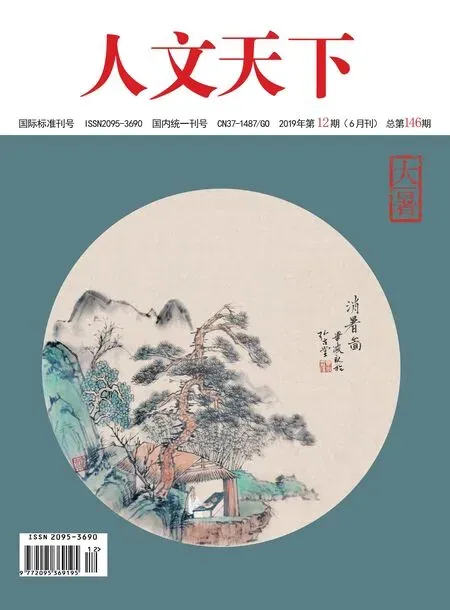感受 “十二艺”
孙海翔
时隔三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如期而至。依然百花齐放,剧目纷呈。参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17台戏曲类剧目、14台歌剧舞剧类剧目以及7台话剧类剧目,均有着唱响主旋律,彰显时代情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主流价值的取向。本届艺术节最终获得十六届文华大奖的10个剧目:话剧 《谷文昌》 《柳青》、秦腔 《王贵与李香香》、豫剧 《重渡沟》、苏剧 《国鼎魂》、河北梆子 《李保国》、民族歌剧 《马向阳下乡记》以及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天路》 《草原英雄小姐妹》,更是对爱国主义、红色记忆、时代风貌、奋斗精神的多角度、多方位展现。以它们为代表的现实题材剧作,无疑已成为当今舞台艺术的主力军,正在承载着发新时代之声的重任。而这些作品的集中亮相,则映射出当前舞台艺术创作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是主题立意上,逐渐走出了对本土的狭义理解,引申为更宏阔的家国情怀
“十二艺”参演剧目中,本土题材剧目依然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且以戏曲类中的地方戏曲剧目尤为突出。比如几部扶贫题材戏:黔剧 《天渠》、豫剧 《重渡沟》和秦腔 《民乐情》;地方名人戏:京剧 《杨靖宇》、黄梅戏 《邓稼先》、河北梆子 《李保国》;甚至苏剧 《国鼎魂》、荆州花鼓 《河西村的故事》、白剧 《数西调》等,均基本延续了近些年戏剧创作大气候中各地注重本土题材创作的意向。这当然与地方戏曲擅长表现流行地本土特色故事的艺术特性有着直接关系,似乎并无不妥,但客观来说,这样的创作意向虽然离质朴而熟悉的生活接近,却很容易一不留神,就陷入地方性的思维圆环,从而欠缺对时代大格局的融入性思考。因此,只有在普遍事件中提取更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更具核心价值的部分,让那些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名人成为典型性形象,或者将发生在地方的一般性事件萃取加工成为超越普通的一例,方能走出对本土的狭义理解,也方能使剧目在主题上脱颖而出。而本届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地方戏曲剧目中,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艺有限公司演出的 《李保国》、上海沪剧艺术传习所演出的沪剧 《敦煌女儿》等,就无论在题材的选择还是主题的设定上,均具有立足本土而超越本土的家国情怀,从而显现出一定的时代视角。
相较于地方戏曲与本土题材之间比较明显的共生关系,多数 “十二艺”话剧类剧目的本土属性并不特别突出,与前些年相比,关注意识形态和话剧本体表现的趋势更为明显。几部地方院团的话剧,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的 《追梦云天》展现的民航人的家国情怀,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 《苍穹之上》表现的航空人的使命担当,在题材的选择上比较宏观。西安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 《柳青》虽然在选材上具有一定的本土属性,但是人民作家深入生活,书写人民、书写时代的主题却超越了本土。
话剧剧目中本土色彩最为浓重的 《干字碑》属于典型的主题性本土题材剧目。擅长现实主义创作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带来的这部话剧,仅就其表现核心人物毛丰美的主题而言,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同时,该剧所具有的本土属性,显然不像地方戏曲那样是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而是很大程度上与 “辽艺”的艺术风格有关。因此,就只能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来考量。
二是表达方式上,逐渐回归民族叙事传统,彰显出更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
本届艺术节获奖剧目在表达方式上有着一个共性特点,就是10部剧作中,除了以一个家族保护国之重器的故事,抒发爱国情怀的 《国鼎魂》在时间线上跨越了晚清-近代-新中国几十年时间之外,另外几部剧作均聚焦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而纵观“十二艺”期间上演的大多数剧目,这一中国化的结构及表达剧情的方式,无疑已成为主流。这样的表达,显示出当前舞台艺术的创作思维开始回归中国 “剧”的传统,即重回 “以歌舞演故事”或托物言志的中国戏剧表达。
诚然,戏曲和话剧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一直以来都是以讲述故事或塑造人物展开。难得的是“十二艺”期间上演的歌剧舞剧类剧目,也整体走出了曾经有过的各种花哨 “意象”,大多是以中国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尤其是几部民族歌剧和民族舞剧的演出,更令人为之一振。
广州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演出的 《醒·狮》,是一部真正配得上民族舞剧名号的舞剧。就舞剧层面来说,该剧以南粤醒狮为核心素材,以近代鸦片战争时期为年代背景,阐述了一个由阿醒、龙少、风儿、醒母几人为主演绎的,富有南粤风情的国事与家事交织故事。并且,该剧最终以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为爆点,将舞台叙事推进到高潮,完成了整部剧的故事讲述和人物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醒·狮》基本摆脱了需要借用舞蹈语汇之外手段来注解剧情的舞蹈连缀式 “舞剧”创作方式。全剧没有旁白,只凭借舞台呈现和演员肢体表演,就清晰地完成了剧情的叙述、人物个性的塑造以及情感情绪的变化。而就更具体一些的民族舞剧层面看,该剧可谓更进一层。
首先在表现手段上,该剧不但将醒狮、南拳、中国鼓等具有符号性质的中国民间元素充分融入舞蹈,大大丰富了舞剧的民族语汇,并且在民族性中融合了创新型的表现。比如茶楼场景中,桌子呈立面的舞蹈;三元里狮王争霸赛一段呈现出的镜头感等,都对舞剧表现的新鲜感有所提升。在舞美与舞蹈融合方面, 《醒·狮》的舞台主体装置中有一个大型的竹编舞狮头部骨架,贴题而简洁,同时具有写意性的舞台美感。此外,这一竹编舞狮头骨并非单纯为了舞台装饰,它在剧情中有时是舞蹈动作的载体,有时则化身为情感情绪的表达,既体现出浓浓的民族艺术创意,又成为关联着剧情的有生命的道具。
其次,在戏剧结构与人物塑造上, 《醒·狮》也充满了中国式的巧思。剧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阿醒和龙少两个后生,是原本处于对立关系中的一对舞狮者,后来由于故事主题的深入,二人为了民族大义站到了一起,同心协力,抵御外敌;少女凤儿,是龙少的妹妹和阿醒的爱慕者,被设置为领狮人的角色。在剧中,她一直为阿醒和龙少的对立关系而苦恼,最终是因为她的自我牺牲,完成了对阿醒和龙少这一对 “狮子”的精神提升与引领;阿醒的母亲则充当了击鼓者的角色,由她引领的一段振奋人心的击鼓场面,直接点燃了人们反抗侵略的热情,并将故事推向高潮。这样的人物设计,是将处于剧情中的人物与舞狮表演中的角色一一对应,不但增强了舞剧的巧思,更彰显出具有中国文化的深厚韵味。
三是审美表现上,显现出综合性、多样化甚至复杂化的状况
如果说 “十二艺”剧目的主题,主体为讲述中国故事,其主要表达方式,是整体注意到运用中国语汇的重要性。那么在审美追求上,则较少整体性的指向,而由于本届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剧目以各地推荐为主,在创作水准和艺术质量上客观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在以审美追求为基础所形成的可看性和观赏性方面,自然呈现出不同层级的表现。
总体来看,本届艺术节期间演出的歌剧舞剧类作品,在观赏性上要略胜一筹。若与戏曲类作品相比,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着部分创作意识上的主观原因。
客观上,首先是歌剧和舞剧的包容性比戏曲要广,对于民族歌剧或舞剧剧目来说,民间艺术、非遗因子和戏曲元素,都是能够被轻易吸收容纳进剧目表达内容的元素。以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演出的 《马向阳下乡记》为例。该剧演员阵容中其实有不少戏曲演员,并且这部分演员在表演上也是带有戏曲化表演痕迹的。但是这样的加入,在这部表现农村生活的民族歌剧中非但不嫌生硬,反而成为了 “加分”项。戏曲因素的植入,不仅为部分剧中角色赋予了个性化的创造和更多生活化表现,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歌剧的韵味。
其次,近年来比较常见的名编剧+名导演创队团队的创作模式,对于歌剧舞剧甚至话剧来说,客观上是具有一定提升作用的。由见多识广的主创团队炮制的非戏曲类舞台艺术作品,在创作思维上无疑具有更多的创新性,但是对于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而言,有些非专业的加入则有可能弱化戏曲的程式及其个性表现。
而从戏曲创作的主观角度看,一方面,熟悉戏曲的创作者们由于业务范围所限常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习惯性思维,这样的创作思维,是戏曲的本体特性决定的。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展现更宏阔的主题,以及运用更具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对从业人员都是不小的考验。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出现老观众不买账,同时又无法吸引新观众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戏曲的核心是讲述故事。因此有些题材并不一定适合以戏曲形式来表现。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好剧种特色元素和植入地方特色资源就成为吸引观众的一个选项。虽然在结果上未必能获得所有观众的认可,但因其带有戏曲审美渗透的意味,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展的方向。比如国家京剧院演出的 《红军故事》由三个拥有共同主题的小故事连缀而成,在体现传统的戏剧性方面并不占优势,更多是在艺术审美和综合性表达上下了一番功夫。其中, 《半条皮带》中小旦角色与小武生角色的互动,有戏曲表演身段的呈现。 《半条棉被》中四个旦角的合 (轮)唱段落,有编曲的匠心。 《军需处长》则运用了更多的综合性表现。尤其是军需处长在风雪之中弥留之际的一段独角戏,考虑到现代观众的 “快感受”审美习惯,加入了人物思念家乡、想念未婚妻的联想段落,继而打破了独角戏的单调,丰富了舞台呈现的层次。在揭示人物此时复杂心理活动,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他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我伟大精神的同时,还以类似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意识流段落,使观众体验到具有温暖和治愈作用的观感。
虽然舞台艺术作品的审美追求并没有客观标准,但贴近剧情且让观众赏心悦目却是一个必需的条件。然而本届艺术节中的个别剧目,虽然有着不错的主题,在审美艺术上的表现却 “复杂”得让人一言难尽。这说明,目前的艺术创作,尤其是目标性剧目创作中,依然有不少平庸之作甚至浮躁之作的存在。
以历史的眼光看,目标性艺术创作本身本无可厚非,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反映时代,书写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核心。但是如何能从创作的 “高原”中脱颖而出,成为 “高峰”,并不仅仅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转化过程。也就是说,舞台艺术作品数量上的积累,并不能成为其产生精品力作的必然前提。积累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吸收,继而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这一方面,无论对于艺术创作的主导者还是创作的实践者,都需要提升思考站位、强化专业认知以及解除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式。而对于创作的实践者来说,还进一步需要戒除浮躁之心,避免自以为是,以对时代的浸入式思考和对生活的体验式理解,进行艺术创作,接受时代和人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