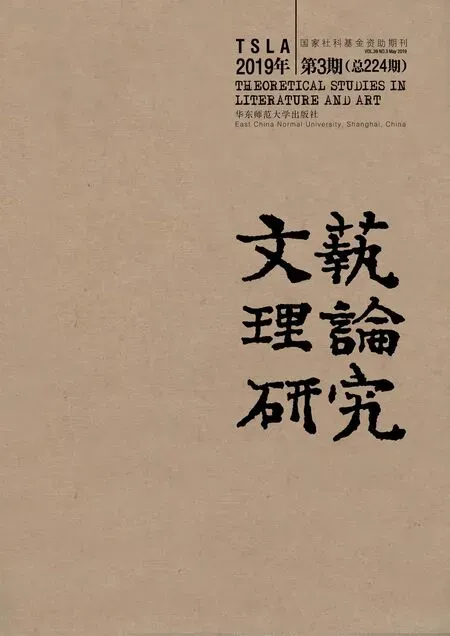自然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冯晓玲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象喻传统,学界的探索目前已有不少,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以人体自身为喻,早期探讨如钱钟书所说的“人化传统”,吴承学进一步概括为“生命之喻”;二是以人类社会中的人文器物为喻,已有的研究包括以锦绣喻文、以兵法喻文、以兵器喻文、以容器喻文等;三是以自然物为喻,包括以山水、日月、风景、动物、植物等自然界中的事物来譬喻文学的现象。在自然物之喻的研究中,目前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个别的自然物之喻,如以水喻文、以山水喻文等。不过,与文学批评中的人化之喻、人文器物之喻相比,自然物之喻的研究尚不充分。其实,以自然物喻文的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大量存在,内容丰富复杂,对其做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以此为题,做一些分析。
一、自然物喻文的历史发展
所谓自然物之喻,是指以日月、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物象作为喻体来譬喻文学的批评方式。自然物之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其发生、发展、演变、传承的过程。
汉末魏晋时期,被一些学者视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白华 177)。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不再像汉代《诗大序》那样凸显儒家诗教观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而是开始大量地以自然物象来譬喻文学。在《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经典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有体现。如,陆机《文赋》云“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36),是用“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等自然景象来形容文学的构思、想象等活动。又如,钟嵘《诗品》评颜延之时引用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270),便用芙蓉出水的自然景象及错彩镂金的人文景象来分别形容谢灵运、颜延之的诗歌风貌。又如,《诗品》评范云、丘迟诗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312),便用“流风回雪”“落花依草”两种自然景象来形容范云、邱迟诗歌的审美风貌。再如,《文心雕龙·风骨》篇云“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刘勰 321),以翚翟、鹰隼的“色”“彩”与飞翔状态等比喻文章之“才力”,用“鸷集翰林”来比喻“风骨乏彩”,用“雉窜文囿”来比喻“采乏风骨”,都用自然界中飞鸟的外在形体与飞翔状态等来比喻文章的文采与风骨。又如,《文心雕龙·隐秀》篇论文章之“隐”时说,“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431),论文章之“秀”时说“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431),是用“川渎韫珠玉”“远山浮烟霭”等自然景象来形容所论述的文学风格。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自然物之喻已经在文学批评中广为应用,并且涉及文学构思、文学审美等多个文学活动层面。
唐宋元时期,文学批评中的自然物之喻进一步发展壮大、范围拓展,在新兴的诗格、文格、诗话、词话、文章学等相关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广泛使用。譬如,晚唐五代诗格著作如《诗格》《风骚旨格》《雅道机要》等,都有以“势”论文的特色,而所谓的“势”,大都采用自然物之喻的方式来表述。如齐己《风骚旨格》中的“诗有十势”是“狮子返掷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毒龙顾尾势、孤雁失群势、洪河侧掌势、龙凤交吟势、猛虎投涧势、龙潜巨浸势、鲸吞巨海势”(403—404),而这十种诗歌之“势”,都是用自然物象的譬喻方式来表征诗歌的一些规范与体式。又如,宋朝张炎《词源》中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16),也是用自然物象来譬喻词风的批评方法。自然物之喻在宋元时期新兴的文章学著作以及文学评点中也有表现。例如,宋朝谢枋得《文章轨范》评韩愈《送孟东野序》云,“有顿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扬,如层峰叠峦,如惊涛怒浪”(1059),用“层峰叠峦”“惊涛怒浪”等自然景象来形容韩愈文章句法多变之美。这一时期的自然之喻,从批评范围看,从早期诗文评拓展到诗、文、词等多种文体之中。从批评方式看,形成了一些带有程式化倾向的术语,如诗格中的自然物象之“势”等。从批评文体看,无论是专门的诗文评著作(如诗话、词话、诗格、文格)还是新兴的评点类著作(如总集、选集类的评点)都运用了自然之喻的批评方式。
明清时期,自然物之喻进一步拓展到新兴的曲论、戏曲批评、小说批评等领域中,并且一些固定化、程式化的批评模式继续使用。如,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评论各位元曲作家艺术风格时,大量选用由四字组成的自然风景词汇来譬喻,如“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22),“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22),“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22),“李寿卿之词,如洞天春晓”(23)等;论述“国朝十六家”时,同样也用四字的自然风景来形容,如“王子一之词,如长鲸饮海”(28),“刘东生之词,如海峤云霞”(28),“杨景言之词,如雨中之花”(29),“夏均政之词,如南山秋色”(29)等。这种四字格的譬喻方式已经具有程式化、模式化的色彩,与唐宋时期“诗格”“诗式”中的“格”“势”的四字譬喻法一脉相承。明清时期小说批评中,也使用自然物象来譬喻文学之美。以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为例,如“《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朱一玄 刘毓忱编 302)一段,用自然界中的风景变幻来形容小说叙事的变化多端;“《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303)一段,以自然界中横云断岭、横桥锁溪的风景连断来形容小说叙事的连断之妙;“《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303)一段,用自然界中前后相序的风景来形容小说中相关事件衔接组合之妙;“《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304)一段,用自然界中“浪后波纹、雨后霡霂”的自然景象来形容小说叙事中描写后事、交代下落的余波之妙;“《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304)一段,用自然界中冷热交替的现象来形容小说节奏紧张与舒缓相间、张弛有度的情形;“《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307)一段,则用自然界的山峰对插等情景来形容小说叙事中事件与事件之间形成的相反相成的组合状态。
绾结而言,自然物之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展。从被譬喻的文体来看,自然物之喻随着各文学文体的兴衰更替,从早期的诗文批评一直拓展到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等各类文体的批评中。从譬喻方式来看,汉魏晋时期多采用对具体自然物象进行描述的方式,唐宋元时期则形成了一些与自然物象相关的“格”“势”等模式化、程式化的四字批评范式,明清时期这种模式化、程式化的批评范式则进一步固定下来,并且多用来譬喻文学的“格”“势”“式”及作家作品的美学风格等。从譬喻层次来看,自然物之喻涉及文学的构思、文学的构成、文学的风格、文学的审美风貌等各个层面。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涉及多种文体、多个层面,并以多种譬喻方式呈现,自然物之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
二、自然物喻文的学理依据
中国文学批评中以自然物喻文的现象,有其深层的学理依据。
首先,从文学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发生与自然物之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物感论”是中国文学发生论的重要观点之一。如钟嵘《诗品序》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又如《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493)四季风物、自然风景的轮转变迁,使诗人感发情志,触动灵感与才华,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产生,常常与自然物的感召有关。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文赋》《文心雕龙》中运用自然物象来譬喻文学的想象、构思等活动,因为文学的产生、想象、构思等活动往往是在与自然物的接触之中有所感兴才能产生的。正因如此,汉魏晋时期自然物之喻的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对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绘较多。同样,在古代书法批评、绘画批评等其他艺术批评中,自然物之喻能够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些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与自然世界有着紧密联系。譬如,中国文字、中国书法、中国文明的起源都与自然物象相关。在出土文物中,早期文明的起源常常与一些图象、刻符相关。而这些图象、刻符既是对自然物象进行观察的印记,是中国文字、中国文明的源头,又是后世书法、绘画等艺术的萌芽。在中国汉字造字法中,“象形”是重要的造字原则之一,而“象形”也同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与表现相关。这样,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生与自然物有关,于是在书法、绘画等艺术批评中,以自然物象来譬喻书法、绘画的造型方式、构成特点等也就成为可能。因此,从文学艺术发生论的原理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等艺术批评的自然之喻,符合文学艺术发生学原理。
从中国美学传统来看,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采用“物象表达”的方式,符合中国美学的一贯传统。所谓“物象表达”,指的是古代文学批评中,通过描述自然界中一些具体的景象、物象等,来描述、传达文学想象、文学构思、文学经验等文学活动。这种文学批评“物象表达”的过程中,批评家没有对文学活动本身的构成机制进行分析和解剖,而是通过对文学之外的他物(即自然物象)进行描述的方式来比附、形容文学。这种以描述他物的方式代替分析此物的做法,符合中国艺术批评、中国美学的一贯传统。
譬如,在中国书法美学中,以自然界的各类物象来形容书法之美是书法理论最初的表达方式。当代学人将最古的书法理论称之为“喻物派的书法理论”(熊秉明 5),认为“最古的书法理论是用自然事物之美来描写书法之美的[……]评论家用自然事物描写书法之美,是一种比喻的说法”(5)。在一些产生较早的书法理论文献中,以各种各样的自然物象来形容书法之美确实大量存在。例如,东汉蔡邕《笔论》论书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6)其中,便以虫食木叶、利剑长戈、强弓硬矢、水火、云雾、日月等多种物象来形容书法之美,这些物象中既有自然物象,也有兵器等人文物象。又如,西晋索靖《草书势》云:“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虯蟉,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欻奋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窿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19—20)其中,用大量的自然物象如惊鸾、虫蛇、骐骥、海水、芝草、棠棣、玄熊、飞燕及其动作、形态等来形容草书之形状。这种以自然物象来形容书法的“物象表达”方式,是中国书法美学的早期传统之一,也是中国美学的传统表达方式之一。古代文学批评正是延续了中国美学这种“物象表达”的方式,所以唐宋元时期文学批评中的“格”“式”“势”等也多用四字组成的自然物象来表达。也因这种物象表达传统的存在,由四字组成的自然物象譬喻方式,在后世文学批评中又呈现模式化、程式化的倾向。
从中国美学的特征来看,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模式,符合中国美学的农业文明特征。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模式中,用以形容文学的譬喻之物,多是自然界中的山川草木、四时风景等农耕文明中的常见事物,这是中国美学农业文明特征的体现。关于中国美学的农耕文明性,已有学者做过相关论述,如刘成纪在《中国美学与农耕文明》中所言,“农耕背景下的时间和空间,是被自然表象的时间(四季)和空间(风景),它的自然性即可感性,它的可感性即审美性。同时,人参与农事就是参与自然,就是将个体纳入到自然时空的生命律动[……]农耕文明不但塑造了中国人的时空体验和四方想象,而且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质性的审美内容”(9)。在这样一种农耕文明的生活环境中,中国古人的生活、中国古人的艺术、中国古人的审美,都与农耕背景的时间与空间相关。在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方式中,作为喻体的自然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中活动的四季与风景。中国文学批评中,以农耕文明四季风景中诸多自然物象来譬喻文学活动,正与中国美学农耕文明的特质相关。
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来看,自然物之喻所用的“物象表达”方式,符合中国哲学观物取象的认识论传统。上文所论,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自然物之喻,往往是通过对某种自然风景、自然景象的描述来代替对文学活动机制本身进行分析与解剖。这种“物象表达”的方式,与中国哲学“观物取象”的认识论相关。“观物取象”的认识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周易·系辞》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表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寿祺 张善文 572)其中所说的“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符合周易的特点。《周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其具体的形象。《周易》的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中都有着重要影响。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等文艺批评中,对于自然物象的大量取喻与大量运用,也是通过对天地自然、飞禽走兽等自然事物的形象描绘来表达在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等过程中的种种体验和感受。因此,“观物取象”的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也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特点。
观物取象的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根源。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存在已久。《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和传说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代学人认为是先民记忆的保存,或可帮助我们窥测先民的一些表达方式或者思维方式。《山海经》卷三《北山经》中介绍带山时说,“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文[……]其中多鯈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袁珂 82)这种“其状如……”的表述方式,在《山海经》中大量存在。在这种表述方式中,我们能够追索早期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思维特点。有学者认为,“如……”样的表述方式是“将陌生的知识和事物向已知事物同化的一种表述方式,暗示出中国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比类取象特点”(户晓辉 44)。可以说,“比类取象”是早期中国人观察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和特点之一。而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美学传统中的自然物之喻,都能在中国哲学中“观物取象”的认识论传统、以及早期中国人“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中找到最原初的文化基因。既然“观物取象”是中国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古人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也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来观照与分析各种文体,由此,自然物之喻便能在文学批评中的各类文体、各个层面中广泛使用。
从中国哲学的生命观来看,自然物喻文所代表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评符合中国哲学的宇宙生命观。蒲震元认为,“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是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要形态,所谓“泛宇宙生命化”批评,蒲震元释为“以天地万物所表现的生命有机整体性特征来观察艺术作品”。在古代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的自然物之喻中,喻体囊括了山川日月、四时风景、动物植物等各种各样的宇宙生命。并且,这些山川日月、自然风景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譬如,传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中,论“纤秾”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郭绍虞 7),论“缜密”云“水流花开,清露为晞”(26),论“形容”云“风云变态,花草精神”(36),论“超诣”云“如将白云,清风与归”(37),其中的流水、远春、花草、清风、白云等用以形容美学风格的自然物象,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而这种“泛宇宙生命化”批评的方式,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生命观及宇宙生命意识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三家学说都有较为强烈的宇宙生命意识。儒家哲学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比德意识,赋予自然山水以道德人文的色彩;道家哲学中,“逍遥游”的精神追求以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主体意识,代表了一种将人类世界会通于宇宙生命世界的追求;佛教哲学中,有“众生平等”、万物皆可成佛的观点,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皆俱真如佛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赖永海 302),花与竹等自然事物也都具有生命色彩。因此,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中视宇宙自然中的一切事物皆有生命,体现出一种宇宙生命观的生命意识。《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黄寿褀 张善文 569),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生命观念的典型表达。“泛宇宙生命化”的批评模式是中国哲学的宇宙生命观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体现。而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模式,正与这种宇宙生命观相符合。
三、自然物喻文的批评意义
自然物喻文具有多方面的批评意义。
首先,以自然物喻文,将文学世界与宇宙自然世界联系起来,使文学活动兼具人文、天文、地文的意义,拓宽了文学艺术的言说空间与意蕴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天”“地”“人”三才的相应活动分别具有天文、地文、人文活动的意义。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人文领域的活动,文学的产生、接受等活动也都是在人类活动的领域中进行。而在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体系中,用以譬喻的自然物包括宇宙天地的诸多事物。从天上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到地上的山川草木、江河湖海,都能作为譬喻之物进入文学批评的系统中。当这些宇宙天地间的自然事物进入文学批评时,文学的构思、创作、审美、鉴赏等相关活动不仅具有“人文”活动的意义,也具有了“天文”“地文”的意义;文学不仅与人类精神活动相关,也与宇宙自然中诸多事物的活动相关;文学不仅能在人文空间、人文世界中言说,也能在天文世界、地文世界等更大的宇宙空间中言说。文学批评的以自然物喻文,使作为一粒微尘的文学活动,具有了普现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活动意义,使人类活动与宇宙境象之间,呈现出“‘两镜相入’互摄互映”的华严境界。因此,以自然物喻文,将文学构思、文学审美等相关人文活动与天地宇宙间自然万物的运行等天文、地文活动连接起来,使文学活动的空间从人类世界拓展到自然万物所存在的宇宙天地世界之中。
其次,以自然物喻文,打通了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批评之间的界限,凸显了各种文艺批评之间在美感生成、审美经验等方面的共通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中一些常用的、具有特定审美意蕴的自然物象。

再次,以自然物喻文,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命精神,并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美学的生命意识。如前所述,以自然物喻文,是中国古代“泛宇宙生命化”文艺批评模式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而“泛宇宙生命化”批评模式又与中国哲学的宇宙生命观相关。古代文学批评中,以生命有机体喻文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人体自身喻文,即钱锺书所说的“人化”之喻,吴承学所概括的“生命之喻”;一种是以自然事物来喻文,即蒲震元所说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评。这两种批评中,无论是以人体为喻,还是以自然事物为喻,所用以譬喻的人体以及自然事物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这种以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蓬勃生机与生命特征来譬喻文学的方式,赋予中国文学批评以生命精神。在自然物之喻的文学譬喻系统中,用作喻体的自然事物如日月星辰、四时风物,都具有内在运行节律与生命运行机制特征。作为被譬喻之物的文学,也就如同具有生命有机体的自然万物一样,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艺术具有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从宗白华到朱良志,都曾经予以论述。如朱良志所论,“中国艺术家视天地自然为一大生命世界,一流荡欢快运动之全体,鸟飞鱼跃,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树,一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命。”(8)其实,不仅中国艺术与天地自然生命相连,富有生命意识,而且,当天地自然中的自然物象进入到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之时,也使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等审美活动与天地自然的生命世界紧密相连。因此,不仅中国艺术富有生命精神,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美学同样也充溢着蓬勃的生命精神。

余 论
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传统,在现当代批评家手中依然传承。譬如现代美学家朱光潜评论古代诗人陶渊明时说,“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朱光潜 277),是用“秋潭月影,澈底澄莹”的自然景象来形容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又如,现代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在给李广田《画廊集》作序时(署名刘西渭)评论李广田散文说,“犹如蜿蜒的溪流,经过田野村庄,也经过圆囿城邑,而宇宙一切现象,人生一切点染,全做成它的流连叹赏”(李健吾 184),这是用蜿蜒的溪流等自然景象来形容李广田散文内容的包罗万象。再如,当代文学批评家陈思和评论沈从文的《电》《边城》时说:“《电》就像在黑暗社会里的一道道闪电,《边城》却如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山溪边,都没有丝毫混浊气”(陈思和 144),也是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描述来比喻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比较而言,朱光潜、李健吾、陈思和所用的这三个譬喻中,朱氏的“秋潭月影,澈底澄莹”所采用的两个四字词组譬喻法与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四字譬喻(如前文所举的“格”“势”等四字譬喻)更为接近,其句式句法、审美风貌都更接近于古典美学,而李健吾、陈思和的譬喻方式则是用白话的散文句式对自然物象进行描摹,其句式句法、审美风貌都更具有现代气息。可见,自然物喻文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的文学批评、美学著作中,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新变。在现当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中,自然物喻文所用的语言、物象、表达方式等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其内在的文学批评传统却是一以贯之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以自然物喻文与“人化”之喻、人文器物之物鼎足而立,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譬喻系统。自然物喻文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与多方面的批评意义。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上,自然物喻文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拓展其批评领域与批评范围。自然物喻文的批评方式与文学的发展演变相伴相随,并随着时代发展而注入新的因素,历久弥新。
注释[Notes]
① 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锺书就曾探讨过中国文学批评中“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现象,参见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4(1937)。90年代,吴承学又将其概括为“生命之喻”,参见吴承学:“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文学评论》1(1994)53-62。
② 以锦绣喻文的论文主要有古风的三篇文章,即“丝织锦绣与文学审美关系初探”,《文学评论》2(2007):153-59;“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文学评论》4(2008):37-42;“‘以锦喻文”现象与中国文学审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1(2009)161-73,208。其中,前两篇分别是对文学批评中以锦绣喻文的初步思考和个案研究,第三篇则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中以锦绣喻文的综合分析,包括其历史起源、学理基础、文学审美批评意义、审美批评范式的现代传承等问题。以兵法喻文的论文有吴承学的“古代兵法与文学批评”,《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以兵器喻文的论文有黄敏雪的“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兵器喻笔现象——兼论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的取喻系统”,《文艺理论研究》1(2018):89-98。以容器喻文的论文则有闫月珍的两篇:“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6(2013):167-85,208;“容器之喻——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评论》4(2014):44-50。其中,以兵法喻文、以兵器喻文、以锦绣喻文、以容器喻文等,都属于文学批评中以社会人文器物喻文的范围。
③ 对文学批评自然之喻单个喻体的研究中,以水喻文、以山水喻文的研究较多,如:吴中胜的“文学如水——中国古代文论以水喻文批评”,《理论月刊》7(2004):128-30;廖建荣的“论《文心雕龙〉的山水为喻”,《集美大学学报》3(2012):64-67;潘殊闲的“论宋代山水象喻文学批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1(2015):91-100。不过,山水喻文仅仅是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的一种或一类,山水之喻应当隶属于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的整体批评体系。
④ 在晚唐五代直至宋元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明确以“文格”命名的文章学著作。但是有学者认为,宋元时期一些文章学著作以“格”法论文,在形态功能等方面起到了“文格”的作用,参见祝尚书“文格论”,《中山大学学报》3(2006):1-9。
⑤ 关于晚唐五代诗格著作中“势”的含义、来源等,可参见张伯伟《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关于“势”的相关论述。
⑥ 关于书法批评的自然之喻与器物之喻,学界也有相关研究。例如闫月珍、赵辉的“器物之喻与中国书法批评”,《文艺研究》8(2017):117-25,该文专门论述中国书法批评中器物之喻的表现、意义。又如王岩的“中国汉唐书论中的物喻”,《中国书法》4(2017):165-70,将汉唐书论中的物喻分为动物、植物、景象、美人、器物四类来介绍。
⑦ 参见蒲震元:“‘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要形态”,《文学评论》5(2006):180-86。该文讨论了“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两种批评形态的生成原因、特点、价值,并揭示其与中国古代大宇宙生命美学的内在联系。
⑧ 按:《二十四诗品》尽管被陈尚君、汪涌豪认为非司空图作,是明人伪作,但依然不影响其文学批评价值和美学价值,故本文依旧引用。
⑨ “‘两镜相入’互摄互映”是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对于华严美学境界的概括,此处借用这一表述来形容自然物喻文的所达成的美学境界,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74页。
⑩ 参见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编(广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1-102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5—6。
[Cai,Yong.“On the Brush.”Selected
Works
of
Calligraphy
Theory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Shanghai: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1979.5-6.]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Chen,Sihe.Fifteen
Lectures
on
the
Masterpiec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郭绍虞:《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Guo,Shaoyu.Collected
Interpretations
of Critique of Poetry.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63.]户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发生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Hu,Xiaohui.A
Study
of
the
Genesis
of
Chinese
Esthetic
Psychology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3.]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Huang,Shouqi,and Zhang,Shanwen.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
.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1.]金圣叹:《金圣叹全集》,陆林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Jin,Shengtan.The
Complete
Works
of
Jin
Shengtan
.Ed.Lu Lin.Nanjing: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08.]赖永海:《佛典辑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Lai,Yonghai.The
Summar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李健吾:《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Li,Jianwu.Collection
of
Tasting
Flowers
.Shanghai:Culture Life Press,1936.]刘成纪:“中国美学与农耕文明”,《郑州大学学报》5(2010):7—10。
[Liu,Chengji.“Chinese Aesthetics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5(2010):7-10.]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iu,Xie.Annotated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Ed.Zhou Zhenfu.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1.]陆机:《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Lu,Ji.Collected
Interpretation
of
Lu
Ji
’s
Treatise on Literature.Ed.Zhang Shaoka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2.]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4(1937):1—22。
[Qian,Zhongshu.“On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Magazine
1-4(1937):1-22.]——:《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 - -.On
the
Art
of
Poetry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3.]齐己:“风骚旨格”。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397—416。
[Qi,Ji.“Format of Poetry”.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Poetic
Format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Ed.Zhang Bowei.Nanjing: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397-416.]索靖:“草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9—20。
[Suo,Jing.“The Style of Cursive.”Selected
Works
of
Calligraphy
Theory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Shanghai: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1979.19-20.]卫铄:“笔阵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21—22。
[Wei,Li.“The Picture of Battlefield of the Brush.”Selected
Works
of
Calligraphy
Theory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Shanghai: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1979.21-22.]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历代文话》第一册,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37—64。
[Xie,Fangde.“The Norms of Articles.”Remarks
on
the
Essay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Vol.1.Ed.Wang Shuizhao.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1037-64.]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
[Xiong,Bingming.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ianjin: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2.]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
[Yuan,Ke.Annotat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Chengdu:Bashu Publishing House,1992.]张炎:《词源》,夏承焘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Zhang,Yan.The
Origin
of
Ci
-Poetry
.Ed.Xia Chengtao.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1.]钟嵘:《诗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Zhong,Rong.Collected
Interpretation
of Critique of Poetry.Ed.Cao Xu.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4.]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Zhu,Guangqian.Theory
of
Poetry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4.]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Zhu,Liangzhi.The
Life
Spirit
of
Chinese
Art
.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5.]朱权:《太和正音谱笺评》,姚品文笺评。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Zhu,Quan.Brief
Comments
on
Tables of Correct Tones for a Period of Great Peace.Ed.Yao Pinwe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朱一玄 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
[Zhu,Yixuan,and Liu Yuchen,eds.A
Sourcebook
of
The Three Kingdoms.Tianjin: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8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77—94。
[Zong,Baihua.“The Beauty ofThe
Tales
of
the
World
and the Jin People.”Taking
a
Walk
in
Aesthetics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1.177-94.]——“意象”阐释的几组重要范畴的语义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