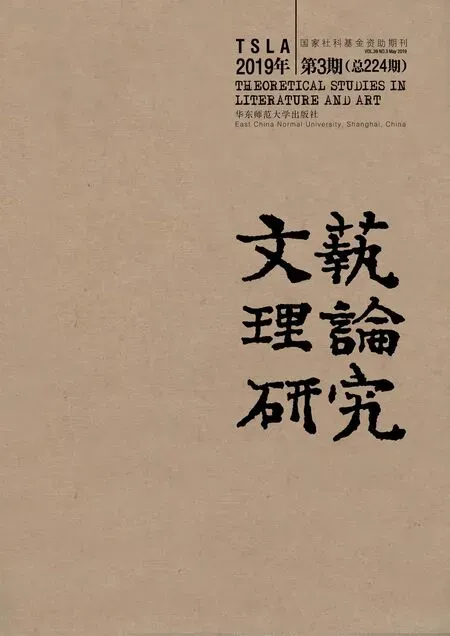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
——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核心问题与思路
张振华
在1934—1935年冬季学期的课程《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中,海德格尔说过这样一段话:
“祖国”(Vaterland)乃是存有本身
,它从根基上承载并构造着一个在此存在着的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它的历史之历史性。[……]祖国之存有,亦即民族的历史性此在,被经验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存有,面向存在者整体的基础立场从这种存有中生长出来并赢获其整体构造。(《荷尔德林的颂歌》 144)熟悉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会觉察到,海德格尔在此提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说法。他把第一哲学的核心论题“存在”(存有)直接等同于带有具体历史内容和意涵的“祖国”。而且,海德格尔还以加强的语气指认说,祖国就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本身。存在没有像海德格尔在其他文本中惯常所做的那样,被思考为解蔽与遮蔽间的澄明游戏(Lichtung),被思考为在场(Anwesenheit),被思考为本有(Ereignis),而是祖国。如此明确地以“祖国”作为存在之思的焦点,这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去关注这一讲课,关注这一段时期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征。
一
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是,这个讲课是海德格尔校长任职的政治实践(1933—1934年)失败后的第二个讲课,同时也是他开始对荷尔德林进行详细解释的第一次讲课。这暗示着时代环境。毋庸讳言,当时的时代氛围正是纳粹运动以及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如火如荼的时候。政治运动成为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关注核心。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是以存在之思的形式切入这一时代氛围,将抽象的存在论(或译“本体论”)与具体的时代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瑞士圣加伦大学的迪特·托梅(Dieter Thomä)所说:“海德格尔在1933年试图将他的哲学变得具有实践性。”(608)然而,刚刚在政治实践上铩羽而归的海德格尔同时自觉地与时代政治拉开了距离。这种拉开距离的意识和行动表现为,他尝试以纯粹思想的方式对具体政治发起批判性反思。因此,在海德格尔的这一讲课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海德格尔把存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近,“存在”的玄奥之思在“祖国”这里得到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落脚点;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把存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远,通过对“祖国”之本质发起存在论的追问,暴露出当时现实政治在本质层面的追问不足与根基缺失。德国吕纳堡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雅默(Christoph Jamme)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海德格尔这次课程的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对纳粹运动的反思和界限划清,另一方面又同时是对自己本人政治思想的推进(653)。
在存在之思与现实政治间的远近运动中,对诗人荷尔德林的解释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选择荷尔德林的颂歌体诗作《日耳曼尼亚》作为他解释的出发点。在1934年12月21日致德国教育学家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的信中,海德格尔表示:“我从晚期诗歌最内在的中心出发,从对《日耳曼尼亚》的暂时性解释出发。”(Heidegger and Blochmann 83)《日耳曼尼亚》被确定为荷尔德林晚期诗歌最内在的中心。在海德格尔看来,《日耳曼尼亚》最后的道说内容正是“祖国”(《荷尔德林的颂歌》 142)。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有意识地在讲课伊始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对于最高之物我欲沉默不言。/禁果,如同桂冠,却/最是祖国”(3)。在讲课结束时,海德格尔则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要学习去自由地运用民族性的东西(das Nationelle)对我们而言是最为艰难的。”(358)合观这几处文本,对祖国、民族的强调表现得异常显豁。荷尔德林作为一个民族性的诗人恰到好处地连接起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政治关切。
20世纪初的荷尔德林再发现切中了当时德意志民族情绪和政治运动的需要。面对这股荷尔德林热,海德格尔同样保持了远近之间的审慎。一方面,海德格尔并不回避热潮,他细致又带有创造性地解释荷尔德林诗歌;另一方面,作为哲学家的他又有意同这股热潮保持距离。在1935年12月20日给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评论说:“荷尔德林现在变得时髦了。他落入了那些不真切的手中。因此我不想就此出版任何东西。”(Heidegger and Blochmann 87)
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祖国”其内涵是什么?海德格尔把祖国称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存在”(das geschichtliche Sein)或者“历史性此在”(das geschichtliche Dasein)(《荷尔德林的颂歌》 142、143)。在海德格尔心目中,像希腊、德意志这样的民族属于拥有特定命运的历史性民族。因此,“祖国”植根于一个有着特定历史传统及其命运性展开的民族共同体。正如英国学者朱利安·扬所指出的:“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石是民族(Volk)这个概念。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所有的演讲都是由复兴民族共同体(Volkgemeinschaft)以及使德国民族(Volk)成为符合其历史使命的民族这个目标所支配。”(17)我们可以由此把海德格尔在第一次荷尔德林解释课程中的核心问题表达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生成并得到维系的。在这个文本中——甚至只有在这个文本中——可以辨认出一个清晰的民族共同体生成的结构。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课程,辅以同时期的其他文本,来重构海德格尔对民族共同体的发生结构的解说。
二
对于民族共同体如何生成这一问题,海德格尔的回答并不迂曲缠绕。在他看来,民族共同体的创建需要诗人及其诗歌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在政治实践失败后,会把眼光转向诗歌,转向艺术。这非但不是抛弃政治,躲进艺术的角落寻求避难,恰恰相反,在海德格尔眼中,诗歌对于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本真政治的思想争夺在诗歌解释中得到展开。诗学在海德格尔那里与政治哲学无法分离。
为什么是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在常常把诗歌当成个人体验之表达的今天,我们还能理解海德格尔的宏大思考吗?且看荷尔德林的长诗《如当节日的时候……》中的如下一段:
应当站立于神的雷霆之下
你们诗人啊!凭赤裸的头颅,
用自己的手去抓住
天父的光,他本身,并且将天空的礼物
裹藏在歌之中传递给民众。(《荷尔德林的颂歌》 36、37)
这一段是理解诗人及其作品的关键。首先,诗人与神域相关,他站在“神的雷霆之下”。按照希腊人的看法,雷霆和闪电是神的语言(38)。站在神的雷霆之下意味着诗人谛听神的消息。从荷马史诗开始,这被认为是诗人独有的能力,一种超凡的聆听官能。在稍后对雷霆的提及中,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说:“雷霆,闪电,雷暴对荷尔德林而言是那种东西,在其中不仅仅呈报出一种神性之物,而且神之本质还在其中敞开出来。”(295)雷霆不仅仅是外在于神的“现象”,它昭示了神之本质。诗人在神面前的这种站立是如此直接、如此一无保护,因此荷尔德林描述说诗人的头颅是裸呈着的,诗人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神。其次,诗人不仅面向神性领域,他还同时面向民众。通过诗歌创作,诗人将神的消息保存在诗歌作品中,将负荷着神之闪电的礼物柔和化,缓解并转化雷霆之力,从而进一步将其传递给民众,为民众所享用。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中介者的诗人的身位,他直面神性领域,接收神的消息,并通过创作活动将神的消息传达给民众,由此完成民众与神的连接。
对于诗人直面神性领域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入于存有的威力之中的绽出性直临”(Ausgesetztheit in die Übermacht des Seyns)(37)。在此,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诗歌中提到的神性领域解说为“存在”。存在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这里的解说中,存在带有很强的神性特征。如此这般的“存在”充满威力,绝非常人可以随意抵达和接近的场所。Ausgesetztheit是海德格尔对诗人身位的命名。这个词来自于动词aussetzen,在日常德语中aussetzen有“丢弃,放生,使遭受”等意思,其形容词形式ausgesetzt的意思是“暴露的、无遮掩的”。而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的使用更需从字面加以理解:setzen是设置,aus是向外,Ausgesetztheit的字面意思是设置在外。这更加表明了诗歌不是诗人内在的灵魂体验,而是一种向外的出离。诗人的存在状态的敏感性也正在于这种向外出离。因而我们尝试将这个词翻译为“绽出性直临”。只有诗人,带着“纯洁的心脏”“宛若儿童”“双手清白无邪”(《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58),才具备这种“绽出性直临”的灵魂,超出日常事物的逼涌,扶摇直上,抵达神性之域。
三
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如此这般的结晶体的诗歌作品,为民族“创建”起真正的存在。(《荷尔德林的颂歌》 39)在1934年12月21日致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直陈自己的荷尔德林解释关键:“诗歌的基本理解建基于《追忆》一诗的最后一行:持留之物,诗人创建。诗人乃是先行创建起存有的人——先行建基了存在并且在初始的命名与道说中将存在者提高入存有中”(Heidegger and Blochmann 83)。克里斯托弗·雅默概括得不错,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的核心是实践哲学、政治哲学(Jamme 653)。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存在论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因此更为严谨的表达应当是: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同时是存在论的和政治哲学的。
在此,“创建”(stiften)一词是海德格尔对诗歌与存在之关系的特别命名,是连接起诗学(艺术哲学)与存在论的关键概念。这个词的日常意思是“捐赠,创办,促成”,它既有创造的意思,又包含辅助、引发之意。在这个讲课同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对“创建”一词进行了细致发挥,将其分解为三重涵义:(1)赠予(schenken);(2)建基(gründen);(3)开端(anfangen)。这三重涵义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诗歌的存在论意义。
首先,“赠予”指的是艺术的创造特征。海德格尔说:“在作品中开启自身的真理绝不可能从迄今为止的事物(das Bisherige)那里得到证明并推导出来。迄今为止的事物在其特有的现实性中被作品所驳倒。因此艺术所创建的东西,决不能由现存之物和可供使用之物来抵消和弥补。”(《林中路》 54)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艺术创造不是从过去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那里按部就班地产生的,在艺术中蕴含着本质性的创造与发生。艺术家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在先的模板可供调用,他将闻所未闻的东西开辟出来,因此艺术创作仿佛是一种凭空而来的“赠予”。
但是,这种作为创造的“赠予”绝非无缘无故,它有其历史传统的根基。因此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将到来的保存者,亦即被投向一个历史性的人类。但这个被投射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任意僭越的要求。真正诗意创作的筹划是对历史性的此在已经被抛入其中的那个东西的开启。那个东西就是大地。”(55)艺术创作诚然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依循,但也绝非任意妄为的结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都已经被“抛入”它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如此这般的历史传统被海德格尔以特别的方式命名为“大地”。作为历史传统的“大地”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身的基础。但这样一个基础并不是现成发挥着作用的,它需要经由艺术作品而重新得到开启、奠基和“引出”(55)。传统必须得到激活,基础才由此得到“建基”,真正成为其基础。
最后,作为“赠予”和“建基”的艺术具有“开端”的能力。海德格尔所说的“开端”指的是历史之发动:“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之中,历史才开始或者重又开始。”(56)因此海德格尔谈论的艺术绝不限于个人体验,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大艺术。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家和诗人,在希腊是荷马,在德国是荷尔德林。荷马属于西方思想第一开端中的诗人(《荷尔德林的颂歌》 223),荷尔德林则是面向西方思想另一开端的诗人(220—21)。他们写下的诗篇是具有民族和历史意义的大诗,前者意味着历史之发动,后者意味着历史之重新发动。
四
那么,为何诗歌作品对一个民族之存在的塑造而言具有如此根本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回答同样简单明了,因为诗歌同语言相关,诗歌运行在语言的领域内。
我们决不能小看语言的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工具而已。语言“不是人类所拥有的诸多能力与工具之一种,而是那种反过来将人类拥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根底上构造(fügen)并规定着如此这般的人类之此在的东西”(79)。之所以语言从根底上构造着人类,是因为“在语言之中发生着存在者之敞开”(die Offenbarung des Seienden)(73)。语言通过其命名的力量揭示了事物在其中呈现的总体的意义境域,这样一个总体的意义境域的发生,是具体事物与我们发生对待关系的前提。总体的意义境域敞开了具体事物,使具体事物能够为我们所通达,具体事物由此才有了远近、快慢、高低、幸与不幸的区分和纹理。在脱胎于这一课程、做于1936年的演讲《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更具体地描述说:“惟在有语言的地方,才有关于决断和作品、关于行动和责任的持续变化的领域,但也包括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40—41)这样一个“持续变化的领域”(Umkreis)的预先敞开,依靠的就是语言之力量。因此,人类的存在受到语言的在先规定,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语言塑造成形。这是规定了海德格尔中后期基本思想的“语言存在论”的见解。
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是任意一种形式,还是存在某种突出的、占据优势地位的语言形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和语言之间并不相同。在众多语言形式中,诗歌是最具本质性的语言形态:“语言的至纯本质开端性地展开在诗歌之中”(《荷尔德林的颂歌》 75)。在海德格尔心目中,诗歌语言远远超越于日常语言。事物首先在诗歌中得到敞开,它们才进而在日常语言中得到谈论。因为上面所说的总体的意义境域的语言性开启,实际上是诗歌的任务。
从整个民族的角度看,诗歌被称为一个民族的“元语言”(Ursprache)(75)。这样的“元语言”规定了一个民族的“基础构造”(Grundgefüge)(79)。也就是说,一个民族通过其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打开了一片特定的意义境域,在这一意义境域中,价值尺度才在民族内部建立起来,高贵与卑贱、好与坏才产生了明确区分。对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参看《艺术作品的本源》对希腊悲剧的意义的深刻描写。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悲剧中的语言不是一种对事件的静态描述,相反,它意味着事物的开启和决断,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隶”(《林中路》 25)。这种区分好坏、高低、善恶的活动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它制造出了一个民众在其中得以呼吸的大气层,也使得一个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这便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揭示的,一个民族如果不首先进行估价,就不能生存,而这个民族估价的方式又不得不区分于其他民族(68)。一旦这个“大气层”毁灭,意义—价值境域崩塌,便是虚无主义的蔓延。而这种根基处的民族价值观的生成,在海德格尔看来依靠的是诗人的诗歌创作,依靠语言。语言就像一束光,它点亮了意义,把光明从黑暗中区分出来,让民众以特定的方式通达并评价事物。
五
但事情也不仅仅关乎语言。荷尔德林《日耳曼尼亚》第二节中有一段诗是这样的:
因为既然一切已经结束,而白昼已然消隐,
首先击中的是祭司,而神庙和形象以及祭司的礼仪
也怀着爱意紧随祭司
进入黑暗之国,无物再可显现。(《荷尔德林的颂歌》 12)
荷尔德林原诗描述的是希腊诸神消亡、隐去的历史过程,亦即祭司、神庙、绘画和雕塑、礼仪等事物相继湮灭不闻。这段带有叙事性质的诗看起来平常无奇,但海德格尔的解释颇可玩味:
只有在作为诸神的历史性此在的神庙和形象耸出日常活动及家居并将它们维系起来之处,礼仪(Sitte)和风俗(Brauch)才存在。但只有在那些伟大个体存在之处,形象和神庙才存在。那些伟大个体在认知和创造中直接经忍着诸神的现身在场和离场,并在所创造的作品中将其带向分解。(116—17)
海德格尔在此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精彩阐释,描述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生成和维系的顺序。这段诗完全可以倒过来解读:民族共同体中日常的活动及其家居需要礼仪和风俗来维系,它们代表着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伦理法则和价值尺度。这种礼俗既包括祭司的礼仪,亦即宗教、祭祀仪式,也包括民众的日常风俗习惯、伦理法则。这两者区分出一个下降的过程,由祭祀的礼仪下降而灌溉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宗教仪式和日常风俗区分开了大地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它们像无形的丝带一样把民族内部的民众联系起来,使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但是,这种礼仪和风俗并非单纯人为制造的产物。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不能使礼仪和风俗产生持续的约束力。这些礼仪和风俗需要“神庙”和“形象”的在先敞开(“形象”在此指的是摹写诸神的神像、瓶画等)。“神庙”和“形象”代表着诸神的现身在场(海德格尔所说的“诸神的历史性此在”),它们具有非凡的超越性。这些“神庙”和“形象”展开了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空间,因此海德格尔说它们“耸出”(überragen)日常活动及家居。这些耸出性的神性力量并不是一味向上而去,它们又反过来维系着日常活动和家居,是日常活动的意义来源。
海德格尔指出,神庙和形象并不是现成的,它们的发生和成立需要“伟大个体”。因为神庙和形象不是物质意义上对神的外观的感性模仿,相反,它们就意味着神的在场,就像《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说的:“它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得神本身现身在场,因而就是神本身。”(《林中路》 25)而神的在场不是静态的状态,它是一个发生事件。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这些超越众人的伟大个体才能经验这一事件,目击神的在场或者离场。这些伟大个体一方面对神域有所认知,另一方面又基于这种认知而进行作品创造。他们是广义的“诗人”,涵摄了宗教、艺术和风俗。
六
诗人通过其创造性活动连接着神性领域与民众,在如此这般的中介者的意义上,诗人被海德格尔称为“半神”。如字面所示,“半神”不是通常的人类,也并非完全的神。半神高于人,同时又低于神,半神因而既是“超人者”(Übermenschen)又是“亚神者”(Untergötter)(《荷尔德林的颂歌》 199)。作为“半神”的诗人是沟通人神的“祭司”,如荷尔德林在《面包与酒》写道:“但是你说,他们[诗人],犹如酒神的神圣祭司”(232)。无怪乎20世纪初的领袖型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将荷尔德林描述为“祭司诗人”(Priesterdichter)(Mehring 17)。这是对诗人的剥离了任何浮夸修饰的内在力量和根底处的骨血的揭示。
作为半神的诗人所面向的诸神不是任意的诸神,它们是民族之诸神。他迎向诸神的领域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自己的家乡和民族。诸神必须为了本民族之故而得到接纳(《荷尔德林的颂歌》 205)。只有接纳了相应的诸神,一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立起来。用《哲学论稿》中的话说:“唯当一个民族在寻找自己的神的过程中分得了自己的历史,它才成为一个民族。”(425)民族与相应的诸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诗人通过他的吟唱完成着民族及其诸神的连接。因此,作为半神的诗人有一个特定的站立位置,他站立在家乡的界限上。在这一界限上,诗人一方面望向陌生而遥远的东西,也就是一片未曾建立尺度的、混沌的领域;另一方面,诗人通过对诸神的接纳而使家乡的边界得到确立,使民族的真理得以发生。家乡的边界意味着区分各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诸神形象、语言、习俗等,它们把民众生活得以可能的意义领域展开在民族共同体中。

诗人从一种情调(Stimmung)而来进行言说,这种情调规—定(be-stimmt)了基础与地基,并且贯通性地调谐着(durchstimmt)一个空间,诗性之道说在这个空间的基础上,在这个空间之中,创建了一种存在。我们将这种情调命名为诗歌的基础情调(Grundstimmung)。(94)
海德格尔用“情调”这个词来意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他通过德语stimmen(调谐,调音,使具有……情绪)的词根,形成了一个可供发挥组合的词群:Stimmung(情调),Mißstimmung(坏情绪),Verstimmung(恶劣情绪),Ungestimmtheit(了无情绪),Grundstimmung(基础情调),Gegenstimmung(对反情调),Umstimmung(变调),bestimmen(规定),durchstimmen(贯通性调谐),gestimmt(得到了调谐的)(169)。但海德格尔说的情绪不是私人的主观情绪,不是偶发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体性的、辽阔的存在感受。这种存在感受犹如一片境域之光,以支配性的方式把诗人、世界、具体事物囊括为一个统一体。就此而言,诗人是在由基础情调所调谐的空间中言说的。这是诗歌发挥作用的力量之域。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阅读诗歌也正是为了进入这样一种基础情调,如此才能与诗歌的道说产生真正关联。
从前期的“处身性”(Befindlichkeit)到中后期的“情调”,情绪问题在海德格尔思想中自始至终占据一个中心地位。海德格尔认为,离开了情绪的敞开性力量,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衰败为空洞的概念游戏。而在这一讲课中,海德格尔对情绪问题做出了独一无二的阐释,强烈地拓展了情绪问题的讨论维度。海德格尔将基础情调分解为四重内涵,它们分别被简称为:(1)移离(entrücken);(2)移入(einrücken);(3)开启;(4)建基(166—67)。第(1)点“移离”指的是面向存在者整体以及诸神的出离。这是半神的特征,具有常人不可企及的超越性。entrücken在日常德语中有“使脱离、使离开、使出神、使入迷”的意思,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明诗人灵魂的绽出特征。诗人超出日常流俗事物的轨道之外。可以发现,这个词和前文引用的“绽出性直临”(Ausgesetztheit)的意思相通。因此诗歌和情绪在海德格尔看来不是发生在诗人灵魂内部的主观的、私人的体验,相反,它是一种极端在外的状态(37)。第(3)点“开启”指的是对“存在者”的开启,也就是说,诸种具体事物在情绪的敞开域中得以通达。第(4)点“建基”则是指对“存在”的基础奠立,它是具体事物得以显现的一片意义境域。
以上第(1)(3)(4)点涵义我们在前面多少已经有所触及,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2)点涵义。海德格尔说的“移入”是指移入到“大地”之中:“诗人受到这种思想以及他在其中所思想的东西的突袭。这种突袭将他带回到家乡的大地上,亦即将他移入到历史性的此在及其大地性、地方性的根基中”(220)。这里的“大地”指的是“家乡”与“地域”(Landschaft),也就是一个民族世代生存的土地。这样的大地并不单纯意味着一个民族所在的地理空间(124),大地有其深厚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移入大地”根本上意味着诗人对于民族传统的归属,意味着诗歌创造的民族性与扎根性。基础情调不是一种任意的情感,而是受到民族之历史传统的规定。诗人在出离而延伸入神性领域的同时,“回向联系”(Rückbindung)(220)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对于如此这般作为历史传统的大地概念,我们在援引《艺术作品的本源》对“创建”一词的解说时已经触及。
由基础情调的这四重内涵而来,我们直观地看到了诗人的生命状态:他的灵魂裸呈于神性领域,他的脚跟立足于家乡大地,他通过诗歌创作敞开着赋予存在者以光亮的意义境域(存在)。就此而言,他乃是连接神性领域和民众生活的半神。
七
前面我们提及的都是诗人的角色,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力量一道参与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在?的确,海德格尔认为,这些力量其实一共有三种:诗歌,哲学,政治(海德格尔称为“国家创立”)(171)。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将真理的发生方式分为四种:艺术,建国,献祭,思想(《林中路》 42)。在1935年夏季学期的课程《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则举出了诗人、思想家、祭司和统治者(《形而上学导论》 177、220)。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在荷尔德林的讲课中祭司和献祭实际上融合在了诗人的角色里。
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关系。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哲学和政治在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忽前忽后”,“不可计算”(《荷尔德林的颂歌》 171)。另一方面,从海德格尔的具体表达中我们又可以辨认出一个先后次序:
基础情调,而这意味着一个民族之此在的真理,源初地经由诗人得到创建。但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思想家而得到把握、接合(gefügt)并因而被首先敞开为存在。而以如此方式得到把握的存在通过那种方式被设立入存在者的最终与最初的严肃之中,亦即被设立入得到调—谐的(be-stimmte)历史性真理之中,这种方式即民族被带到自己本身面前而成为民族。这通过国家创立者对规定着民族之本质(seinem Wesen zu-bestimmten)的国家的创立而发生。(171)
海德格尔在此对诗歌,哲学和政治的任务做了具体的描述。诗歌因其创造性特征而占据一个最为源初的地位。诗人“唤醒”基础情调,亦即存在的敞开,意义境域的发生。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是民族的“先行者”(Erstlinge)(173—74)。所以海德格尔一再强调,要进入另一开端,必须学会倾听诗人荷尔德林(《哲学论稿》 214、428、445)。诗人源初创建起来的“存在者之存在”通过思想家得到进一步把握与解释。经过思想家的把握与解释,源初统一的存在开始产生较为明确的秩序与结构。海德格尔使用的“接合”(gefügt)一词就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秩序性。由诗人原初创建、思想家进一步把握的“存在”最终下降到民族之中。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国家”中达到一种自立和自我认识。在1934年夏季学期课程《逻辑作为对语言之本质的追问》,亦即这次荷尔德林解释之前的一次课程中,海德格尔强调了国家的必要性:国家是历史性存在的本质法则,它保证了民族的历史性延续,争得并保存了民族的使命。国家就是民族的历史性存在(Logik
165)。而国家创建的政治行动是由国家创立者完成的。一个民族由此形成一种政治层面的自觉。这整个过程是“存在”从发生,到结构化,到最终落地的下降过程。也是“存在”从无到有,越来越具体化的过程。对此,海德格尔在课程另一处有一个更加简洁明了的表达:“而这种存有(指历史性民族——笔者注)在诗歌中得到创建,在思想中被构造起来、置入到认识之中,并且植根于大地上的国家奠基者的行动和历史性空间。”(《荷尔德林的颂歌》 143)至此,我们才更深地理解了本文一开始的引文,“祖国”作为“真正的存在”的内涵:祖国是存在之发生最终的承担者和凝聚处,是哲学之真理真正实现自身的地方。
八
通过我们的重构性解读,海德格尔那里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从神(存在)到诗人到民众的生成结构,一个统一了神学、诗学、存在论、政治哲学四重领域的宏伟图景。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如此这般生成并得到维系的。海德格尔将这套结构具体应用到德意志民族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解释荷尔德林的诗。
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上,海德格尔将德意志与希腊紧紧联系在一起。1933年夏季学期课程《哲学基本问题》对这一点表达得非常直接:“希腊人的民族,其族群和语言与我们具有同样的起源[……]”(Sein
6)而希腊的诸神已经不再对当今世界产生效力了。荷尔德林经验了这种诸神的逃遁。因此,《日耳曼尼亚》这首诗开篇讲到的情绪是“哀恸”(“但是/你们家乡的河水啊!此刻随你们一道/当心中的爱发出哀怨,它还想要别的什么/神圣哀恸者?”)。“哀恸”,海德格尔说,是这首诗歌的“基础情调”,它承载着其他的情绪,将它们统合为一(《荷尔德林的颂歌》 96)。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在对希腊诸神之离去的经受中,诗人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的窘迫的当下处境;同时,又在这种窘迫中产生预感,做出准备,准备迎接新神的到来。“神圣哀恸、但却预备着的窘迫”是对完全展开了的基础情调的描述(122)。此间,哀恸联系于过去,即诸神的逃遁;窘迫联系于当下,即诸神的悬缺;预备联系于将来,即新神的到来。这一切来自一种过去、当下、未来相互绽出的源初时间经验。这种时间性和民族的历史性相连。至于当下的时代处境,海德格尔说:
神死了,形象和神庙永远不可能通过有奖竞赛而生成。诸神之闪电不发作,就不会生成祭司。家乡的大地及其如此这般的整个民族不置身于雷霆空间当中,诸神之闪电就不会发作。而处于其如此这般的历史性此在中的整个民族,不对诸神之死的最内在的急迫加以本质经验并且长久忍受,它就不会移入这一雷霆空间当中。(118)
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首先需要有诗人。因为诗人作为半神与神性领域相连,经验到诸神之死,从而唤醒一个民族的基础情绪,使得一个民族进入到面向神的雷霆空间中。
不过,只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吗?在前面的论述中存在一个问题:创建和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既包括诗歌、语言,也包括神庙、形象和礼俗。那么前者与后者是什么关系?站在海德格尔的立场上,语言更加优先于神庙、形象和礼俗,因为它敞开了一个民族的无形的意义世界。在《艺术作品的本源》讨论其他艺术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时,海德格尔把诗置于一个基础的地位:“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林中路》 54)这进一步意味着,带来事物之敞开性的语言是一切思考、行动、言说得以可能的前提。海德格尔总是致力于阐明语言的存在论意义。相形之下,他对神庙、形象尤其是礼俗缺乏更加具体地探究与展开。这是海德格尔的高明处,也是海德格尔的限制处。

注释[Notes]
① 引文中的“存有”(Seyn)是德文“存在”(Sein)的旧体写法,海德格尔在这段时期试图以此区分于传统的存在理解,这个做法后来被放弃,下同。
② 海德格尔在讲课中以批判的态度提及亲纳粹的知识分子罗森伯格(Rosenberg)和科尔本海尔(Kolbenheyer)(《荷尔德林的颂歌》 32),并且批判性地提到“民族性”(Volkstum)、血(Blut)和土(Boden)的纳粹口号(《荷尔德林的颂歌》 309)。
③ 法国学者、重要的海德格尔作品法文译者弗朗索瓦·费迪耶(François Fédier)也指出了这一点(Fédier 63)。
④ 德国学者斯特凡妮·博伦(Stephanie Bohlen)将诗歌中的神庙、形象和礼俗分别理解为宗教、艺术和道德(Bohlen 61)。宗教和艺术没有问题,但道德的提法值得探讨。德语的Sitte既有风俗习惯的意思,也有道德的意思。但此处将其理解为道德似乎不很准确。海德格尔将Sitte和Brauch连用,是从风俗的方向理解Sitte的。英译本将诗歌中的Sitte翻译为custom,将海德格尔的Sitte und Brauch翻译为custom and tradition(H
ölderlin
’s
Hymns
89),这佐证了我们的理解。⑤ 在罗伯特·多斯塔尔(Robert Dostal)看来,将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导致了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它取消了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存在(扬 185)。我们的目标在于刻画海德格尔心目中的民族生成结构,至于其评价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
⑥ 在安雅·索尔巴赫(Anja Solbach)看来,这种时间经验延续了《存在与时间》中作为“绽出”(Ekstasen)的时间理解(Solbach 147)。但需注意,海德格尔在此并未像《存在与时间》那样赋予“将来”的时间面向以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这里的绽出也不再是个体此在的时间性,而是和民族的时间性相关。科里安多(Paola-Ludovika Coriando)则认为“哀恸”中的时间结构与《哲学论稿》中的基础情绪“克制”(Verhaltenheit)具有同构性,颇有道理(Coriando 18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ohlen,Stephanie.Die
Übermacht
des
Seins
.Heideggers
Auslegung
des
Bezuges
von
Mensch
und
Natur
und
H
ölderlins
Dichtung
des
Heiligen
.Berlin:Duncker &Humblot,1993.Coriando,Paola-Ludovika.Zu Hölderlins Wesensbestimmung des Menschen,in:Vom
R
ätsel
des
Begriffs
.Hrsg.Paola-Ludovika Coriando.Berlin:Duncker &Humblot,1999.Fédier,François.Hölderlin und Heidegger,in:“Voll
verdienst
,doch
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
.”Heidegger
und
H
ölderlin
.Hrsg.Peter Trawny.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0.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Heidegger,Martin.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Trans.Sun Zhouxing.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12]——:《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Wang Qingjie.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12.]——:《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 - -.Interpretation
of
Holderlin
’s
Poems
.Trans.Sun zhouxin.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02.]——:《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 - -.H
ölderlin
’s
Ode
to
Germania
and
Rhine
.Trans.Zhang Zhenhua,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18]——:《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 - -.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Sun Zhouxi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8.]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
[Han,Chao.Heidegger
and
Issues
of
Ethics
.Shanghai: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07.]Heidegger,Martin.Logik
als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8.- - -.Sein
und
Wahrheit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1.- - -.H
ölderlin
’s
Hymns
“Germannia
”and
“The
Rhine
”.Trans.William McNeill and Julia Ireland.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Heidegger,Martin,and Blochmann Elisabeth.Briefwechsel
1918
-1969
.Marbach am Neckar: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1989.Jamme,Christoph.Hölderlin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Zur Diskussion um “Andenken”,in:Zeitschrift
f
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42,H.4,1988.Mehring,Reinhard.Heideggers
“gro
ße
Politik
”:Die
semantische
Revolution
der
Gesamtausgabe
.Tübingen:Mohr Siebeck,2016.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Nietzsche,Friedrich.Also
Sprach
Zarathustra
.Trans.Sun Zhouxi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Solbach,Anja.Seinsverstehen
und
Mythos
.Untersuchungen
zur
Dichtung
des
sp
äten
H
ölderlin
und
zu
Heideggers
Deutung
.Freiburg/München:Verlag Karl Alber,2008.Thomä,Dieter.Die
Zeit
des
Selbst
und
die
Zeit
danach
:Zur
Kritik
der
Textgeschichte
Martin
Heideggers
1910
-1976.
Frankfurt am Main:Surkamp Verlag,1990.朱利安·扬:《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陆丁、周濂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Young,Julian.Heidegger
Philosophy
Nazism
.Trans.Lu Ding and Zhou Lian.Liaoning:Liaoning Education Press,2002.]